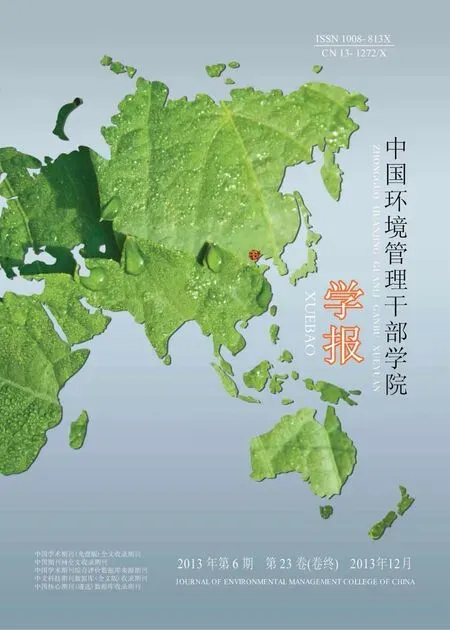国际环境法对我国环境保护的启示
代 佼 ,操 飞
(1.攀枝花市环境监测站,四川 攀枝花 617000;2.攀枝花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四川 攀枝花 617000)
从生态环境上来看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环 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但在过去的100年间,气候的剧烈变化以及频繁的自然灾害让人类认识到了环境保护的紧迫性,国际环境法在世界各国的不断推动和努力下逐渐建立起来。我国作为气候变化的受害者和国际环境法的缔结者之一,近些年来积极履行自身的责任和义务,如在全球环境保护大趋势下开始得以逐步贯彻和实施清洁生产和节能减排等措施。然而,由于世界各国不均衡的经济基础,国际环境法在建立和实施的过程中遇到越来越多的新问题。
1 国际环境法的内涵与基本原则
1.1 国际环境法的内涵和发展过程
国际环境法即调整国际法主体在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与资源中所形成的各种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国际环境法是国际法的主体,体现了各国保护和改善环境方法达成的共识以及协调意志,具有普遍的法律性,对各成员国之间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世界上第一部具有类法律性质的关于环境保护的国际多边协议《保存非洲野生动物、候鸟和鱼类公约》诞生于20世纪初,随后陆续出现了多部国家间或者地区间关于环境保护的协议,但这些协议不具备法律的性质,对各协议国缺少法律的约束。直到1992年5月,联合国总部通过了首部具有法律效力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首次明确了国际环境保护各缔结国的权利与义务,旨在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并得以实施。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共制定了200多项全球性或区域性国际环境条约,基本形成了处理各领域环境问题的国际法律体系[1]。
1.2 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
可持续发展原则、预防原则、国际合作原则、国家环境主权原则和共同但有区别原则被公认为国际环境法以及处理国际环境纠纷的五大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重在要求为子孙后代谋求和创造与现在相同的发展空间,不以牺牲后代人的生活环境为代价换取当代人类的一时繁荣。预防原则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处理环境污染问题的首选,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中逐渐为人们所接受,这一条原则正式的法律文本源于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宣言中第l5条规定:“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按照本国的能力,广泛适用预防措施。遇到有严重或者不可逆转损害的威胁时,不得以缺乏科学充分确实证据为理由,延迟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防止环境恶化。”[2]国家环境主权原则是解决国家争端的最基本的准则,也是国际法立法的先决条件,即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前提下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各国家有权开发利用本国的环境和资源,同时负有确保其管辖范围内的活动不致损害其他国家或各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生态环境的责任;国际合作成为了当前解决国际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逐渐认识到开展广泛的交流合作和多边磋商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方式。如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敦促各缔结国履行《京都议定书》,缔结新的减排协议,并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明确的减排目标以及达成该目标所需要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内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法律。由于各国对世界环境变化产生的影响不一致以及各国对环境保护的能力高低不一,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作为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已经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和认同。共同责任既强调了各国对于环境变化所共同承担的责任,同时兼顾了责任的差别性[3]。关于区别责任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和争议,发达国家认为世界应该为环境的恶化负有共同且相同的责任。但无论从历史上发达国家发展经济掠夺式的开发自然资源和过度的排放温室气体,还是现在发达国家居高不下的人均碳排量,发达国家都应该为环境污染产生的恶果负主要的责任。有数据表明,在过去100年间,占世界人口20%的发达国家对全球碳排放量的63%负有主要责任[4]。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达国家应该率先制定减排目标和实施减排措施,并且利用现有的先进科技和雄厚的资金力量帮助发展中国家采取措施治理污染和控制碳排放量。可是围绕区别责任的争论仍在继续,这也是造成近几次有较大影响力的环境会议如“哥本哈根会议”、“德班会议”开得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
2 我国环境保护法的现状和问题
2.1 环境保护立法趋于完善,但滞后性明显
经济建设是我国首要的任务和目标,是党和国家制定政策和法律的基本出发点。建国以来环境问题一直为人们所忽略,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三年自然灾害的发生给政府敲响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警钟,环境保护立法才逐渐提上了议程,到1979年我国才通过了第一部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环境保护法》。截止到2011年底,我国共制定11部环境保护法律,25部自然资源法律,制定颁布了环境保护行政法规60余项,部门规章和地方环保法规近2000件,军队环境法规和规章10余件,国家环境标准1100多项,批准和签署多边国际环境条约60余项[5],初步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体系的环境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但法律存在滞后性,而且法律的滞后性在环境保护领域体现得更加强烈。作为我国现行环保基本法之一的《环境保护法》中第一条指出,“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制定本法”。“促进经济发展也是环境保护的最终任务之一”这样的法律解释很容易造成司法裁定的自相矛盾,即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矛盾的时候,环境保护很可能就成了附属条件,为经济发展让路,而现实情况也是如此。例如我国现行《海洋环境法》中第50条规定,“对于造成严重海洋污染事故的企业或者单位,处以罚款金额最高不得超过20万元”。2011年渤海湾漏油事件中,按照该法肇事方美国康菲公司最多支付20万元的罚金,这对于上百亿美元资产的康菲公司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正是由于环保法律的滞后性,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已经成为环境保护领域的普遍现象,因此,环境保护法应该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一起与时俱进,体现环境法立法的初衷。
2.2 环境保护法律执行不利
虽然我国现有的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以及标准总数超过100部,但是缺少相关的配套行政法规和规章,很多法律条款规定原则化和抽象化,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保证其实施,立法过于原则和粗略。例如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增加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增加了“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条款中并没有明确具体哪些机关和组织可以针对污染环境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二,制度的缺失和经费的限制是造成环境案件执法难的另一重要原因。虽然目前环保工作是在环保部的统一协调下进行,但是地方环保人员编制和经费都受地方政府主导,尤其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环境保护为经济建设“让路”的现象十分普遍。再者,面对环境违法案件时,法律没有赋予环保部门强制执行的权力。目前环保部门仅拥有环评和排污的审批权,只要通过了环评项目审批,环保部门就难以对运行状态的项目进行有效的污染控制。而面对环境污染较大的企业,环保部门缺少有效的执法手段,而当行政相对人是资金雄厚的大企业时,走完立案、调查取证、审查、告知、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执行等法律程序,相对于违法行为已经过去相当长的时间,这期间企业的违法排放行为仍在继续。对环境违法行为,即使环保部门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若不主动履行,环保部门只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6]。由于法院执行的周期长,手续较为繁琐,违法者有充足的时间周旋和销毁证据,环保部门不具备其他行政机关的强制措施,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管。
3 国际环境法对我国环境保护的启示
3.1 制定明细的配套法规,强化执法力度
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国际环境法在其配套法规及标准方面难以统一,实施和执行一直是国际环境法得以履行的最大障碍。就我国现行的环保基本法来讲,多带有经济建设优先的色彩,并且暴露出了单纯追求经济社会发展的单维价值取向的弊端,已经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7]。我国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多而杂,数量虽多但质量一般,很多法律在运行过程中难以实施。我国相关的水资源保护法有5部之多,由于都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在效力上不分上下,而在一个法律体系中,如果不能确定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上位法,且各部法律由不同部门执行,那么在贯彻实施中必将出现严重冲突[8]。鉴于现有我国环境保护的固有模式政府主导和企业自律,因此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下,需加大投入进行环境资源调查和基础研究,广泛进行以民众参与为主,并结合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不断完善实施过程中的配套法律与规章,赋予环保部门单独的执法权,全面建立一整套以法保环境的奖、罚、惩的措施,通过制定明细的配套法规解决执法难的问题。
3.2 加强各行政机关间的交流与协作,统筹应对复杂的环保形势
国际磋商合作已被实践证明是当今解决国际环境问题的最有效和最主要的途径,这一成功的模式值得借鉴。例如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之间围绕保护多瑙河生态环境的问题,统筹建立了一整套水资源保护和管理的法律体系[9]。莫桑比克,南非和坦桑尼亚针对海洋环境污染问题签订有法律约束力的三方协议,联合划定了跨国海洋保护区[10]。事实上我国环保部门完全受制于地方政府,环境保护“多家管”的现状是造成目前环保部门难以统一管理的重要原因。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国外在《环境保护法》中明确规定:保护环境是国家、政府、每个公民、企业、社团的共同责任,各级政府首长是本区域内环境保护的第一责任人。目前我国对同一条河域,环保部门拥有环境污染数据,相关的水文数据归属水文站,而资源数据又归属国土资源局,各个单位之间无协调机制,共享资料异常困难,出现环境问题时各部门之间极易出现相互争权或者相互推诿的现象。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在于法律规定不明确,因此必须以立法的方式进一步规定各部门间的权限,突出环保部门的执法依据和权力;国家应将各机关的协调工作放到新的高度,通过试点的方式找出一条各部门间协调统一应对问题的办法;自上而下将环境质量列为当地政府干部官员考核的一个重要项目,促使地方政府将环境保护事业落到实处。
3.3 发达地区扶持不发达地区发展环保事业
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背景下,“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逐渐成为各国应对环境问题的思路。由于历史和政策等因素,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了环境保护事业发展不一致,东部强于西部,城市强于农村,工业地区强于农业地区。在这样的现状下,国家应该加强协调,建立一个长效的协调机制。在环保方面打破行政区域的局限,促进各环保资源在区域内的畅通流动;健全合作机制,激励和支持各地区开展各种形式的区域合作,技术交流和人才合作等;建立扶持机制,发达地区可以采取常用的对口帮扶的办法,加强资金的支持,优惠技术转让,增加人才的交流机会,通过派遣专家和技术骨干赴实地指导,派遣当地的技术人员赴发达地区考察学习,以此开拓环境保护的新思路和提高环境保护的技术力量。
4 结语
从“抗洪抢险”到“载人航天计划”可以看出,我国比其他发达国家具有更巨大的执政优势,即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全球环境是一个有机整体,环境保护工作是关系到我国生存发展的大事,只有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促进国际环境法的日益完善,巩固国际环境法的实施成果,才能抑制世界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同时以推进和履行国际环境法为契机,可以帮助完善我国环境保护相关的配套法规,强化环保执法的法律体系,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环境保护的难题。
[1] 郭冬梅.《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履行的环境法解释与方案选择[J].现代法学,2012,34(3):154-163.
[2] 左安磊.国际环境法上风险预防原则基本问题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1(23):7,9.
[3] 姜玥.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的再探讨[J].商品与质量,2011(SA):84-85.
[4] 林灿玲.国际环境法理论与实践[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54-54.
[5] 蔡守秋.中国环境法40年历程回顾[J].世界环境,2012(3):32-33.
[6] 侯浩波.浅谈我国环保工作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2(17):117.
[7] 靳韬.我国环境保护法存在的问题和立法的建议[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2009(9):180-181.
[8] 张小丽,李彦彬.我国水资源保护立法现状及其完善的对策[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1,11(6):47-48.
[9] JANSKYALIBOR,I.PACHOVAANEVELINA,MURAKAMIB MASAHIRO.The Danube:a case study of sharing international waters[J].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2004(14):39-49.
[10] GUERREIRO JOSE,CHIRCOP AlDO,DZIDZORNU DAVID,et al.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instruments in enhancing transboundary marine protected areas:An approach in East Africa[J].Marine Policy,2011(35):95-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