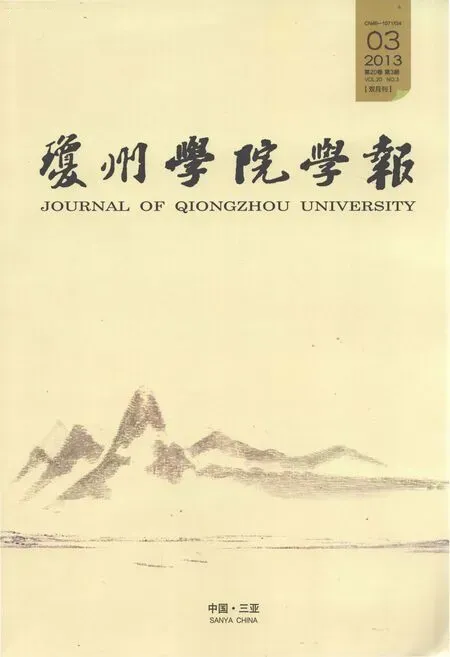潮流之外
陈东东
海鸥的暴风舞蹈,海豹的嗥叫比赛,
在海面上,在海水里……
神圣的多余的美,
控制比赛,君临命运,催树生长,
拔山巍耸,推浪倒倾。
欢乐,这难以置信的美
像燃烧的星,照耀着嘴唇的结合,哦让我们的爱也结合,没有一个
为爱燃烧,为爱饥渴的少女,
有我的血对你的爱还要强烈的爱情,海豹的岸边,正当翅膀
在空中像编网一样织出
神圣的多余的美。
——罗宾森·杰弗斯
一个观摩了何多苓画作的美国人,将一本罗宾森·杰弗斯的诗集送给画家。“相信你会喜欢”,赠书者说。他大概看到了何多苓跟杰弗斯气质的某种相像。那是1985年的事情。画家后来回忆:“诗集对我的影响很大……那些诗,我当时还试图翻译……”(唐丹鸿《何多苓访谈录》)。获赠的是《无一例外》(Not Man Apart),最初由塞拉俱乐部于1965年编成。汇集起来的杰弗斯诗作间穿插着不少加利福尼亚大苏尔海岸的照片。那些风景,一定先于诗作吸引过画家的注意。而当何多苓以其玩票式翻译细读和理解杰弗斯的时候,更注意了这位离群索居的诗人严肃得过于严厉的诗观和人生观。
费时多年,自己动手采石,敲凿,吊装,堆垒,用泥浆把巨大的花岗岩砌起,杰弗斯为其独特的诗艺建筑了下俯群山延绵的大苏尔海岸的鹰塔。“他把爱默生式的个人主义发展到了令人惊奇的程度。那孤零零的高塔巍然屹立,代表着他的自我独立,而这种独立又反过来把他的厌世思想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罗宾森·杰弗斯一直就住在鹰塔和塔边同样由他亲手建筑的石屋里写作,远离尘嚣,也远离了他那些在现代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里事端迭出,惊世骇俗的同行。然而他的鄙视虚伪,憎恶嘈杂,不合潮流和孑然倨傲,不也是事端,不也惊世骇俗吗?有一个时期,推行新批评的现代主义知识界甚至把他视为全美最不值一提的诗人——一个形象的比拟说:在十二音的时代,他还在用全音斟酌推敲。——然而这不是事端,不惊世骇俗吗?“对我来说”,杰弗斯在他的诗选前言里写道:“很显然,诗倘要生存,必须重新获得仓卒间让给了散文的某些力量和真实性……诗变得越来越脆弱、异想天开、抽象、不真实、古怪……诗必须重新获得物质和思想、生理和心理的现实……”。
简略得几乎变了形的杰弗斯剪影,跟与之偶然相逢的何多苓还真有几分相像。不过这相像只限于提喻层面的举隅。隐喻和换喻的层面,悲怆地面对加利福尼亚大苏尔海岸澎湃荒凉的诗人,跟恬然生活于四川成都烟火气里的画家,并不对应,也无法借代。可以找到的他们核心的共同点,或许,仅在于从各自的自我出发,对“神圣的多余的美”的阐发、演绎和奉献。将视线从共同点移开,扩展,去鸟瞰全景,那么,可以看到,他们所处的文明、时代、国度、历史、文化,他们的生活方式,生命形态,相差何止从四川成都到加利福尼亚大苏尔海岸的距离……
然而不妨再看一眼,譬如,鸟瞰1985年的景象,却又会发现,相对于他所来自的中国当代艺术界,何多苓反而跟那时已逝去二十多年的罗宾森·杰弗斯更为接近。这一年,应马萨诸塞州艺术学院的邀请,何多苓赴美讲学。正是在波士顿,他读到了大半辈子隐于鹰塔和石屋,忤逆时代写作的罗宾森·杰弗斯——这如果不是一个象征,也会是一个颇为视觉化的戏剧场面——何多苓在这一年的这一次(头一次)出国远行,让他外于,甚或背向中国当代艺术那汹涌激越的新潮流的形象,显得触目。
要是去编撰中国当代艺术的大事系年,那么,这一年—1985年,应该改用粗体字书写。已见的几种中国当代艺术的“大事记”或“大事年表”,也的确对1985 这个年份特写而大书。这个中国当代艺术粗体字的1985年—“85 新潮”,要比日历上的这一年开始得更早,而且,不妨说,这粗体字的年份或显或隐地仍在延续……
依照艺术史、艺术辞典的定义,“85 新潮”系指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艺术家们掀起的以现代主义为特征,将西方现当代思想、观念和艺术直接“拿来”或从中获得启示,受到影响,激发灵感的新艺术运动。
1979年9月27日,在正举办“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的中国美术馆馆外公园铁栅栏上挂出“奇怪的”油画、水墨画、木刻和木雕的“星星画展”,算是85 新潮的一个先声。更为认同现代主义的艺术家们反感于政治化的写实路线,进而挑战窒息艺术自由的官方体制。为争取美学自治,“星星画展”的艺术家们还被迫组织了长安街上的示威游行。
1985年5月,举办于北京的“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被视为“85 新潮”的一次展开。一批不迎合政治口号、摆脱文学描述、打破自然时空和方式多样化的作品得以呈现。有文章说“它像一个标杆,竖立于中国向现代化进军的美术起点;它像一篇宣言,预示了现代艺术的流向;它又像一面旗帜,启迪着青年艺术家们施展才华。”(张蔷《绘画新潮》)
不同类型的艺术展览和学术研讨会在各地出现,许多艺术群体相继形成。后来有人回忆,“在那几年难忘的日子里,几乎你2-3 天不看《中国美术报》或闷头画画,你就会错过了2-3 个群体的最初萌生。”(抗间《在现实与内心之间一新具象艺术》)据说,从1982年到1986年,新出现了79 个艺术群体,分布于中国版图的23 个省市、自治区;举办了97 次艺术活动。(吕澎、易丹《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人数众多、作品庞杂,渠道广泛,观念颖异,印迹深刻……这便是“85 新潮”的波澜壮阔。如此叙述并不夸张——新艺术的锐气和巨大活力猛烈地冲击着旧传统、旧立场、旧格局、旧方法。北方艺术群体、厦门达达、江苏红色·旅、浙江池社、湖南《画家》群体、湖北部落·部落、北京盲流艺术家、上海M 艺术体、广州南方艺术家沙龙……他们突显于“85 新潮”,操练西方现当代的众多艺术样式,风格流变,形成和发展自己艺术或反艺术的情绪、态度、思维、个性、理论、作品和派头。
1989年2月5日至19日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可说是“85 新潮”的直接后果,并且启发诸多新的可能性。这个推迟了将近两年,场地终于定在北京中国美术馆的展览,尽管以“禁止调头”的交通标志为标志,却还是成为了当代中国艺术转折的一个标志。十五天的展期,伴随着枪声、恐吓、拘捕和两次叫停,种种兼为事件的作品和兼为作品的事件引来普遍的哗然。而后,它在一片喧闹之中结束。
对“85 新潮”,对“中国现代艺术展”的直观感受,也许会让人想起叶芝《基督重临》里的句子:
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
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
或这个诗人写在《1916年复活节》里的句子:
但一切变了,彻底变了:
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
波普、涂鸦、抽象、玩世、泼皮、艳俗、图像、装置、观念、方案、行为……后面则一律不妨缀以“艺术”二字,这大概便是中国当代艺术已经诞生的“可怕的美”。在“85 新潮”,在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的现场,它们差不多一应俱全,尽管有些还只是初露端倪,甚或隐而不现。之后的二十多年,这潮流时而遭遇到譬如说政治的险阻冰封,时而壮大于譬如说资本的推波助澜,左奔右突有之,决堤改道有之,几乎就汪洋恣肆,蔚为大观了。从“社会学意义上的群体角度”——2006年,何多苓跟他的多年老友,诗人欧阳江河在一次谈话里,议及了如此“可怕的美”的进展——“应该说,这个角度给当代中国艺术带来了活力和成功,带来了标签、符号、定位、倾向性,当然,还带来了全球市场。这里面既有积极的东西和有生命力的东西,也有负面的,急功近利的,泡沫的东西,这本来是文化和时代精神之常态,……不正常之处是批评界的反应与市场的动向几乎完全趋于一致,完全合流……”并且,它带来那仿佛正当的,几经预告、正在上演、已无悬念而仍要以悬念的方式推进的大结局——“从此,没有人敢于问‘什么是艺术’这样的问题。”(吕澎《我们今天不能问“什么是艺术”》)
“可怕的美”的潮流里,并无何多苓的身影。他1985年的远行美国,尽管不过是巧合,却仍可以视作一个颇具表现力的姿态。而只要略微了解一下何多苓及其绘画,就不难想见,如果那一年未有美国之行,何多苓之于“85 新潮”,也一样只是隔岸,就像他这么多年来之于中国当代艺术潮流的惯常风度。大概正是出于一种基本判断,在波士顿,那个美国人才会赠送罗宾森·杰弗斯的诗集给画家,才敢那么肯定:“相信你会喜欢”。
何多苓无疑是当代中国一位杰出而重要的艺术家,当代美术史的一般叙述,则总是不忘强调这位艺术家的“颇为独特”。他的绘画艺术虽然差不多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开始的中国当代艺术同时起步,他的艺术历程虽然更是和中国当代艺术的历程同时推衍,但是,可以说,何多苓跟中国当代艺术的普遍进程并不同向,也不同步。有意思的是,在那些着眼于风云、形势、征候、运动、争议和新闻的中国当代艺术“大事记”或“大事年表”里,几乎就难以找到何多苓的名字——在弄潮逐流的起事心态和生事策略成为当代艺术家一大成功要诀的时代,何多苓在“大事记”或“大事年表”里的这种缺席和隐匿,他的远离事端,实在发人深省。“在喧嚷的潮流中是多么寂寞,”(何多苓《自序》)曾经,何多苓忍不住如此感叹。这声感叹满含着孤身一人自外于潮流对一个当代艺术家的况味。实际上,何止寂寞——他虽自外于潮流却分明在潮流的裹挟之中,要艰难地竭力去站住脚跟,竭力找寻和走通自己的道路,有时候,他几乎不得不逆潮流而进……“但使我满意的是,”何多苓说:“从一开始我就是只身一人,潜心作画,未成为任何潮流的主将或附庸。”欣慰和苦困之因,何多苓也讲得明确:“我多年来始终强调绘画性,强调绘画过程中的个人感受。我独特的地方大概就是不从群体角度出发。”——经由何多苓自我认知的独特性,不仅提示他的性格、气质和本能(何多苓:“本能使我对潮流和时尚有天生的免疫力。”),也表明了他的人生态度和从中生发、与之一致的艺术态度,并显现为一种仿佛从容、甚或优雅、实则奋勇乃至奋不顾身的超越。
当他起步于中国当代艺术的起步之时,何多苓的绘画,被评论界有点儿轻易地划到了“伤痕美术”的忧伤和反思之下,后来还曾被目作在“伤痕美术”和“乡土绘画”方面颇多实绩,佳作迭出,形成了所谓“四川画派”的其中一位代表性画家。那正是新艺术在当代中国的觉醒期,他画了令他声名鹊起的《春风已经苏醒》(1982)和被奉为八十年代油画经典的《青春》(1984),之前那幅《我们曾经唱过这支歌》(1980)因受阻参加全国美展而引来话题,再早一幅现在只留下精细的素描草图的《在收获的土地上》(1980)如果不告夭折,相信会引起艺术界极大的震动(吕澎,易丹《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这些作品,因为“我们时代”的形象、复杂化的人道情感、深省的回忆、可贵的清新、真切和诚实,以及对技法的探索追求,跟一时主流的“伤痕美术”,跟以扎实的绘画功底见长的四川美院油画系出身的一批画家,具有了取向的一致性。但是,何多苓这一时期作品里抒情的多义、思想的严峻、语言的自觉和象征的表达,却早已逸出了“伤痕美术”和“四川画派”这样的概括。
从一开始,何多苓的艺术便有着疏离的倾向。对时代和潮流的疏离,甚至时而表现为对过去自我的疏离,仿佛与生俱来,一直伴随着何多苓绘画的演进。疏离更多是一种感觉,陌生的、清寂的、幽雅的、自守的、不盟的、辽远的……却并不会引起绝对的孤独,不会有罗宾森·杰弗斯那种“非人道主义”的悲观主义后果。然而疏离并非不构成反叛,并且,实际上,在另一方面,何多苓正不妨是这个时代以反叛精神为特征的艺术思潮的积极响应和推行者。就行动而言,譬如,远在85 新潮的史前期,何多苓就曾参与到群体之中——跟星星画展几乎同一时期的另一个民间画展,1980年1月11日出现于重庆沙坪坝公园的“野草”画展上,何多苓的身影,简直可以是一个掀启中国现代主义艺术运动新潮的身影。只不过,他在昙花一现般的“野草”画展出现的如此身影,更是昙花一现。就绘画而言,譬如,从杂志封底发现20 世纪杰出的美国画家安德鲁·怀斯,被印刷得很差劲的《克利斯蒂娜的世界》里那片草地的密度所震撼,何多苓以《春风已经苏醒》(1982)和《老墙》(1982)等作品,为中国当代油画带来了后来一度形成潮流的“怀斯风”。此处可见出典型的何多苓方式:他在画笔间引入怀斯,从而疏离在当时语境里正统得僵化的写实主义绘画,从而以“更加理性和哲理化”、“更为客观、精确”的绘画语言突围流行风格和自我;可是当周边“怀斯风”盛行起来,他便又独自疏离开去,摆脱开去,更加“无声无息地、艰苦地寻找自己的语言。”
安德鲁·怀斯,人称“现代隐士”,他面对人生和艺术的态度,他的独持己见一意孤行,跟大他三十岁的罗宾森·杰弗斯颇多共通之处。何多苓之喜爱怀斯,正如他对杰弗斯的喜爱,细究起来,自有其更为内在的性格和精神因素与之呼应。疏离本就是何多苓气质的一部分,“我不擅长与人交际,”他说,“绘画正好成全了我,因为绘画是我可以独立完成的一件事,不需要与人合作。”何多苓又曾这样自陈:“我从来不会去追求自己得不到的东西,或许这种态度是消极的,但对我而言它是一种带着淡淡诗意的消极。它可以让人在精神上获得解脱,不管这种解脱是虚无的还是消极的,它们本身都不是贬义词,而只是一种状态的缓冲。”作为一个天生就缺乏奋斗意志和革命性、认同无神论、以天人合一为人生理想、以存在主义态度看待世界的人,这个混合体的何多苓对自身有着足够的了解——尽管“对于人性的弱点、社会的现状,我一直都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我是一个不愿与人同流合污的人,纵使无力反抗,我也从来不介入各种复杂的情况……我习惯于以自我的方式来对待自己,对待世界,因此我算是一个与生俱来的自由主义者。”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契诃夫笔下的几位艺术家乃至契诃夫本人。事实上,契诃夫正是何多苓一向就喜爱有加的一位作家。何多苓艺术世界里的抒情和诗意,简直跟契诃夫息息相关。他于1986年创作的组画《带阁楼的房子》,除了致敬契诃夫,也是在讲述不得不讲述的艺术家自己的故事。“我对契诃夫笔下的画家有着一种强烈的认同感,事实上我这辈子也确实遵循了这样一条路线。”(杜曦云、赵子龙《静谧中的伤逝——何多苓访谈》)可以说,何多苓对怀斯和杰弗斯的喜爱,是以对契诃夫的喜爱为底色的。如果去比较怀斯、杰弗斯和契诃夫的形象,以及何多苓对他们不一样的认同程度,那么,何多苓形象的某一侧面会更为清晰。
1985年在美国,就在何多苓接触到杰弗斯诗歌的差不多同时,他也有幸细看了一些怀斯的原作。然而,挂在博物馆里的怀斯原作反而让何多苓感到失望。不是因为怀斯画得不好,而是怀斯的那种好,跟何多苓几年前透过印刷品所理解的怀斯之好相差甚巨。何多苓的表达是:“还不如印刷品,不看也罢。”——那么,何多苓当初由怀斯而找到自我表达的画法,正所谓六经注我。在他的艺术实践中,这算是最为显著的一例。其他,举凡他对杰弗斯的喜爱,对契诃夫的倾心,对音乐的专注,对现代诗的重视和理解,对建筑的兴趣直到参与和动手设计,对中国古代艺术的重新发现,对明清情色小说和春宫的在意,对周边同行作品的品评……也都不乏六经注我而为其画笔所用的意味。跟美术史上一些名作的互文、对照和对话,也塑造着何多苓绘画艺术的自我。这种互文、对照和对话,大概开始于他对怀斯《克里斯蒂娜的世界》里那片草地的征用。实则,安德鲁·怀斯对何多苓真正的启示,或何多苓跟安德鲁·怀斯真正的契合在于:虽一生经历现代艺术潮流的种种变化,却始终孜孜于拓展和深化自己的风格和语言。那落落寡合的疏离的另一面,是苦心孤诣的求索。
“重要的是(也许仅对于我自己),在可能性与自由多得令人绝望的现代艺术中,我或许能找到一种新的秩序和限制,在具象和抽象之间寻求和解,赋予我根深蒂固的浪漫意识与对优雅的渴求以一个新的、站得住脚的物质框架。”何多苓如是说。他把受到怀斯影响的作品《春风已经苏醒》视为个人艺术史的出发点,他的艺术迈进——经历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抒情、诗意、象征和神秘意象时期(《老墙》、《带刺的土地》、《天空下的孩子》、《青春》、《1970年慧星与火把节之夜》、《蓝鸟》、《塔》、《小翟》、《乌鸦是美丽的》、《亡童》、《偷走的孩子》、《午后》和《向树走去》……);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后来被他自认为“很轻率,很冒失,很多人觉得完全不能接受”,然而未必不是深思熟虑和没有必然性的“全盘否定的时期”(《迷楼》系列、《庭院方案》五连画和《后窗》系列……);以及本世纪十年的成熟和自由时期(《女人体》系列、《舞者》系列、《躺着的女孩》系列、《婴儿》系列、《落叶》、《青春,2007》、《重返克里斯蒂娜的世界》、《克里斯蒂娜以后的世界》、《小绿人》、《孩子在寻找他的声音》、《这个世界哭声太多,你不懂》、《野园》、《沼泽女儿》、《山水间》和一连串以“兔子”为题的画作……)——越来越明确、越来越义无返顾地以绘画性或曰绘画的诗学为旨归。
“对我来说,最好的东西就是绘画性。”(《欧阳江河与画家何多苓的对谈》)这种绘画性或曰绘画的诗学,努力要把画作提升至佩特所说的一切艺术都向往的音乐状态。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有一次引用了佩特的那句话并解释道:“也许是因为在音乐中意义即形式,因为我们无法用我们能够重述一段故事情节的方式重述一段乐曲。”将这一解释移来说明绘画性或曰绘画的诗学,那么它除了提示一重要义——艺术的不可复制性;它提示的另一重要义——形式跟意义的合一性,会让人想起何多苓说过的一句道理一脉相承的话:“技艺即思想”。
何多苓绘画艺术的不可复制性,总是由他那抵及人性本真表达的手艺匠人的技艺来实现的。“我不非议那些认为绘画不依赖技巧的观点,那是需要另一种意义上的大智慧的。而我自己是喜欢手艺的人,是个匠人。”——何多苓热衷于学习技法、琢磨技法、发明技法、谈论技法、传授技法,因为在他看来,“绘画到技巧为止。实际上技巧最重要。”(唐丹路《何多苓访谈》)这样的观点,让他后来对自己的成名作《春风已经苏醒》持一种稍稍否定的看法,因为“那幅画在技巧上实际上是很拙劣的……刻意去画那一片草地,但我的画法非常不对……”据此,可以说,他的个人艺术史的出发点,也是他要求技法革新的出发点。何多苓艺术的演进,跟他绘画技法的演进相伴随,诸如写实、象征、超现实、表现、幻觉、印象以及建筑化的风格特征被各有侧重加以矫正地利用,去最为直截了当地展现绘画本身,“通过绘画本身来打动人。”他的关键技法貌似简单,实则高难度——“用笔……用笔本身在光滑的画布上画出来。”多年以后,进入艺术成熟和自由时期的何多苓说:“我认为我现在的技巧是比原来高得多。”其表现便是画得“松,非常之松,不像原来用某种预设的、做作的办法,现在更为随意了,收的时候又能把它收到一个我限定的框架里面。”“而‘松’就是那种信笔挥来,看似漫不经心,实际上达到效果,类似‘笔不到意到’”,“更接近国画意义上的写意”。——对于绘画,无疑,这样的技艺更为本质。
如何多苓所言:“从狭义的角度讲,绘画就是一种手上的技巧,运用笔和颜料接触画布后,最终在画布上留下一些痕迹或者效果。”这些痕迹、效果,形成了一幅画面的形象。信奉“技艺即思想”的画家并不会限于让以手运笔的技法仅用于摹勒,他更要让以手运笔的技法直接去呈显——技法赋予的痕迹和效果除了形成画面的形象,也还是艺术家思想情感的终极表现。而这即所谓绘画性——它意味着“绘”跟“描”的千差万别;意味着灵感与质感结合的画意,取决于创造者的心性和内在视觉真态,要经由恰如其分地流露思绪形象化清晰踪迹的“绘”的激发而构成。对以写意见长的中国画来说,这正是一种至高的境界;对于传自西方的油画,这却是从来稀有的品格。
见过何多苓如何在画室里工作的人,都会对画家“手极为灵敏,手感惊人地好,某些手型和动作通过笔触在画面上存留下来”(《欧阳江河与画家何多苓的对谈》)的情形印象深刻——手的灵动、捷巧,手腕的控制,下笔轻重的讲究,恰是何多苓一直追求的技能,它们给他的油画作品带来了仿如国画的审美特征。艺术评论家栗宪庭曾对何多苓说:“我注意到你特别的强调了一种笔触的表现力,非常接近中国传统文人画‘笔情墨趣’的语言规范,每一笔都是靠你的手的敏感,在表达你对对象的感觉和你心中所要的意象。”——理想的、无以言表的、越不确定越好的诗意和无分油画国画的殊途同归,恰是何多苓技法运用追求的目标,这个目标的呈现,便是何多苓意义上的,让人看得出技巧高超但却无话可说的一系列“好画”。
何多苓把他的技艺方式称为“典型的‘绘画’”,并且说:“专业性很强的绘画性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我的画就很有绘画性……”何多苓这种出自技艺追求的绘画性,几乎是他天性的一部分。他很小就开始画画,几岁的时候,他母亲就曾将其画作投给儿童杂志而得以发表。回顾往昔,他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个画画的,并且始终喜欢技艺。“我从来没画过平面儿童画,一画就自然是三维视觉关系的画,小时候我就画得相当成熟了。当我真正从事绘画创作时,一开始就是严肃绘画,依赖技巧。我认为对技法的迷恋和精研可以给我带来愉悦,在某种意义上讲,我是为这种愉悦而画的。”他的疏离感,他的个人化和独特性,他之不愿意汇入潮流,在最本真的层面上,也可以说是由于他的迷恋。何多苓所迷恋者甚至不是画成的作品,而是绘画的过程,这似乎一直都没有改变。“我也觉得绘画是件带给人愉悦的事,画家所观察到的客观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可以表达出来,而且画家可以将自己的主观感受,将自己的心灵嵌入这个表达,在这个表达中可以给自己留有足够的娱乐空间,否则我连娱乐的权利都没有我还画什么呢?”自我的欢愉被放在了第一位。那是一种游戏,荷兰人赫伊津哈意义上的游戏。它为何多苓从社会生活里隔离出一个自己的空间,这个被标示出来的空间无论在物质上、精神上还是观念上都被刻意不同于周边的日常环境——“我对绘画有一些非常偏执和固执的见解。我关心社会生活,也关心政治,但这些永远不会出现在我的绘画中。我的作品完全是游离于这些因素之外的。”——对于何多苓,这种游戏的绘画观之意义无异于杰弗斯为自己建筑的鹰塔。然而,更有意义的实在是它跟鹰塔又那么不一样。作为复杂的文化现象和文明规则的游戏最值得深究的,是它外于现实世界之逻辑架构的多余性和在那多余的游戏过程中的神圣感,时常会唤起人性中对美的渴念。正是经由这“神圣的多余的美”的途径,何多苓的天赋、性格、气质和他为追求自我愉悦而迷恋的技艺走出鹰塔,提供了具有共同体意义的当代可能性。
他称之为道具的何多苓式光照、地平线、天空、草地、鸟、墙、楼道、窗景、院落和女性形体的多义被他自己日益削减,去除,从受潮流影响的因素回归其本真。画作里,轮廓几乎消失,人物融入环境,而环境只不过是一种非环境,对应和呼吁着空白与空无,外界和内在已没有差别,可以相互逾越……“我现在取消所有的道具。所有的词汇,所有的思想,所有瞬间感受全部融入笔法。时间,空间,静与动,所有影射这些东西的道具都不再使用。”(《欧阳江河与画家何多苓的对谈》)他不断去重复笔触间某些微小的元素,“这是我的兴趣之所在。往大处说,我认为这是宇宙构成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令其绘画徘徊于写实与抽象,繁复与极简,理性与抒情,观念与风格而难以界定;令何多苓的艺术家形象,仿佛隔绝于正大行其道的观念艺术、复制艺术、方案艺术和放弃艺术最根本的技艺性、完全丢掉手艺的这么一个被叫作“当代艺术”的历史时期。然而却又因此,何多苓的艺术更有其针对性。何多苓的游戏,也因此成了一种探险——装置、行为和新媒体遍及天下,横行世界之际,绘画性能走的,或许也惟有鸟道——只不过,鸟道有时候正好是玄路。
走向鸟道玄路,并将之走通,用何多苓的说法,为了“追求一种很虚无缥缈的东西,更加接近中国文人画的本质——心手合一的自由。”要是把这种自由表述为天人合一的境界,当不会错。何多苓对这种境界的追求,在初始阶段,是去表现人与自然的并峙,而后发展到书写心中意气,以笔势笔触体现一种内在气韵,“是‘写’,而不是画,”何多苓强调:“我虽然没画过国画,但我现在作画用的方法更多是中国传统的笔墨,而不是学院派的油画方法。”于是,何多苓出自技艺追求的绘画性,也延展了反叛、颠覆和革命——去除却油画的某些特性——用这一西方画种的样式、工具和材料,反过来抵制其惯常的西方美学趣味,譬如肌理的制作,光与色的交织,对比强烈的效果,美善的经典形象、密集物质化的信息等等,而以平、虚、淡、远相替代,更接近中国传统的绘画美学。画面上有意为之的平、虚、淡、远,也克制、“蕴含住”了何多苓作品丰沛盈溢的抒情力量,使之不像早年那般汹涌,那般深沉,而是要么冷寂、反讽、晦黯、辛涩,要么平和、含蓄、宁穆、悠邈。何多苓的诗性更加不确定,更加无以言表,更加千头万绪,也更加富于思辨……
行于鸟道玄路的何多苓的艺术历程,也是他的心路历程,跟时代潮流的愈益疏离,使之愈益走进自己的内在。何多苓所言“技艺即思想”,跟大涤子石涛“一画落纸,众理随之”的一画法之论相通。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下笔有神,其天赋、本能、性情、才学、经验、理想、思虑和颖悟尽皆倾注于手的灵动和画笔一捺一拉、一撇一划、一杵一收的无悔。何多苓创造的艺术世界,正是一个精神世界。在何多苓的这个世界里,总是有一个说“不”的声音,反对着当代艺术的流行见解和花样翻新,拒绝着当代艺术的无所不能和怎么都行。他喜欢引用斯特拉文斯基在《音乐诗学》里的所言:“艺术越是有控制、有限制、越经琢磨,就越觉自由。”以及“我把自己的活动天地限制得越小,为自己设置的障碍越多,我的自由就越大、越有意义。”因为这几乎就是何多苓自己的所言。而他在国内外主流艺术空间甚嚣尘上着“绘画已死”口号的当代坚持其绘画性的追求,孜孜不倦地寻找绘画性在当代转换的可能性,将自己的表达严守于架上画框和手艺匠人的技法,更是身体力行了如此所言。“我现在的画是一个螺旋形的上升,更归于本质。”有一次,当建筑师刘家琨到何多苓工作室看画的时候,何多苓这样说及自己:“……我没有改变过。第一,我的画从不出现政治符号,不搞政治波普,这是我的底线。我认同的还是内心感受,人文主义的东西。第二,文人精神就是书写心中意气,更多体现在内在气韵上。”
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何多苓艺术进程里出自技艺追求的绘画性或曰绘画的诗学,其作品散发的人文气息、诗意和诗性,他用油画这一来自西方的艺术样式去接近、去重新发明东方画意和艺术精神,去承继、去发扬蹈厉中国的抒情传统,以仅属于何多苓的方式达成潮流之外与众不同却又具普遍意义的另一种当代艺术可能性的努力,体现的正是一以贯之的担当和执行。这不免让人想起古代中国“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的那种称之为“士”的人物。“士志于道”《论语·里仁》,是文明基本价值的维护者,自始至终担当和执行着文化思想之传承和创新的中心任务。何多苓从一己的天性、兴趣和秉赋出发,从神圣的多余的游戏出发,去完成其美的创造的同时,并非不自觉地,他也践行着士道,以其个人化的疏离、内敛、优雅和高贵,将士的精神面貌体现于当代。
我走在荒原上。
我望着地平线。当我想到,有一天它将被无数高层大楼割裂开来,我不由在心中珍藏起这美好的印象。地平线对我来说是一个终端——在我的画面上,它是一切线条的归宿。而对于我置身其中的伟大景观,它是沉默而响亮的自然交响诗的终止和弦,一个永恒的纪念象征。
四十年代末,美国诗人罗宾森·杰弗斯这样写道:
文明像屠杀兔子一样屠杀了美
他早已死去。他的罪恶的诅咒被遗忘了。物质文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混凝土比沙漠还要无情地吞噬着土地。不管漠然无视也好,自我陶醉也好,曾经作为艺术历史的无尽源泉的这个自然生态是改变了。田园诗的美学寿终正寝,代之而起的是“都市”与“超级都市”的美学,即机械文明所造成的新的生态环境中新的审美观念与价值。与自然的逐渐隔离,拥塞的物质环境、疯狂的速度与节奏效,使人变得过分敏感、脆弱、多疑与自我怀疑。他被日益紧缩的空间压抑着,在他的自我和谐的愿望中挣扎;“本能”就在这时被召唤出来,成为精神的至高无上的对等物。人的目光被局限了,于是他倾向于内省,从自身行为功过循环中去发掘另一种美,从潜意识的不可遏止的官能欲念中寻求生存的价值。
……
不管这种症状引起的高烧兴奋状态还要持续多久,人类和艺术的前途并不是那么悲观的,一个重建起秩序、克制和自我约束的理性时代即将到来。人将在新的、健康的文明的基础上与自然重归于好。理想将重新出现在人与自然的本质和谐的观念之中。如果说,艺术比其它领域更敏感地对这种和谐的消失作出反应,那么它绝不应该仅仅是后者的被动的逻辑完成。艺术的使命是首先重建起这和谐,哪怕只存在于理想之中。
——这些话录自许多年前何多苓一篇题为《信念——人的自然与自然的人》的文章。现在,他大概已经不喜欢那时的文风,以之对照何多苓后来的进程,也会看到他心路的曲折和目标的转换。但是,何多苓的信念而今依旧,并没有泯灭,那“另一种美”,仍被发现着。
何多苓并不觉得他已经走尽了他的鸟道玄路:“我希望我还能画出更好的,这种希望是一种悬念,这种悬念是生活的一种魅力,假如缺乏这种悬念的话,人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探险还在继续,无止境地“任重而道远”。并且,新的前景里——
……我已经从一种美
进入了另一种美,一种安宁,一种夜的壮丽。
——罗宾森·杰弗斯《西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