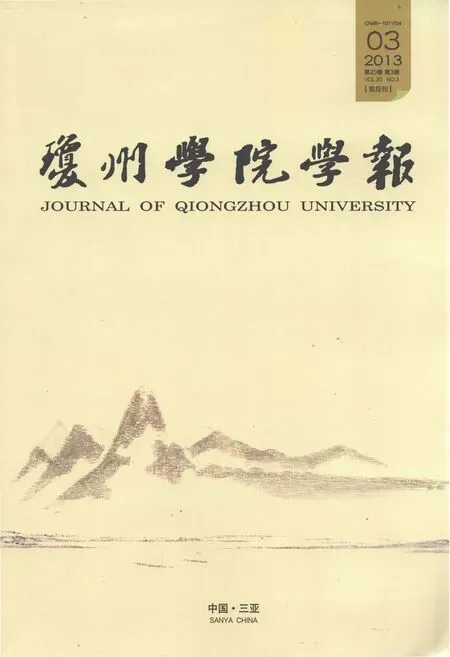木斋古诗曲词研究的时代意义
江晓辉
(中山大学 中文系,台湾 高雄 80424)
一、问题缘起
木斋先生关于古诗以及曲词发生问题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也有一些质疑。先生当下在台湾中山大学开设选修课,就有本科生同学向其请教:既然现在没有新材料出现,即是说今人和前人看到的材料都是一样的,为甚么前人没有发现这些问题?为甚么直到现在这些问题才被提出而有新的突破?这个问题无疑是非常尖锐而且深刻的。清代学者的朴学考据,胡适以来众多的大师,在这一问题上为何没有得出如同木斋所研究出来的结论?笔者认为,概而言之,这是时代的原因所造成。时代的演变造就了意识形态的解构,学术思想的解放和新的方法论的出现,成就了木斋的两大研究。
总体来看,先生之研究既新亦旧:新者,是指在当今学界(不论是学者还是学生)对传统文学史普遍接受的情况下,先生的理论似乎是标新立异,不符旧说,不能为很多人接受。旧者,是指某一些议题上,古人早有成说(例如曲词的起源发生及其音乐性的问题),或已提出合理质疑(如曹植、甄后关系及古诗十九首的作者问题),只是后来的文学观念不同,才被忽略或打压,先生所做的其实是拨云见日的工作,以新方法、新角度发明旧说,还原历史真相。
笔者认为,木斋先生的这些研究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标新立异之说,相反,古代一些思维较为通脱敏锐的诗人学者,已对相关的问题提出质疑,例如上面谈到的古诗十九首的时代和作者问题,钟嵘的《诗品》早已质疑:“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客从远方来、桔柚垂华实,亦为惊绝矣。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至于曹植、甄后的关系,在东晋到隋唐,更成为画家诗人的题材和典故。关于词起源,古人普遍认为李白是“百代词曲之祖”,而李白之词为宫廷应制之作,则词非源民间,可以明矣。
然而,为甚么这些说法多不见载于文学史?窃以为原因有二:其一,虽然若干学者已意识到这些问题,但碍于当时的时代风气和学术潮流,无法进一步去探明真相,或是虽有异议却不敢提出。其二,后来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观的影响下,本来是历史真相、有根有据的说法,被刻意的忽略、掩埋和扭曲。综论之,是不同时代的因素令古人原本合理的说法被忽视,历史的真相被掩埋。而木斋先生生于现代,亦正因为这时代的因素,使他有更全面而广阔的学术视野和高度,更自由的学术环境,更严谨的研究方法,以及中外不同学者互相印证交流的平台,去进行使历史真相重见天日的研究。
二、时代因素对研究的影响
木斋先生之曹、甄关系研究及曲词起源发生这两个课题,正好作为例子说明时代因素对研究的影响。在历史上,古人对“感甄说”的接受,有一个明显的现象:自东晋到唐,自顾恺之到李商隐,曹、甄之间有暧昧关系的说法,都在很多的诗人文士间流传,不管他们抱持的是中立、感叹、讽刺等何种态度,他们都对曹、甄间的恋情毫不讳言,李白、元稹、李商隐等都以之为诗料或典故。①李白“洛浦有宓妃,飘飖雪争飞。轻云拂素月,了可见清辉。解佩欲西去,含情讵相违。香尘动罗袜,绿水不沾衣。陈王徒作赋,神女岂同归。好色伤大雅,多为世所讥”(《感兴》);元稹“班女思移赵,思王赋感甄”(《代曲江老人百韵》);李商隐“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无题》)、“来时西馆阻佳期,去后漳河隔梦思。知有宓妃无限意,春松秋菊可同时”(《代魏宫私赠》)、“宓妃愁坐芝田馆,用尽陈王八斗才”(《可叹》)、“宓妃漫结无穷恨,不为君王杀灌均”(《涉洛川》)、“国事分明属灌均,西陵魂断夜来人。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时赋洛神”(《东阿王》)。宋代开始,情况截然相反,不少学者大力挞伐“感甄说”。②宋人刘克庄:“《洛神赋》,子建寓言也,好事者乃造甄后以实之。使果有之,当见诛于黄初之朝矣。”(《后村诗话》前集);清人何焯:“植既不得于君,因济洛川作为此赋,托宓妃以寄心文帝,其亦屈子之志也。自好事者造为感甄无稽之说,萧统遂类分入于情赋。于是植既为名教之所弃,而后世大儒如朱子者,亦不加察于众恶之余,以附于楚人之辞之后,为尤可悲也已”(《义门读书记》);清人潘德舆:“子建人品甚正,志向甚远,观其《答杨德祖书》,不以翰墨为勋绩,词赋为君子;《求通亲亲表》、《求自试表》,仁心劲气,都可想见。即《洛神》一赋,亦纯是爱君恋阙之词。其赋以“朝京师,还济洛川”入手,以“潜处于太阴,寄心于君王”收场,情词亦至易见矣。盖魏文性残刻而薄宗支,子建遭谗谤而多哀惧,故形于诗者非一,而此亦相类也。首陈容色以表其才,次言信修以表其德,继以狐疑为忧,终以交结为愿,岂非诗人讽托之常言哉?不解注此赋者,何以阑入甄后一事,致使忠爱之苦心,诬为禽兽之恶行,千古奇冤,莫大于此。”、“子桓日夜欲杀其弟,而子建乃敢为“感甄”赋乎?甄死,子桓乃又以枕赐其弟乎?揆之情事,断无此理。义山则云:“宓妃留枕魏王才。”又曰:“来时西馆阻佳期,去后漳河隔梦思。”又曰:“宓妃漫结无穷恨,不为君王杀灌均。”又曰:“宓妃愁作芝田馆,用尽陈王八斗才。”又曰:“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时赋洛神。”文人轻薄,不顾事之有无,作此谰语,而又喋喋不休,真可痛恨!”(《养一斋诗话》卷二》);清人朱绪曾:“一庶人之家,污其妻若母死必报,岂有污其兄之妻而其兄宴然,污其兄子之母而其子宴然?况其身据为帝王者乎?”(《曹集考异》);清人丁晏:“序明云拟宋玉神女为赋,寄心君王,托之宓妃、洛神,犹屈、宋之志也,而俗说乃诬为感甄,岂不谬哉!”(《曹集铨评》)不同时代对于“感甄说”的接受程度,与当时儒家的礼教、伦理观的强弱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儒家思想在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后被定于一尊,但在三国之后却开始动摇。魏晋时人,放浪形骸,轻视礼教,自不消说;南北朝时列国争战不休,统治阶层道德丧乱,社会风气败坏,百姓命在旦夕,儒家的价值信仰备受怀疑;到了唐代,因其统治者作为胡人,本已带有通脱不羁的性格,加之唐帝国作为当时的国际都会,四方文化交汇,形成多元包容、浪漫开放的社会风气。在这些儒家礼教观念消减的时代中,“感甄说”容易流行。但自宋代理学兴盛以后,维护传统伦常礼教,强调“严男女之大防”,此观念除了元代异族统治、明中晚期个性解放,而稍有松懈外,一直到清朝,都成为社会主流。在这种道德观念下,曹植和甄后的关系自然被视为禽兽不如而加以攻击。学者既不承认曹、甄的关系,自然无法解开古诗十九首的作者身份之谜,因此也不可能解决古诗起源的问题。
而关于曲词的起源发生,现在的文学史亦大都主张词起源于民间,但稍加细想即不难发现此说的不合理性。例如,词作为“雅文学”,不但注重文词的典雅,尤其特别强调音乐性,如何会源出于民间?须知道词发生于盛唐,盛唐犹是以贵族为统治阶层的社会型态,专业的音乐歌舞的创作和演唱,仍握在宫廷贵族阶层手中,民间何能发展出须与音乐结合的词?况观早期词的内容,大多非民间所能参与或接触到的,所以,“民间说”存在着很大的疑点。然而,既然“民间说”存在这么大的疑点,为何近现代的学者都提倡“民间说”?只要翻阅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史,可以发现“民间说”盛行于20世纪初,由胡适和陈独秀等人倡导的新文学运动。胡适在《词选·序》说:“词起源于民间,流传于娼女歌伶之口,后来才渐渐被文人学士采用,体裁渐渐加多,内容渐渐变丰富。”断言词出于民间。不止是词,他在《白话文学史》中更武断地指出“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对新文学运动的理念和方向起了指导性的作用,影响十分巨大。新文学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延伸,不单纯是一场文学运动,更是一场思想、文化的改革运动。当时的知识分子目睹中国状况,认为要改革中国,必先从改革国民思想上入手,故大力提倡西方的科学和民主,又认为国民思想须从封建的旧文化中解放出来,才能改进民智。文学作为思想的载体,自有改革必要,因此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无不强调文学的“大众性”。如果作为单纯的文学运动,这种观念自然可以提出来加以讨论和宣扬,但新文学运动自始即与政治运动挂勾,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功利性,使得他们往往对很多问题的讨论碍于成见、失于偏颇。正如词曲起源这问题,在古代本就有很多文献证据说明词是出于宫廷,①详参木斋《唐宋词流变》、《曲词发生史》等著作。但胡适等人往往被当时的风气思潮所局限,或为了符合自己的文学观,对证据视而不见,未能作客观审慎的分析。“民间说”的流风所及,披靡一两代学者,更影响了后续的文学史,如此因循相袭,自难揭示历史真相。
从上述所举的两个情况,可以归结出两种影响研究的时代因素。一是因伦理、道德规范所形成的势力;二是学术、政治运动所形成的思潮。而在这两种因素下研究问题,往往不是对文本、证据作理性、纯学术的讨论,而是偏向对研究者、持论者的人格、动机的抹黑,例如潘德舆就骂李商隐诗中写曹、甄之事是“文人轻薄”。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往往会自我设限,难以取得突破。步入廿一世纪,以官方意识型态作主导的文学思潮或文学运动日趋减弱,学术研究趋向更多元、包容、理性,加上对研究方法的重视,中外学者频繁交流等因素,使得某些研究可以超越前人,有所创获。木斋先生众多发前人所未见的研究,正是在这些时代的因素下开展的—如果在其他时代,曹、甄关系的研究很可能被视为“轻薄”,古诗十九首、汉乐府、曲词非出于民间等研究,很可能被视为“反动”、“封建”,而被主流所忽视,甚至打压。
三、木斋的研究成果与时代之关系
那么,木斋先生的研究如何突显了时代的因素?他的个人特质又如何促成他的研究?以下分从四方面略作论述:
(一)研究态度-敢于挑战权威
在近现代社会,随着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知识的普及、个人意识抬头,旧日的权威已失去了绝对的话语权。不管是政治上的当权者,还是思想界、文学界中的伟人、大师,都不再高高在上。在文学上,传统的主流说法固然有其理据,支持这些说法的学者亦多学术精深、地位尊崇,但并不表示其说法无可质疑。古诗十九首、汉乐府、词源于民间的说法,在胡适等人的论述、文学史的宣扬下,已经成为一种权威,俨然不可侵犯。木斋先生年轻时上山下乡,在当知青的岁月中,面对种种艰难和威权,毫不屈服,因而培养出独立思考和质疑权威的精神。龚斌先生为《历史的化石-知青十五年》写的书评文章中就这样说“许多学人对过去的学术权威和政治权威,即使有与之不同的见解,也不敢公开质疑,甚至还在说一些违心的话。这种猥琐的作风,在木斋身上完全看不到。他口中所言,即心中所想。当经过深思熟虑,认为自己的判断正确时,就敢于作“惊人之论”。②龚斌《独立特行的性格与超凡脱俗的学术——评木斋自传《历史的化石》》,《天中学刊》,2010年第6期,18页。时代和个人的因素相合,乃使先生能截断众流,得出颠覆旧说的新成果。
(二)研究方法-回归人性的研究
在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儒家思想规范着人的感情和行为,特别是两宋时的理学家,强调“男女大防”、“存天理,去人欲”,礼教森严,对人性造成压抑。在这些理学家或儒家信徒的诠释中,历史人物往往被判然二分地划成忠奸好坏,受其嘉许的都是义理昭然、规行矩步的忠臣孝子、义夫义妇,行为稍有出格的即受其抨击,甚至为了维护一些历史人物的正面形象,会忽视其人性一面,将之塑造成合乎儒家典范的刻板人物。这种去人性化的诠释,不但影响后人对历史人物的理解,更会掩藏了在道德面具下的历史真相。例如,曹植的诗赋和相关的史料中,有大量的佐证透露出曹、甄间的恋爱关系。爱情本就是人性最基本的需求,情之所钟,一往而深,可以超越年龄和身份的界限,在历史上和生活中屡见不鲜,为何偏偏不可以发生在曹、甄身上?①笔者曾在本斋先生“东坡诗”课堂作不记名的统计调查,询问女同学如果代入甄后的身份及处境,会否爱上植。28名女同学中,17名表示会,11名表示不会。询问男同学在13-14岁的青少年时期,有否喜欢过或倾慕过比自己年纪大的女性。15名男同学中,6名表示有,9名表示没有。虽然此统计调查并不严谨,但大略可以说明青春期的男性喜欢或倾慕比自己年长的女性的可能。认为曹、甄间因年龄差距而不可能产生爱情的说法,反而是没科学根据的。
所幸到了现代,理学对人的思想行为的束缚松绑了,人性得到相当程度的解放,我们可以自由追求自己所想,可以面对自己的欲望,因而更了解人性,也更能体会历史事件或文学作品中被压抑、被歪曲了的欲望。不过,即使人性得到解放,也不是每个学者都看到人性在研究中的意义,因为要有相当的经历、丰富的情感和同理心,才可以代入历史人物或作者本身去发现问题,再以理性去分析推理。木斋先生正是这种具备理性分析能力和丰富情感的学者。读其《历史的化石-知青十五年》,可知其生活经历之丰富及对人性体会之深,而且他又是一名诗人,诗人多愁善感的气质,使他更容易体会文学作品中的人性。笔者还发现在“感甄说”的接受史中,有一个特别的现象,正好和木斋先生的情况相符:历史上接受“感甄说”的多以诗人为主,而反“感甄说”的则多是固守儒家伦理的学者。先生以与其诗人气质而能接受“感甄说”,不亦宜乎?
木斋的曹植甄后以及古诗研究,从以前的只见历史人物的政治面孔,或说是以政治为本质来记载和诠释,一变而为以人性,特别是其中的恋情为中心,为本质,使僵死的政治人物成为了活生生的有着鲜活生命感的人物,从而实现了从以政治为中心到以人性为中心的学术自觉。
(三)研究形式的改变
在古代,除了官方性质的编修、研究工作外,一般学者通常采用“单打独斗”的形式研究问题,与其他学者少有交流。纵使想与其他学者交流辩论,亦没有一个公开的平台,因而可能只是透过书信和聚会的方式讨论,参与的人数必然不多,更难以共同分工处理一个课题。这不但局限了研究的广度和持久度,更重要的是,由于缺乏交流和补充,没有其他观点的刺激,研究的成果往往流于一得之见。直到清末民初,引入西方的学术模式,大学的创立,学刊学报的出版如雨后春笋,改变了传统“闭门著述”的习惯。学者有了固定的场域、公开的刊物作交流讨论,激荡出新的火花。到了现代,大学的数量和门类更多,学刊出版更频繁,读者层亦更广,更利于讨论。木斋先生的研究,正是通过在学刊上的互相交流、辩论而展开的。当下《社会科学研究》、《学习与探索》、《河北师范大学学报》、《中国韵文学刊》、《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天中学刊》、《琼州学院学报》等七、八份学刊学报设有古诗研究的专栏,围绕相关研究邀约稿件作专门的讨论,反应之热烈,是历来少见的。以一个群体去研究相关课题,其好处是既可以使研究更持久和深入,亦可以从多角度去探讨问题,使研究更全面而立体。亦由于如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和日本学者铃木修次《汉魏诗之研究》等外国学者的研究结论,竟可与先生的研究互相印证和补充,甚至已有学者撰文比较先生和宇文所安的研究。②张朝富:《事实与逻辑之间:木斋、宇文所安“汉五言诗”研究的启示与追问》,《中国韵文学刊》,2013年第2期;张朝富:《以他者的视角:木斋汉魏五言诗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这种交流和讨论的范围已不止限于两岸三地,更涉及到日本和欧美的学者,其间的比较会否启示新的意义,犹未可知,但可以反映研究的形式已从古代的“单打独斗”、“闭门著述”,转变为现代的兼容并包、多方参与。
(四)多元的研究视角
古代对文学的研究,主要是在版本源流、声韵训诂、格律意境、创作手法、内容真伪、典故名物、寄托喻意、作者生平等角度入手,不离传统国文学门的范畴。随着社会的日趋复杂、学科的分化发展,新理论的提出,特别是文本理论和诠释学的重视,我们现在可以以更多元的角度作研究,发掘作品中可能的面向。例如中山大学博士生从女性化写作的角度有意研究古诗十九首,又有硕士生同学以心理学、性科学的角度研究曹植有没有可能爱上甄后。这些新视角、新理论的采用,是古人无法想象的。另外,先生亦曾以量化分析的方法比较不同的古诗之间某些意象和词汇出现的频率及相似性,以推论作者的可能身份。这种量化分析、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亦是以往的研究中所欠缺的。
四、小结
木斋先生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和启发性,在于他不是站在过去看过去的问题,而是立足现在去重新检视过去的问题。古代的研究视角、方法往往有其限制,很多问题纵使已经被研究到烂熟,却依然困在瓶颈,无法突破。我们生于现代,得时代之便,正好用新态度、新方法、新视角去重新检视旧问题,才不会浪费时代给我们的有利条件。也许我们的研究,不是每一项都能完满地解决问题,但能提出新的论点、抛出新的问题,从而引起更多的检讨辩论,可能更具有学术意义。道理是越辩越明的,只要我们在证据的基础上,理性的疑古辨古,必会更接近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