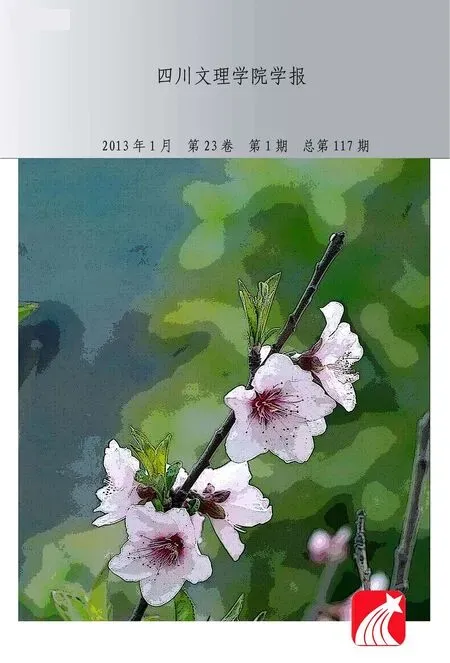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阁楼上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十九世纪文学想像》
易 平
(成都中医药大学 外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7)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鲜明的政治性别意识介入文学批评,广泛吸收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结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的文学批评理论,以解构和颠覆为其批判的手段,逐渐成为当今最具影响的文学批评理论之一。
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先驱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女性创作的文学是怎样表达或表现女性生活与体验的特点的。它也研究男性主宰的法则,以了解男性是怎样运用文化来推进他们对女性的主宰的。”[1]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向文学史中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主义提出挑战,批判文学作品中对女性的歧视和控制。英国的弗吉尼亚·伍尔芙和法国的西蒙·德·波伏娃正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先驱。“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关注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分析,从根本意义上看,它是一种政治批评和社会批评。”[2]女性在传统上受到父权制和男性霸权主义的压抑:在父权制社会中,妇女缺乏平等的工作权利和报酬,经济上不能独立,无法得到完善的教育,受困于孩子的抚养和家庭的琐事中,很难有从事写作所需要的独立空间和完整的时间。因此,伍尔芙指出:“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3]妇女的独立首先应该是经济上的独立,只有经济的独立才能摆脱男性的束缚和压抑,才能拥有写作的独立时空。伍尔芙这种强烈的女性独立意识极大地影响和积极地推动了女性文学的创作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同时,弗吉尼亚·伍尔芙还提出了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极具影响的“双性同体”的思想。伍尔芙认为每个人身上都存在两种力量:一种是男性的力量,一种是女性的力量。“双性同体”是理想的创作状态,纯粹的男性作品和纯粹的女性作品都不是完美的文学作品,“‘双性同体’的思想是对男女二元对立观念的解构,也显示了对男性中心的单一标准的抗议”。[4]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1949年)被称为西方妇女的“圣经”。波伏娃提出:“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5]这一观点对女性文学创作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女性的某些气质特征和思维、行为方式并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形成的,传统的习俗和男性中心主义社会造就了女人。因为女性在经济上的不独立,女性的生存依附于男性,就不得不遵循男权社会为其制定的价值规范和道德标准:对男性的顺从就是“天使”,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就是“疯女人”。
二、西方女性主义的三个发展阶段
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最活跃、影响最大的理论家之一的伊莱恩·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将西方女性主义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初期阶段:女性主义批评主要集中在批判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厌女症”。即,西方文学中的传统的歧视妇女、歪曲和诋毁妇女,并把众多的女性作家排除在文学史之外。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r)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1970)就是这一阶段的代表著作。
第二阶段:女性主义批评主要集中在发掘被父权制文学传统埋没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同时重新评价传统文学史中女性作家和作品。在这一阶段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论著,诸如:帕特里夏·迈耶·斯帕克斯(Patricia Meyer Spacks)的《女性的想像》,肖沃尔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1977年)等。这些著作在不同程度上修正或重写了文学史并创立了妇女文学史。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第三阶段:女性主义批评对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反思,对建立在男性文学体验基础上关于阅读和写作的传统理论观点作出了修正。在前两个阶段所取得成果的基础上,一些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在努力地建立和完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例如,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提出了“女性文体”(ecriture feminine)和“女性行为”(gynesis)批评的理论。肖沃尔特还提出了“女性批评”(gynocritics)和“性属理论”(gender theory)。
三、《阁楼上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十九世纪文学想像》
1979年,美国女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合作出版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十九世纪文学想像》(The Mandwoman in the Attic: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Century Literature Imagination,1979),打破了民族、地域与政治的疆界,将19世纪的英美妇女文学视为一个整体进行了综合考察,对性别与文学关系进行了全新的阐释。[6]该著作在2000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重版。《阁楼上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十九世纪文学想像》,共计16章,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进行有关方法论的阐述;第二部分分别对玛利亚·埃奇沃思、简·奥斯丁、约翰·弥尔顿、玛丽·雪莱、艾米丽·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乔治·艾略特等的作品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阐释;最后一部分集中讨论了伊丽莎白·巴瑞特·勃朗宁等19世纪女作家的诗歌,着重分析了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作品。
在论文中,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尖锐地提出了“笔是对阴茎的隐喻吗”这样一个问题。在男权社会与传统文学中,写作本质上被视为是男性的,是男性生殖行为的延伸。这种文化赋予男性作家以权威,赋予他们创造、控制和占有的权力。无论从生理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妇女都是不可能从事写作的。妇女作家对自己艺术创造的资格与能力感到强烈的困扰,对作为作家的合法性产生了深刻的焦虑。两位学者在“影响的焦虑”基础上,将这种困扰与焦虑概括为“作者身份焦虑”。她们对自我表现的胆怯、对艺术上男性权威的畏惧、对女性创作的不适当性的忧虑等等,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自卑情结。这种情结成为女作家为在艺术上进行自我界定而斗争的标志。[7]吉尔伯特和古芭把19世纪的女性作家的处境比喻为“阁楼上的疯女人”。正如弗吉尼亚·伍尔芙宣称的那样,我们妇女要成为真正的作家,必须“杀死”“屋子里的天使”;同样,所有的妇女作家还必须杀死天使的对立面和替身——屋子里的“魔鬼”,因为,正是这样的形象抹灭了妇女的创作能力。西蒙·德·波伏娃认为,男性作家对女性形象的界定,其实也是他们自己的一种矛盾心理,因为作为男性,他们无法控制自己身体的存在、自己的出生和死亡,他们是从女性的身体里孕育出来的,而作为“他者”的女性,则代表生命的偶然性。
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指出,到了19世纪末(在这本著作中可以看到文学史上一个最重要的现象),妇女不仅开始了文学创作,而且重新构建着这个被父权统治和颠覆的文学世界。“疯女人”的形象也象征了一种微妙而复杂的文学策略。按照吉尔伯特和古芭的说法,这种计策赋予19世纪女性小说以革命性的锋刃。在女性真正建立起能够脱离男性中心主义标准的文本话语模式和文学标准之前,女性作家只能套用男性的文本模式。[8]她们采用“暗度陈仓”的计策,以中性甚至男性化的笔名进行文学创作,一方面以满足男性主义作家及其男权社会的需求,创建他们心目中“天使”般的女主人翁——性格内向、温顺、谦逊、无私奉献,另一方面又塑造出作为主人翁对立面的疯癫形象——性格暴躁、疯狂而又强悍,让这些疯癫形象充当那些安分守纪的自我的社会替身。在文本中,她们建构起一套对立模式,实现了解构男性中心主义文学标准的策略:即从正面表现社会可以接受的“天使”,从反面表现自己的秘密欲望“魔女”。
最后,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在著作中总结道:从安娜·里奇、安娜·艾略特到艾米丽·勃朗特、艾米莉·狄金森,这些女性作家的代表们,她们都从“男性作家文本的玻璃棺材”站了起来,透过“王后的窥镜”,看着这个死亡的无声舞蹈成为了胜利的舞蹈、宣讲的舞蹈、权威的舞蹈。“女作家通过把她们的愤怒和疾病投射在可怕的人物身上,为她们自己和女主角创造出黑暗的替身(dark double),她们便与父权制文化强加在她们身上的自我定义(self-definitions)等同起来,同时对之又加以修正。”[3]总的来说,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的《阁楼上的疯女人》不仅是“历史上的一刻”,更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75.
[2]程锡麟,王晓路.当代美国小说理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63.
[3]程锡麟.天使与魔鬼——谈《阁楼上的疯女人》[J].外国文学,2001(1):42.
[4]弗吉尼亚·伍尔芙.一间自己的屋子[M].王 还,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77.
[5]迈克尔·莱恩.文学作品的多重解读[M].赵炎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66.
[6]莫依·陶丽.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性主义文学理论[M].林建法,等,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55.
[7]邱运华.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3.
[8]杨莉馨.标出那新崛起的亚特兰蒂斯——简评《阁楼上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十九世纪文学想[J].妇女研究论丛,2008(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