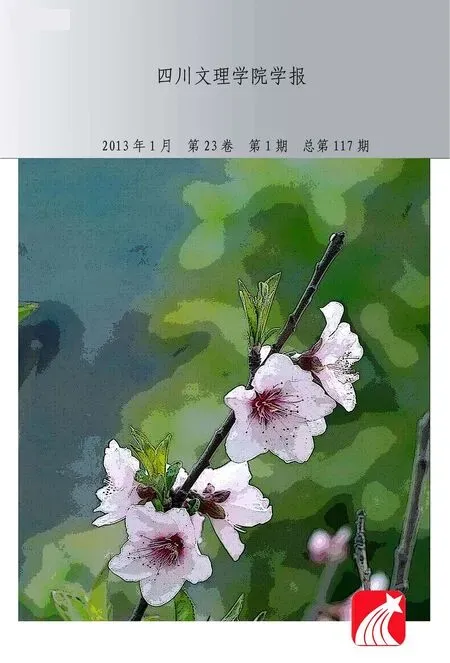侦查行为的法律规制
——以新《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为视角
朱 鸿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侦查系,江苏 南京 210023)
侦查行为的法律规制
——以新《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为视角
朱 鸿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侦查系,江苏 南京 210023)
侦查行为是侦查主体行使侦查权的外在表现。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免受侦查权的侵害,对侦查行为必须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新《刑事诉讼法》在辩护制度、证据制度、强制措施、侦查程序等涉及侦查行为合法实施等方面,都注意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对侦查行为的改进,必须树立两方面都要加强的理念,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对侦查机关进行授权;另一方面,要严格对侦查行为,特别是强制性侦查行为进行严格规制。
侦查权;侦查行为;规制
侦查权是一种重要的国家权力,它承载着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及侦破案件的重要使命;同时它也是保护被害人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侦查行为是侦查权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侦查主体行使侦查权的外在表现。由于侦查权具有暴力强制性、侦查主体单方面拥有权力性等特点,为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免受侦查权的侵害,对侦查行为必须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以达到侦查行为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实体真实与程序真实、维护秩序与追求自由之间的平衡。
一、当前侦查行为法律规制存在的问题
(一)有关强制侦查行为的法律规制不完善
强制侦查行为是指在侦查中不需要考虑侦查对象是否自愿配合,使用带有强制性、侵权性的方法对侦查对象较为重要的权利造成损害的行为,如扣押、搜查、逮捕等。与强制侦查行为相对的是任意侦查行为,即由有关人员自愿配合,不使用强制手段,不对有关人员的重要生活权益造成强制性损害的侦查活动,如询问证人、讯问犯罪嫌疑人等。强制侦查行为与任意侦查行为不同,强调的是侦查行为应当实现刑事实体目的,不以公民意志自由为前提,侦查机关为了侦查的需要可以使用对公民重要权益造成损害的强制性调查手段,侧重的是刑事诉讼价值中秩序价值的实现。
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人员可以对与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身、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地方进行搜查, 也有权扣押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的各种物品、文件、邮件、电报,冻结存款、汇款等。但法律仅是赋予了侦查机关上述搜查、扣押等强制侦查权,并未就监督制约这些强制侦查行为的行使作出相应的规定,也没有设置适用有关强制侦查行为的必要司法审查程序。在缺少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的情况下,强制侦查行为的实施涉及到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财产权等宪法权利问题,很难防止侦查权的滥用。
(二)对技术侦查等秘密侦查行为的法律规制缺失
在我国的侦查实践中,技术侦查等秘密侦查行为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作为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秘密侦查行为,其法律规制仍是一个空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对秘密侦查手段予以明确规定,也没有专门的单行法规制秘密侦查。只是在《人民警察法》和《国家安全法》中原则性地规定了调查有关犯罪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侦查机关的一些内部规定涉及到了规范秘密侦查措施。由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未将秘密侦查纳入法律规制,造成这些侦查行为在刑事诉讼中使用的合法性受到置疑,取得的证据效力也陷入困境,所获取材料的运用难以有统一的做法。侦查实践中秘密侦查措施的使用无法受到法律的有效规制,为滥用这些侦查手段侵犯公民的隐私权与自治权提供了条件。目前实践中曝光的诱惑侦查等各种秘密侦查滥用的情况,极不符合建设法治国家对人权保障的要求。因此,必须对秘密侦查实行有效的法律控制,实现秘密侦查的法治化,以限制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确保在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达到必要的平衡。[1]
(三)侦查阶段赋予犯罪嫌疑人的法律保障有限
侦查阶段是刑事诉讼的起始阶段,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容易遭受非法侵害,因而是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关键环节。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效果,将对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权利的保障产生重要的影响。近些年来,为了有效打击犯罪,侦查权不断强化,律师的辩护、代理权大有回落与萎缩的态势。现行《刑事诉讼法》将律师介入刑事辩护排斥于侦查程序之外,在犯罪嫌疑人最需要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时律师无法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丧失了对侦查行为进行监督制约以及充分保障人权的最佳时机。辩护律师只有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才能申请查阅案卷材料。这使得律师难以有充足的时间全面掌握案件情况,不利于其开展有效的辩护工作,也不利于为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提供充分的保障。
二、新《刑事诉讼法》对侦查行为的规制
(一)确立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
继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对宪法进行第四次修正,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之后,“尊重和保障人权”被正式写入新《刑事诉讼法》总则第二条,而且在辩护制度、证据制度、强制措施、侦查程序等涉及侦查行为合法实施等环节,均通过有关规定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新《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是将宪法精神落到了实处。
(二)进一步完善了辩护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身份和地位,增加了辩护人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保障的规定,健全了侦查阶段法律援助制度,从而完善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制度。
侦查阶段律师介入客观上有利于侦查机关依法进行诉讼,表现在:一是侦查阶段侦查机关采用各种强制性措施时,为了自身办案的便利,存在滥用乱用强制性措施的情形,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律师的介入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侦查机关强制性措施的不适当使用;二是侦查阶段侦查机关收集证据的过程中,存在为了达到侦查目的,不惜使用违法手段收集证据的情形,律师的介入有利于促使侦查机关全面、合法、客观的收集证据。[2]确立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可以更有效地发挥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作用,加强侦查辩护职能的行使,抑制侦查违法。
(三)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不仅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还增加了“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主要包括了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的排除、人民检察院对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调查核实、法庭审理过程中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法庭调查、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证明责任以及非法证据排除的判定标准等内容,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正式确立。这充分体现了贯彻和落实宪法以及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能够遏制非法侦查取证行为的发生,制约侦查权对公民合法权利的侵犯,加强人权保障的力度,实现刑事诉讼过程中的程序公正。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能够最大限度地使无辜者不必因为难以承受酷刑而受尽冤屈,避免其陷入贝卡利亚描述的“因为你是罪犯;因为你可能是罪犯;因为我想你是罪犯”的困境。[3]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法确定的“准确、及时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诉讼任务。
(四)对强制措施进行了较大幅度修改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延长了特定情况下传唤、拘传的期限;增加了对现场发现的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可以口头传唤的法律规定;增加规定了在传唤、拘传期间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这项法律要求充分体现了人权保障的理念,体现了刑事执法规范化、人性化的要求。
新《刑事诉讼法》区分了取保候审与监视居住的适用情形,扩大了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完善了保证人担保的法律规定,规范及细化了没收、退还保证金的程序;增加规定了监视居住独立适用的情形,明确规定了监视居住的执行地点、指定居所执行监视居住的应通知家属及辩护人的委托和会见;完善了人民检察院对监视居住监督的规定。
针对侦查机关适用刑事拘留和逮捕存在刑事拘留适用对象随意,逮捕条件过于抽象,羁押率偏高及逮捕审查程序的行政化等问题,新《刑事诉讼法》对这两种强制措施作了有针对性的修改完善。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拘留、逮捕后立即送看守所羁押,完善了拘留、逮捕后通知家属的规定。对逮捕的条件中“社会危险性”的情形进行了细化,同时增加了“应当”逮捕的适用情形和“可以予以逮捕”的规定。增加了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时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法律要求。这在程序上保证了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正确性,以实现程序正义。同时规定了在审查批准逮捕过程中,对证人的调查和对辩护律师意见的听取程序,这些规定有利于实现程序正当性、科学性、规范性,提高审查批准逮捕办案质量的需要,也是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的需要,以防止错捕和不捕,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4]
(五)增加了技术侦查措施等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作为第二编第二章侦查部分的内容之一,弥补了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技术侦查以及秘密侦查的立法空白,是程序法定原则的体现,为有效规制技术侦查、秘密侦查等侦查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新增加的此部分内容仍属原则性的规定,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不足:首先,新《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或者说是秘密侦查的种类没有进行规定。其次,虽然规定了适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案件范围,但没有规定秘密侦查的案件范围。适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案件范围是否适用于秘密侦查不明确。最后,对适用技术侦查、秘密侦查等侦查行为的原则规定不够全面。秘密侦查行为是一种侵犯公民基本私权利的行为,为防止其滥用,立法应对其进行有效规制,明确规定秘密侦查应当遵循的原则。一般来说秘密侦查的适用应当遵循必要性原则、侵犯最小原则和最后手段原则。上述三个原则中只有必要性原则在新《刑事诉讼法》中有一定的体现。
三、完善侦查行为法律规制的立法建议
对侦查行为的改进,必须树立两方面都要加强的理念:一方面,为了加大打击力度,发挥侦查权的作用,要尽可能地对侦查机关进行授权,保证侦查机关能够准确及时打击犯罪,实现侦查目的;另一方面,为了保障人权,防止滥用侦查权,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要严格对侦查行为,特别是强制性侦查行为进行严格规制。[5]
(一)加大侦查行为的规制力度
应进一步完善侦查行为的法定性,将可能侵犯人身和财产的侦查行为详细规定,尽量将侦查中不可避免需要运用的侦查行为种类,明确写进刑事诉讼法条文中。同时发挥侦查主体的积极性,对不侵犯人权的行为不限制,对有的措施进行概括性授权,但要控制范围。立法必须明确规定侦查行为的执行主体、侦查行为的种类、适用侦查行为的要件和范围、实施侦查行为的期间及延长程序,明确适用侦查行为所获得材料信息的保存、使用及销毁程序,非法采用侦查行为的法律责任,等等。
(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在其排除条件、程序设置等方面不乏一些有待完善之处,同时还应注意此规则与相关配套刑事司法制度的衔接与配合,需要在今后的立法中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应当完善的内容包括:首先,应当通过立法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删除“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全面落实“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其次,完善侦查取证环节的相关制度性规定。设立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在场制度;规定严格的搜查、扣押程序;建立对非法取证人员的惩戒制度。最后,严格区分对待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对于言词证据,必须明确界定禁止采用的非法形式以及种类。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如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由法官自由裁量,决定其可采性。[6]
(三)完善秘密侦查行为立法
为防止侦查权的滥用以及非法取证,应加紧完善对秘密侦查行为的立法工作,规范秘密侦查行为。由于侦查实践中实施秘密侦查行为涉及到的问题较多,应当从事前审批、事中控制以及事后监督等环节进行程序设计,以实现对秘密侦查行为的法律规制。对其立法过程中应充分体现全面、细致以及区别对待的原则,应注意到技术侦查与秘密侦查行为之间的关系,对各种秘密侦查行为作出准确界定并根据其侵犯公民权利的程度和范围的不同而进行相应的规范。
(四)建立科学的审前羁押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改变现行审前羁押不区分“逮捕”与“羁押”的基本制度框架,不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未来应当建立科学的审前羁押制度,首先是要将逮捕定位于羁押的前置程序,实行“逮捕前置主义”,实现逮捕和羁押相分离;其次是要建立必要的羁押司法审查程序,以有效控制羁押的适用。这种以逮捕为前置程序的审前羁押制度,不仅能够有助于适当放宽逮捕的适用条件并简化其审批程序,以满足侦查机关侦查犯罪的现实需要,还可以通过强化羁押的司法审查来规范和控制羁押措施的适用,充分体现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
[1] 丁延松.法治语境下我国秘密侦查制度的现实困境和出路[J].政法论丛,2011(4): 117.
[2] 李 静.解析新刑事诉讼法视角下的侦查阶段辩护制度[J].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2): 21.
[3] 王颂勃.《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评析[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 76-77.
[4] 徐晓玲.刑事强制措施的修改与适用[J].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2(3): 11-13.
[5] 王德光.侦查权原理[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230.
[6] 赵红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若干问题的思考[J].河北法学,2012(9): 89-90.
[责任编辑邓杰]
OntheLawStandardofDetectionAct:ExamplesfromtheNewCriminalProcedureLaw
ZHU Hong
(Detection Department of Nanjing Forest Police College,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The detection is an external form of a subjective detection right. The detection action must be limited by effective law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human rights. In the new Criminal Procedure Law, the legal terms concerning the advocacy system, proof system, coercive measures and detection procedure stress the principle of respecting and ensuring human rights. The improvement of detection lies in both stresses on the rights of detective organization and on the strict stipulation of detection act, especially the coercive detection act.
detection right; detection act; stipulation
2012-09-12
朱 鸿(1974—),男,内蒙古牙克石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侦查学研究。
D925.2
A
1674-5248(2013)01-0057-04
——以《警察法》的修改为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