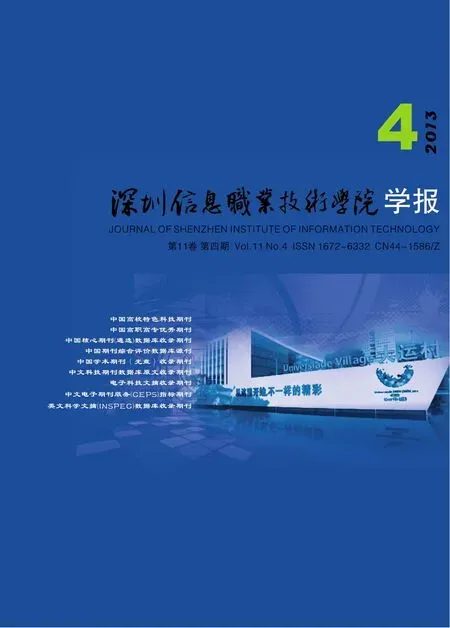朱熹的“以意逆志”论
曹海东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早在先秦时代,孟子论述解《诗》之法,就提出了“以意逆志”说。《孟子·万章上》有云:“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至宋代,朱熹对孟子的“以意逆志”说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曾作过深入的思考和探究,形成了一些重要而独到的见解,在其经典解释学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其“心性论域、伦理视野凸现了汉语文化中理解观念的基本特色,具有汉语经典命题的价值空间,成为后世关于理解问题的思考基点”[1]。朱熹讨论经典文本的理解问题,就正是以孟子的“以意逆志”说为思考基点,由此展开深入探索和论究。先看如下材料:
所谓“以意逆志”者,逆,如迎待之意。若未得其志,只得待之,如“需于酒食”之义。后人读《诗》,便要去捉将志来,以至束缚之。(《语类》卷一一七,2813①)
“以意逆志”,此句最好。逆是前去追迎之之意,盖是将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诗人之志来。……如等人来相似。今日等不来,明日又等,须是等得来,方自然相合。(《语类》卷五八,1359)
董仁叔问“以意逆志”。曰:“此是教人读书之法:自家虚心在这里,看他书道理如何来,自家便迎接将来。而今人读书,都是去捉他,不是逆志。”(同上)
“逆志”是将自家底意去推迎等候他志,不似今人硬将此意去捉那志。(《语类》卷七九,2037)
由是观之,朱熹是把“以意逆志”的“意”指为读者的“自家意思”(即读者主观方面所具有的东西),把“志”说成是经典作者的创作意图。在他看来,读者采取“逆”的方式来使“自家意思”与经典作者之“志”相互接触、沟通,以至自然相合,生成意义,就有一个理解的过程真切地发生。此外,朱熹很多有关经典理解问题的论析,虽然没有使用“以意逆志”的名目,但实际上也是以“以意逆志”说为基点展开的。例如:
须是己之心果与圣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断他所书之旨。(《语类》卷八三,2154)
入道之门,是将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渐渐相亲,久之与己为一。而今人道理在这里,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语类》卷二○,446)此中所谓“己之心”、“自家身己”②云云,都有涉于读者“自家意思”;所谓“圣人之心”、“那道理”都与经典作者之“志”相关。在朱熹看来,这两者相亲相合的过程,也就是理解形成的过程,它能使读者“可断他所书之旨”。
朱熹对“以意逆志”说的阐论,以及基于“以意逆志”说所展开的论析,尽管不一定尽合孟子的本意,“可能与孟子有所差距”[2],但仍有其理论价值;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朱熹对经典理解的形成机制问题有过深入的思考,认为经典解释实践中一个理解过程能够实实在在地形成、发生,主要依靠“以意逆志”的诠释行为所达成的读者与作者间的思维性沟通。
孟子所提出的、朱熹所推重的“以意逆志”说,与现代解释学理论中的“视域融合”说有相通之处。周光庆先生有云:“以‘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为枢机,体察作者的情志……其解释的功能主要是使解释者由‘言内之意’走向‘言外之意’,在‘共同视域’中与创作者实现今人所谓的‘视域融合’。”[3]邓新华先生也说:“孟子当然不可能使用‘视域融合’的概念,但他以‘逆’的方式来沟通解释者与解释对象,认为只有通过‘逆’,才能消除解释者和解释对象之间在时间和历史情境方面的距离,才能最终获得对作品意义的理解和把握,这与伽达默尔‘视域融合’的理论观点在精神实质上无疑是相通的。”[4]
现代解释学理论中的“视域融合”说,是指理解主体的视域与理解对象的视域相互同化融合。它认为,理解活动中总是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视域:一为文本的视域,是由作为特定历史存在的作者给定的;二为理解者当下的视域,是由理解者自己的历史境遇赋予的。由于时空间距等因素的影响,这两种视域之间自然存在着差异甚至矛盾。因此,理解者面对一个文本,只有把上述两种不同特质的视域进行融合,使之相互吸收、彼此容纳,才会有理解真正形成。即此而观之,朱熹对“以意逆志”说的阐论,的确有相通于上述“视域融合”说的地方。其所谓读者“自家意思”,其实也就是理解者的当下视域;其所谓作者之“志”,也就是文本的原初历史性视域;其所谓“自然相合”、“神交心契”云云,实际上是指通过前述两种视域的相互沟通、交融,形成一种真正的理解。
综观朱熹对“以意逆志”的论说,可以看到,他虽然认为经典解读过程中读者不能完全抛弃自己当下的视域,需要有“自家意思”的能动参与,但他同时也十分看重经典作者(文本)原初视域在理解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读者不能简单粗暴地将“自家意思”强加于作者的“志”中;真正的“以意逆志”,是在充分尊重作者(文本)权利、关注作者历史性的前提下,读者以“自家之意”去迎受、融合作者(文本)的原初视域;那种无视经典作者(文本)原有的视域,率凭胸臆地“自作意思”,直以己意强置于经典文本的做法,不能算是“以意逆志”,而只能叫做“以意捉志”,它无法使理解真正形成。朱熹曾说:
孟子说《诗》,要“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逆者,等待之谓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来时且须耐心等待,将来自有来时候。他未来,其心急切,又要进前寻求,却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牵率古人言语,入做自家意中来,终无进益。(《语类》卷一一,180)
某尝说,自孔孟灭后,诸儒不子细读得圣人之书,晓得圣人之旨,只是自说他一副当道理。说得却也好看,只是非圣人之意,硬将圣人经旨说从他道理上来。孟子说“以意逆志”者,以自家之意,逆圣人之志。如人去路头迎接那人相似……如此方谓之“以意逆志”。今人读书,却不去等候迎接那人,只认硬赶捉那人来,更不由他情愿;又教它莫要做声,待我与你说道理。(《语类》卷一三七,3258)
由此可见,朱熹十分强调经典作者(文本)的原初视域在“以意逆志”过程中的作用,而认为读者“以意捉志”、“硬将圣人经旨说从他道理上来”,是一种撇置文本本意、强经就我的解读行为,它无法促成思维性沟通,产生真理解,为无所“进益”之举,因而与“以意逆志”相乖违。
朱熹的上述看法,与现代解释学的“视域融合”说的理念颇相近。如德国当代解释学家伽达默尔认为,理解者在视域融合中“不是使另一个人受制于我们自己的标准”[5]。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说告诉我们,解读者只是促成意义发生的参与者,而不是意义的决定者”。因此,“那种撇开文本原有的视域于不顾、任凭读者自己的先见‘投射’的做法根本谈不上视域的融合。因为这种理解和解释抛弃了文本及其解释的传统,它是有悖于伽达默尔的原意的”[6]。
综考朱熹关于“以意逆志”的论说,还可以看到,读者通过自家之“意”去“逆”——推度、追溯和迎受③——作者之“志”,使二者沟通融合,形成理解,其所获得的意义多为经典作者(文本)的原意;在经典解释活动中,读者“以意逆志”,应当把对作者(文本)原意的探求、获取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朱熹有云:
然圣人之言有近有远、有缓有急。……大抵读书,须是虚心平气,优游玩味,徐观圣贤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后随其远近浅深、轻重缓急而为之说。如孟子所谓“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文集》卷四六《答胡伯逢书》,2149)
字字考验,句句推详,上句了然后及下句,前段了然后及后段,乃能真实该遍,无所不通,使自家意思便与古圣贤意思泯然无间,不见古今彼此之隔,乃为真读书耳。(《文集》卷六二《答林退思书》,2992)
朱熹此论的意思很明白:读者解读经典如能做到“以意逆志”,则可令自家之意与圣贤之意融合无间,达成思维性沟通,其理解所得乃为圣贤立言本意;如果能获得这种本意,才算是真理解、“真读书”。
对于经典解读活动中的“以意逆志”,朱熹也注意到了另外一种情形:读者“以意逆志”而促发理解,所获得的意义有时却是一个新的意义,它既不完全是作者(文本)的原意,也不等同于读者“自家意思”。他曾说:
大抵前圣说话,虽后面便生一个圣人,有未必尽晓他说者。盖他那前圣,是一时间或因事而言,或主一见而立此说。后来人却未见他当时之事,故不解得一一与之合。且如伊川解经,是据他一时所见道理恁地说,未必便是圣经本旨。要之,他那个说,却亦是好说。(《语类》卷一○五,2625)
这里所谓前圣一时间所立之“言”与“说”,实际上都属于作者(文本)之“志”。在朱熹看来,后人解经以“他一时”之意去推迎前圣当时之“志”,由于历史的疏异化作用,致其理解之所得难以“一一与之合”、“未必便是圣经本旨”,而是一个新的意义。但是,这种理解之所得仍有其可取之处。
就朱熹的相关论述文字看,读者“以意逆志”,实现视域融合,形成理解并获得新的视域和意义,这一情形比较多地见于《易经》的解读实践:
缘《易》是一件无头面底物,故人人各以其意思去解说得。近见一两人所注,说得一片道理,也都好。(《语类》卷六七,1678)
读《易》若通得本指后,便尽说去,尽有道理可言。……如筮得乾之初九,初阳在下,未可施用,其象为潜龙,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得此爻者,当观此象而玩其占,隐晦而勿用可也。它皆仿此,此《易》之本指也。盖潜龙则勿用,此便是道理。故圣人为《彖辞》《象辞》《文言》,节节推去,无限道理。(《语类》卷六八,1695)
这说明,后人读《易》,都是怀着各自当下的视域(所谓“人人各以其意思”)进入文本,以与《易》之原初视域(所谓“本指”)沟通互融,产生创发性的理解和解释,故人人都“说得一片道理”,于其“本指”均有所推展,创生出了新的视域和意义。朱熹还曾举例说:
如“元亨利贞”,文王重卦,只是大亨利于守正而已。到夫子,却自解分作四德看。文王卦辞,当看文王意思;到孔子《文言》,当看孔子意思。岂可以一说为是,一说为非! (《语类》卷七六,1941-1942)
《易》之“元亨利贞”,本来只是大亨而利于正。……后来夫子于《彖》既以“元亨利贞”为四德,又于《文言》复以为言……夫子见文王所谓“元亨利贞”者,把来作四个说,道理亦自好,故恁地说,但文王当时未有此意。……要之,文王者自不妨孔子之说,孔子者自不害文王之说。然孔子却不是晓文王意不得,但他又自要说一样道理也。(《语类》卷一○五,2625-2626)
此二条,论及孔子对文王《易》的理解与解释。朱熹认为,孔子在“晓文王意”的基础上,从个人独特的视域出发理解和解释文王之《易》,将“元亨利贞”分作四德看,形成了新的视域,酿造出了新的意义,其虽与文王之意稍远,然“道理亦自好”,“自不害文王之说”,有其存在的价值。可见,朱熹对孔子通过视域融合而形成的创发性理解和解释,表示了尊重。又如:
问张子“贞胜”之说。曰:“此虽非经意,然其说自好,便只行得他底说,有甚不可?大凡看人解经,虽一时有与经意稍远,然其说底自是一说,自有用处,不可废也。不特后人,古来已如此。”(《语类》卷七六,1941-1942)
程《传》但观其理……则其意味无穷,各有用处,诚为切于日用工夫。但以卦画经文考之,则不免有可疑者。(《文集》卷五○《答郑仲礼书》,2318)
由此看去,张载对《周易·系辞下》“贞胜”的解说,伊川对《易》的传解,都在视域融合后形成了新视域,生成了新意义,其虽“与经意稍远”,但仍是值得尊重的,不可遽废。
除《易经》之外,其他经典的理解和解释也存在着类似情形。如《诗经》,“吕氏《诗记》有一条收数说者,却不定。云此说非《诗》本意,然自有个安顿用得他处,今一概存之。正如一多可的人,来底都是,如所谓‘要识人情之正’”④。这说明学者们各以其意推逆《诗经》作者之志,往往有超逾于《诗》本意的新视域、新意义产生;这种视域和意义也并非毫无价值,故应以宽容、尊重的态度待之。
在此,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因为朱熹是把“以意逆志”的主要目标拘定在对作者(文本)原意的探求、获取上,所以,对古人依其当下视域解读经典而创生出的新视域、新意义,并非总像上文所述那样示以尊重或宽容,而在很多时候是持否定性态度。仍以《易经》的理解和解释为例,我们可以看到,换了场合,朱熹对古人在“以意逆志”过程中创生的新视域、新意义又衡以原意至上的原则,不予认可:
伏羲画八卦,那里有许多文字言语,只是说八个卦有某象……及文王、周公分为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早不是伏羲之意,已是文王、周公自说他一般道理了。……及孔子系《易》,作《彖》《象》《文言》,则以“元亨利贞”为《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孔子之心,不如文王之心宽大,又急要说出道理来,所以本意浸失,都不顾元初圣人画卦之意,只认各人自说一副当道理。及至伊川,又自说他一样,微似孔子之《易》,而又甚焉。故其说《易》,自伏羲至伊川,自成四样。某所以不敢从,而原《易》之所以作而为之说,为此也。(《语类》卷六六,1629-1630)
寻绎这段文字可知,伏羲以后,文王、周公、孔子、程伊川等人解《易》,都是“各以其意思去解说”,所以他们“自说他一般道理”,自成一样,且与其各自所解读的文本的视域不完全相同:文王、周公所解说的“早不是伏羲之意”,孔子所说的不同于文王之《易》,伊川所解只“微似孔子之《易》”。对此,朱熹是深致微词,谓“都不顾元初圣人画卦之意”,某“不敢从”,可见他对文王、周公、孔子、程伊川的诠释成果颇不以为然;依他的看法,解《易》应当“原《易》之所以作而为之说”,以求其原初之本意。
综上所述,一个理解过程能实实在在地形成、发生,主要依靠读者“以意逆志”活动所达成的思维性沟通;“以意逆志”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促发理解、产生意义的过程。朱熹所认为的“以意逆志”,近于现代解释学所说的“视域融合”。
最后附带提及的是,朱熹的“以意逆志”论与其经典解释理论的相关论述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性。朱熹阐论“以意逆志”说,肯定了读者“自家意思”作为一种个性化存在、一种先入之见在理解中的合理合法性及其积极作用;但是,论述经典解释问题,他有时又宣称读者只有把自己变成没有“自家意思”的“奴仆”,一切听任圣贤之“志”的役使,才会有真理解产生:
自家当虚心去看,又要反求思量,自己如何便是好德,如何便是好色,方有益。若只管去校量他,与圣人意思愈见差错。圣人言语,自家当如奴仆,只去随他,教住便住,教去便去。今却如与做师友一般,只去与他校,如何得?(《语类》卷三六,978)
由此看,读者解读经典时“当如奴仆”,要自觉地摆落自己的意识而进入圣人的意识,惟“圣人意思”是从。像这样鼓倡读者弃逐“自家意思”,显然与其“以意逆志”论相牴牾。朱熹又曾说:
某如今看来,惟是聪明底人难读书,难理会道理。盖缘他先自有许多一副当,圣贤意思自是难入。(《语类》卷一三九,3317)
其中的“一副当”,实际上是读者基于自身历史性存在而形成的见解。在朱熹看来,此类见解在解经实践中会对“圣贤意思”形成屏遮,是阻碍读者理解生成的消极因素,故当予摒弃。这样一来,经典理解在他那里便成了一种与读者的个性化存在没有多大关系的行为。这与他所讲的“以意逆志”不免有点相左。
此外,朱熹的“以意逆志”论与其解经实践之间也存在某些不一致性。如前所述,朱熹认为读者“以意逆志”的主要目标应规定在探求和获取作者(文本)的原意上;为了使一种重建原意的理解能够形成,他有时甚至主张读者干脆放逐“自家意思”,以牺牲读者自己的个性化存在为代价来保全和换取作者(文本)的历史性。但是,他在解经实践中的作为,并没有完全契合自己的理论主张。观其理解之形成的过程,他不仅没有抛弃“自家意思”,反且常是怀着自己的“一副当”——新儒学“理”的观念——进入文本,使之成为一种文化视域、一种先入之见参与经典理解;他在“以意逆志”的过程中也并没有把目标锁定在作者(文本)的原意上,而往往是以自己“理”的视域与经典作者之“志”相融相合,形成新的视域,建构出新的意义空间;其理解之所得大都偏于“理”之一端,使文本原意得到了创生和更新。如对经典中“道”的理解就是如此:
《礼记·中庸》:“道之不行也。”朱熹注云:“道者,天理之当然,中而已矣。”
《论语·里仁》:“朝闻道。”朱熹《四书或问·论语或问》解此云:“吾之所谓道者,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当然之实理也。”
显然,朱熹对经典中的“道”所作的这些理解,均是其理学的文化视域交融于经典文本的原有视域而形成的创发性理解,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和历史性,其既关联于经典文本的原意,但又与此原意不全同。确切地讲,它们都是由经典文本的原意引发出来的新思想,包含了历史精神与现时生命的“共建”。因此,有论者说:“朱熹对‘四书’的解释,是站在自己的‘视域’之境上,依据自己建立理学体系的需要,在‘四书’本身‘视域’的基础之上,而对‘四书’各自的内容作了不同的发挥。以《中庸》为例,给‘性’‘道’等概念赋予了等同于‘理’的形而上学的意义,从而发挥出自己所需的‘理一分殊’的宇宙论。”[7]可见,在理解生成的过程中,朱熹并没有像他自己所主张的那样涤净自家“一副当”;他之理解所得,也并非像他自己所追求的那样都是原汁原味的圣贤本意。
注释:
①此处《语类》是《朱子语类》的简称,后接阿拉伯数字是该书中华书局1986年版的页码。下文均同。另,下文引用朱熹《朱文公文集》中文字亦仿此,简称《文集》,后接阿拉伯数字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朱子全书》中该书之页码。
②此所谓“自家身己”,实指读者自身本具的“道理”。《语类》卷一○有云:“学问,就自家身己上切要处理会方是,……自家身上道理都具。”
③《语类》卷四五云:“孟子所谓‘以意逆志’,极好。逆,是推迎它底意思。”
④见《语类》卷一一七,第2813页。按:引文中“多可”一词意为“多所许可”、“宽容”。
[1]杨红旗.以意逆志诠释史研究[J].西南大学学报,2007(3).
[2]黄俊杰.孟子运用经典的脉络及其解经方法[A].李明辉编.儒家经典诠释方法[C].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173.
[3]周光庆.中国训诂学断想[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8(1).
[4]邓新华.“以意逆志”论[J].北京大学学报,2002(4).
[5]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394.
[6]何卫平.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200.
[7]黄荟. 从“视域融合”的视角来看朱熹对“四书”的解释[J].兰州学刊,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