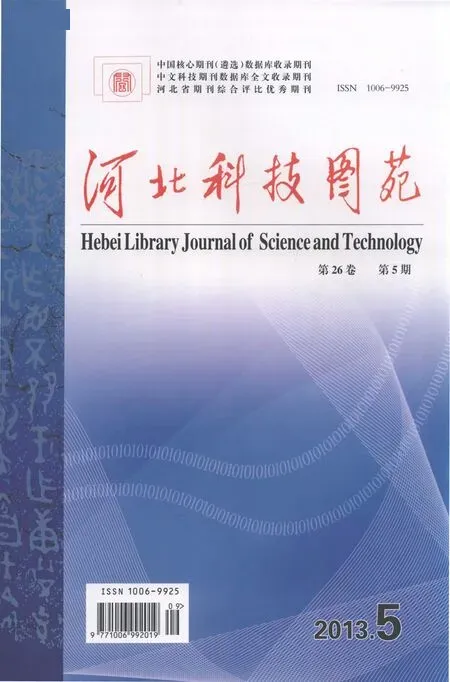中国古代目录沿革与学术流变★
刘丽斌
(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清人章学诚提出的“辨证学术,考镜源流”,最能体现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精髓,素来为学者推崇。中国古代目录是文献与学术的结合点,通过目录一方面可以了解文献的产生和累计情况,另一方面可以了解相应的学术发展状况。
1 古代目录的产生与《别录》、《七略》
我国古代目录的编制有悠久的历史。《隋书·经籍志序》说:“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湮灭,不可复知。”姚名达认为目录之渊源,可最早至夏商[1]28-29。春秋时代,“典司之官,藏守之所,分类之名,皆昭昭可考也”[1]20-22。秦朝藏书亦有目录[1]18。在汉高祖时,“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汉武帝时,杨仆撰《兵录》,《兵录》为兵书之目录。
刘向自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奉诏校书,每校定一部书,就在书后写一篇叙录,著录书名与篇目,记录校雠的过程,介绍著者的生平事迹和思想观点,说明书名的含义、著书的原委、书的性质、书的真伪,叙述学术源流,评论书的价值。后来将这些叙录集中起来,编成一部书,即《别录》,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提要目录。清人卢文弨说:“古书目录,往往置于末,《淮南》之《要略》,《法言》之十三篇序皆然,吾以为《易》之《序卦传》,非即六十四卦之目录欤?《史》、《汉》诸序,殆昉于此。”(《钟山札记》卷四)在刘向以前,就已经有“条其篇目,撮其旨意”的叙录了,《淮南·要略》、《法言序》、《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叙传》与刘向撰写的叙录的体例是相合的。撰写叙录虽然不是刘向首创,但刘向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并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总结、提高,使其发扬光大,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
刘向之子刘歆在《别录》基础上进行简化,编成《七略》。《七略》是我国目录学史上第一部全国综合性分类目录。《七略》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六大类,每一类中又分小类,总共是三十八小类。这三十八个小类三十三个有小序(“诗赋略”五小类均无序),六大类都有大序,全书又有总序。《七略》不但建立了系统的图书分类法,还通过大序、小序叙述了学术源流。刘向《别录》、刘歆《七略》的最重要的学术价值,就是以目录的形式揭示了先秦至西汉的学术源流与格局,从而建构了学术史的坐标系。在刘氏父子看来,所有学术共同拱卫的核心理所当然是六艺,也就是五经之学。确立了六艺这个核心,然后就可以由中心向边缘一圈一圈地扩展开来。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六略,不是并列而单行的六种学术而已,而是从属于一个“中心-边缘”的有机关联结构[2]45。由六经向外扩展,则是诸子九流十家。诸子的主张五花八门,但在本质上都是从属于六经的,故而说“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汉书·艺文志》)。诸子之外,依次是诗赋、兵书、数术和方技,又都是沿经传与诸子的余绪发展出来的。
《七略》已经佚失,但是它的基本内容保存在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班固认为,史书应当反映历代的文献典籍变迁。他在皇宫的藏书库兰台、东观、仁寿阁等处整理典籍,撰修史书,以刘歆《七略》为蓝本,“删其要”,编成《汉书·艺文志》。自从班固首创了在正史中修《艺文志》的这一体例,后代的史书,多设《艺文志》或《经籍志》,一时未修,也有后人补修,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史志目录”系统,可以据此考覈古今文献及相关学术的基本状况。
2 新旧分类法交替与四部分类法的初创
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纷繁多彩的局面,因此,这一阶段的图书分类法,也呈现出复杂的状况,不同分类法并立。一方面,以《七略》为标志的两汉时期的图书分类法逐渐不适应发展了的学术新局面,四部分类法在酝酿;另一方面,由于新分类法的不完善,图书分类法又时有复旧的趋势。在新与旧交替的阶段,图书分类法有的创新,有的守旧,有的折衷,但最终奠定了以经、史、子、集部类的四分法的基础。
西晋荀勖以魏郑默《魏中经簿》为基础,编《晋中经簿》十四卷,以甲乙丙丁类分群书为四部,始创四部分类法。甲部纪六艺及小学,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荀勖的四部分类涉及学术变化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把《七略》中的兵书、数术、方技三略的内容合入诸子之中,从学术上说,这三类的学术也由此被视为诸子学之附庸,开了后世子部先例;二是把《七略》中隶属《春秋》的史书独立出来,另立一部,也就是所谓史部;三是著录了当时新发现的出土文献——汲冢书[2]105。此外,姚名达认为《晋中经簿》后面附录了佛经,这是古代目录附载佛教、道教典籍的肇始[1]58-59。东晋李充作《晋元帝书目》,调整了荀勖的四部分类,以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进一步完善了四部分类法。
两晋以后的目录大多沿用荀、李的四部分类法。南朝刘宋时期谢灵运等修撰《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宋、齐之间,王俭修了一部《宋元徽四年四部书目》,又自撰了一部《七志》。梁刘孝标等撰《梁文德殿四部目录》、殷钧撰《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这两部书都包括了四部分类,但又都多出了一类,前者与四部之外又单列出了术数类,后者则把对艺术作品的著录单列了出来。
南北朝最有代表性的目录是王俭的《七志》和阮孝绪的《七录》。《七志》的分类基本沿袭《七略》,只在个别地方有不同。《七志》的“经典志”与《七略》的“六艺略”内容相同,包括六艺、小学及史书;《七志》的“诸子志”与《七略》的“诸子略”内容相同,只收诸子;“文翰志”即“诗赋略”;“军书志”即“兵书略”;“阴阳志”即“数术略”;“术艺志”即“方技略”。《七志》与《七略》不同之处在于,王俭改六艺为经典,改诗赋为文翰,改兵书为军书,改数术为阴阳,改方技为术艺,这是名称上的改动。王俭独创图谱一志,并附道经、佛经于篇末。王俭的分类法因循守旧,将当时藉由四部分类法独立出来的史部又推回到了“经典志”之中,这一做法是不合时宜的。后世的目录学家还大多批评其图谱不必单列一志。但当时的很多图,可能是以图本的形式单独流传的,并不都作为书的附件,如果单列一类,这样的图本可能会被更好更多地保存下来。
阮孝绪《七录》分内、外篇,其内篇有“经典录”、“纪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外篇有“佛法录”与“仙道录”。其中“纪传录”专记史书,又分十二类。史部离经而独立虽然始于荀勖,但细目的厘定却始于阮孝绪。后来《隋书·经籍志》史部所分小类,就是参考了《七录》而稍加变通的。仅看《七录》“纪传录”所分十二类以及著录史书的数量(1 020种,14 888卷),便可知阮孝绪所在的时代,史学已经成为独立的学科,由附庸蔚为大国。阮孝绪所分七类,其实是经、史、子、集、术数、佛、道,可以说是综合了《七略》、《七志》和《梁文德殿四部目录》的内容,为后来走向正统地位的四部分类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七录》在四部分类法的初创与最终被确立之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
3 四部分类法的确立与繁荣
唐代初期修《隋书·经籍志》,将群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集部之后附道、佛二类。隋代道经、佛经自有专门的目录,因此《隋书·经籍志》录其大纲,附于四部之后,不列书名,与经史子集四部的体例不能相比。《隋书·经籍志》与《七录》相比,只是将术技一录并入子部。《隋书·经籍志》还承继了《七略》的传统,全面作了总序、大序和小序,使每一部、每一类图书的传承、存佚、相关学术与思想意义,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揭示。
在《七略》中,诸子一类只包括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可说是名副其实的诸子类。四部分类法中的子部,所含内容却复杂得多。汉代,儒家典籍被奉为官方经典,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罢黜百家而独尊儒术,儒家学术居于统治地位。诸子的生存和发展失去了客观历史条件,诸子其他各家便逐步衰微,“其中或佚不传,或传而后莫为继”。这种学术上的变化反映在古籍目录中,就是诸子类典籍减少,不能独自成类,只得与其他类目合并。四部分类法中的子部,正是以《七略》中诸子、兵书、数术、方技四类为基础而形成的[3]。自此以后,历代目录子部的类目,大都据《隋书·经籍志》子部的分类,稍作变通而成。东汉以后,各种文体因社会变革而日渐齐备。由于儒家思想的削弱,文学开始摆脱经学的束缚,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阮孝绪因“顷世文词,总谓之集”,于《七录》中设“文集录”,著录文学作品。“文集录”分楚辞、别集、总集、杂文四类,可见当时文学作品在种类、数量上都很可观。后来,《隋书·经籍志》改“文集录”为“集”,成为四部分类法中的集部。
《隋书·经籍志》使四部分类法完成了定型,是对魏晋以来图书分类法的总结。它标志着荀勖所创的粗疏的四分法走向了成熟,魏晋以来由于学术的变化引起的不同分类法的互竞、并立的局面宣告结束,图书分类领域开始了以四部分类法为正统的新阶段。
此后,无论是官修的政府藏书目录、史志目录,还是私修的私人藏书目录等,大都遵循四部分类法,并略作改动,逐步完善。唐代主要有开元年间的《群书四部录》、毋煚编的《古今书录》;五代后晋朝修撰了《旧唐书·经籍志》。宋代是我国目录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极大地促进了书籍的流通,为目录学的繁荣兴盛提供了客观物质条件。宋初欧阳修等编纂《新唐书·艺文志》。宋仁宗时,编修《崇文总目》;宋徽宗时,又在《崇文总目》基础上增补书籍,更名为《秘书总目》。南宋时期官修目录有《中兴馆阁书目》、《中兴馆阁续书目》。宋代私人藏书目录流传下来的有三部: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尤袤的《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宋代学术呈多元共进、百家争鸣之态势,学术之各方面、文化之各地域都有蓬勃发展,其后则逐渐收煞,归于道统之论,以理学作为主体。《崇文总目》之提要还是从文献论文献,从学术论学术,尚没有党派的痕迹。《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则作于朱熹确立理学道统之后,故均染上了门户习气。《郡斋读书志》因本有家学之故,其见解相对比较独立;《直斋书录解题》则服膺程朱之学,倾向性十分明显。从《崇文总目》到《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虽然著录的书籍越来越多了,但就提要的思想内涵而论,眼界似乎越来越窄了,这也恰好反映了从北宋到南宋学术由宽到窄的历史趋势。元明时期,目录编制方面没有显著成就。明代私人藏书盛行,所以私人目录相当可观,而官修目录却十分潦草。明人目录大多数没有解题,有些只做简略注释。因为明人目录多是基于私人藏书编纂的,故而多重书籍之年代与版本,对于其中的义理与学术则不是很在意。这些目录对于考证书籍之存佚与版本来说,或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要据之了解一代学术之源流与格局,则帮助不是很大。
清代目录与明代目录不可同日而语,不仅新编纂的目录数量大增,且能考述版本,校勘同异,辨析源流。《四库全书总目》不仅是该时期最突出、最重要的一部目录,而且是我国古代最庞大的一部官修目录,是中国目录学史的集大成之作。《四库全书总目》之总序、类序、提要与案语是最有学术内涵的部分,其中包含辨章学术源流、考据、辨伪、辑佚等多方面的学术内容。清代学术尽管汉学、宋学并行,但真正代表清一代学术的,毕竟还是汉学,或称实学、朴学。《四库全书总目》虽然作出一副公正不倚的姿态,标榜所谓一本至公,但是事实上,其多有攻击宋儒之辞,对心性之学的痛恨与不屑多有表露,其尊汉学而斥宋学的门户之见是较明显的。
自隋唐至清代,历经一千多年,其间学术的变化繁杂,不可同日而语,而图书分类法一直以四部分类法为规制,虽然微小的改动、变动未有间断,但总的分类原则并没有变。因此,使用四部分类法统辖不断变化的典籍,必然会产生许多抵牾不合之处。事实上,伴随着四部分类法的代代因袭,其他分类法的产生,也是历代不绝。如南宋郑樵的《通志·艺文略》、王应麟的《玉海·艺文》,宋末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明代的《文渊阁书目》,清代孙星衍的《孙氏祠堂书目》等等。
4 结语
“目录之书”包含“学术之史”,这是中国古代目录的一个传统特质。古代目录与其中所包含的传统学术是一致的,目录的格局和学术的格局是基本相重的;而现代目录则使这些书籍分别隶属各种现代学术,这些现代学术基本上是按照近代以来引入的西方学科体制划分的,从中已看不出传统学术的原貌。随着“国学”的复兴,有必要在中国传统学术领域里摆脱现代学科体制的局限,重建古代目录学。
[1]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王锦民.古典目录与国学源流[M].北京:中华书局,2012.
[3]高路明.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5):85-9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