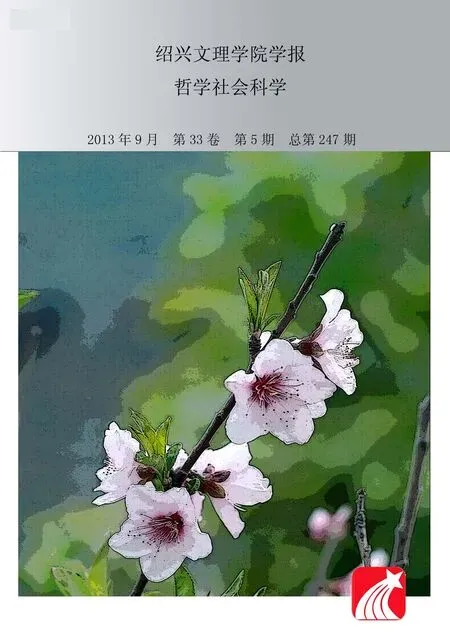工作场所侵犯行为的研究:形式、影响因素和预防措施
郭晓飞
(绍兴文理学院 教育学院,浙江 绍兴312000)
工作场所侵犯行为(workplace aggression)是指发生在工作场合的针对员工或组织的侵害行为。工作场所侵犯行为有相当高的发生率,Cortina等(2001)[1]的调查显示,在美国公共部门有71%的雇员报告过去五年中在工作场所曾受到过侵犯。有些领域的员工(如电话客服人员、宾馆服务员、精神病护士等)更有可能遭受侵犯。所有形式的工作场所侵犯行为都会对受害员工的身心健康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也影响其工作绩效。所以,研究工作场所侵犯行为,探索预防措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对国外工作场所侵犯行为的概念、形式、影响因素及预防方式的有关研究进行了评述,对今后有关研究在中国的深入开展提出了建设性建议。
一、工作场所侵犯行为的界定
个体的侵犯行为是心理学领域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各种心理学理论学派都曾经就此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对工作场所侵犯行为的研究则近些年才受到关注。大概在1990年,一位在瑞典工作的德国医生Heinz Leymann开始着手研究工作场所中的欺负问题,随后研究者将研究范畴进一步拓展到工作场所侵犯行为问题。
许多研究者基于自己研究的需要,对工作场所侵犯行为进行过界定。Baron和Neuman(1998)[2]强调工作场所侵犯行为发生于人际,是个体试图伤害自己目前正在工作或曾经工作过的组织中的其他成员的行为。Barling(2009)[3]强调工作场所侵犯行为可以针对员工,也可以针对组织,是有意对组织内个体造成伤害或对组织造成损害的行为。
回顾有关观点,我们看到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倾向于从侵犯行为的实施者角度进行概念界定,并且特别强调侵犯行为对组织的损害及对员工的伤害。我们总结工作场所侵犯行为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对象的针对性。侵犯行为针对的对象是组织或员工。二是目的的明确性。侵犯行为的目的是要造成侵犯对象的一定的损失或伤害。三是客观的危害性。侵犯行为会导致受侵犯个体的身心伤害和受侵犯组织的损失。所以,可以把工作场所侵犯行为看作是发生于工作场合中的针对员工个人的身体或心理的伤害行为以及针对组织的损害行为。
在对工作场所侵犯行为的界定中,我们需要厘清几个概念。工作场所侵犯行为的概念来源于英语“workplace aggression”,国内研究者也翻译为“工作场所攻击行为”,这两种翻译都没有错误。从有利于研究的角度而言,我们认为翻译为“工作场所侵犯行为”比较好。因为攻击行为概念容易产生歧义,仿佛“workplace aggression”只包含对员工的言语和身体攻击。侵犯行为概念包容性更好,可以包容包括目光敌意、散布恶意谣言等不能用攻击行为概念包容的侵犯行为。
现在研究者一般倾向于把工作场所欺负(workplace bullying,也翻译为工作场所欺负行为)和工作场所攻击行为割裂开来加以研究,我们认为工作场所欺负属于工作场所侵犯行为,原因在于:一是从民俗学的角度而言,欺负一般理解为强势个体对弱势个体的欺凌或侵犯行为,如上级对下级、男性对女性、群体对个人(或人数多的群体对人数少的群体)。如果弱势个体联合起来侵犯强势个体,被称为“mobbing”。侵犯行为除了发生于强势个体对弱势个体以外,也可发生于弱势个体对强势个体,如员工暴力侵犯上级,或背后恶意中伤等。二是从语义学角度分析,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欺负”解释为“用蛮横无理的手段侵犯、压迫或侮辱”,而所谓的“压迫或侮辱”也属侵犯手段,因此欺负其实是强势个体“用蛮横无理的手段”对弱势个体的侵犯行为。三是在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欺负行为一般归属于侵犯行为的范畴加以研究,如金盛华等[4]把欺负看作是一种更具体的侵犯表现形式。所以,我们认为可以把工作场所侵犯行为和工作场所欺负整合起来加以研究。
二、工作场所侵犯行为的形式
关于工作场所侵犯行为的类型方面得到公认的是Baron、Neuman等(1999)的研究结论[5]。他们通过员工回答问卷方式描述了工作场所内40种侵犯行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频率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其中的33种侵犯行为落在三个区间内,因此形成了工作场所侵犯行为的三个维度:一是敌意表达(Expressions of hostility);二是蓄意阻挠(Obstructionism);三是工作场所暴力行为(Workplace violence)。
在Baron、Neuman等的研究中,敌意表达包括这样的侵犯形式:对某人怒目而视;在他人面前贬低某人的想法和意见;在某人背后说坏话或散布谣言;向上级传达对某人的负面评价等。蓄意阻挠包括这样的侵犯形式:故意不回某人的电话;在某人请求帮助时断然拒绝;故意拖延与某人有关的工作。工作场所暴力行为包括这样的一些侵犯形式:使用武器对某人实施袭击;损坏某人的资源;故意推搡、挤靠和碰撞某人等。
Pcharlotte(2005)[6]研究指出,不友善的目光接触、恶意的非语言暗示、损害性谣言等敌意表达方式是组织中最常出现的侵犯行为。言语形式的性骚扰是属于第二位的侵犯形式。蓄意阻挠也是发生率极高的侵犯行为,这种行为的目的是妨碍个体的能力发挥,阻挠组织目标的达到。
关于工作场所欺负的形式,也有研究者进行了分析。Leymann等(1996)[7]探索出七种形式:利用组织措施进行攻击(attacks with organizational measures)、社会孤立(social isolation)、侵犯私人生活(attacking private life)、身体暴力(physical violence)、攻击性态度(attacking attitudes)、言语侵犯(verbal attacking aggression)和传播谣言(rumors)。Einarsen等(1997)[8]探索出三种形式:个人损毁(personal derogation)、工作相关的骚扰(work related harassment)和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
比较侵犯行为和欺负的形式,可以看到,欺负的形式都可以包括在侵犯形式中,比如Einarsen等的研究中,个人损毁可以包括于侵犯行为的工作场所暴力行为中,工作相关的骚扰其实是一种蓄意阻挠行为,而社会排斥是一种敌意表达行为。因此,就形式角度而言,工作场所欺负也可以从属于工作场所侵犯行为的范畴加以研究。
三、工作场所侵犯行为的影响因素
研究者指出,有许多潜在变量能够预测工作场所侵犯行为,包括社会的、组织的、身体的、认知的、人格的、态度的等因素。Neuman、Baron等(1998)[9]研究提出了一个工作场所侵犯行为的模型,该模型后来被称为侵犯行为通用情感模型(The General Affective Aggression Model,GAAM),认为工作场所侵犯行为的主要预测变量来源于个人因素和组织因素两方面。个人因素方面,核心预测变量是人格特征(如A型人格)、情绪状态(如被激怒、受挫等)和侵犯经验(如敌意归因倾向)等。组织方面的核心变量是组织公平、组织气氛或文化等。
(一)个人层面的因素
1.员工的人格特征
员工的人格特征与侵犯行为有密切关系。研究表明,工作场所侵犯行为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个体的人格特征,因为个体的人格特征影响了其心智水平和情绪表达方式,也影响个体的行为模式。Zapf(1999)[10]研究指出,具有嫉妒心和敌意的员工倾向于会在工作场所对其他员工实施侵害行为,而那些对自我提升不自信、具有高水平风险逃避风格的员工比较容易遭到欺负。Baron、Neuman等(1999)研究证明,个体在A型行为模式的测验分数上得分越高,往往具有较高水平的易怒性,他们也更容易产生嫉妒和敌意,因此更有可能对其他员工实施侵犯行为。而B型行为模式的员工侵犯倾向明显比较弱,C型行为模式的员工由于比较懦弱、压抑、不善于表达和沟通,可能容易成为被侵犯对象。
2.员工的情绪状态
研究显示,侵犯行为与员工的情绪状态有密切关系,许多负性情绪会导致侵犯行为,这些负性情绪包括:愤怒、苦恼、悲伤、紧张等。Hepworth[11]等(2004)研究显示,在员工的愤怒情绪状态和工作场所侵犯行为之间具有较强的一致性,愤怒情绪状态是员工的侵犯行为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为什么愤怒情绪会导致员工的侵犯行为,研究者认为原因在于个体情绪对其理智和行为具有极大的影响力量,研究也显示愤怒情绪会使员工处于失控状态,变得缺乏自知力,也丧失自控力,因而在实施侵犯行为时变得无所顾忌。[12]
3.员工的侵犯经验
Bandura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人的侵犯行为倾向由早年学习获得。研究也证实,侵害有时由工作场所的偶然冲突引起,具有侵犯倾向的员工易被激怒而实施侵犯行为,而受害者会被污点化,他们因无法应对这种情境可能会持续受侵害[13]。研究证实遭受伤害的员工可能反过来以各种手段进行还击。研究者将受害者的应对方式分为四类:自我怀疑、消极应对、问题忽略和问题解决等。采取前两种应对方式的受害者会以类似方法对侵害者加以反击[14]。我们推测曾经有过侵犯行为的员工有可能还会实施侵犯行为,而受到过侵犯的员工可能还会受侵犯,或者他们会报复,或者他们会侵犯那些更容易受侵犯的员工。
(二)组织层面的因素
1.组织公平
工作中情境因素或组织因素对员工的侵犯行为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研究显示在工作情景中,组织公平、员工人际平等的情况下不容易产生侵犯行为,而不公平的工作场合,员工之间更加容易产生侵犯行为[15]。研究显示当组织发生变革,员工面临突然解聘时比较容易引起侵犯行为。研究发现常常不是突然解雇的结果本身引起员工的侵犯行为,而是员工被突然解雇时所采取的方式。如果员工面临突然解雇,而组织又没有采取恰当的补偿方式,使员工感到组织不公平,或者员工被突然解雇时还被欺负或侮辱,员工会产生不满和愤怒情绪,员工感到气愤不平,最后可能会导致发生侵犯行为[16]。
2.组织气氛
美国人类学家Ruth Benedict选择“高协和”与“低协和”描述两种类型的文化氛围。Maslow解释说,在高协和的社会里,人们互相合作,总能善有善报。在低协和氛围中,个人需通过战胜他人获得利益,失败者不得不小心谨慎,所以有更多冲突、侵犯发生[17]。相类似,低协和的组织气氛会助长侵犯行为。Kessler(2008)[18]编制暴力氛围量表(The Violence Climate Survey),该量表在美国的不同组织环境中进行的测试结果显示侵犯行为与工作中员工面临的压力呈现显著相关,而员工压力与组织气氛显著相关。组织环境中高度竞争、紧张的气氛导致员工处于高应激水平,易引发员工的侵犯行为。
对于组织因素如何引起侵犯行为的问题,一种合理的解释是首先因为这些因素会引起个体产生负面情绪,随后唤起了个体的侵犯意向,在有明确的对象的情况下导致侵犯行为发生。
四、工作场所侵犯行为的预防
对工作场所侵犯行为,研究者探索了两方面的预防措施,一是从组织层面探索预防或避免侵犯行为的措施;二是从受害者角度探索避免侵犯行为发生的预防措施。
1.组织层面的预防措施
研究者指出要预防侵犯行为发生,组织层面需要制订制裁措施,在制订制裁措施时,不能仅仅笼统地列出项目,而是要把侵犯行为的细目列举出来。组织的管理者必须能够做出明确承诺,确保对侵犯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组织层面还必须让员工能够清楚认知这些制裁措施及管理层零容忍的态度。Dekker等(1998)[19]研究指出员工对组织的制裁措施的清楚认知能够抑制侵犯行为,他们在研究中发现男性员工如果相信组织会严厉制裁实施性骚扰的员工的情况下会显著减少性骚扰行为。Kathryne等(2006)[20]的实验研究也证明当被试认知到自己的侵犯行为会受到严厉制裁时会抑制其实施侵犯行为。
要预防工作场所侵犯行为,Douglas等(2001)[21]提出组织还要采取措施评估和筛选具有潜在侵犯倾向的员工并加以干预,比如筛选出那些处于愤怒情绪状态且具有侵犯倾向的员工。在评估方法方面,Lutgen-Sandvik等(2008)[22]认为运用多等级系统评定(如360度评价)能对员工行为有全面评估,能鉴别和监督工作场所侵害行为。
2.个人层面的预防措施
从个人的角度而言,研究者提出要预防或阻止侵害行为,员工首先需要能够界定欺负或侵犯行为,并且能够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应对。Macintosh(2006)[23]提出员工若受到侵害,需要向工会、EEOC、老板、律师等提交正式与非正式的投诉,以防止侵害行为再次发生。受侵害员工也要能够自我保护和获得支持,比如获得家人和朋友的支持。获得与自己同等地位的同事的支持也非常重要,同事的支持有时能有效防止侵害行为重复发生。
个人能够与潜在的侵害者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能够减少侵犯行为的发生。Gail(2009)[24]研究表明,与顾客维持积极联系,避免触发顾客的厌倦和挫折感是第一线情绪劳动者避免受到侵犯的有效方式。Salman等(2010)[25]研究提出,员工与顾客的成功互动依赖于员工能够创造一种吸引人的、积极的情绪氛围,包括能够付出极大努力控制消极情绪,保持积极情绪状态,让自己有适当的声调、面部表情、身体语言等。这些研究表明,员工培养良好的沟通能力,善于与潜在的侵犯行为实施者良好沟通能使自己免受侵犯。
五、工作场所侵犯行为研究的展望
1.有关概念的界定问题
Bowling等(2010)[26]指出,尽管在工作场所侵犯行为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是有许多问题仍有待深入探讨,在一些基本的概念的界定方面也需要有更多共识。我国有关研究中,也遇到类似问题。与工作场所侵犯行为相关联的概念,除了工作场所欺负(workplace bullying),还有工作场所暴力行为(workplace violence)、工作场所粗野行为(workplace incivility)、组织攻击行为(organizational aggression)、工作场所越轨行为(workplace deviant behavior)、反工作行为(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等。对于这些概念的表征及相互关系的辨析尚未取得统一意见。我国的有关研究中应该厘清这些概念的本质及其关系,使研究工作能深入和系统开展,以提升研究的影响力并产生实践价值。
2.工作场所侵犯行为的测量问题
有些学者研究了工作场所侵犯行为的测量问题,编制了有关的量表。如Baron和Neuman(1996)编制了工作场所侵犯行为量表(Workplace Aggression Scale,WAS),该量表区分为三个子量表:敌意表达(Expressions of Hostility)、蓄意阻挠(Obstructionism)和公然侵犯行为(Overt Aggression Behaviours)。有关量表能够用于测评工作场所侵犯行为,但其效度和信度一直是个问题。因为有些当事人可能夸大事实,而有些受害者则因为害怕受到报复而不敢吐露真实情形。虽然运用多等级系统评定方法有助于更加准确测量侵犯行为发生的实际情况,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碰到种种困难,特别是在我国的人文环境中运用时会遇到更大阻力,比如人情面子的问题会极大地妨碍评价工作的有效展开。这个问题是我国研究者需要深入探索和想办法解决的问题。
3.工作场所侵犯行为的预防和干预问题
对于工作场所侵犯行为的预防问题,国外已经有了一些前瞻性的研究,研究者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建议。我国对工作场所侵犯行为的预防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关研究工作尚待开展。我国有关研究中一个可喜的现象是关于受侵犯员工和侵犯实施者的干预研究已经起步。员工心理援助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逐渐受到一些组织管理者的认同,有关研究工作和实践探索正在逐步开展。而员工心理援助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就涉及受侵害员工和侵犯行为实施者的心理干预问题。作为我国研究者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是,一方面需要系统研究工作场所侵犯行为的实施者和受害者的干预问题,另一方面,需要付出努力让更多组织管理者认识到有关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能够使有关工作产生实效。
总之,由于工作场所侵犯行为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广的复杂问题,作为研究者来说,在重视其测量、预防和干预研究的同时,也需要在研究方法创新及多学科合作展开研究方面付出更多努力。
参考文献:
[1]Cortina,L.M.,Magley,V.J.,Williams,J.H.,et al.Incivility in the workplace:incidence and impact[J].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2001,6:64—80.
[2]Baron,R.A.,Neuman,J.H.Workplace.aggression-the iceberg beneath the trip of workplace violence:evidence on its forms,frequency,and targets[M].Public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1998,21:446—464.
[3]Barling.J.,Dupre,K.E.Predicting workplace aggression and violence[J].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2009,60:671—692.
[4]金盛华.社会心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320.
[5]Baron,R.,Neuman,J.,& Geddes,D.Social and personal determinants of workplace aggression:Evidence for the impact of perceived injustice and the Type A Behavior Pattern [J].Aggressive Behavior,1999,25:281—296.
[6]Pcharlotte,P.A diagnostic approach to measuring and managing workplace aggression[J].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2005,3(1):1—5.
[7]Leymann,H.The content and development of mobbing at work[J].European Journal of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1996,5(2):165—184.
[8]Einarsen,S.,Raknes,B.Harassment in the workplace and the victimisation of men[J].Violence and Victims,1997,12:247—263.
[9]Neuman,J.,Baron,R.Workplace violence and workplace aggression evidence concerning specific forms,potential causes,and preferred targets[J].Journal of Management,1998,(24)3:391—419.
[10]Zapf,D.Organizational,work group related and personal causes of mobbing/bullying at work[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power,1999,20:70—85.
[11]Hepworth,W.,Towler,A.The effects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charismatic leadership on workplace aggression[J].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2004,9:176—185.
[12]Glomb,T.Workplace anger and aggression:Informing conceptual models with data from specific encounters[J].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2002,7:20—36.
[13]Notelaers,G.,Einarsne,S.,Wittel,H.,et a1.Measuring exposure to bullying at work:the validity and advantages of the latent class cluster approach[J].Work and Stress,2006,20(4):289—302.
[14]Lee Brotheridge,M.When prey turns predatory:workplace bullying as a predictor of coping,counter aggression/bullying and well—being[J].European Journal of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2006,15(3):352—377.
[15]Sandy,M.,Michelle,I.,Manon,M.,Niro,S.,& Kara,A.Predicting Workplace Aggression :A Meta-Analysis[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7:92:228—238.
[16]Brockner,J.Why it’s so hard to be fair[J].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06,84(3):122—29.
[17](美)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M].吕明,陈红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20.
[18]Kessler,S.R.,Spector,P.E.,Chang,C.H.,et al.Organizational violence and aggression:development of the three-factor violence climate survey[J].Work and Stress,2008,22(2):108—124.
[19] Dekker,I.,& Barling,J.Pers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redictors of workplace sexual harassment of women by men[J].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1998,3:7—18.
[20]Kathryne,E.,Barling,J.Predicting and Preventing Supervisory Workplace Aggression[J].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2006,11(1):13—26.
[21]Douglas,S.C.,& Martinko,M.J.Exploring the role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prediction of workplace aggression[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1,86:547—559.
[22] Lutgen-Sandvik,P.,& McDermott,V.The constitution of employee-abusive organizations:A communication flows theory[J].Communication Theory,2008,18(2):304—333.
[23]Macintosh,J.Tackling workplace bullying[J].Issues in Mental Health Nursing,2006,27(6):665—679.
[24]Gail,K.Emotional labour and strain in “front-line” service employees:Does mode of delivery matter? [J].Journal of Managerial Psychology,2009,24(2):118—135.
[25]Salman,D.,& Uygur,D.Creative tourism and emotional labor:an investigatory model of possible interaction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e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search,2010,4(3):186—197.
[26]Bowling,N.,& Gruys,M.Overlooked issues in the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J].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2010,20:5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