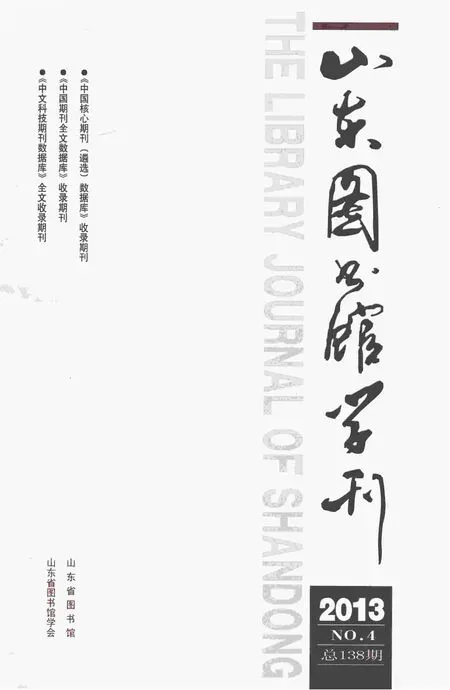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理想追求*
傅荣贤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作为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现代图书馆学也是遵循马克斯·韦伯所谓“理性化”的道路发展的,其学术背景是欧洲启蒙运动以来自然科学理性在图书馆领域中的延伸。理性化的基本特征是崇尚理智分析,基本目标则是追求文献信息传递的预期效率最大化,达到“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um)或“帕累托有效”(Pareto Efficiency)。因此,近现代图书馆学总体上并没有突破现实维度。
和西方式的“智性”图书馆学不同,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崇尚道德理性,本质上是“仁式”传统文化在图书馆学思想中的反映。因此,古人在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的现实层面之外,还致力于提高主体人的道德素质、达成社会教化、实现理想生态,建构了近现代图书馆学所无法企及的学术范型。
1 参与理想人格的构建
西方自亚里斯多德以来的主流思想强调“求知是人的本性”,“人”被设定为知性主体。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贤哲认为,人与禽兽之间的区别“几希”,有限的区别在于人是有道德的,如果没有道德则堕落为禽兽。相应地,与图书馆有关的“人”(包括文献的作者、馆员和读者)都是道德主体,因此,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理想追求的一个重要内容即在于努力构建这些“人”的理想人格。
1.1 从作者来看
作者是文献的主体,现代文献被定义为“记录有一切知识的载体”,本质上反映了西方“智性”文化的特征。“知识就是力量”是这一文化取向的经典表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该文化取向在中国特定社会时代下的翻版;而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知识集合说”、“知识资源说”、“知识组织说”等各种以“知识”为关键词的认识,则是“智性”文化在中国图书馆学界的反映。
我们知道,知识是认识主体对认识对象的客观反映,具备被证实的(justified)、真的(true)和被相信的(believed)等方面的特征。因此,记录知识的文献便具有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属性,文本完全可以独立于作者而存在。在此意义上,“作者已死”,馆员或读者完全可以直面文献本身而无需关注作者。而这无疑也是近现代图书馆学从未将作者纳入研究视野的根本原因。
中国先贤则认为,文献是“文”(文字记录)与“献”(贤才)的统一,扬雄《法言·吾子》曰:“在则人,亡则书,其统一也。”并且,文本与作者之统一,主要是为了凸显作者而不是凸显文本。所以,《法言·吾子》又曰:“然则五经不亡,无异仲尼常在,故去圣五百年而其人若存者,书在则然也。”这里,肉身寂灭的作者(仲尼)完全可以借助于五经文本而“常在”、“若存”,对比于西方的“作者已死”,似可表述为“作者复活”。《淮南子·泛论》指出:“诵先王之书,不若闻其言;闻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其实质也是要强调作者对于文本的优先性。
由此形成了中西图书馆学思想中对文献的不同认识路径:西方主要从知识客观性的角度来研究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文献的主要视角是文献的形式特征以及可以形式化的内容特征(如,学科属性和主题概念的逻辑类项);中国古代则把文献的认知转换为对作者的认知,因此,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的一揽子过程主要是以对作者德行的品评为对象的。清孙庆增《藏书纪要·购求》云:“夫天地间之有书籍者,犹人身之有性灵也。人身无性灵,则与禽兽何异?天地无书籍,则与一草昧何异?故书籍者,天下之至宝也。人心之善恶,世道得失,莫不辨于是焉。”这里,书籍不再是简单的客体,而是和主体人此包彼摄、主客互渗的价值论存在。对书籍的认知必须服从于“人心之善恶,世道得失”的道德约定。
事实上,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旨趣就在于从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的现实操作中,强调作者个人德行的重要性。例如,《四库总目》强调“论人而不论其书”以及“论书而不论其人”的原则。前者是说,书的内容并不太高明的,但其人在“忠节”之例,则书的身价要提高,分类也要设法显示其身份。如黄道周《礼论》五篇,本意不是解经,而是借以纳谏,本不应入经部,但编者强调他“不失圣人垂教之心”,虽然不是“解经之正轨,而不能不列之经部”。后者是说,作者人品不好,但其书可取,也要破例加以录取。如耿南仲《周易新讲义》提要说他“沮战守之说,力主割地”,认为耿的“经术之偏,祸延国事”。像这种人品本不足道的奸臣,在政治上批判之后,认为他们的著作内容颇有可采之处,故略其所短,取其所长。显见,无论是“论人而不论其书”还是“论书而不论其人”,都要强调对作者人品的评骘,本质上是认为,文献活动并非单纯的学术行为,而是关乎世道人心和社会教化的。
1.2 作为文献整理者的馆员本质上是道德主体
知识论意义上的文献,可以从物理形态和主题概念的逻辑类项上加以打量,因而成为类似于牛顿的苹果那样的纯粹客观之物,主体人可以对它们进行测量、制造和控制。相应地,馆员的职业训练和工作准则也主要是客观、公正、形式化地收集、整理、编码和保存文献。比如,在文献整理和编码方式上,应该持守客观化的原则,“天才著作和下流作品同样都是书目中的一个类号”。所谓合格的馆员,就是熟悉文献资源建设、文献分类编目工作等具体业务的技术人员,而这些也是当今图书馆学教育的全部旨趣。总之,作为文献工作者的馆员只是一个具备职场工具理性的知性主体,人格操守成为可有可无的非关键性因素。在此意义上,今天的馆员只是崇尚具体图书馆业务的“技术训练狗”,他们的工作甚至可以被智能化的工具(如自动分词技术)所取代。
古代馆员也有现实层面上的业务要求,“典籍”、“正字”、“校勘”等等这些表征具体业务工作的名词,甚至成为他们的职业称谓。然而,由于古代文献并非知识论存在,古代馆员们的文献工作也不局限于仅仅提供知识服务,而是要致力于某种价值层面上的突破与超越。因此,馆员的人格操守遂成为全部文献工作的首要前提。相应地,在古人“必试而后命”的馆员职业准入和任职要求中,道德是主要条件之一,馆员只有作为道德主体才能胜任形而下的具体文献工作。简言之,只有首先做一个有修养的道德人,然后才能充任馆员。
馆员通过提要、分类等文献行为努力达到彰善瘅恶的道德目标,而对孰善孰恶的认定又需要馆员的“准确”理解,从而也凸显了馆员的道德主体(而不是知性主体)的属性。例如,《四库总目》编者在黄道周《易象正》一书后所加案语中说:“此及倪云璐《儿易》,有于易外者,犹有据经立义,发挥于易中者,且皆忠节之士,宜因人以重其书。故此二编仍著录于经部,非通例也”。“非通例”而为特例,旨在表彰作者“死不忘君,无惭臣节”。另外,龚诩和杨继盛的文集、周宗建的经解也都因作者“人品高尚”而“强为之”入经部。可以肯定,这种对文献背后作者之道德境界的判分,是以馆员自身的道德标准和品行涵养为依据的。
显然,古代的文献观也是文化观,它肯定了人文精神的价值,有助于我们今人重新考量文献“知识”定位的局限,启发图书馆如何在知识服务的基础上提升道德修为和道德境界。
1.3 作为文献利用者的读者也是道德主体
现代文献的“知识”定位,默认读书就是为了获得知识,从而就是获得培根所谓的“力量”。时至今日,“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已成为读书和上学的全部动机。换言之,“读书”与人格的养成无关,德行也不被视为“力量”的基本源泉。
中国先贤认为,文献的本质是文字记录背后的“道”,唐人毋煚《古今书录序》云:“夫经籍者,开物成务,垂教作程,圣哲之能事,帝王之达典。”所以,文献不是记录知识的纯粹客观之物,而是主体人(作者)的心性显现,读书是为了“求圣贤之道”,把握修身立世的道理。文献的这一基本性质,经过馆员主体的刻意弘扬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读者并非直接面对文献,而是经过了馆员的文献收集和整理的中介。古代馆员在文献收集、整理和保存中所呈现的人道指向,施之于读者的文献检索和阅读的整个过程,让读者在形而下的文献获得和利用之中,提升个体人格,培养高尚的道德。例如,《隋书·经籍志序》曰:“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益者,并删去之。”《四库总目·凡例》云:“辨厥妍媸,严为去取。”馆员对“违碍”文献规定了严格的去取标准,从而直接限定了读者的文献获得并助益读者“读好书、做好人”。此外,馆员还通过类目的特定设置或对具体文献所作的提要,直接干预乃至训导读者深刻体会文本的道德内涵,并转化为读者个体人格的提升。例如,读者藉由查找文献的书目,也被馆员设计成了“大弘文教”的“为治之具”,读者在由书目而文献的查找过程中,不能不受书目所构建的人伦境界所左右。例如,《汉志·六艺略序》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这里,所谓“古之学者”的经学,主要是通过主观身心的修养达到“畜德”的目的,“后世”的“博学者”实指今文经博士,他们偏离了“古之学者”的经学取向。这样,读者涵泳于馆员的独特的书目体系中,在文献检索的同时也增强了读书之“畜德”目标的认知,体会到道德的崇高。
这种将文献之收集、整理和传递的整个信息交往过程与现实的人伦理想和政治教化功用完美地结合起来的图书馆学取向,并不是从原子分析主义的观点出发追求某种可验证的信息编码与解码效果,形式或性质上的“真”不是它的主要动机。相反,它以“善”为取向,是高度张扬人生境界、强调润泽生命的学术范型。从馆员在文献收集和整理中构成的形上境界,到读者查找和使用文献的形下践行,完整地构成了对道德理想的普遍追求,使得古代图书馆学思想所呈现出来的精神境界既志存高远又具有现实操作性。
2 参与理想社会和理想生态的构建
古人将作为一种具体技艺的文献活动“进之于道”,这既表现在参与个体人格理想的构建之上,也表现在参与理想社会和理想生态的构建之上。
2.1 就理想社会的构建而言
儒家追求“内圣外王”的价值理想,“内圣”即修身、齐家,旨在熏修个人的理想境界;“外王”即治国、平天下,要求以理想的个体人格,建构整个社会关系的和谐有序。因此,除了建构理想人格之外,在具体文献活动中构建理想社会也是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题中应有之意。
不妨以古代书目为例试为申论。一方面,古代书目的学术旨趣包括文献检索和考辨学术两大现实层面的内涵;另一方面,也包括“申明大道”的超越旨趣。而其所“申”之“大道”的重要内容之一即是参与理想社会的建构。
例如,古代书目通过对不同内容文献的刻意分类和排序,在文献规整性的“小序”的基础上,努力揭示社会人伦的“大序”。如刘宋王俭《七志》首列“孝经类”,因为“孝乃百行之首,实人伦所先”;《七略》以“易经”居六艺略之首,是因为《易经》既是“诸经之源”又是“道之源”等等,皆是显例。因此,基于分类而形成的文献秩序,直接对应于社会理想秩序。又如,《隋志》力图在文献秩序的基础上,“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其教有适,其用无穷”。《通志·校讎略》体现了郑樵“会通”的史学哲学思想,最终目的是要会通天地人三材之道,实现“寻纪法制”、“可为后代有国家者之纪纲规模”(《夹漈遗稿·寄方礼部书》)的社会理想。再如,《四库总目·史部·传记》下分五目,其次第分别为:圣贤(指孔子、孟子、周公一类人物)、名人(指正人君子、名臣高士、孝子隐逸、道学忠义、贞女烈妇以至翰墨文章)、总录(一书记载很多人的传记)、杂录(有关传记资料的书)、别录(所谓“逆乱”人物的传记)。这是在列类标准及其先后次第中寓褒贬、辨妍媸,从而警示天下学者“写好书、做好人”。另如,《四库全书·常建诗提要》曰:“(常)建名位不昌,沉沦一尉,而遗诗五十七首,往往与王、孟抗行。所唱和交游,非唯无一显官,即知名之士,亦仅王昌龄一人。盖恬淡寡营、泊然声利之外者,宜所造独深矣。”这是通过提要的形式由褒扬常建的作品转而表彰其人格,从而启发天下作者砥励品行的重要性。
显见,古代图书馆学从不固步自封地将研究领域局限在纯粹“为图书馆学而图书馆学”的学术范围之内,而是密切联系当时社会政治和人伦生活的一种更为广泛而深邃的学术标准与追求。由此,古代图书馆学成为入世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注重政教人伦上的实用性,不仅是一种文献行为,更是社会伦理概念。它将图书馆行为和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融为一体,极力张扬图书和图书馆在治国安民中的重要作用,反映了汉民族意识中的实用理性精神。清高宗在《文渊阁记》中认为,《四库总目》的文献著录、分类、凡例、类序、案语及提要等,其根本目标是“盖如张子(按:张载)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集中反映了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对理想社会的追求。
2.2 就理想生态的构建而言
基于主客二分的西方哲学,其“本体论和宇宙论是有严格分殊的。前者是研究存在的理论,而后者是研究宇宙的结构和生成发展的学说”[1]。但中国古代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持守“天人合一”观,肯定人类与宇宙万物的有机联系,宇宙之“天”往往成为论证社会之“人”的依据。反映在图书馆学思想中,即是将理想社会的诉求奠基于理想生态的诉求之上,力求与天地自然的协调与和谐,达到理想化的生态平衡境界。相应地,文献行为参与理想生态的构建,也成为章学诚所谓“申明大道”的另一个旨趣。
例如,清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以十二月为计,将文献分为十二个大类,是为了“应岁周之数”。《四库全书》选用四种不同色彩的包背绫衣来区别四库图书,乾隆皇帝在一首诗里这样写道:“浩如虑其迷五色,挈领提纲分四季。终诚元矣标以青,赤哉亨哉史之类,子肖秋收白也宜,集乃冬藏黑其位。”大意是说,为了易于识别,用象征四季(亦配东南西北四方)的颜色来标志四部图书的类别。经书居典籍之首,如同新春更始,应标以绿色;史部著述繁盛,如火如炽,应用红色;子部采撷百家之学,有如秋收,以白色或浅色为宜;集部文稿荟萃,好比冬藏,应用黑色或深色。“从文渊、文源、文津、文溯四阁书的装帧情况来看,与诗中所描述的情况虽然稍有差别,但大体上还是不错的”[2]。事实上,我国古代首部系统书目《七略》,“其所使用的范畴、推理程序、论证方式和逻辑思考等等都与汉民族的本体论哲学有整体协同的关系”[3],是古人看待宇宙万物和社会人文的世界图式在文献活动中的表征。例如,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
这是对《六艺略》下所分的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小类文献所作的文字说明。其核心思想有三:一是述五经(乐、诗、礼、书、春秋)的价值功能,如“《乐》以和神”、“《诗》以正言”;二是将五经与仁、义、礼、知、信“五常”相配,如《乐》是“仁之表也”、《诗》是“义之用也”等等。由此形成一个“五常之道,相须而备”的自足体系。三是在此基础上,强调《易》为五经“之原”,“与天地为终始”,将五经所代表的五常人伦秩序与天地之道联系起来。
显见,古代的文献行为要努力遵循宇宙天地的规律,从而将文献行为从理想社会推广到了理想生态,并强调“天文”作为道德之源对于“人道”的至高无上的价值。我们知道,美国学者J·H·谢拉提出的“图书馆哲学”,本质上反映了西方后现代思潮对理性在图书馆中的滥用而引发的一种忧虑和反思,是要在科技层面之外,思考作为科技之理论根基的形而上层面的一般问题。但是,西方原子分析和主客二分式的学术范型,决定了谢拉等学者有关图书馆哲学的思考只能局限在“人文”层次,而缺乏对于“天文”层次的深刻洞见。相反,中国古代书目所反映的文献秩序,既是社会人伦秩序同时也“应岁周之数”、“合四时之序”从而“与天地相参”,真正达到了图书馆哲学的本体论境界。
3 结语
古代图书馆学是活跃在信念层次上的,它重视人文道德教化、社会有序和谐,并在天人贯通的高度把文献活动与“仁道”理想结合了起来。它能够启迪现代图书馆在文献传递效益之外,追求更大的目标、担当更多的社会道义。事实上,近年业内提出的知识自由、信息公平等理念,表明图书馆在文献传递效率的“理性化”诉求之外,另有更高目标。这似乎也暗示,古代图书馆学思想中的理想追求完全可以和现代图书馆目标相衔接。
〔1〕 张汝伦.邯郸学步,失其故步:也谈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反向格义”问题[J].南京大学学报,2007(4):60-76
〔2〕 华立.四库全书纵横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70
〔3〕 傅荣贤.《七略》目录学整体观刍议[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3(5):4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