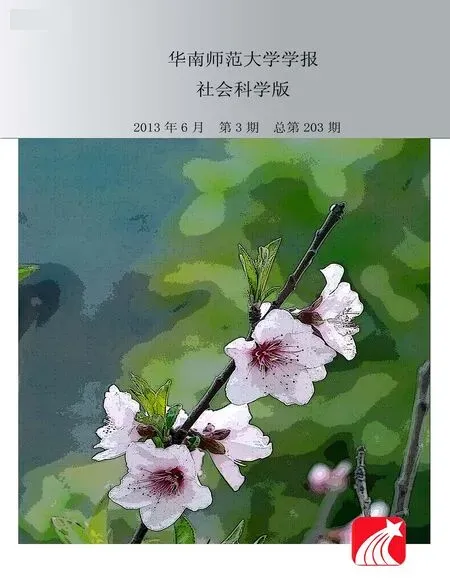京派作家乡土文本的审美内核
胡 西 宛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文学院,广东 珠海 519087)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地层中沉积着中西文化激荡、冲刷的痕迹,凝结着多元价值。其主流价值当属以启蒙精神为核心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而被称为文化守成主义的价值,如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作家序列所表现的,虽然未处在主流地位,却凭借其份量站上了和主流价值共生互补的席次。启蒙作家推崇西方现代文明价值,清算传统文化,意图是向现代化方向改造社会和人,而非消解自身文明的主体性;所谓守成的作家中,也并无肯定现存社会秩序者。二者有着共同的民族主义情感和文化主体性认同。在他们的乡土文本中,基本区别见于价值层面的不同取向和艺术表现的不同空间。在价值层面上,启蒙作家强调引入重建民族文化的异质资源,守成作家侧重固守本土文明核心价值;在艺术表现空间方面,启蒙作家着眼现实,守成作家致力审美;前者立足现实义,后者立足隐喻义。这里要强调的是,守成作家更具理想主义精神,他们的价值也是启蒙作家的终极追求。
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人以乡土表达其正向价值。乡土主题在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都具有母题意义。在现代中国,它又因为文明传承、文化冲突、社会转型以及价值递嬗等复杂背景,累积了文化精英们的多重文化思考和生命体验。乡土承载着这些作家的根本文化信念。这批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现代知识分子,把乡土营建成了一个系统性的价值结构。他们继承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精神,也代表了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表达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共同价值。他们的乡土,既是个体生命的起源,又是族群文明的载体,更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故乡,成为一个蕴藏着多层涵义的意象。
一、乡土:根源性的文化记忆
乡土的原型多是作家本人的故乡,所以许多乡土文本都存在双重视角:知识分子视角和儿童视角。处于隐蔽状态的儿童视角,表明作家不自觉地在以少年时代的眼光和高度看待故乡。视角不止是角度问题,还具有过滤和着色功能。儿童视角天然、单纯,在乡村世界摄取了自然界的光景,而穿不透遮盖着成人社会恐惧和焦虑的幕布,使得童年记忆携着美和善变作一种幻美体验,写进最初的生命过程中。这种个人早年的生命经验,记录了人对世界、对生命的原初体验,塑成了人格基底和价值观的源代码,并因日后成人世界负面经验的对比而日益增值,造成了一段理想化的生命记忆,成为逝去的永远的美好。这是人类生命意识中的永恒之美。儿童视角的乡土书写正体现着人类对这种永恒之美的追怀。这是蜿蜒在乡土文本深处的一条生命意识之根,这种生命意识是乡土文学的多元价值中高度重合的部分。严厉审视传统文化的鲁迅,也还有温馨的百草园、童话般的海滩瓜地、乡风浓郁的社戏;以悲剧心态观照儿时故乡的萧红,也对故园故人和逝去的岁月一往情深;对乡村持有批判立场的莫言,也视故乡为原始生命力和激情的源泉。这种乡土追怀,隐含着作者对其生命源头的追踪愿望和冲动,是人类对生命来路的无意识追怀。
而知识分子视角中的乡土则出现价值分野。周作人、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这一作家序列,以其文化理想、生命理想、人生经验和艺术观念把乡土酿成一种正向的文化价值。童年记忆被修改,在早年生命状态的理想化想象和幻美体验之上,还叠加着知识者对其文化母体、对其所属族类文明渊源的怀想和向往以及对其历史文明价值的崇拜。这种乡土追忆不能仅解释为怀旧倾向。它是一种文化隐喻,折射着民族文明的历史影像。所以,他们的乡土中还深深地扎着更为粗壮的文化之根。
《故乡的野菜》的表层内涵是作者本人的童年记忆:挽着苗篮采野菜的妇女儿童、“上坟船里的姣姣”、祭祀的乐队、浙东田野风光等风俗画面和自然景色。在其深层却叠印着中华文明早年的风姿:那是《诗经》中《关雎》、《卷耳》、《芣苢》、《采薇》等篇章所记载的先民田野采摘的情景和男女相悦的场面以及文化典籍中记载的各种民间礼俗。
《菱荡》中的乡土固化为一套完整的人文景观:瓦屋、石塔、农人、河水、渡船、竹林、花草;《边城》几乎就是这种景观的复制:木楼、白塔、山民、河水、渡船、竹林、花草;《受戒》再一次复制:院屋、庙、农人、河水、渡船、芦荡、花草……。这种蒙太奇式的组接,使乡村天地化作历史文化时空:自然环境、民居、宗教建筑、社群活动秩序井然,农事、民俗、宗教层次分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精神方式交相辉映。作家的乡土记忆暗含着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文化图式。
在这种统一的格局和型制中,环境特征以水最为突出,湖荡、河、溪环绕,使社会生活显得明艳、柔美、富庶、诗意。人物特征上表现为女性主人公居多,且以少女为主:《故乡的野菜》中有“嫁在后门头”的“姊姊”、“上坟船里的姣姣”,《菱荡》中有二老爹的孙女儿、石家井的小姑娘,《边城》里有翠翠,《受戒》里有小英子、大英子,还有《竹林的故事》、《萧萧》、《大淖纪事》等等皆可为佐证。文本中这种内敛、宁静、阴柔、秀美的形象和由此呈现的诗性风格,就表现对象而论,体现了作者故乡江浙和两湖地区的自然与人文地理面貌和社会风情,是长江流域文明传统的表征;从作家的审美理想方面说,则流露了这些南方作家的古典婉约诗风倾向的审美情趣,可看作是这些作家审美意识中的美学原型;从文化资源上讲,体现了作家对上古文化、文学遗产的肯定和接受:文本中的采摘、踏青、祭祀等活动和相思故事等等,都体现了古典文学自诗骚以降对妇女活动的艺术表现。在这条文化源流中,氏族社会时代的文化痕迹也若隐若现。
两种视角下的乡土中,盘曲着人类生命意识之根和民族文化之根,蕴含着根源性的生命记忆和文化记忆。这些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乡土,成了人类生命意识和民族文明的载体。这使中国现代文学的乡土主题在世界文学中获得了独立价值。
二、“经典中国”:中华文化形象的审美建构
考察这些乡土文本中的自然、社会和人,可发现其统一的审美特征。这主要体现为传统社会中人的生存的诗意性,包括生活环境的诗意性、生存方式的诗意性、人际关系的和谐、人性的美和健康、人的精神的完满自足等等。这实质上是对宁静、和谐、华美、诗意的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的文学摹写,是对以中华文明为核心价值的中国形象的诗性想象。一个巨大的文化形象——“经典中国”出现在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人的乡土文本中。
这些现代作家对“经典中国”形象的建构,集中表现为对传统社会的审美想象。这里采用的是典型的知识分子视角,体现的是典型的知识分子趣味;而这种趣味的培养与形成,要追溯到他们的启蒙时代。“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成为经典蒙童读物的这首宋诗,就是知识分子心中传统社会日常生活图画的简化版。而《故乡的野菜》绘成的浙东农村、《菱荡》的陶家村、《边城》的山水人家和《受戒》的庵赵庄,就是这幅图画的升级版。《菱荡》作为小说却抹掉了叙事特征,以至有些散文选本把它选进去。[注]如王剑冰主编的《百年百篇经典散文(1901—2000)》,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即收入废名《菱荡》。这个小说文本虚化时代背景、淡化故事情节、弱化人物性格、简化人的精神世界,刻意与表现对象保持距离,只以中景和全景表现陶家村这个传统民间社会的自然环境和日常生活形态。《受戒》更刻意突出乡间自然风光和传统社会风情。这些文本中描画的桃花、桑树、溪流、湖荡、田园、村舍、农人、蛙声、荧火、流星等等,全都是内涵具体清晰的传统中国意象。追根溯源,《桃花源记并诗》便是所有这类图画的经典版。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人的诸种文本都隐含着陶渊明的文本,就连它们的文体特征都何其相像。
历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有这样一个“桃源情结”。他们钟情于传统社会的生态之美,欣赏乡民们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的自在与自由状态,向往那种生存形式的诗性特征。而这些,或许已成为全人类再也无法追回的生命价值。
在与前文形成对比的同时,以“她”、“它”同音的双关渲染了一种人与胡同虽一同老去但胡同可新生人却无力扭转的厚重悲凉感,令人慨叹。
《故乡的野菜》从民俗和文学的角度突出对传统社会的审美想象,最能代表知识分子的传统审美趣味。从乡间祭祀活动——清明扫墓,作者首先联想到的是鼓乐声中“上坟船里的姣姣”和船头篷窗下紫云英和杜鹃的花束。如果说这是作者个人的审美想象,那么,文本中展开的吴地三月三荠菜花开,“侵晨村童叫卖不绝”的情景,则向我们暗示了典出《临安春雨初霁》的诗意图景[注]陆游:《临安春雨初霁》:“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春日里妇儿挽着苗篮采摘荠菜的叙述,更把我们引向《诗经》的《国风》、《小雅》中的先民风习;而“三春戴荠花,桃李羞繁华”等民谚和童谣中,又浮现出陶渊明笔下“童孺纵歌行,班白欢游诣”[注]陶渊明:《桃花源记并诗》。的景象来。考察《故乡的野菜》中隐含的众多文本,才发现它系列地为我们呈现了先秦的中国、六朝的中国、唐宋的中国、明清的中国。区区一把荠菜,竟可以接通遥远年代的民间生活和古典诗人的审美趣味,通向幽深的中国历史文化空间,展现经典的中华风物和诗性的中华精神。民俗的本土性、民俗的民族本己性,使周作人文本中的中国文化形象兼具色彩感与质感,文化内涵丰富,诗性特征突出。联系周作人的其他作品如《乌蓬船》、《喝茶》及“草本虫鱼”系列,可以发现,他以民俗学视角穿透现实生活、民间文化和中国历史,从共时性和历时性向度上为读者呈示了最具本土色彩的中国形象,其力度超过了前述三位作家在小说文本中的表现。
人性美和人情美是这些乡土文本的另一个内涵层面,一般认为这表现了作者的人性理想。但我们还要看到,作者钟情的人物不外是中国的传统文明准则和道德理想的化身,体现的是儒家的伦理情感、道家的诗性人格、佛禅的生命觉悟等等精神风范。这说明他们强调的是体现在主人公道德原则、生命信念中的中华文明传统的核心价值。从这个角度看,表现人性美、人情美也是作者们“经典中国”建构工程的主体部分。
这些乡土文本对中华民族传统形象的审美想象,体现了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和人性理想,包含了中华文明的物质遗产和精神遗产,组成了他们文明信念中永恒的“经典中国”。“经典中国”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文化记忆,是全体华夏族裔的民族信仰。以中华传统文明为主体价值的“经典中国”形象,是起始于华夏人文初祖,各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共同参与,主流文化、民间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汇融合,经由不同时代继承、扬弃、发展,从而塑造完成的文化正宗和民族品牌,是具有文化本位意义的历史符号。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作家尤其醉心于其美与和谐的诗性特征。作为对本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肯定,作为对人类文明永恒价值的追求,这与其他对传统文化持批判立场的作家并无价值上的冲突。正如周作人自己,既与“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一样尊崇西方科学理性,又醉心于从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化中寻找建设理想社会和人生的资源。对“经典中国”的审美想象,体现了这些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性思潮和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自觉的民族身份认同意识,守护本民族主体文化价值的历史责任感。
当然,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原本并非擅于制度设计。桃花源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和谐安宁,唯一和“制度”沾边的也仅是“靡王税”[注]陶渊明:《桃花源记并诗》。而已,向上可以追溯到孔子的“无苛政”[注]《礼记·檀弓下》。。这从政治学意义上看,似透露出些许无政府主义倾向;稍有制度设计痕迹的孟子,也多是鼓吹“发政施仁”[注]《孟子·梁惠王上》。一类士大夫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道德理想。有别于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关于政治、法律、经济等层面的理性规划,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理想国的基本价值是美、善和自由,凸显出他们社会理想的感性特征和审美特质。中国现代乡土作家也一样。他们接过传统知识分子的入世情怀、“兼济”道义和审美趣味,把前辈代代描绘的社会理想塑造成民族形象、提升为文明信念,从而构建起了属于全球华人的“经典中国”的审美形象。这是这些现代乡土文本的重大价值之一。
三、凝视中的“他者”:生命理想的投射
崇尚本真状态的生存,追求心灵的宁静、和谐与自由,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怀有的生命理想。上述乡土文本的主人公身上,多可见到这一理想的光芒。
这些乡村社会的生存者,总体上是真善美的化身,统一的精神特征则体现为真。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自然”概念的基本内涵,指人精神的本真状态和生存方式的本然状态和生存环境的本然状态。总之,人既没有受到世俗环境恶质的污染,也没有背负现代社会加给的精神重压。《边城》中的翠翠、《受戒》中的小英子和明海、《故乡的野菜》中“上坟船里的姣姣”,是天然长成的生命,纯粹、健康;《菱荡》中的洗衣妇张大嫂、《受戒》中的村人,不受仪规、戒律的约束,淳朴、自由;《菱荡》中的陈聋子,与外部世界没有冲突,内心世界也没有波澜,与生俱来地保持着从容、淡泊、空明的心境,颇见禅的静虑风神。这些真善美者,因其生存的本真、良心的纯洁和灵魂的宁静,内心是和谐而自由的。
为什么知识分子的价值偏偏寄托在缺少知识的传统乡间和底层农民身上,为什么不能正面建构起承载知识分子价值的知识分子形象系列呢?因为这缺乏现实合理性。在这些作家的现实世界里,找不到成功入世或成功出世的知识分子,只看见吕纬甫、涓生、倪焕之、高觉新、莎菲、汪文宣、方鸿渐们的苦难历程以及此后知识分子精神的垮塌。现代知识分子继承了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传统,宿命般地重演了多数前辈在“穷达”—“出入”式的人生设计上的失败实践,却再无缘重返前辈们入世失败后寄情山水的独立自足的精神境界。因此,这些现代知识分子只好寄情乡间的纯朴生命,从“别处”寻找其生命理想,以艺术想象化解现实困境。
看来,这些本真的人物具有某种“他者”的意义。“他者是主体建构自我形象的要素。他者是赋予主体以意义的个人或团体,其目的在于帮助或强迫主体选择一种特殊的世界观并确定其位置在何处。”[注](英)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第129页,张卫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正是这些“化外”的本真和健康的自在生存者,定义了“文明世界”里异化的生存者,知识分子们当然也包括在内。这虽然显示了作者一类知识分子潜意识中的优越感以及与下层的距离感和区隔意识,但其本意则是借人物宣扬自己的生命价值和生命理想,并对异化的生存现状作出批判。
四、面对乡野:解放的需求与想象
人物掩映在乡野的自然山水中,人与自然景物浑然一体,难分彼此,这是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人的乡土文本中颇为独特的景象。在这里,自然景观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环境描写,甚至并非环境描写。它是和人物具有同等价值的艺术表现对象,具有独立意义。本质上,乡野蕴含着作者们向往的生存和生命的至高境界,是这些作家的乡土写作最终到达的地域。“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注]陶渊明:《归园田居》。“归田”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原始冲动,执着入世如孔子,也会情不自禁地附和寄情大自然的学生。[注]《论语·先进》:“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归田的本义就是归向生命的本真和本位,归向知识分子的性灵空间。“归”是中国知识分子内心的永恒追求,已被写入他们的文化基因。现代作家的乡土书写可看作是他们归田的虚拟形式。
这些乡土文本中的乡野是自然山水,其中暗寓着生命与自然的原初关系的想象,是生命起源与归宿的象征;乡野与科学和商业文明保持距离,是本然世界和本然人性的象征。在佛家看来,自然界的一切无不是佛性和智慧的显现。在天然、和谐、宁静、优美的意义上,乡野是精神解放的象征。乡野以其强大精神引力,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图腾。面对乡野就是寄情山水,寄情山水就是超越现实,找回和面对本心本性。因此,面对乡野就是体悟生存、洞见灵魂,其现实意义是暂时解脱世俗的羁绊、生存的压力、现世的苦难和肉体的束缚,终极意义则是重返自由心灵,获得宁静和愉悦,实现内心的空明清澈,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中国知识分子多愿接受身心二元论,把主体的心灵当作非物质性的实体,不论是主动进入还是被迫退守,那里永远是属于个人的自由王国。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强大的现实阻碍也许难以克服,但营建个人性灵的空间则如蜘蛛缀网、蜜蜂营巢一样,不但擅长,而且出自本能。从本质上讲,它体现了积极思考人的解放的理想主义精神,这与向来对其所作的逃避现实的批评是有距离的。
在《菱荡》的乡野中,潜隐着一种存在秩序。“菱荡圩算不得大圩,花篮的形状”,“环着这水田的一条沙路环过菱荡。”“荡岸,绿草散着野花,成一个圈圈。”“走路是在树林里走了一圈。有时听得斧头斫树响,一直听到不再响了还是一无所见。那个小庙,从这边望去,露出一幅白墙。”“如果是熟客,绕到进口的地方进去玩……或者看见一人钓鱼,钓鱼的只看他的一根线。一声不响的你又走出来了。”菱荡圩是封闭的圆环结构。在封闭的意义上,它是一个完整世界和自足系统,和陈聋子的生命特征同构,对应和提示着陈聋子独立自足的精神状态,是自足精神的隐喻;在圆环的意义上,它在静态中蕴含着无始无终的运动,可看作是时间化的空间,暗合中国民间的一种生命信念:循环观。给这种观念以支持的,除经验层面的四季与阴阳轮替、人世兴衰与祸福往还外,还有先验层面佛家的轮回允诺。依这种周行性的时间观和生命观,自然和生命存在表现为周而复始的无穷运动,具有无限性和永恒性。这算得上是传统文化关于时间和生命存在的哲学认识。封闭圆环形的菱荡就是这种生命观念的图示,所以它实质上是空间化了的时间。这个圆环中进一步布置了画龙点睛式的存在物:小庙、钓者、伸开手脚躺在大地上闭眼向天的人。这些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价值符号的加入,显现了主体与对象世界的特殊关系结构。这不是人与实践对象的关系,而是精神与它的客观对应物的关系:人在自然中瞥见自己心灵的镜像,识见存在的本相。这种人与自然对话的格局,透露出万物与我齐一、以有限融入无限的精神欲求。具体到废名的文学语境,这显现了废名的读者常常体悟到的所谓“禅意”与“禅境”:在“静虑”中“自识本心”而进入静寂空灵的生命境界。菱荡的深林中传出的斧头斫树声,也引发读者朝向“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注]王维:《鹿柴》。的境界的联想,也是对禅意和禅境的一重印证。这应该是中国知识分子理解和喜好的“禅”吧。
当心灵与自然实现对话时,它就由世俗而超越、由有限而永恒,进而来到大解脱的圆满境界。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层生命体验,是对自我生命存在的审美体验和审美观照,是对于生命的自由王国的自觉建构,是具有终极关怀意义的生命价值追求。如马尔库塞所说,是“深入到人类生存纵深维度的解放的需求与想象”[注](德)马尔库塞:《审美之维》,第234页,李小兵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既带着宗教般的情感,也体现出强烈的存在意识,具有超越时代、社会和民族界限的价值。
以人物寄托知识分子的人性理想和生命理想,是这些乡土文本的显性的内涵层面;在乡野的自然山水中表现对生命境界的追求,则是这些乡土文本的隐性的内涵层面。
回望正消失在历史视野尽头的农业文明和与之相伴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审美方式,现代作家的这些乡土文本成了写给逝去的历史时空的挽歌;但守护着中华文明传统以及人性理想和生命理想这些属于全人类的永恒价值,又使周作人、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等人完成了一次现代作家的浪漫主义的精神寻根之旅。
五、“关键少数”: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之一
在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废名、沈从文同属“京派”作家,汪曾祺则被认为是“京派”传人。周作人和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又是两对师生关系。沈从文和汪曾祺也都表示自己受过周作人和废名的影响。[注]沈从文:《论冯文炳》,见《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汪曾祺:《万寿宫丁丁响》,载《芙蓉》1997年第2期。这显然是一个有明确思想艺术传承关系的作家序列。流派和师承关系并不妨碍作家各自的独立思想和艺术个性。如果具体而论,四人作品的美学风貌是有显著差别的,其思想价值和思想资源也有很大不同。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的乡土文本表达的文化理想和生命理想具有一致性。这集中体现在其乡土写作中对民族文明的根源性的文化记忆、对“经典中国”形象的审美想象以及他们的人性理想和存在思考上面。
然而,这种一致性,仅用流派或师承关系来解释又是不够的,它的精神根源在哪里呢?可以认为,在于他们思考中国现代化问题时体现的牢固的民族主体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外来异质性文化资源价值的警觉意识。一方面,这些现代知识分子并不是思想、政治上的守旧派,他们代代都秉承“五四”精神,都认可西方科学民主的价值。周作人对所谓西方新知的宣传、对封建文化的猛烈批判更是有目共睹。但另一方面,他们又都是受中国传统文化透彻熏染的现代知识分子。如果简单举证,儒、释、道传统,古典文学与文化传统等等在四人身上都能够寻到确凿的印迹,自觉持守中华文明传统是他们的内在要求。与以激进姿态反传统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们既有认识西方文明正面价值的前提,又有固守本土文化主体性的理由,更有反省现代文明弊端的勇气,因为他们觉悟到某些现代性价值可能与其坚守的本土价值相悖。因此,本土价值自然成为他们乡土文本的主导意识。他们的家国情怀、他们崇尚的或儒、或释、或道的精神传统以及由此形成的带有鲜明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人文性格色彩的道德感情和对理想生命境界的崇拜,无不打着醒目的民族主体性的印记。这些不同层面的价值,在何处归于统一?统一在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与伦理共识的基础之上。[注]关于“民族认同与伦理共识”问题的详细论述,参见郭齐勇、秦平:《儒家文化:民族认同与伦理共识的基础》,载《求是学刊》2006年第6期。亦如该文所言,中华民族民族认同与伦理共识的基础并不仅仅是儒家文化。
中国终于逐步走向现代化了,并且还始料未及地迎来了全球化。当此之时,追求民族认同与伦理共识,已然成为主流的声音。而在当年的启蒙与现代化思考中,周作人、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在其乡土文本中表现的基于民族认同与伦理共识的文化守成主义立场,却处在边缘地位。立场的边缘性使得他们的文学史地位也一度边缘化;但正是这类边缘式人物,在当年充任了“关键少数”的角色。“关键少数”之所以关键,原因在于他们的价值的无可替代性。这一价值的存在,形成了对后发现代化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偏误的矫正机制,形成了文化批判价值和文化守成价值互补共生的思想生态。在反抗、破坏、创造、新生的呐喊声达到峰值的时刻,他们的声音是微弱的,但这微弱的声音却从来没有中断过。这也说明,他们与承担着批判、清算传统文化任务的知识分子阵营并不存在根本冲突,原因就在于双方的民族身份认同、文化生命理想和社会革新的使命感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固守的价值,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本民族“固有之血脉”[注]鲁迅:《文化偏至论》,见《鲁迅全集》,第1卷,第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完整意思是:“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如果更客观一点看,他们是中国近现代启蒙语境中文明对话的不可或缺的一方。他们的文化思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天然组成部分,是现代中国文明进步思想原动力中的主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