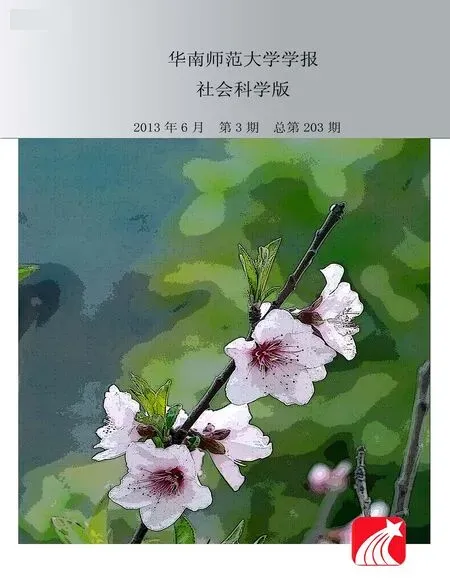“鬼魅”的权力斗争
——当代美国作家诺曼·梅勒作品主题思想再思考
谷 红 丽
(华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当代美国作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 1923—2007)曾经获得两次普利策文学奖。一次美国国家图书奖,2005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基金会授予他终身成就奖。他去世后,汤姆·伍尔夫(Tom Wolfe)评价说:“他是整个文学界巨大的能量来源,是马达、发电机。”[注]Alex Tresniowski:Pulitzer Prize Winner Norman Mailer Dies, http://www.people.com/people/article/0,20159578,00.html。理查德·拉卡罗(Richard Lacayo)认为:“现在没有人敢说自己有着和梅勒一样的魄力和富有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没有人敢说自己有资格取代梅勒的位子。”[注]Richard Lacayo:Why Norman Mailer Mattered,http://www.time.com/time/nation/article/0,8599,1682741,00.html。勿庸置疑,诺曼·梅勒在当代美国文学和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梅勒自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裸者与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 1948)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他的评论层出不穷,研究视角也非常丰富。对于他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主题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反极权主义思想、“白皮肤的黑人”思想、存在主义思想、反女性主义思想、关于身份和个人主义的思想、关于政治和权力的思想等等。本文认为梅勒作品中最显著的主题思想是权力斗争。
学术界已经有不少对于梅勒作品中权力主题的研究成果。美国学术界比较有代表性和系统性的研究成果有罗伯特·恩里奇(Robert Ehrlich)的专著《诺曼·梅勒——激进的希泼斯特》(Norman Mailer: The Radical as Hipster, 1978)和奈格尔·莱(Nigel Leigh)的专著《激进小说与诺曼·梅勒小说研究》(Radical Fictions and the Novels of Norman Maile,1990)等。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任虎军的论文《诺曼·梅勒小说的书写动机与主题》、张涛的博士论文《诺曼·梅勒的存在主义及其前期小说主题研究》和王延彬等的论文《诺曼·梅勒小说主题与泛极权主义情结》等。从研究范围上看,这些研究成果大多是对梅勒的某几部作品或某个历史时期作品的主题研究。从研究视角上看,它们关注的几乎都是梅勒作品中权力斗争的某个方面,比如恩里奇探讨的是梅勒激进的“希波斯特”(Hipster)思想;莱关注的是梅勒作品“从意识形态激进主义到神话诗学激进主义”的转变;[注]Nigel Leigh:Radical Fictions and the Novels of Norman Mailer, London: The McMillan Press Ltd., 1990: ix。张涛提出在梅勒的思想体系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其存在主义思想”;[注]张涛:《诺曼·梅勒的存在主义及其前期小说主题研究》,山东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任虎军认为梅勒的小说通过再现“美国社会中性别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等权力意识”,体现了梅勒的反性别主义、反种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意识。[注]任虎军:《诺曼·梅勒小说的书写动机与主题》,载《当代外国文学》2009年第3期。不难看出,这些研究成果缺乏对梅勒的所有作品进行比较全面和动态的主题研究视角。
本文拟从比较宏观的视角对梅勒的整个创作生涯进行研究,认为梅勒作品中最为显著的主题思想是权力斗争;而且,他作品中的权力斗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权力斗争往往以反抗者的失败而告终,比如《裸者与死者》中的哈恩和《鹿苑》(The Deer Park, 1955)中的艾特尔。而在他的后期作品中,情况发生了变化。反抗者往往以侥幸或暂时的胜利而结束,比如《一场美国梦》(An American Dream, 1965)中的罗杰克和《刽子手之歌》(The Executioner’s Song, 1979)中的加里·吉尔莫。此外,本文还认为,《白皮肤的黑人》(The White Negro, 1957)一文的发表是这种转变的开始,它标志着梅勒所倡导的 “希波斯特”(Hipster)思想的成熟。此后发表的小说中的反抗者往往表现出“希波斯特”的特征。另外,本文还认为,梅勒作品中主题思想的改变体现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和欧洲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对他的影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体现了梅勒对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中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批评理论的呼应。
一、权力斗争中反抗者的失败主题
诺曼·梅勒的大部分作品都体现了他对于权力的关注。正如梅勒自己说的那样,他的每部作品都是对权力具体或者抽象的表现:“我认为我所写的任何东西都表现了对于权力的关注——存在于各种关系中的权力、世界的权力、世界的无力、所有那些主题……”[注]Nigel Leigh:Radical Fictions and the Novels of Norman Mailer, London: The McMillan Press Ltd., 1990, p. ix,viii。美国著名文化评论家阿尔弗雷德·卡津就曾把梅勒称为“一个以宏大的现实主义模式记述权力的编年史家”[注]Nigel Leigh:Radical Fictions and the Novels of Norman Mailer, London: The McMillan Press Ltd., 1990, p. ix,viii。。
梅勒关注最多的是政治层面的权力,比如他的小说《裸者与死者》(1948)、《鹿苑》(1955)、《我们为什么在越南?》(1967)和《哈洛特的幽灵》(1991)等都与美国的政治有关。其实,梅勒在发表《裸者与死者》之后,就曾经明确表达了他对于作家与政治之间关系问题的思考。他说:“在这个特殊时期,我认为没有一个作家可以对政治避而不谈。遗憾的是,在过去十年,美国作家有种非政治化倾向。我想这就是这段时期美国文坛作品贫乏的部分原因。”[注]Hilary Mills:Mailer: A Biography, New York: Empire, 1982:108。他对美国政治的关注使约翰·维伦-布里奇(John Whalen-Bridge)不无感慨地说:梅勒是个“过度政治化的作家”[注]John Whalen-Bridge:Political Fiction and the American Self,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103。。弗兰克·兰特里基亚(Frank Lentricchia)把诺曼·梅勒、唐·德里罗(Don DeLillo)和罗伯特·库弗(Robert Coover)等一起归为具有政治意识的作家,并对其大加赞扬。[注]Frank Letrichhia:The American Writer as Bad Citizen∥Frank Lentricchia: Introducing Don DeLillo,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6。
然而,在梅勒的早期作品或者可以说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作品中,权力斗争往往以反抗者的失败而告终,权力方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地位。这一点在《裸者与死者》和《鹿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裸者与死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极权主义思想倾向的批评。它通过描写军官卡明斯和克罗夫特对哈恩中尉等士兵的精神控制和虐待,表现了极权主义的可怕和反抗的必要性。
对于卡明斯将军来说,军队就是自我社会试验室,第二次世界大战只不过是他实现政治目的的途径之一。他统率部队的目的是要根据自我意志改变部下,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的变革。克罗夫特和卡明斯持有相同的观点。只不过,卡明斯是个思想家,而克罗夫特则是个实践家。他把卡明斯的理论付诸实践,哈恩中尉和其他士兵就是这个试验室等待解剖和改造的受害者。虽然哈恩也曾经对卡明斯和克罗夫特的变态行为进行过反抗,但在故事临近结尾的时候,哈恩中尉却在一场混战中死亡。而即将上任的戴尔森是一个相信卡明斯理论、并且已经被这种极权主义思想驯服的人。这样的结尾表明了在权力斗争中反抗者行为的彻底失败。
梅勒在创作《裸者与死者》的时候,与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和作家一样,在政治意识上持左派的激进主义思想。他的偶像是詹姆斯·法雷尔(James Farrell)、多斯·帕索斯(Dos Passos)和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等关注社会现实、具有自然主义写作风格的作家。
此外,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的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部小说的主题。华莱士认为,二战后的美国有一种明显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梅勒则把华莱士所说的法西斯主义倾向称作极权主义。这种极权主义试图控制人的思想和制约人的行为,最终把人训练成铁板一块、毫无生气可言、任人摆弄的机器人。不管梅勒在《裸者与死者》中持有什么样的政治思想,故事的结尾都体现了他的悲观和无奈。
梅勒的第三部小说《鹿苑》从表面上看是一部关于好莱坞的小说,其实,他探讨的仍然是政治层面的权力斗争问题。正如《裸者与死者》中以美国军队和二战为背景一样,好莱坞只是虚设的背景。梅勒的本意不是要探讨好莱坞电影制作的生态环境,而是要剖析存在于好莱坞的极权主义及其对于人性的压迫。发生在工作室的导演之间的斗争、导演和演员之间的冲突以及导演和管理层之间的矛盾,都只是大的政治氛围影响下的局部表现。小说中的颠覆委员会才是真正有威胁的、也是梅勒在小说中真正关注的主题。其他一切矛盾冲突都源于这里。梅勒对于颠覆委员会的刻画是通过国会议员理查德·克利恩和他的两个助手表现出来的。
理查德·克利恩无论是外形还是行为风格上都与《裸者与死者》中的卡明斯将军相似。他与卡明斯最本质的相似是对美国自由思想的严酷压制。斯坦利·加塔曼(Stanley Gutman)曾经批评说:“正如梅勒描绘的那样,颠覆委员会有力地影响着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它的兴趣不在于安全、平安或者真理,而在对于美国人民自由意志的镇压。”[注]Stanley Gutman: Mankind in Barbary: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in the Novels of Norman Mailer, Hanover, New Hampshire: The University of Vermont, 1975: 35。毫无疑问,它代表着权力关系中的支配者和主导者。而小说中的艾特尔导演则代表着权力关系中的被支配者和受压迫者,像《裸者与死者》中的哈恩一样是权力企图压迫和控制的对象。在与颠覆委员会的较量中,艾特尔最终屈从于权力的淫威。艾特尔为了得到电影公司的导演职位,不得不向颠覆委员会坦白了自己曾经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虽然艾特尔早已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坦白的内容也并无新意可言,但这个行为却意味着向权力的妥协和反抗的失败。不仅如此,为了被高级电影公司所接纳,埃特尔还不得不放弃自己希望执导的剧本。经过政治意识和艺术上的两次妥协之后,艾特尔终于进入了好莱坞,满足了职业上的虚荣心。然而,他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他同时丧失了政治信念和艺术追求上的双重自由意志。
从以上两部小说的分析可以看出,梅勒在艺术生涯的早期(即20世纪四五十年代),对于美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投入了很大的热情,对美国的社会走向也有很强的责任感,但是他的态度却是悲观的。
二、权力斗争中“希波斯特”的胜利主题
1957年《白皮肤的黑人》一文的发表对于梅勒的创作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梅勒创作思想的转变。在这篇文章中,梅勒认为二战后的美国社会充斥着严重的极权主义倾向,人们明哲保身、混沌度日。为了彰显自我、保全自我,大家应该注重追求自我的本能反应,去寻求冒险、刺激、极端甚至病态的生活体验,注重当前的生活状态。他把这样的人称为“希波斯特”。可以说,梅勒的这种具有存在主义特点的“希波斯特”思想与美国当时的反文化运动息息相通。在此后发表的小说中,梅勒对权力斗争表现出了明显的乐观态度。反抗者对于权力的斗争往往能够取得某种形式的胜利,虽然这种胜利是微弱的,甚至是前途渺茫的。梅勒的小说《一场美国梦》和《刽子手之歌》等都体现了这种乐观的态度。
在《一场美国梦》中,权力是一个包括大学、媒体、政府情报部门和黑手党等在内的权力网络,反抗者罗杰克是一个曾经身处这个权力网络的中心、后来放弃权力、试图通过一些极端途径追求自我生存价值的个人。罗杰克曾经做过国会议员、大学教授和电视节目主持人,获得过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实现了传统意义上的“美国梦”:成功的事业、富裕的物质生活、显赫的社会地位。他的岳父是美国社会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家族在商界、政府部门甚至宗教领域和黑手党组织都有一定的话语权。然而,“美国梦”的实现并没有给罗杰克带来成就感和满足感;相反,他感受到的是巨大的虚无。他主持的电视节目因其反主流文化的风格遭到了来自权力的压力,他们要求他把节目转型,以迎合普通大众的欣赏口味。罗杰克的自我追求与权力之间发生了矛盾。与此同时,妻子黛博拉在家庭生活中对他的侮辱和控制也让他感到窒息。这些来自外部的控制和压力使他感到自我的完整性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因此产生了强烈的仇恨心理和自杀倾向。最后,罗杰克选择了暴力手段,杀死了黛博拉,放弃了一切社会地位,逃之夭夭。
梅勒不仅把罗杰克的谋杀行为合理化,而且还为罗杰克设计了一个浪漫的未来——让罗杰克去南非度过余生。在梅勒的引导下,罗杰克的谋杀行为不但没有遭到法律的制裁,而且还让读者对之产生了同情之心。批评家对此感到非常气愤。与唐·德里罗(Don DeLillo)出版《天秤星座》之后的境遇一样,《一场美国梦》出版后梅勒受到了来自主流社会的排斥和抨击。伊丽莎白·哈德维克(Elizabeth Hardwick)把梅勒称为“坏孩子”[注]Elizabeth Hardwick:Bad Boy,Partisan Review 32,Spring 1965): 291-294。,罗伯特·露西德(Robert Lucid)把这部小说称为“诺曼·梅勒的一场恶梦”[注]Lucid, Robert:Norman Mailer: the man and his work. NY: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71.。
在传统的道德观念审视下,罗杰克对于自我的坚持和追求方式确实是“一场恶梦”。他否定了既有的身份和地位,嘲弄并颠覆了根植于美国人心目中的“美国梦”,并侵犯了他人存在的权力。但是对于梅勒来说,这是对抗极权主义、保全自我的积极行为,是值得鼓励和赞美的。可以说,罗杰克是梅勒所欣赏的典型的“希波斯特”形象。他在与权力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虽然这种胜利有违道德规范。
在后来的创作中,梅勒又多次描写了在权力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杀人犯形象,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刽子手之歌》中的加里·吉尔莫。加里·吉尔莫在冲动下杀死了两个无辜的男人。在被判处死刑后,吉尔莫拒绝提出上诉,反而要求对他执行死刑。此外,他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表达过后悔的心情。在梅勒笔下,一个失去理智的杀人犯变成了一个对生死有着深刻理解、敢于面对死亡、追求自我本能体验、在压力之下仍想保持优雅风度的海明威式的英雄。
《刽子手之歌》中的权力表现为美国的法制体系和罪犯叙事模式,吉尔莫的行为则表现了对这两种权力形式的藐视和颠覆。在传统的美国法制体系中,即使是杀人犯也有上诉的权利和缓刑的可能性。然而,吉尔莫却不愿意上诉,并要求对他行刑。也就是说,他不愿意按照既定的社会规范生活,他不愿意向世人表现他的懦弱、对生的留恋和对惩戒制度的妥协。他表现出来的是面临死亡时的坦然、勇气以及对于惩戒制度的不屑。
梅勒显然把吉尔莫浪漫化了,他根据自己的理解把吉尔莫塑造成了一个英勇的存在主义英雄。戴维·格斯特(David Guest)评价了小说的这个特点。他认为,吉尔莫的犯罪行为被梅勒描写成了“一种获取崭新的、更大范围的个人权力的仪式,而不是在压力下有条件的反抗行为”。而且“这个哲学意义上的心理变态者消除了他顺从的、遵纪守法的自我,抛弃了传统的道德感,是一个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冷血的、强大人物”[注]David Guest:Sentenced to Death: The American Novel and Capital Punishment, Jackson: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Press, 1997: 151。。也就是说,吉尔莫的暴力行为不是一种普通的反抗行为,而是一种仪式,是一种自我发现、自我成长的行为。这就是梅勒“希波斯特”的思想精髓——为了自我需要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格斯特的这个评价是中肯而恰当的。然而,格斯特还认为,吉尔莫的死与反传统英雄人物的死并不相同。吉尔莫其实是被权力抑制了的精神变态者,他的死反证了法律和惩戒制度的必要性。因此,吉尔莫的死不仅没有起到颠覆权力的作用,反而像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所认为的那样被权力所抑制了。
虽然从表面上看,吉尔莫被处死的事实表现了权力的胜利,他对暴力和死亡的看法也的确有违常理;但从本质上看,吉尔莫要求行刑的平静和坚决的态度却体现了他对于司法制度的反叛,尤其是他在行刑前广为流传的那句“让我们开始吧”更是其勇气的体现。同时,这句话也体现了他对于自己死亡行为的参与和一定程度上的控制力。它让人觉得是吉尔莫在要求行刑官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是他在与行刑官进行合作,而不是单方面、被动地接受处罚。换句话说,是权力机构在服务于吉尔莫的要求——虽然权力与此同时也达到了自己的惩戒目。
此外,吉尔莫在行刑前的这种态度也是对另外一种权力形式——罪犯叙事模式——的抵抗和颠覆。在传统罪犯叙事中,罪犯在临刑前往往后悔不已,并表现出如果有来生将改过自新的愿望,甚至还希望大家以此为戒,不要重蹈覆辙。也就是说,罪犯变成了权力用以规范社会、震慑他人的工具,处决行为充满了教诲意义。然而,吉尔莫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悔恨的心情,其行刑也没有任何上述叙事特点。梅勒把处死吉尔莫的那一章起名为“射杀火鸡”( “The Turkey Shoot”),这个标题暗示了梅勒对于权力随意性的批评。它表明对于吉尔莫的行刑就像人们对于火鸡的扑杀,充满了游戏色彩,颇具节日的狂欢氛围。吉尔莫的冷漠态度和众多媒体记者的参与使吉尔莫的行刑现场缺少了严肃性和道德上的教化意义,反而成了一个具有节日狂欢效果的景观。这种叙事手法显然区别于传统的罪犯叙事。它的讽刺口吻使整个行刑事件丧失了应有的教化意义,也缺少了宗教和政治上的严肃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吉尔莫的行为的确构成了对权力的反叛,并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权力的压迫。因此,梅勒为他谱写的是一曲赞歌。
三、权力斗争主题的理论背景
那么,梅勒作品的主题思想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的变化?对他的作品进行这样的历史分期是否合理呢?
其实,梅勒本人曾经对他的作品进行过历史分期。他在一次访谈中表示,他的整个创作生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裸者与死者》的发表开始到1959年《为我自己做广告》的出版结束;第二阶段是指整个20世纪60年代;第三个阶段开始于《玛丽莲传》(1973)的发表。[注]John Whalen-Bridge:The Karma of Words: Mailer since Executioner’s Song,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Vol. 30, No. 1 (Autumn, 2006)。不过,梅勒并没有对这种分期的原因作进一步解释。本文以为,他的分期动机与美国的历史文化背景有着紧密的联系。20世纪60年代对于美国来说是个动荡的时代。席卷欧美的反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 movement)[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教授Theodore Roszak把反文化归结为1960年代发生在美国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一切青年人抗议运动,“既包括校园民主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同性恋者权利运动等方面的政治‘革命’,也包括摇滚乐、性解放、吸毒、嬉皮文化及神秘主义和自我主义的复兴等方面的文化‘革命’。”转引自赵梅:《美国反文化运动探源》,载《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尤其是嬉皮士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女性解放运动、反战运动等诸多政治文化事件让美国人民应接不暇,无所适从;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各种后现代文艺思潮暗流涌动、相互交织,震撼、动摇着人们已有的知识框架和认知方式。因此,20世纪60年代被美国学界公认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分界。从这个视角看,梅勒对自己作品的阶段划分就变得非常容易理解。而本文则认为,他在《为我自己做广告》这部文集中收录的《白皮肤的黑人》(1957)一文是他创作思想乃至艺术形式转折的重要标志。这篇文章标志着他的“希波斯特”(Hipsterism)思想的具体化。
可以说,梅勒的“希波斯特”思想与美国反文化运动的精髓一脉相承,与欧洲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也有着深厚的渊源。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这两点内容已经有很多的研究成果,[注]国外比较有代表性的相关科研成果有:Steve Shoemaker:Norman Mailer’s “White Negro”: Historical Myth or Mythical History?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Vol. 37, No. 3 (Autumn, 1991); J. D. Connor:The Language of Men: Identity and Existentialilsm in the American Postwar, dissertation of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1999; Andrea Levine:The (Jewish) White Negro: Norman Mailer’s racial bodies,MELUS, Vol. 28, No. 2 (Summer 2003)。国内相关的科研成果有杨昊成:《论〈白色黑人〉的精神品格与写作动机》,载《当代外国文学》2001年第1期;张涛:《论诺曼·梅勒的“白色黑人”理论》,载《济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诺曼梅勒的存在主义及其前期小说主题研究》,载(山东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邹惠玲:《论诺曼·梅勒在创作中对嬉皮哲学的探索与追求》,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等。这里就不再赘述。总体看来,梅勒在《白皮肤的黑人》中表达的“希波斯特”思想有以下几个特点:(1)反叛性:不满美国战后墨守陈规、压抑个性的极权主义精神氛围,强调自我和个性的释放;(2)行动性:希望人们能够行动起来,积极主动地对抗主流文化,而不是消极被动地构建个人的浪漫梦想;(3)非理性:梅勒认为只要是有利于释放自我、保全自我的方法都值得尝试(包括极端的性行为和暴力),这也许是梅勒的“希波斯特”区别于“垮掉的一代”乃至“嬉皮士”们的主要地方;(4)存在主义特点:梅勒在《白皮肤的黑人》中曾多次使用“美国的存在主义者”一词。不过,梅勒的存在主义融合了他本身的犹太文化和他所推崇的黑人文化特点,因此与欧洲的存在主义思想有着很大的区别,具有美国特质。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对当下的关注和执着追求。
这几方面的特点极大地震撼了当时的美国思想文化界,也明显地改变了梅勒的艺术创作。笔者认为,这些思想导致了梅勒作品中权力斗争结果的改变。无论是《一场美国梦》的罗杰克或是《刽子手之歌》中的吉尔莫,身上都具备了《白皮肤的黑人》中所描绘的“希波斯特”特点。他们敢于反抗主流文化的压迫,暴力是他们的行动手段,他们只注重当下体验和对自我精神家园的追求;更重要的是,他们这种非理性的反抗行为取得了一定意义上的胜利。这可以说是对梅勒“希波斯特”思想或美国式的存在主义思想一定程度的文本诠释。
另外,梅勒作品中的权力斗争主题也是对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批评理论一定程度的呼应。虽然梅勒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他曾经阅读过福柯的权力理论,也没表现出对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兴趣,但梅勒作品中对于权力的表现却与他们关于权力的理论不谋而合。
在福柯看来,权力无处不在,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对权力的抵抗最终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因为抵抗最终总是会被权力所抑制。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等新历史主义学家深受福柯的影响,也认为文学文本和文化现象里面充满了各种权力关系,而权力斗争的结果是反抗一方被权力一方所抑制。在他们看来,虽然颠覆行为不可避免,但是社会的调整和规范力量总是大于颠覆者的力量;而且他们还认为颠覆行为是必需的,因为权力需要通过颠覆行为来加强自己对现实和常态的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说,被压迫的颠覆行为反过来服务于权力。格林布拉特在描述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现象时说:“颠覆行为是权力的产物,但又为权力的目的提供了服务。”[注]Stephen Greenblatt, Invisible Bullets: Renaissance Authority and its Subversion,Glyph,1981(8)。可以说,梅勒在1940和1950年代的小说体现了福柯和新历史主义理论家关于权力的观点。《裸者与死者》中哈恩中尉的死亡和《鹿苑》中艾特尔导演的妥协都体现了颠覆行为的失败,也证明了权力抑制力的强大。
然而,在梅勒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作品中,权力斗争的结果又和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关于权力斗争的乐观态度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虽然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家们也像福柯和新历史主义者一样,认为所有文本都是权力的载体,但是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家对权力斗争的结果更加乐观。他们认为,被权力压迫的一方通过反抗行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自己的目的,虽然这种成功是短暂而微弱的。正如理查德·威尔逊(Richard Wilson)和理查德·德顿(Richard Dutton)评价的那样:“如果说新历史主义在福柯的影响下认为权力是铁板一块的,那么文化唯物主义则认为,占支配地位的一方并没有控制文化的全部。”[注]Richard Wilson and Richard Dutton: New Historicism and Renaissance Drama, Harlow: Longman, 1992: 145。虽然《一场美国梦》中的罗杰克还在逃亡的途中,《刽子手之歌》中的吉尔莫最终也难逃死亡的命运,但是他们都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达到了自己的抗争目的。他们的结局象征着某种意义的胜利。
梅勒的作品数量众多,写作风格繁杂多变,个人生活放荡不羁,行为言论狂妄偏激。批评界对他的评价也褒贬不一。无论从个人生活还是艺术创作方面看,都体现了让人琢磨不定的“鬼魅”特质。这从上文对他作品中权力斗争主题的分析中可以窥见一斑。然而,这些“鬼魅”特质并非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它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梅勒作品中那些身陷各种权力关系之中、或失败或成功的英雄或反英雄体现了他对于极权主义的批判和对于美国式的存在主义者——“希波斯特”形象——的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