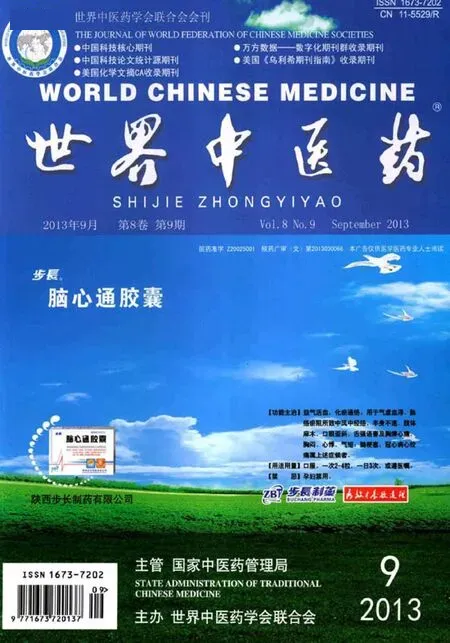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古籍出版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王 琼 金芷君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研究所,上海,201203)
中医学是经验医学,中医药古籍的开发与利用对于当代中医药学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对建国以来的中医药古籍的出版工作进行历史回顾,并对中医古籍的数字化、数据库化等问题进行展望。
1 古籍出版工作的历史回顾
从学理上讲,中医古籍出版的目的主要有3个方面:一者,继承之需;二者,中医古籍文词古奥,对今人而言,义晦难明,故需注释、今译、语释;三者,中医古籍因年代久远,讹误难免,故需校勘后再出版。建国以来,我国对于中医古籍的整理、出版和利用可简要分为几个阶段和类型,不同时期的中医古籍出版工作,伴随着政治的需要、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变迁均体现了不同特色,与时俱进[1]。
1.1 经典中医古籍的今译及语释 建国初期至文革前,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主,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为工作重心,医疗卫生工作虽有较大进步,但中医古籍整理与利用基本上处于起步阶段。1954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整理出版中医古籍,出版中医中药古籍,包括整理编辑和翻印古典的和近代的医书”。此为中央首次对中医古籍整理工作的批示[2]。其后两年间,中医研究院与四所高等中医学院的成立,推动了中国中医学科的建立,也为文献整理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人民卫生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出版社,影印出版了一批中医古籍,如《素问》《灵枢》《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并以今译或语释等方式,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书进行了整理研究,促进了经典文献的学习和普及[3]。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3月,卫生部为了落实国家十年规划第36项“整理语译中医古典著作”的规定任务,对《素问》《灵枢》《难经》《针灸甲乙经》《脉经》《诸病源候论》《针灸大成》等7本古典医著,按校勘、训诂、集释、语译、按语等项进行整理研究。首批经典文献的今译和语释,促进中医药高等教育的教学工作,有利于中医文献学在学科体制内的复苏与确立。古籍的今译与语释的工作,曾被文革打断,但这项基础性工作随着时代的进步,日益受到重视。当前图书市场上,一些古籍图书有各种今译本,琳琅满目,可谓丰盛,但读者也颇有无所适从之感[4]。一些热门经典古籍被重复出版,如《黄帝内经》《金匮要略》《本草纲目》等书,版本形式更名目繁多,普通本、精装本、点校本、白话本、文白对照本等不一而足。事实上,某种或某类中医古籍的语释本或今译本毋庸过多,只要该领域的优秀专家出一两种权威版本即可,这样既可节省出版工作中的重复劳动,又能有效的引导初学者、爱好者[5]。
1.2 出版工作的专业化与专门化 改革开放之后,中央着力加强了中医古籍出版工作。1982年,卫生部决定对中医古籍进行整理出版,6月,召开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工作座谈会,初步拟定了中医古籍出版的九年规划和落实措施。1983年1月,中医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正式成立,办公室设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办公室的成立,使古籍出版整理成为国家行政中的日常工作。本应在50、60年代完成的经典著作的整理工作被重新提上日程,3月,卫生部下发文件,将《伤寒论》《神农本草经》《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金匮要略》《中藏经》列为第一批重点整理书目。同时,人民卫生出版社组织征求了国内部分中医专家意见,制定了中医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4月,卫生部中医司在沈阳召开了中医古籍整理出版座谈会。在原6种的基础上,又新增了6种中医古籍,准备共12种古医籍整理出版任务。增加的有《素问》《灵枢经》《脉经》《难经》《黄帝内经太素》《内经知要》(此书后来被撤消)。这11种医籍整理历经数年,并于1988年左右定稿、出版[6]。卫生部将古籍校勘整理与编辑工作要求以文件的形式下发,对工作进行了标准化的要求,在全国实行分片负责、分级管理的组织工作。此外,办公室还落实了《中医方剂大辞典》《中华本草》《中医古今脉案》《中医年鉴》《汉方研究》等5种大项目。1985年,卫生部下达“关于对中医古籍与文献整理研究工作进行调查的通知”,对全国现有的中医善本图书及从事中医文献整理研究的机构和人员进行了摸底调查。同时,一些专门的中医古籍出版机构也纷纷涌现,为系统地整理中医文献带来了方便[7]。如成立于1980年10月的中医古籍出版社,是国内首家中医古籍专业出版社,对我国中医药典籍开展了系统的现代整理出版工程,曾推出了《中医珍本丛书》《珍本医籍丛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医家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善本医书》等大型中医古籍丛书,其中有大量险些流散的中医孤本、善本、珍本古籍。1983年,由上海市中医文献馆创办《杏苑中医文献杂志》,后改名为《中医文献杂志》,是目前为止国内唯一的中医药文献研究期刊,为中医古籍文献研究提供了专门的交流平台。书目编纂工作是文献学的基础,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以来,曾在1958年与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联合主编了《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但未能正式出版。1991年,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再次进行全国中医古籍资源调查,编纂出版了《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而近两年出版的《中国中医古籍总目》则更完整地反映了全国150个图书馆(博物馆)馆藏的1949年以前出版的中医图书13 455种[8]。
1.3 海外中医古籍的复制回归 近代战乱,大批古籍流失海外,中医药类古籍尤甚,但受国际交流条件及经费所限,中医药文献学者往往望洋兴叹。改革开放以后,国际交往日益频繁,为海外中医文献的回归提供了条件。20世纪80年代,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马继兴曾到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鉴定中医古籍版本[9],并撰有《美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中医药古籍目录》,之后数年,其又赴日本考察,了解了日本收藏的古代中医文献[10-11]。进入90年代,文献整理与校勘工作日益受到重视,国内外研究基金也对基础性工作给予支持。1996年、1997年、1999年,中日学者以“日本现存中国散佚古医籍的考察与出版研究”为题,向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亚洲中心3次申请课题经费,回归古医籍善本130余种[12]。2001年至2002年,国家科技部设立基础性工作专项科研基金,“国内失传中医善本古籍的抢救回归与发掘研究”成为其中中标课题,复制回归海外收藏古籍260余种,并对海外中医古籍收藏状况做了初步调研。该调查报告收集了11个国家与港、台地区的130个图书馆的230余种书目,从中查得以上国家和地区收藏的中医古籍31 250部,明确了分布世界的3万余部中医古籍的详细资料[13]。在此基础上,还完成了“中国大陆失传中医古籍种类调查报告”。调查结果显示,现存中国的明代医书1 200余种中,有120余种国内失传,失传的善本版本在200种以上。经过此项目,复制回归海外所藏中医古籍266种,其中善本233种。此项目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校点海外回归古医籍61种,编成《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分12册,550余万字,中医古籍出版社影印古医籍8种[14]。
1.4 中医经典古籍的外译与传播 中医经典古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海外中国文化爱好者、研究者的重视。早在18、19世纪,中西互通,欧洲外交官、传教士均将中国医书携带回国。当时,欧洲出版的针灸书约50种,以法国最多。但是这些出版物影响并不太大,且每有译误之处。后来,经典文献受到重视。从1925年到2003年近80年间,据统计,共有9种《黄帝内经·素问》的英译本问世[15]。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医药被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特别是针灸师在美国加州行医资格的法律确认,中医古籍外译也开始活跃,将中医的典籍翻译成各国文字的国家也开始增加[16]。2003年,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史研究所文树德教授(Prof.Paul U.Unschuld)主持的《黄帝内经·素问》英译课题结题。该项目与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合作,其英译本已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2003年出版的首册是《黄帝内经素问——中国古代医学典籍中的自然、知识和意象》(Huang Di Nei Jing Su Wen:Nature,Knowledge,Imagery in an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Text),该册相当于整个译本的概论。书后附有《黄帝内经素问中的五运六气学说》(The Doctrine of Five Periods and Six Qi in the Huang Di Nei Jing Su Wen),是为当代西方学者首次最系统的中医运气学说介绍[17]。在西班牙语界,中医经典的翻译也有了2本,《内经》和《难经》,有的综合多种英译本翻译而成,也有从中国白话本直接翻译而来。在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曾专门聘请我国文献研究专家赴美指导整理美国所藏的历代中医药学古籍资料。《黄帝内经》在美国就有3种译本。近年来,美国更出现了一些以中医药学书籍为主的出版公司,如马萨诸塞州的Redwing公司等。这些公司出版的中医图书即包括有《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的古典译本。德国文树德教授的中医古籍入门手册《中医古籍介绍》(英文本)也为该公司出版。在亚洲,日本与中国同处汉字文化圈,随着汉方医学在日本的重新复苏,中医古籍也自然受到推崇。毋庸讳言,中医古籍的的外译起到了传播中医的作用,引起了许多外国学者对中医的兴趣,这些贡献是不可忽视的。但各种译本质量参差不齐,令人担忧[18]。可喜的是,国家对中医古籍的外译工作备加重视,如国家新闻出版署的十一五规划中,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的《中国典藏中医古籍英译本》项目即被列为重大出版工程[19]。
2 中医古籍的数字化与数据库化展望
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学热与传统文化的回归,中医古籍文献的社会重视程度水涨船高。一些基本文献如《本草纲目》《汤头歌》也被国学班诵读。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市面上各种版本的《本草纲目》竟有十几种之多,同时,各种中医类保健养生书籍在街头巷尾出现,以“汉方”“本草”为关键词的食品与化妆品市场热销;影视剧中《大宅门》《大国医》等以中医药世家为内容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更吸引着国人对中医、对中医古籍的兴趣。这些,均对新世纪的中医古籍利用和再生提出新的挑战[20]。中医古籍的再生保护是以微缩胶片开始的,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首开风气,但由于胶片物理特性及使用寿命,以及胶片不便于阅读等问题,微缩工作告一段落[21]。随着互联网与信息时代的到来,古籍数字化已成趋势[22]。2001年,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在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资金的帮助下,与书同文电子有限公司合作,启动了“1 100种中医药珍籍秘典的整理抢救”项目,开发了“书同文古籍浏览系统”,读者在阅读古籍全文影像的同时,可以对内容进行简体、繁体两种方式的检索[23]。2005年,根据科技部“再生性古籍保护”项目的要求,图书馆依托自身的技术力量,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古籍标注系统和古籍发布系统。并从单一的数字化文本,发展出带有数据库特征的应用系统[24]。从长远来看,数据库优越于数字文本,而且数据库方便使用,从文献利用的角度来看,价值更高[25]。但现有的一些古籍数据库系统,为网络性数据库提供了相关的经验,有相当的医学、教学作用,但均无法通用共享。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数字化工作的不充分,不完善[26]。中医古籍中有许多抄本,据2006年的统计数据,我国现存5 000种中医古籍抄本,均面临破损与亡佚的危险[27]。进行校勘、注释、今译的数据库工作更是来不及。在技术力量方面,国内存有中医古籍的图书馆中,技术力量不一,设备设施参差不齐。所以,数字化是数据库化的基础。数字化再生是首要的工作[28]。
因此,我们认为,目前中医古籍文献开发利用的首要工作,要以国家卫生行政力量主导,仿效普通古籍数字化标准,建立可延续的中国中医药古籍的数字化标准[29],以方便、快捷、易保存,易操作,费用成本低廉为特征[30],在各图书馆推而广之,力争将全部古籍数字化[31]。在此基础上,中医古籍数据库的工作才能顺水推舟,光明在前。
[1]李其忠.中医古籍中的人文伦理和哲学思辩[N].健康报,2011-8-5(006).
[2]张灿玾.新中国中医文献整理研究工作简要回顾[J].中医文献杂志,2003,21(3):49-51.
[3]朱玲,崔蒙,贾李蓉,等.中医古籍语言系统中的语义类型分析研究[J].中国数字医学,2012,7(4):5-8.
[4]黄鑫,贾守凯.论中医古籍编辑的专业素质[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2,23(2):317-319.
[5]刘从明.新中国古籍出版工作概述[J].贵阳中医学院学报,2008,5(30):1-3.
[6]余瀛鳌.中医古籍整理与文献研究的今昔观[J].轩岐论坛,2008,3(3):8-10.
[7]邓伟,张伯伟,毛超一.中医古籍出版社体制改革的三点认识[J].中医药管理杂志,2010,18(4):369-370.
[8]马艳茹.中医古籍整理与出版的策略与思考[J].中医学报,2012,27(7):56-58.
[9]万芳,黄齐霞.中医古籍版本研究与思考——兼谈马继兴与中医古籍版本研究[J].北京中医药,2011,30(4):278-279.
[10]梁永宣.日本各地收藏中医古籍的图书馆(一)——宫内廷书陵部[J].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2013,8(1):92-93.
[11]梁永宣.日本各地收藏中医古籍的图书馆(二)——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J].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2013,8(3):313-314.
[12]陆伟路.试论中医古籍的保护[J].上海中医药杂志,2010,9(44):16-17.
[13]张伟娜.全国中医古籍保存与保护现代调查分析[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9,6(16):1-3.
[14]马继兴,郑金生.国内失传中医善本古籍的抢救回归与发掘研究[J].医学研究通迅,2005,34(5):28-29.
[15]赵丽梅.从外宣翻译的特殊性看中医英译[J].环球中医药,2011,4(6):478-480.
[16]邱玏.中医古籍英译史实研究综述[J].中西医结合学报,2011,4(9):459-464.
[17]孙海舒,符永驰,张华敏,等.基于本体论构建中医古籍知识库的探索[J].医学信息学杂志,2011,3(32):64-68.
[18]游越.文化多样性视域下中医翻译的语言障碍[J].时珍国医国药,2012,23(11):2877-2879.
[19]冷皓凡,谢玲,胡素敏.中医古籍文献信息化管理研究概述[J].江西中医学院学报,2010,1(22):46-47.
[20]焦振廉.中医古籍文献的存佚、形式及其文化内涵[J].中医药通报,2012,11(1):31-34.
[21]吴桂英.中医古籍文献数字化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医学信息杂志,2010,4(31):54-56.
[22]符永驰,李斌,郭敏华,等.中医古籍电子化系统的研究与实现[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8,15(2):103-104.
[23]裴丽.曹霞.中医古籍数字化多功能阅读环境模型构建[J].中医药信息,2010,27(1):118-120.
[24]李兵,刘国正,符永驰,等.中医古籍数字化整理方案探讨[J].中国数字医学,2010,5(5):33-35.
[25]佟琳.中医古籍“孤岛现象”及其对策[J].河北中医药学报,2010,4(25):6-8.
[26]蔺焕萍.中医古籍数字化建设存在的问题探讨[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2,22(18):45-46.
[27]裘俭,符永驰.中医药古籍抄本的研究现状及其价值[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6,13(1):100-101.
[28]马艳茹.中医古籍整理与出版的策略与思考[J].中医学报,2012,27(7):825-826.
[29]李兵,贾守凯.常用中医古籍数据库评价与分析[J].陕西中医学院学报,2009,4(32):86-87.
[30]胡晓峰,张丽君.略论中医古籍图像的特点与价值[J].中医文献杂志,2012,30(3):10-12.
[31]杨德利,刘家瑛,亢力,等.谈拓展中医药古籍图像的深度研究[J].世界中医药,2012,7(3):253-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