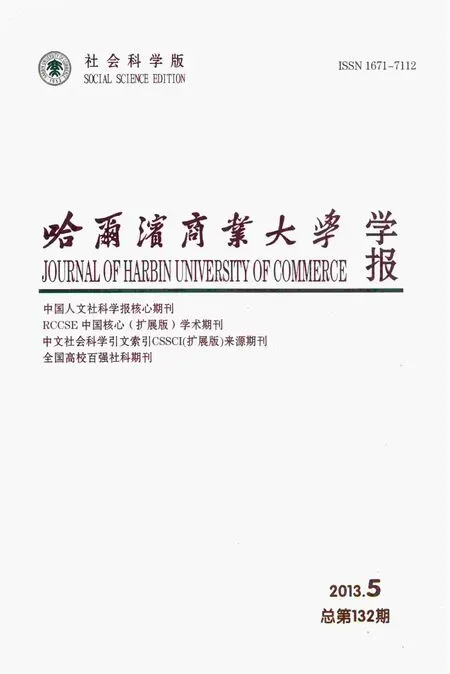基于信息技术的休闲问题研究
刁志波
(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辽宁大连116025)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中期以来,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一批新技术出现,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变革,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约翰·奈斯比特曾预测“信息社会即将取代工业社会”[1],阿尔文·托夫勒提出第三次浪潮: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了信息化社会[2]。正如他们的预测,人类社会历经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已经进入信息社会,即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社会。通常来说,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简称IT)是关于数据与信息的采集、传输、处理、存储、应用、安全等方面的技术统称,涉及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仿真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微电子技术等。
从休闲的角度看,我们已经进入普遍休闲的社会。休闲活动自古有之,但20世纪90年末,休闲产业、休闲经济才成为中国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中国内地的休闲研究也相应展开。就中国内地的情况来说,1995年开始实行双休日,目前的法定节假日已达到115天,公务员、国有企事业等单位职工已经实现了8小时工作制和带薪假期。2000年后,以手机、互联网、数字电视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应用逐渐普及,三网融合(广播电视网、电信网与互联网)正在实施,信息技术应用对人们的休闲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目前,信息技术应用已经成为人们休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的实践案例十分丰富,但理论研究滞后。因此,以信息技术为背景来研究休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信息论视角的休闲含义
1.休闲的含义概述
关于休闲(Leisure)的含义,众多的学者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美学、经济学等视角给出了他们的理解,如亚里士多德、马克思、凡勃伦、皮普尔(Pieper)、杰弗瑞·戈比等,他们从时间、活动、存在状态、心态等角度来解读休闲。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被认为是最早研究休闲的学者,他把休闲誉为:“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并认为:“休闲是科学和哲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只有休闲的人才是幸福的”[3]。马克思提出了自由时间理论,认为休闲就是“非劳动时间”,在其著作的英文版中一般用Free Time来指代“休闲”[4]。凡勃伦认为休闲的内涵是“对时间的一种非生产消费”[5]。瑞典天主教哲学家皮普尔在《休闲:文化的基础》一书中,指出休闲是人的一种思想和精神的态度,不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也不是空闲时间的结果,更不是游手好闲的产物[6]。杰弗瑞·戈比认为,“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并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7]
2.信息论视角的休闲含义
从日常生活的观察可以发现,信息社会的休闲与之前的休闲具有明显的差异,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劳动和休闲活动的界限变得模糊(下文具体阐述),因而不适合从时间或活动的角度来理解休闲。
从信息论的角度分析,休闲可以理解为:在人脑对信息的接收、处理、反馈等连续的过程中,借助信息技术为工具和手段,个体所达到的自由和愉悦的状态或心态。这种休闲是在信息技术创造的信息系统里实现的,既表现为人机互动,如人与计算机、手机、数字电视之间的互动;又表现为基于信息技术的人际互动,如手机通话、短信、网络视频、网络聊天、电子邮件等。这种休闲既是个体沉浸于信息世界的一种客观状态,又明显地表现为个体自我感知和认定的结果。因此,这种休闲应该主要是获得精神上的放松和愉悦。与散步、健身、舞蹈等传统休闲活动相比,信息技术背景下的休闲明显具有“静态”的特征,个体往往局限于狭小的空间,并相对独立、封闭地进行休闲活动。
三、信息技术主导的休闲方式分析
信息技术的出现,既改变了传统的休闲方式,使之形式和内容进一步丰富和多样化。同时,又创造出一些全新的休闲方式,这些休闲方式也是划分不同类型人群的重要标志,如“乐活族(LOHAS)”、“90后”等。
1.信息技术创造的休闲方式
该类休闲方式指的是以前社会不曾有的、由信息技术创造出的全新的休闲方式。例如,数字电视、数字电影院、3D电影、手机、掌上电脑(PDA)、平板电脑、网络电视与广播、虚拟旅游、部分网络游戏、网络视频、网络聊天工具、科技展示、模拟体验等已经越来越普遍,信息技术及其产品已经走进大众生活。尤其是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等,可以将虚拟的或人类难以亲身体验的内容展示出来,达到普通休闲难以达到的效果。
以虚拟旅游为例,它是通过虚拟现实、多媒体和3D等技术和设备,在相关的网站实现三维实景虚拟旅游,操作者在显示器前就可以体验知名旅游景点,达到身临其境的效果。虚拟旅游既对应着现实的旅游活动,又可以与现实的旅游活动完全不同,例如,模拟太空旅游、海底旅游、丛林旅游、峡谷旅游等人迹难以到达的地方。此外,科技展示也是如此,包括对人体奥秘、宇宙奥秘的科普展示活动,也是必须借助信息技术完成的。
2.信息技术改变的休闲方式
该类休闲方式指的是以前社会曾有类似的情况,但被信息技术改变了休闲的形式和内容,休闲的主体也相应发生了变化,相当于以往休闲方式的信息化。例如,数字图书馆、数字科技馆、部分网络游戏、网络购物、网络聊天、电子书刊、网络音乐、网络文学、在线教育等等,这些分别对应着现实生活中的图书馆、科技馆、游戏、购物、聊天、纸质书刊、现场音乐表演、文学创作、学校等。例如,就博客和微博来说,其本质可以认为是传统的日记、日志与信息技术结合的产物。
这两类休闲有时难以区分,没有明显界限。例如,网络游戏就是如此,棋牌类网络游戏是现实棋牌类游戏的网络化,3D虚拟科幻游戏、大型实景游戏、枪战类游戏(反过来影响现实中的枪战游戏)则完全是基于网络和计算机设计出的产品。
此外,信息技术主导的休闲,也可以分为消遣型,如看电视、听广播、网络音乐、网络新闻、网络视频、网络游戏、网络购物;社交型,如手机通话、短信、网络即时通信、电子邮件、社交网站、论坛(BBS)、博客、微博;学习型,如在线教育、电子图书馆、电子图书和报刊、网络文学创作。
四、信息技术背景下的休闲现状分析
就中国内地来说,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转型期,但又表现出一些信息社会的特征。因此,其休闲现状具有内在的矛盾性。学生、在职人员、退休人员等群体需要休闲,却不能休闲或不知如何休闲,而信息技术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缺,形成了信息技术主导的休闲现状。
1.全民休闲方式的趋同
2013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北京发布了《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该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64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42.1%;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4.2亿,较2011年底增加6 440万人;手机网民在总体网民中的比例进一步提高,达到74.5%,移动上网应用出现各种创新。此外,网络休闲的主要项目,包括网络音乐、网络新闻、即时通信、网络游戏、博客应用、网络视频、电子邮件、社交网站、网络文学、网络购物、论坛(BBS)的用户规模惊人,其中的论坛用户最少(超过1.49亿人),即时通信的用户最多(超过4.68亿人),新推出的微博用户达到了3.09亿人,使用手机收看视频的用户达到1.3亿人。
以上数据已经十分说明问题。以手机、互联网、数字电视等为平台的休闲方式,在城市人群和年轻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进而渗透进农村地区和儿童、老人这样的群体,人们开始习惯信息技术提供的休闲生活。这类休闲方式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全民参与性,每一类典型的休闲方式都具有上亿人的休闲主体参与,并成为各个群体典型的共同语言。例如,当你第一次尝试某个知名网络游戏时,你轻而易举地会在身边找到一群人来学习、探讨游戏的技巧。这类休闲方式可以说是当前“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和“快餐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其类型多样、体验丰富、吸引力强,不追求深刻性和内涵,并产生了明显的群体效应。为了融入某个群体或彰显前卫与时尚,后来者往往必须要接受相同的休闲方式并投入足够的金钱和精力,例如,要加入某个QQ群,或达到某个游戏等级。当然,农民工、蚁族等群体还在为生存而挣扎,没有足够的闲暇时间,甚至休息的时间都不够,他们无法沉迷于各类休闲活动,要求他们进行审美等高雅休闲活动也不现实。
2.传统休闲方式的衰落
整个社会出现了休闲的信息化、网络化、虚拟化,信息技术支持的手机、互联网、数字电视等成为了新型的、最为普及的、大众各阶层最喜好的休闲活动。信息技术不仅创造了更多的闲暇时间,而且创造了更多的廉价、方便、大众化、低门槛的休闲活动,使任何人都有可能参与进来,但它也使休闲活动向低水平、劣质、庸俗化方向发展。休闲单一化现象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单向度”的人,①相关内容参见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使人们丧失了反思、批判、创新的能力。
在信息技术主导的休闲活动占据优势地位的同时,传统休闲活动,如读报、看书、走亲访友、看戏、棋牌、收藏、养鱼、园艺、登山、健身、诗词、绘画、音乐等,无论高雅、通俗与否,都开始萎缩或局限于某些群体。这两类休闲活动没有表现出很好的互动关系,优秀的传统休闲活动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而是被替代。一方面,曾经热衷于传统休闲活动的人转向了信息技术主导的休闲活动,很多人每日耗费大量的时间用于网络游戏或整日冲着数字电视发呆。另一方面,“90后”等是在信息技术环境下成长的一代,从小习惯的就是信息技术主导的休闲活动,他们成年以后会对传统休闲活动有感情吗?他们有能力完成传统的休闲活动吗?
我们不得不感叹传统休闲活动、儒家休闲方式的衰落,实则是传统文化的衰落,那么多优秀的休闲活动只能成为遥远的记忆。人们更习惯于将休闲看作是“娱乐”,而不注重自己的修养。在信息技术的背景下,传统文化如何继承和发扬是需要关注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怀疑,休闲到底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3.休闲的异化
信息技术主导的休闲已经明显出现了“异化”现象。第一,信息技术本应是休闲的工具,却变为休闲的目的,明显而普遍地被误用。尤其是很多人沉迷于电视和网络,或一刻不停地使用手机的音乐、视频、聊天、上网等功能,并将这些当成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进而导致人格及心理问题。第二,各类违背休闲本质的伪休闲活动充斥于日常生活和网络中,包括暴力性网络游戏、网络色情、网络欺诈、网络暴力、网络炒作等,以及由此产生了芙蓉姐姐、凤姐、犀利哥等网络现象,这些都引发了社会信任、道德规范和传统价值观的弱化。第三,过度的这种休闲往往会影响身体健康,造成神经紧张和精神压力,引起肥胖、腰颈等疾病。
这些异化的背后原因是人们的精神世界出现了问题,人们需要在戏剧或网络的虚拟世界中,摆脱现实世界生活的不幸、困惑或焦虑,实现虚拟的价值和虚幻的满足。这种异化的结果致使人们不愿意走出家门,放弃了行走的能力,不愿意回到现实世界,甚至出现各类“问题”人群。信息技术主导的休闲过多、过滥,容易使人们的思维能力下降,无法直接观察世界,缺乏直觉和形象思维,创造力也必然随之下降。
4.信息技术背景下休闲活动的主导者
当信息技术主导的休闲活动越来越普及时,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其背后的原因,应该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廉价与便利;满足感;信息技术企业的推动。信息技术主导的休闲比一些传统休闲方式更便宜更便利,能带来后者无法提供的满足与成就感,信息技术企业的推动更是功不可没。目前,从城市到乡村,数字电视、手机、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应用覆盖广泛,成为现代生活的重要和必要组成部分。数字电视和节目供应商、手机厂商和销售商、互联网接入服务商和内容提供商等,通过大量的广告、促销活动和新技术的推广,使人们从最初拥有一个手机、数字电视或电脑,转变为沉浸于这些产品和技术中,并严重依赖于它们,甚至最终离不开它们。
因此,可以说多年来这些厂商不仅成功地卖出了产品和服务,更是成功地改变了人们的休闲,控制了人们的休闲生活,使人们不得不一直依赖他们,就像小孩子一旦吃到糖果就难以放弃一样。但如果人们放弃了人生本应体验的积极的休闲,那么休闲的意义和作用就将大大丧失。以网络游戏为例,盛大等企业在游戏的开发和宣传方面投资巨大,他们提供的游戏种类繁多,从居于主导的大型网络RPG游戏与对抗类游戏,到网络休闲类游戏,都在这些企业的掌控之中。“大众文化”曾被认为是平庸、异化、低劣的商业文化,基于信息技术的“大众文化”虽然给众多企业带来巨额商业回报,但却给大众造成了严重的误导。
五、信息技术对休闲的影响
1.对休闲时间和空间的影响
从休闲时间角度分析,首先,信息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人类的闲暇时间。其次,信息技术及其应用改变了以往对闲暇时间的理解。人们曾将全部时间划分为劳动时间、生活必需时间和自由时间,并认为休闲是发生在自由时间内。这种对时间的严格划分已经不适合今天的工作和休闲的划分,尤其是很多技术类和知识型的工作岗位,员工对信息技术的使用既有工作的内容,又有休闲的内容。例如,当员工在做输入文字或绘图工作时听着音乐、开着QQ聊天,就是典型的工作和休闲交织在一起,对于那些在网站、软件公司等信息技术企业工作的员工来说更是如此。
从休闲空间角度分析,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信息技术与交通技术等密切配合,扩大了人类的活动半径,人类的休闲空间也相应扩大。对于旅游者和出差人士等来说,不管在本地还是外地,他们都严重依赖手机、互联网和数字电视,他们时刻不离手机,没有互联网和数字电视的酒店房间则让他们很难接受,实际上他们一直进行着日常的休闲。对于那些“SOHO”(在家办公)一族、自由职业者等来说,工作和休闲可以灵活安排,可以在家工作、在家休闲,可以白天休闲、晚上工作,连工作场所和休闲场所都难以区分。
此外,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利用信息技术来学习,如电视、互联网中的教育和学习资源,也在进行信息和知识的创造与传播工作。这些虽发生在休闲时间内,但却为工作做足了准备,也可认为是工作的一部分,从而使工作与休闲更难划分。
信息技术的普及,改变了工业社会中劳动和休闲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完全分离。人们的劳动方式由集中化、标准化向分散化、多样化转变,人们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他们喜欢的休闲活动,从短信、通话、网络聊天直到网络购物、写微博等。人们在信息技术创造的信息世界和网络空间中,变成了“地球村”的村民。信息技术主导的休闲恰恰迎合了人们“即时休闲”、“匆忙消费”的心理,避免了时间稀缺对人们休闲造成的压力和束缚。因此,信息技术促进了劳动和休闲一体化,劳动与休闲的时间、空间界限变得十分模糊,劳动与休闲、本地与异地的休闲在趋同化。
2.对休闲主体的影响
信息技术不仅使休闲主体的人数大大增加,而且使他们的年龄、职业、阶层、地域等区别变得模糊,使休闲主体趋同化。信息技术的普及,使应用的门槛大大降低,对休闲主体的能力要求下降,傻瓜型、不需思考式的休闲活动很受欢迎。
对于休闲个体来说,信息技术极大地丰富了信息资源,增强了个体的信息器官的功能,提高了个体的认知能力,使个体获得了更高程度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从这个角度看,信息技术对于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共享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个体对于世界的认知更全面、更接近客观真实,极大地减轻了无知对个体的束缚。
个体也成为了信息传播和知识创造的重要环节。信息技术主导的休闲活动参与者——网友,通过博客、微博、论坛、邮件、短信等方式,不停地传播知识和信息。尤其是“维基百科”的模式,由网友共同贡献知识,形成“知识共同体”,这种模式使知识共享更加便利。在网络原创文学、博客写作、短信创作等活动中,网友、写手们极大地发挥了他们的聪敏才智,达到了精神的愉悦和自由状态。相应地,一系列网络用语、网络行为等逐渐形成,并渗透进入和影响现实世界。例如,“给力”一词的出现和传播就是网民的贡献。此外,博客、微博、论坛等使民间信息传播的通道更加顺畅,并导致官方博客、微博的出现。
信息技术使个体有能力更多地参与社会、经济等事务。例如,短信参与、邮件参与、网络讨论、在线调查等,这些成为官方了解民情的重要渠道。由于“匿名性”等特征,这种参与有时又表现出一定的休闲性,类似茶余饭后的闲谈、聊天、调侃、评论、围观等。这实质是将现实生活通过信息技术来再现或映像,从而达到某种情绪的释放。人们既可以充分地掩饰自我,也可以“浮出水面”以真实身份示人。因此,可以说网络休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充分地展现自我。
六、信息技术背景下休闲的理性回归
1.休闲的教育
当前,人们有了闲暇时间和休闲的条件,但滥用、误用闲暇时间的现象十分普遍,人们普遍感觉到:一闲下来就无所事事。纵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也很难表现出明显差异性,这是全民“休闲教育”或“闲暇教育”缺失的结果。年轻人接受的教育是应试教育,闲暇时间被人为剥夺,休闲方面的技能和品味不会获得加分和重视。而琴、棋、书、画等原本是普遍的休闲活动,演变为专业化的工作或只为了比赛。教育的缺失导致休闲技能的欠缺和对休闲理解的偏差,进而出现休闲活动的庸俗化。
关于休闲教育的含义,理解众多,但学者们和有识之士对于休闲教育的意义、作用和任务基本达成了一致。一般认为,休闲教育是关于闲暇时间利用方面的态度、观念、情趣和能力等方面的培养,旨在指导人们合理利用闲暇时间的自我发展式的教育。休闲教育更符合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理念,从这一角度看,休闲本身其实就是学习和教育。
在休闲教育过程中,重建当代人的价值观是最重要的,这个社会需要有更多的人关注、反思那些根本性的问题:人的本质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自身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人的幸福标准是什么?这些都将影响具体的休闲活动和方式,影响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和积淀。
2.政府部门和企业提供的休闲保障
从某种意义上说,信息技术主导的休闲之所以盛行,恐怕与民众缺乏选择关系重大,这就需要政府相关部门、企业和民间组织等发挥积极的作用,使民众能够找到可以替代的休闲活动和场所。
就政府相关部门来说,需要将民众的休闲作为一项权利来考虑和实施,提高民众的休闲能力,提供休闲的条件。就城市来说,在城市规划之时,需要考虑城市的休闲功能设计,预留足够的休闲空间,包括住宅小区中的休闲空间、市民活动的广场和绿地、城郊的休闲地带等。简单地说,应该是宜居、宜休闲的城市。近年来,有若干城市被评为“休闲城市”,但对于生活在其中的普通民众而言,如果终日为生活而奔波,又如何能休闲呢?“休闲”不应只成为一种标签或旅游宣传口号,而应是居于此地民众的切身感触。如此说来,休闲已经是个民生问题了。近年来,各地的一些公园、博物馆等陆续免费开放,一些旅游部门派发了景点代金券,这是向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值得我们更多的期待。
就企业来说,不管是信息技术相关企业,还是属于休闲产业的企业,都有休闲教育的责任,都有提供符合社会伦理标准的休闲产品和服务的责任,都应使民众自由、快乐而健康地享受生活。对于暴力性网络游戏、网络色情、网络欺诈、网络暴力、网络炒作等问题,信息技术相关企业应该着力解决而不是为虎作伥。以电信企业为例,他们不停地推出各种花样产品和套餐,拿着巨额利润,却对短信欺诈、电话欺诈、垃圾短息、电信消费陷阱等行为不作为、不尽力。那些休闲产业的企业,如剧院、酒吧、茶馆、电影院、度假村、旅游景区等,也需要引导民众的正确休闲,提供普通民众能够接受和喜爱的多样化的休闲活动和服务,引导民众了解社会、体验生活,实现自我提升。
3.民间组织的休闲推广
各类民间组织(NGO)等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各类环保组织、户外活动俱乐部(如登山、探险、漂流、露营、骑马)、各类协会(如观鸟、钓鱼、游泳、书法、诗歌、绘画)等。这些民间组织的出现和发展壮大,说明了民众对各类积极休闲的真心热爱。以一些协会为例,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起到了积极作用,代替了家庭和学校教育的欠缺。在他们组织的各类活动中,不管是体验自然、保护环境,还是修身养性、学习技艺,参与者都得到了自由、快乐,实现了自我价值。他们聚集了大量的参与者和爱好者,推广了各种积极的休闲活动和理念,极大地提升了休闲活动的专业化和组织化程度,应该说对于休闲的发展贡献很大。因此,可以说此类休闲更符合休闲的本质,更适合进行推广。
七、结语
休闲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信息技术主导的休闲是基于信息技术的人际互动或人机互动。信息技术创造了新型的休闲方式,又使一些传统休闲方式实现了信息化。信息技术让休闲方式更加灵活、自由,使个体更容易达到休闲的状态。
在信息技术主导的背景下,出现了全民性的共同休闲方式和休闲的异化,传统休闲方式出现了衰落,信息技术企业应对此结果负有责任。信息技术增加了人类的休闲时间,劳动与休闲的时间、空间界限变得模糊,劳动与休闲、本地与异地的休闲在趋同化。信息技术极大地丰富了信息资源,提高了个体的认知能力,个体成为了信息传播和知识创造的重要环节,个体获得了更高程度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信息技术主导的休闲既有超越传统休闲的一面,又需要向传统休闲回归,最终实现两者的平衡,这实质是科技与人文的统一,这需要政府相关部门、信息技术相关企业和属于休闲产业的企业、各类民间组织等共同努力。
[1]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M].梅 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2]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黄明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4]马惠娣.休闲: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5]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6]托马斯·古德尔,杰弗瑞·戈比.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M].成素梅,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7]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M].康 筝,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