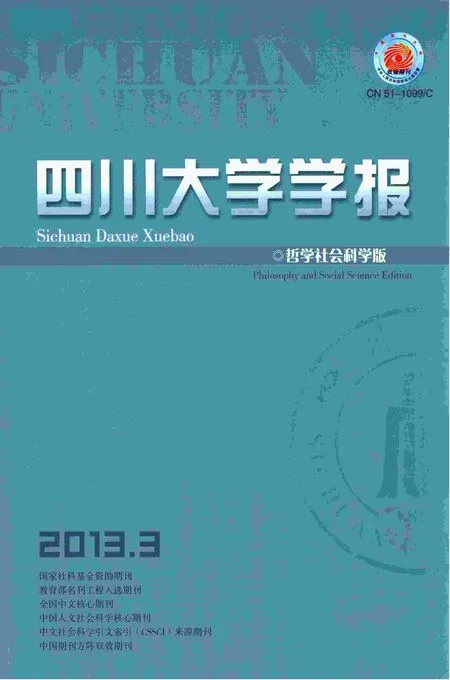新事实与旧理论①:梁漱溟后期政治思想(1949—1988)初探
吴景键
(北京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00)
梁漱溟是一位始终从实践出发、旨在面对现实的“中国问题”的思想家。因此,中国社会在1949年以后翻天覆地的变化势必将会给他的思想带来极大的冲击,促使他重新思考原有的论断,在理论层面对于当前的这些变化有所回应。可另一方面,梁漱溟又是一位极其“固执”的思想家,他绝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见解,而是要努力在现实的逼问与自己的想法之间寻找到一种贯通和平衡,正如他自己所说:“到今天,共产党这条路算是大有成功希望,而我所设想者似乎已经证明不对。但是否真当如此呢?一个真正用过心来的人,是不能随便就承认,随便就否认的。”②《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319 页。而这种思想的紧张性又最集中地体现在两点——阶级理论与人心理论。
就前者而言,梁漱溟与中国共产党当初在阶级理论上的分途最终导致两方分别选择了乡村建设与阶级斗争的道路。可如今,在他看来只有“职业分途”而无“阶级对立”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策略却取得了成功,并且通过他原先在乡建实践中所反对的苏俄道路使中国农村的力量凝聚起来,完成了他所未曾实现的目标。就后者而言,他一直努力昭苏而不得的中国人“人生向上”的心态,却被坚持唯物主义的共产党所实现,全国上下仿佛精神焕发,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正是在这两重张力之下,梁漱溟开始尝试将自己的政治思想与新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之间进行对接,或者更加简练地说,将中国的新事实与自己的旧理论之间进行对接。
毫无疑问,这样的一种对接是复杂的——它既包含梁漱溟自己“人心理论”的“内圣”,又兼备社会主义实践的“外王”;既容纳梁漱溟对“职业分途”的坚守,又不跳脱阶级斗争的思维范式。可恰是这种复杂却又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建国后长期以来中国思想界的现实处境。
然而,在笔者目前所见到的相关著作中,对于梁漱溟后期政治思想有较多涉及的仅有郑大华所著《梁漱溟传》,景海峰、黎业明所著《梁漱溟评传》,刘克敌所著《梁漱溟的最后39年》与梁漱溟之子梁培恕所著《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记父亲梁漱溟》这四种。而这四本又无一例外都是以作传为主,只对其后期思想做了一番大致的梳理,并没有很系统的论述。
因此,本文的宗旨便在于以文本为基础,较细致地厘清梁漱溟后期政治思想的两条脉络,一方面还原梁漱溟后期政治思想的本来面貌,另一方面也为我们今日的思考提供一个线索。
一、阶级理论:转变——回归
“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二千年。根据这种分析,我又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大字。”①梁漱溟回忆与毛泽东第一次延安谈话,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63 页。梁漱溟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认识,核心可以归纳为“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字。其中,“伦理本位”自是针对西方的“个人本位”而来。而“职业分途”对应的则是沉浸于革命语境数十年的中国人所最熟悉的一个概念——“阶级对立”。
早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梁漱溟就提出中国不存在明显的阶级对立,并进而否认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建立国家权力。②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2-87 页。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梁漱溟才选择了以伦理为基础的乡村建设道路。而在之后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梁漱溟结合自身体会与李景汉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中的调查结果进一步阐述了自己“中国缺乏阶级对立”的观点。③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24-139 页。
不仅在理论上作此坚持,梁漱溟甚至还将这种观点反映到了他建国前的政治活动上,正如他自己晚年所回忆:“一旦看见中共倡导抗战而放弃国内斗争(我则笼统以为放弃阶级斗争);便只身奔赴延安,而后奔走团结,争取和平,前后八年不敢惜力;而一待和平无望,即拔脚走开,三年不出。”④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第123 页。然而,也正如梁漱溟建国前政治活动的一波三折所映射出的那样,梁漱溟因“中国缺乏阶级对立”的观点而在建国前始终与坚持阶级斗争理论的中国共产党在思想认识上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⑤笔者以为,建国后梁漱溟延时进京、婉拒进入中央政府任职的邀请或都与此有一定关系。两者在观点上的冲突先是体现在1938年毛、梁首次延安谈话的彻夜争论上,⑥梁漱溟自己回忆说,“其中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毛泽东是强调这点,很突出它的作用的。我们发生了争论……两人相持不下,谁也没有说服谁”。见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第63-64 页。但在当时“抗日”这一宏大主题的笼罩下,这一冲突尚得以被稀释,处于一种隐性状态。而随着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成功与之后一系列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接踵而至,这种冲突便显现出了其内在的巨大张力。一面是坚持阶级斗争理论的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上取得的巨大成功(新事实),另一面则是梁漱溟自己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坚定判断(旧理论)。此时,作为公共人物的梁漱溟又无法通过沉默来消解掉这重张力。于是,梁漱溟便不得不开始对于自己的阶级理论进行一番重新建构,以求能够实现新事实与旧理论之间的贯通。而本节所要探讨的正是梁漱溟重构自己阶级理论的这一过程。
具体来看,梁漱溟的阶级理论可以分为两大部分,⑦这实际是梁漱溟自己在《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一文中所总结的。《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874 页。一是如何“以阶级眼光观察中国社会”,包括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认识与对中国近现代阶级形势的认识;二是能否“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如果能的话,又会涉及到阶级斗争中谁为领导阶级与是否采取暴力手段的问题。下面,笔者便分阶段来概述建国后梁漱溟的阶级理论在这几个部分上的变化。
(1)1949年10月—1953年9月于中央政府会议上被批判前。此阶段中,梁漱溟仍然没有放弃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坚持认为中国社会缺乏阶级对立,在本质上与西方诸国不同。但与此同时,面对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一向从事实出发的梁漱溟也渐渐开始承认,中国社会亦有其可适用于阶级理论的一般性,即使在阶级形势上较为缺乏,但也可以被国际形势所弥补,原先较为薄弱、分散的无产阶级力量也可以通过武装斗争的形式逐步凝聚起来,成为国内阶级斗争的领导主体。因此,他最终在不放弃“中国社会缺乏阶级对立”这一论断的基础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以阶级斗争来建国的理论。
(2)1953年9月—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前。此阶段中,梁漱溟出于种种原因不再强调自己原先所坚持的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只是单方面检讨过去囿于自己的阶级立场忽视了阶级理论的一般性,似乎已经完全接受了正统的阶级理论。但不容忽视的是,梁漱溟对阶级斗争的认同始终是工具性、阶段性的,而且,思想重心从入世逐步转向出世的梁漱溟在此时也仍保持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与自己的佛家信仰,而这三点其实正为梁漱溟之后在阶级理论上的回归埋下了伏笔。
(3)“批林批孔”运动—1988年6月。此阶段中,经过了数年思考的梁漱溟又重新表现出了对于其早先阶级理论的自信,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为孔子辩护的同时,也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有所申张,显现出向其早期阶级理论回归的趋势。而到了文革结束以后,梁漱溟在阶级理论上的这一回归最终彻底完成。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建国后梁漱溟在阶级理论上其实存在着一个“转变——回归”的过程。在下文中,笔者便分阶段具体阐述梁漱溟1949年以后在阶级理论上的变化。
1949年10月—1953年9月。1950年10月到1951年5月,刚刚参观完土改工作的梁漱溟创作出《中国建国之路》一文,这可以视为梁漱溟后期政治思想理论化表述的起始点。此文虽仅有弁言和上篇两部分,但犹可发现不少关于阶级理论的论述,首先看其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认识:“一个国家大体总是统治兼剥削阶级与被统治兼被剥削阶级之两面相对。我们说中国缺乏阶级,主要是说它化整为零,形势分散,未曾构成相对之两面。”可见,此时梁漱溟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认识仍与在《中国文化要义》中的认识相同。那么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坚持阶级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又是如何走出一条“建国之路”的呢?文中说:“我们没有现成合用的一阶级可为武力主体,我们自己便制造一代替品——针对着那所需两条件制造出一‘准阶级’。”①《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330、336 页。这无疑是梁漱溟为了弥合自己“中国缺乏阶级对立”的观点与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实践之间的巨大缝隙而提出的一个创造性解释,而其后所作诸文中,梁漱溟的大多努力便在于反复论证这一“准阶级”何以诞生。
1951年5月到8月,梁漱溟在四川西南土改工作第一团期间,曾说道:“去年我在山东河南以及东北各省区参观,引起我在中国问题的认识上自己作了检讨,而此次参加西南土改工作之结果,就使得这一思想转变得到决定。”②《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864 页。而这一思想转变③在1958年政协整风小组的发言上,梁漱溟说到,“大致从1951年下半年起,在意识上自己否定了旧观点,承认中国共产党毕竟是对了,阶级社会的一般规律也还在中国起着作用”,可见这里所说的转变确实不假。详见《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46 页。是什么呢?便是认定了中国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为何见出无产阶级领导有理呢?须知我原来所见没有错,只是‘知其一,未知其二’。中国诚然缺乏阶级形势,但此形势却由世界形势补充、作背景之下,而有其大形势可见,不可躲闪。国内国外,合为一大形势而分成两面,逼出武装斗争,决一死战。”④《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865 页。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此时的梁漱溟虽仍执着于“中国缺乏阶级对立”的观点,却引入了国际形势补充国内阶级形势的说法来解释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准阶级”的诞生与最终胜利。在他看来,在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大形势下,中国内部的阶级斗争定能被逼出来,而一旦有了这样一个阶级斗争的形势,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斗争策略便具备了现实基础,其最后的成功也就不难理解。事实上,这样的一种解释正构成了梁漱溟这一阶段一系列相关文章的最基本脉络,即“中国缺乏阶级形势——国际形势补充国内形势——国内阶级对立彰显——共产党采取正确的阶级斗争策略从而最终取得成功”。换句话说,就是先将一个弱阶级形势的中国社会利用国际形势加以“阶级化”,其后再以阶级斗争的方法处理它。
1951年10月,梁漱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长文《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这里的“转变”核心便是在阶级理论上的转变,如梁漱溟自己所说:“我过去一直不同意他们以阶级眼光观察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而现在所谓得到修改者亦即在此。”转变的结果呢?便是“觉悟到尽管中国社会有其缺乏阶级的事实,仍然要本着阶级观点来把握它,才有办法”。其中,“尽管中国社会有其缺乏阶级的事实”反映的自是梁漱溟一直以来的观点,而“仍然要本着阶级观点来把握它”却表明了梁漱溟建国后在阶级理论上的转变。从静态来看,中国社会固然是缺乏两面对立的,但是,“在整个世界正从阶级立场分成两大阵营而决斗的今天,其势必然要把中国社会亦扯裂到两边去”,“既然客观形势上中国不可免地要卷入世界漩涡,而终必出于阶级斗争之一途,那么,阶级斗争便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可是,在这样一个梁漱溟看来无产阶级力量薄弱的社会里,代表无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又如何领导得起阶级斗争呢?显然,这又是一个梁漱溟所需弥合的旧理论与新事实间的缝隙。对此,梁漱溟认为,“尽管其人并非无产阶级,而看清了中国革命要如此,还是可以学着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作无产阶级之事的”,就是说,一个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也是可以“无产阶级化”的。而中国共产党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在梁漱溟看来便是暴力革命,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个人的阶级情感才能被铸造出来,“不这样,那完成中国革命的力量便无从培养起来”。①《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874、876、880、881、886 页。
1952年5月,梁漱溟又写出《我的努力与反省》一文,对自己过去的政治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在这篇文章中,除去之前已经反复提到的国际形势对国内阶级形势的补充外,梁漱溟还借用矛盾论的观点,重点反思了自己在过去只看重中国社会缺乏阶级对立的一面,而疏忽了国内社会本身所隐含的阶级本质:“中国社会是不是缺乏阶级,自1911年后是不是没有秩序,本都可以从两面来看,而且几十年中亦何能一概而论。但我总是从一面——缺乏或没有——来强调,总不免一概而论”,“遇到缺乏阶级的社会,依然可以承认其事实;仅承认其有所缺乏,并不曾轻忽其阶级本质。要必在不否认其缺乏阶级之中而把握其多少有阶级一面,然后才有办法能解决社会问题”。“社会生产上剥削被剥削那种阶级矛盾是看轻不得的。在时间上这是人类历史转变发展的线索所在,在空间上则能从这里串联都任何角落”,这些话语诚然在极大程度上反映了梁漱溟此阶段在阶级理论上的转变。但我认为,跋语中的一句话却又暴露了梁漱溟内心深处的某种坚守。“此文最大的缺点即在今天批判自己的话还没有自己讲明过去如何用心思的话多。属文之时未尝不一再删节,而删节下来犹且如是,可见胸中求为人知之念多于其自惭自悔之念”。那求为人知者为何呢?从全文内容来看,梁漱溟以反省的口吻讲得最多的便是自己“中国缺乏阶级对立”的观点。事实上,在全文的一开头,梁漱溟就曾指出,对于“秦汉后的中国没有构成阶级统治”、“中国革命是从外引发的”这两点,他“至今不放弃原有意见”。由此可见,在与正统阶级理论逐步靠拢的同时,梁漱溟心中始终还是萦绕着自己长期以来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认识。在肯定阶级斗争道路的同时,也不全盘否定掉自己原有的观点,而是力求“在原来基础上建立起新见解”。②《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1017、1020、1027、1030、968、902 页。
1953年9月—1974年2月。1953年9月梁漱溟与毛泽东在中央政府会议上的那次争辩到今日已经成为一桩历史公案,此处暂不赘述。本文关注的是,这一次争论对于梁漱溟后期政治思想的重大影响。从此事件之后,到1974年被卷入“批林批孔”运动之前,梁漱溟进入了自己政治上的噤声期,很少公开发表不同意见,在阶级理论上也一律以自我批判为主,很少再像以前一样对于自己“中国缺乏阶级对立”的认识予以公开肯定。③如梁漱溟1956年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1958年在政协整风小组会上的发言以及关于《矛盾论》的两篇、学习心得等。详见《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26-32、33-55、216-217、218-223 页。在我看来,这主要有两点原因。
一是面对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再这样争下去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结果已经摆在那里了,正如梁漱溟自己所说,在事实面前已经“不服自服”。④《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48 页。而且,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确实也动摇了梁漱溟对自己观点的自信。⑤梁漱溟自己说到,“不过不那样自信了”。详见《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34 页。同时,梁漱溟在这一年的日记最后也曾写下“旧时代的残余”、“你这一辈子作过什么好事”这样的话语。见《梁漱溟全集》(第八卷),第512 页。对此,梁漱溟次子梁培恕曾举出过一个很切实的事例来证明其“父亲此时感觉到的精神、情感压力有多么大”,并且,这样一种压力“普遍和持久,而且不是经过加工的”。①梁漱溟去给脾气极好的二婶拜寿,但其二婶却因知其“一贯反动”而对其爱搭不理,这对家族观念很重的梁漱溟产生了很大影响。详见梁培恕:《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记父亲梁漱溟》,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74 页。因此,在这一阶段中,梁漱溟对自己的阶级立场曾进行了多次真诚的检讨,就中国古代社会的阶级定性也不再发表异议。
而较容易被忽视的另一个原因则是梁漱溟此时感觉到自己的异议有违背佛家讲求的“无对”之处。梁漱溟长期有记日记的习惯,在1953年9月11日与毛泽东的那次“廷争面折”后,在梁漱溟的日记中有了以下内容:“忽悟菩萨止于悲之理(如为人子止于孝之‘止’),在儒则只有一片恻隐之心,悲与所悲似相对之两面,然所悲一切众生,自己亦在内,且超于利用与反抗,既是无对。无对而有对,有对而无对。动亦定,静亦定。永不落被动而恒时时主动,换言之,始终有心在。气动即失心,心在则气为心用。” (9月20日)②《梁漱溟全集》(第八卷),第503-504 页。我在阅读梁漱溟的日记过程中还发现,1953年9月以后,梁漱溟阅读佛经的时间大量增加,这或许也是其开始自我反思的一个佐证。可见,梁漱溟在事后一直告诫自己要保持“无对”的状态,不要陷入与别人的对抗之中。因此,对于1953年事件后梁漱溟在政治上的沉默,我们不应当简单地将其视为一种政治上的自我隔离,也应看到其中他对于自己“气动即失心”的自责成分。
而在梁漱溟去世之前对台湾《世界日报》关于1953年公案的询问的口授复函中,我们也可发现类似的证据:“然于激烈争执后,突憬然醒悟自己已落入意气用事……我既省察到自己有杂念,自当不隐瞒,由是在自己思想上对这一错误有检讨之意。中国古人有‘反求诸己’的教导,身体力行此教导全在个人自觉,我省悟及此,也是自觉自愿,认错并非向争执的对方认错。”③梁培恕:《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记父亲梁漱溟》,第279 页。可见,梁漱溟的沉默确有“反求诸己”般的自我反思的成分。他不再就阶级理论等政治问题发表任何不同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担心自己的意见中掺杂了太多诸如个人意气这样的杂念,④李维汉在批判会上曾指出“你今天上午在家里还对人说要和我们决一胜负”,而梁漱溟一听见这句话,就突然冷静下来,觉悟到自己落入意气之争。详见梁培恕:《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记父亲梁漱溟》,第272 页。自以为是心怀天下,而实际上却是在逞一己之能。正如他之后自己所承认的那样:“现在明白自己受病所在,正在这一向以大心大愿自居。”⑤《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51 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中,梁漱溟虽然不再公开表示在阶级理论上的异议,但是,从下述三个方面我们也能预感到其在下一阶段中会出现阶级理论上的回归。
一是梁漱溟虽然接受了以阶级斗争建国的方式,但却始终认为阶级斗争只具有阶段性和工具性,他的真正认同是建立在阶级斗争所要达到的消泯阶级的目标之上。
1964年,在全国政协组织政协委员到山西农村参观“社教”,让众委员谈观感时,梁漱溟便借用恩格斯著名的“自由王国”理论,表达出其阶级理论的真正重点在于消泯人类间的斗争,而共同开始向自然界作斗争。在晚年接受汪东林的访问时,他也曾就建国后是否还要开展阶级斗争的问题回忆到:“但往后呢?是不是还有一个阶级斗争接着一个阶级斗争地搞下去呢?我说不清楚,但我的内心是希望不要一个接着一个,与其多,不如少;与其有,不如没有。”⑥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第162、150 页。显然,在此阶段中,他对于阶级斗争的认同是建立在其目标之上,而并非是“斗争”本身。否则他也不会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时,在日记中特别称赞“毛公可谓贤矣”。⑦《梁漱溟全集》(第八卷),第592 页。正因此,一旦梁漱溟发现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似乎永无终止的趋势后,他定然会对该理论产生怀疑,并进而向其早先的阶级理论回归。
二是梁漱溟既已认识到“国事已上轨道,我无所用其力”,⑧《梁漱溟全集》(第八卷),第558 页。便转而从学理上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实践间的关联问题,而这一过程势必又会坚固一些他对于中国社会特殊性的认识,最为明显的体现便是梁漱溟此阶段创作但未发表的《中国——理性之国》一文。在此文中,梁漱溟指出,中国古代的大儒们虽多出身于统治阶级,但无论从利的角度还是力的角度来看,都大异乎一般统治阶级的立场,往往是站在一种人类立场上思考问题,而这也使得梁漱溟认为,阶级对立的形势“非止不会见于往古中国,抑且永不会冒出于中国社会内”。①《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388 页。
三是梁漱溟此阶段始终没有放弃掉自己的佛家信仰,正如他自己检讨的那样,“改造不了的就是佛家出世思想”。而“佛家以贪、嗔、痴为‘三毒’、‘根本惑’”,阶级仇恨作为一种嗔恚心理自然很难被笃佛的梁漱溟所真正接受。②《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37、120 页。
综合这三点,梁漱溟下一阶段在阶级理论上的回归便也显得不难理解。
1974年2月—1988年。众所周知,1974年的“批林批孔”风波使梁漱溟又重新回到政治舞台。而一旦再度入世,梁漱溟的阶级理论就立马出现了向其早先阶级理论的回转。显然,经过文革中长时间的思考与以上因素的影响,梁漱溟对自己早先的阶级理论又恢复了自信。③梁漱溟晚年自己也回忆到,“多年之后,夙性独立思考的我,渐渐恢复了自信”。详见《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521 页。在1974年2月完稿的《试论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一文中,梁漱溟再次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中国社会特殊论,反对在中国适用正统阶级史观所采用的五分法,主张中国社会属于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存在明显的阶级对立。而在6月完稿的《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文中,梁漱溟指出,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结构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相互影响,最终造成中国阶级对立不明显的形势:“古中国从社会经济上不能不由劳心劳力的阶级分化,却其分化不那么谿刻僵凝,其阶级立场之矛盾对立就不甚。加以其间优秀特出分子更发挥其通而不隔之心,在因袭中有创造,以化导乎众人,这便成为卓然有异于世界各方的中国文化。” “指其表见在社会结构间者,则在其社会阶级非固定成形,而是贵贱贫富上下流转相通,不合于阶级社会通例的孔孟之道,所以出现在此。它既是阶级不固定之果,更重要的是阶级不固定之因”。④《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246-269、308 页。此外,在1975年致友人王星贤的信中,他也写到:“中国缺乏阶级,厌弃斗争,如我所说是散漫而和平的社会,我们的感情当然与列宁异趣。”⑤《梁漱溟全集》(第八卷),第147 页。在当时的语境下,说出“当然与列宁异趣”这样的话无疑具有很大的风险,而这恰也证明了在这一阶段中梁漱溟对自己的认识有着多么坚定的信心。⑥在1976年4月致田慕周的信中,梁漱溟写到,“我的著作将为世界文化开新纪元。其期不在远,不出数十年也。以我自信力之强,讵有所谓消极、积极乎?笑话!笑话!”足见其对于自己理论的自信业已恢复到建国前的程度。详见《梁漱溟全集》(第八卷),第187 页。
文革尚未结束时已是如此。文革结束之后,梁漱溟在阶级理论上的回归更是明显。1977年2月,梁漱溟写出《我致力乡村运动的回忆和反省》一文,公开表示对中国社会结构特殊性的坚持:“具有数千年传统文化的中国社会之特殊性一面,卒必将显现出来。”“无产阶级专政是它翻身起来压资产阶级而专其政;在散散漫漫原乏两大阶级相对形势的中国,只能一时借用之,或为引申譬喻而用之。”而对自己早先的阶级理论,梁漱溟不再加以批判,而只是认为“失之所想深奥”、“失之太早”。⑦《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427、428 页。
随着思想界环境的进一步宽松,1982年1月,梁漱溟又在香港发表了《试说明毛泽东晚年许多过错的根源》一文,非常明确地对阶级斗争理论表达了异议,痛心疾首地指出:“此地果真有阶级对峙,自然就有阶级斗争,避免不得,何须叫喊千万不要忘记呢?这显然在加工制造阶级斗争,逞其主观谬想,荒唐错乱,可笑亦复可哀!” “既然中国社会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了,缺乏敌对的两大阶级了,却为何强要无风起浪,制造阶级斗争”?⑧《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521 页。而越到晚年,梁漱溟的这种阶级理论上的回归就越为明显,直到最后,“阶级”二字甚至都基本淡出了他的话语体系。经过30 余年的曲折过程,梁漱溟最终还是回归到了其早期的阶级理论上。
二、“人心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
除却“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观,梁漱溟政治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便是他的“人心理论”。无论是从最初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还是到后来的《中国文化要义》及《乡村建设理论》,无论是使用“直觉”还是“理性”,梁漱溟始终强调中国人“心”相对于“身”的发育不对称,认为中国人对“心”的重视远远超过对“身”的重视,并以此引出了中国人的“文化早熟”特征。在他看来,中国文化的得失皆在于此,得之在“熟”,失之在“早”。①郭齐勇、龚建平:《梁漱溟哲学思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5 页。而“早”已经成为历史定局,无法推倒重来,因此只能在吸收西方先进之处基础上充分发扬自己的“熟”,也就是发扬人心。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梁漱溟就特别强调这个组织“人生向上”的精神特点。故了解梁漱溟的政治思想,就不能不关注他对政治中“人心”作用的强调。与梁漱溟的“职业分途”学说一样,其“人心理论”在建国后同样受到了唯物主义的挑战,在大量的社会主义实践成就面前面临着解释上的困境。而梁漱溟1949年以后所著《中国建国之路(论中国共产党并检讨我自己)》、《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试说建国十年一切建设突飞猛进的由来》及《中国——理性之国》三篇长文,正是对如何将自己的“人心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贯通的一次尝试性回答。
首先看创作于1950年10月到1951年5月的《中国建国之路(论中国共产党并检讨我自己)》一文,特别是其中的第三章——“透出了人心”。单从章节的名字来看,我们或许就已经能感受到一种鲜明的梁氏色彩,但是也确实会如他所说:“‘透出了人心’这一题目,读者看了亦许惊讶不解我在说什么。”那么,中共的建国与他的“人心”理论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妨看看他自己的说法。在文章的开头,他首先解释了他所指的“人心”到底是什么。“他(罗素)曾把人类行为划归两大来源:一是占有冲动;又一是创造冲动。我这里之所谓‘人心’,亦可以说就是他的创造冲动罢。创造冲动与占有冲动怎么分别?凡是要从外面取得什么东西到自己这里来,就是占有冲动。而创造冲动呢,恰似自己力气有余,不是在想要东西,却是在想要干什么。一切有所创造或贡献于世的人物,正为他衷心富于这种创造冲动。”正如引文中所述,梁漱溟所指的“人心”就是罗素在《社会改造原理》一书中所使用的“创造冲动”。而能否发挥人的这种“创造冲动”,也就是能否发扬人心,便成为了梁漱溟衡量一个政治体制价值的重要标准。那么中共的社会主义实践能不能发扬这种人心呢?梁漱溟是这样看的:“但今天我的路没走通,而共产党的救国建国运动却有成效见于世——特别是见出了人心的透达流行渐有其新路道,人的生命之相联相通渐有其新路道,大致可解答我夙日的问题。”显然,梁漱溟认为中共的社会主义实是开辟了一条可以发扬人心的路道。那这又是一条怎样的路道呢?在梁漱溟看来,就是构建一种有理想的团体生活:“理想的团体生活就是一面其团体既很能负责为分子解决问题,而一面其分子之自觉主动性又很高的那一种。现在他们引进团体生活其方针所指正在此……那种生活,用我的话来说,那正是要把身一面的问题(个体生存问题)基本上交代给团体去解决,而使各个人的心得以从容透达出来。”“总而言之,身的问题解决了,心乃透出”。②《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365、383、384、385 页。从上述引文我们可以看出,在梁漱溟眼里,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其通过团体生活的构建解决了“身”的问题,最大程度地把人心的力量释放出来,才取得了如今这般的成就。因此,对于中共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认同在梁漱溟这里绝对不是对于自己政治思想的否定,相反,恰恰是对自己“发扬人心”理论的再度强化与证明。由此,我们也已不难推出梁漱溟因何会对之后的大跃进持肯定态度了。
下面我们便具体分析一下梁漱溟对于大跃进的看法,这主要见于《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试说建国十年一切建设突飞猛进的由来》一文。此文虽然名曰“试说建国十年一切建设突飞猛进的由来”,可实际上所引事例基本都发生在1957—1958年,由此我们基本可以说,此文提到的“突飞猛进”其实就是指大跃进。正如这篇文章的名字一样,在梁漱溟眼中,大跃进正是“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越是其“大”,越能为“人心的力量”增一分例证,因此他才对此持肯定态度。
在这篇文章中,梁漱溟首先指出,人类创造力的发挥(也就是人心的发扬)是自然而然的,但也常常受到阻碍,而其中最大的阻碍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从过去历史以至今天世界上看,人类创造力的发挥表现正受到重重说不尽的阻碍和埋没……问题恰出在人们自己身上。这就是人们的活动远未能时时都从人类这大立场出发,共同对大自然作斗争,而却有数说不尽的斗争或明或暗起于人与人之间”。①《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420 页。此时,我们若再反观前文对于梁漱溟的阶级理论的论述,我们或许也就不难明白梁漱溟为何对阶级斗争理论只做工具性的理解了。在梁漱溟看来,中共一方面通过团体生活的构建去除了人类创造力的阻碍,另一方面又通过宣传大大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依靠集中领导与统一规划将这种积极性与创造性合到了一处。因此,在这种人心得到最大程度发扬的情况下,大跃进的实现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文中,梁漱溟还举了很多例子以证明大跃进中人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工业方面,如“两参、一改、三结合”、“两条腿走路”、“土洋结合”、“大中小结合”;农业方面,如“种试验田”、“开现场会”和“五定”以及运输车子化、车子滚珠轴承化;商业方面,如突破在“购、销、调、存、赚”五个字上兜圈子等等。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长达六万字的文章中,梁漱溟却恰恰没有提到大跃进时期两个最具有代表性的现象——“大炼钢铁”与“高产卫星”。②此处主要得益于梁培恕先生的总结归纳。见梁培恕:《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记父亲梁漱溟》,第325 页。
在我看来,这种忽略是有一定原因的。一方面,他确实坚信人心的巨大作用并兴奋于为他的理论找到了一些现实的例证,正如他的次子梁培恕所回忆的:“政协学习会时常请劳动模范、学习毛选积极分子给委员们讲自己的事迹。每次听了回来都会高兴许久,多次转述给我听,不仅说,还要比画。如此不寻常的高兴,其实还不限于因为建设突飞猛进,是来自一个我当时不甚了然但现在完全懂了的缘故——劳模们的事迹证明人心在什么情况下特别开窍。”但是另一方面,梁漱溟又是一个绝对求真的人,他所引用的这些事例虽或多或少有些夸大,但基本上都是真事,也确实曾对生产有过帮助。但对于“大炼钢铁”及“高产卫星”,虽然更可为他的“发扬人心”理论提供证明,他却拒绝在文章中引用,或许正是因为他看出了其中的些许蹊跷。③梁漱溟曾有一次向山东郓城县委书记询问“丰产不丰收”的情况,从中便可看出他对于“高产卫星”应该抱有一定怀疑。详见梁培恕:《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记父亲梁漱溟》,第320、319 页。
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梁漱溟之于大跃进的认同从本质上是有别于其他许多在当时鼓吹大跃进的知识分子的。这便是一个“真”字。梁漱溟对大跃进的认同完全是基于其自己的“发扬人心”的理论,是其经过认真思考后得出的结果,而不是时代思潮裹挟的产物,正如他在跋记中所说:“胸中萦回往来者自有其一套见解;有意无意之间辄以己见作说明。”④《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520-521 页。否则,若是套用当时“流行”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不断革命”等理论来解释,一篇六万字的文章何须写上两年时间?正是其力求以自己的思想解释这眼前的状况,这篇文章才会拖上这多时日。
最后,我们再从《中国——理性之国》一文看看梁漱溟又何以会认同文革,特别是文革中的“反修防修”运动。
首先,我们或许要解一解这个题目,因为给文革这样一个疯狂的年代冠上一个“理性”着实显得有些奇怪。那么到底什么才是梁漱溟眼中的“理性”呢?此处暂借用一下郭齐勇先生的解释:“对于理性,梁漱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理性当然并非西方传统哲学中的‘理性’……理性是梁漱溟自青年时代以来一直在寻找的自己行为的‘主见’。理性是一种心思作用,是力图在生活中寻找自己行为准则的心思作用。”⑤郭齐勇、龚建平:《梁漱溟哲学思想》,第119 页。如果按照郭齐勇先生的说法把“理性”解释为一种“心思作用”的话,我们或许对于这个题目便能了解一二了,因为这其实与梁漱溟之前的两篇文章的重点是一致的——人心。而与前两篇不同的是,这篇文章又为这个重点添加了一个比较对象——俄国。
在他看来,中国与俄国同样没有明确经历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历史阶段,但中国的社会主义始终坚稳前进,而俄国却出现了“资产阶级复辟”、“修正主义风靡”,这其中的关键点就在这人心(或是说中国人“理性早启”的特征)上。他认为:“毛主席之领导革命最重视人的因素,从来就是抓紧人的思想(世界观)改造,这却为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后所少见或不见。”“中苏在社会发展史上,缺乏近代西欧资本社会那一段经历虽若相同,但中国人头脑心思自古较少蔽塞于宗教,社会构成于家族而缺乏集团组织,个体生命从来不乏自由活动机会,却甚不同……此一不同则与吾人理性早启、历史绵长、文化深厚,为不可分之一事”。然而,中国人虽然理性早启,却也不可不提防着“苏修”对人心的影响,需要“反对修正主义于外,防止修正主义于内”,“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而这便导致了梁漱溟对于“反修防修”运动的支持以及最终对于文革的肯定,①《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455、456、216、285 页。如其在1966年致中央文革并转毛泽东的信中所说:“主席此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广大群众振起向上精神,鄙视资产阶级,耻笑修正主义,实为吾人渡入无阶级的共产社会之所必要。”②《梁漱溟全集》(第八卷),第79 页。显然,梁漱溟始终是从人心的角度来认识文革和“反修”的必要性的。
然而,如梁漱溟肯定大跃进却不提“大炼钢铁”与“高产卫星”一样,梁漱溟虽然出于对“反修防修”的认同支持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但却并未对文革中其他的一系列过激活动表示肯定。他的支持一直是基于其自身对中国人“理性早启”的思索,而并非是一种文革中普遍的狂热或者屈服。
尤其值得玩味的是,对于明明是猛烈冲击传统、扫除“四旧”的文革,梁漱溟却始终认为它是得益于中国特殊的传统文化的。 《中国——理性之国》一书的第二章便名为《怎样认识老中国的特殊》,在第十五章梁漱溟甚至专门辟出一节,名曰《中国社会的特殊即从毛泽东而可见》。而在1968年致周总理并转毛主席的信中,梁漱溟更是颇为语惊四座地说道:“唯独我中国在主席领导下四十几年来走出一条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国道路,建立起世界革命的旗帜,俨然世界革命的领导力量。此中因果关系能说与老中国文化无关乎?”③《梁漱溟全集》(第八卷),第81 页。我以为,仅这一问就足可见出,梁漱溟在表面的对文革的支持下,其本质仍是一种对于自己政治思想的坚持。大跃进也好、文革也好,在他眼中,其实都只是可以用来阐释自己“人心理论”的例证。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回梁漱溟1949年以后的全部经历,我们还会发现,在这三篇文章的背后,其实有一本专著的创作贯穿始终,那就是晚年最为梁漱溟所看重的《人心与人生》一书。在笔者看来,梁漱溟其实就是在用对中共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阐释来为此书做下一个又一个现实的注脚。
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可以大致勾勒出梁漱溟后期政治思想的两条主线。
在阶级理论上,梁漱溟经历了一个从转变到回归的过程。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在整个思想发展过程中,梁漱溟的关注点其实始终都没有放在“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本身,而是放在其最终所能达到的统一建国的目标上,也就是那个新事实上。一旦新事实与其所盼相符,梁漱溟便致力于将新事实与旧理论相贯通;而新事实若有违其所想,梁漱溟便会转而回归其旧理论。
而在人心理论上,梁漱溟则通过将唯物主义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比附为自己所主张的“理性”或“人心”,从而将其内化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巧妙地实现了人心理论与中共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对接,并利用这些实践的“成就”进一步证明了自己的理论。
因此,笔者以为,梁漱溟后期政治思想的实质其实就是一种融通中国的新事实与自己的旧理论(也就是融通社会主义实践与其所理解的中国传统思想)的尝试。
那么,梁漱溟的这种政治思想转变模式在1949年以后留在大陆的新儒家代表人物中有没有普遍性呢?我认为是颇值得关注的。在《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现代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初探》一文中,郑大华教授曾把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新儒家依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程度不同划分成了三种:“一是以冯友兰、贺麟为代表,放弃了自己的新儒学思想,认同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甚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贺麟);二是以梁漱溟为代表,在坚持自己新儒学的一些基本思想的基础上,也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毛泽东思想)进行过利用和儒化;三是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坚持自己的新儒学思想,基本上没有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①郑大华:《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现代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初探》,《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6 期。其中,笔者对郑教授对冯友兰、贺麟以及马一浮三位的划分是没有意见的,但笔者认为,熊十力的政治思想其实也有过类似于梁漱溟一般的转变。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便是其在1951年间所写下的《论六经》一文,在此文中,熊十力着重阐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化之间的关系,包括心性与革命的内在关联等。②详见刘小枫:《共和与经纶:熊十力〈论六经〉〈正韩〉辨正》,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与梁漱溟在本质上坚持“中国缺乏阶级对立”与人心理论的同时却又力图实现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对接一样,熊十力也是在坚守自己的心性论的基础上做出了类似的尝试。
由此可见,除却极其出世的马一浮,③与其他几位不同,马一浮的出世思想几乎是贯穿其一生的,早期只在小范围的书院讲学,后期则基本隐居在西湖蒋庄。1949年以后,面对社会主义实践的巨大成功,留在大陆的新儒家的理论转向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如冯友兰、贺麟,在新事实面前基本放弃了旧理论,为马克思主义所化,另一类则如梁漱溟、熊十力,力求将旧理论与新事实相对接,试图儒化马克思主义,贯通当代政统与传统中国的道统。而这背后隐藏着的,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中国儒家传统间的巨大张力与可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梁漱溟当年的困惑,今天的我们也同样面对。而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儒家对此问题的回答无疑也为如何面对今天的处境提供了思考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