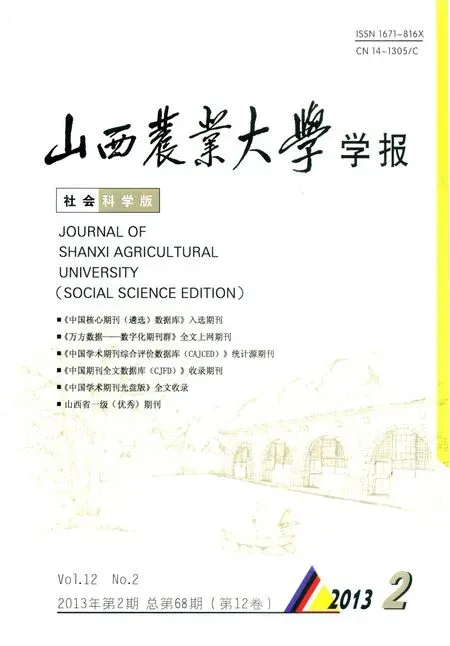“文革”语言的研究对象及其反思
刘苹,李松
(1.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74;2.武汉大学文艺生产与消费调查评估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2)
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史有两个时段的汉语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各自在近现代汉语发展史上占据特殊的地位。第一,20 世纪前后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过渡时期。第二,“文革”时期政治性语言的形成与发展时期。第二个时期的汉语具有鲜明的革命政治特征,为语言学提供了极为特殊的语言现象与颇富价值的研究课题。 “文革”语言是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语言现象,其研究成果在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出现,学术界对如此重要的语言现象的研究,至目前为止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从总体研究来看,巢峰主编的《“文化大革命”词典》[1]和周荐主编的 《“文化大革命”词语辞典》[2]都以典型词汇为核心,以词典的编撰体例对 “文革”时期独特的关键词、高频词进行了语言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维视角的阐释。这两部书态度严谨、选词精当、解释准确,对 “文革”语言进行了全景式深描,都是这一领域的奠基之作。从本文的研究对象来看,笔者将 “文革”语言按照其存在的语境与领域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政治领域中的政论话语、标语、大字报、政治口号等;第二类是文艺作品中的语言;第三类是日常社会语言。需要说明的是,这三者指涉的范围其界限并非判然分明,往往有交叉混融之处。本文拟从学术史角度梳理现有成果,并且结合当下和谐、文明语言环境的创建,对“文革”语言现象进行文化反思。
一、政治领域中的语言
“文革”政治领域中的语言,主要是指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政治意志表征的语言现象与活动。
(一)政论文
政论文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及主流媒体的政治态度,其思想和语言特征具有鲜明的倾向性意义。祝克懿的 《“文革”元旦社论话语的逻辑语义分析》抓住特定时间的典型话语,分析其语义机理。她认为,“文革话语是被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赋予鲜明时代特色的话语,其政治化、模式化的程度,可谓空前绝后。有人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它所写照的极左思潮和空洞的意识形态说教;有人从文学的角度揭示其八股形式掩饰下极端的思想、苍白的形象和亢奋的情绪;有人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它作为政治理念的载体,在表达方式上的形式主义、感情色彩上狂热与粗野的特征。总而言之,不同学科都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文革话语由于受政治权势控制、干预而产生的‘假、大、空’性质特征。但文革话语假在哪里?空在何处?大话有多大?极少有人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明”。[3]据此情形,祝克懿运用可能世界语义学的理论审视 “文革”元旦社论话语,剖析其“假、大、空”话语的性质特征,指出其形成的原因在于把可能当作了必然,把不可能当作了可能甚至必然。祝克懿以语言学理论进行扎实的个案分析,为还原“文革”语言的产生根源、解构 “文革”语言的虚浮特征提供了学理依据。
(二)标语、口号、大字报等宣传语言
在“文革”这个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标语、大字报、政治口号等宣传语言高度浓缩了当时的政治主题和时代精神,主流媒体实现了垄断语言认知、操控意识形态导向的功能。这些工具性的宣传话语本身的语言构成也具有表意抒情的特殊性。贺晓娟概括了这一时期的语言特点,她认为: “在政治运动时期 (1949~1978),标语口号总是围绕某一政治运动,类似战争时期打一场战役,统一号令,统一行动,其内容比较单一,自由度小。而作为政治运动时期的特殊阶段,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标语格式花样繁多,群众组织可以随意制作、张贴大标语……当时的标语明显的带有时代的烙印,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环境和背景下的产物,语言极其暴力化、幼稚化和粗俗化。”[4]贺晓娟从农村标语发展的宏观背景出发,对 “文革”时期标语的发展、分类和变迁的实质进行分析,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林立峰从修辞分析的角度较系统地研究了“文革”的宣传话语。他以宣传话语包括大字报、政治口号、革命歌曲等在内,分析了它们不同的分类及其修辞特点。他认为,大字报的修辞特点是,有组织的话语结构,充满激情的或进攻性的语言表达,大量使用隐喻手法。“文革”时期的政治口号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颂扬政治领袖的。另一类是政治领袖自己的话语,即语录。这些政治口号的修辞主题表现为激进、疏远、否定以及创造神话这四个方面的特征。[5]林立峰的研究并未停留在语言的修辞美学表层,而是由表及里揭示了政治修辞的意识形态与说话者无意识的深层心理。
如果对 “文革”宣传语言的内容进行细分的话,笔者认为可以分为如下五个方面:第一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阶级斗争元话语。例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第二是绝对忠诚的领袖崇拜话语。例如,“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反对我反对”、“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地步”等。第三是国家领袖的最高指示话语。例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不为名,二不为利”、“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抓革命,促生产”、“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等。第四是不同时期的群众斗争话语。例如,“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文化革命齐造反,革命路上当闯将。”“红色恐怖万岁”,“文攻武卫,针锋相对,” “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不低革命头!”第五是敌我阵营壁垒对立的外交宣传话语。例如,“打倒帝修反”,“我们一定要解放世界上四分之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人民”,“东风吹,战鼓擂,当今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等。
二、文艺作品中的语言
“文革”文艺作品中的语言主要是指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歌曲等作品中的语言现象。
(一)“样板戏”语言
“样板戏”是“文革”时期的主要文艺作品,其语言也是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由于 “样板戏”被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要载体,由此而具有了特殊地位和极大影响力。“样板戏”的语言时代特征,具有很大的研究意义。
语言学界的 “样板戏”研究起步较晚,但是成果颇为可观。祝克懿的 《语言学视野中的 “样板戏”》[6]是 “‘文革文学’语言研究中最早的专著;该著作被认为是 ‘文革文学’语言和文学的交叉结合研究上一部开先河之作”。[7]刘超的 《样板戏人物语言分析》通过分析 “样板戏”人物的语言,探寻其成为群众性消费热点的原因。[8]钟蕊的《革命话语和 “样板戏”中的 “英雄”修辞幻象》[9]探讨了革命英雄塑造的修辞策略。笔者认为,在 “样板戏”的语言领域里,以国家、民族、阶级作为规范和标准,个人是从属的。集体代表普遍性,个人仅具特殊性,只能相对集体而存在。在 “文革”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理性掌握话语权,操纵整个语义系统,创造了关于国家的符号、政治的价值、阶级形象和行为规范,而个体只为政治符号服务,以忠诚、耐心和绝对沉默表达了政治符号的意志。在 “样板戏”中意识形态僵硬的政治话语遮蔽了人们日常语言与感受的鲜活与生动。人们不是出于个人体验与感觉来认识、表达对社会、人生的看法,而是以强制性的政治话语约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在艺术作品中,文学语言为了实现最大的表达效率,除了以直白的方式表达意义以外,最具韵味的是通过创造语言的隐喻与象征的符号体系来实现。“样板戏”的言语行为不以相互的交流与沟通作为目的,而是独语式或排他性的。说话的目的在于宣讲、在于定义、在于训导,而不是通过对话进行交流。因而人们往往成为主流政治话语的奴隶,而领袖的 “最高指示”和语录成为了指挥棒。“样板戏”的语言暴力与权威体现在舞台人物的每一个字词、句子之中。“样板戏”创作贯穿着对领袖思想和领袖个人的崇拜,这可以从“样板戏”的创作与最高政治领袖个人著述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来。“样板戏”语言还以仪式这一特殊的方式体现出来,“样板戏”中语言的仪式化场景随处可见。例如,《红灯记》第八场 《刑场斗争》中,在雄壮的 《国际歌》乐声中,李奶奶、李玉和、李铁梅祖孙三代人视死如归,挺胸走下。李玉和临刑前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三代人振臂齐呼:“毛主席万岁!”《沙家浜》第七场 《斥敌》中,老百姓王福根怒斥胡传魁和刁德一道:“汉奸!走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走狗!”胡传魁恼羞成怒,命手下枪毙王福根。王福根高呼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戏剧作品中的这些语言具有强烈的动作性、视觉性和听觉性特点,体现了强化语言内涵的仪式意义。
(二)小说和诗歌语言
“文革”初期,由于大批优秀的作家和知识分子被打倒,小说的创作和出版备受冲击。1971年之后才有一些文学期刊复刊,少数政治权威认可的知识分子开始按照“样板戏”的创作经验进行文学创作,他们创作的主要是 “样板”小说,还有一批短篇小说发表在“四人帮”控制的刊物《朝霞》上。代表作主要有浩然的农村题材小说《金光大道》。邱海珍以“文革”文学作品为对象,研究了“文革”时期女性语言的特征。而诗歌由于可以用来赞颂革命和党,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但是题材比较单一。[10]高群的 《文革诗歌修辞论》通过对“文革”诗歌修辞的研究,展示了“文革”时期现代汉语诗歌语体特定的风貌以及“文革”诗歌修辞形式特征。[11]上述语言学角度的“文革”文学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实证性特点,较好地避免了研究者主观独断的情感偏见,因而是具有独特价值的“文革”文学研究的创获。
(三)革命歌曲语言
“文革”时期的革命歌曲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颂歌,如 《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岁毛主席》、《读毛主席的书》、《红太阳照边疆》、《毛主席是各族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等。第二类是语录歌。1966年9月30日的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加编者按的形式刊登了十首语录歌。例如, 《为人民服务》、 《争取胜利》、《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等。第三类是毛主席诗词歌。如音乐舞蹈史诗 《东方红》选用的 《七律长征》(彦克、吕远作曲)和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沈亚威作曲),《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 《念奴娇鸟儿问答》等。第四类是红卫兵歌曲。例如 《红卫兵战歌》)等。上述革命歌曲有三个方面的修辞特征:革命英雄话语的独语式;阶级情感的极端性;个人情感的隐匿性。自从延安时期开始,毛泽东通俗、活泼、精炼、警策的个性化语言对中国现代汉语产生了广泛影响,而“文革”时期达到了顶峰。这些颂歌、语录歌与毛泽东诗词歌曲的广泛流行进一步放大了毛泽东个人语言在 “文革”期间的影响。
三、日常社会生活中的语言
“文革”日常社会生活中的语言是指人们日常生活中自发出现的语言现象,这种语言种类多、范围广。本文主要以红卫兵语言、知青语言以及生活中的流行语言为研究对象。
(一)红卫兵语言
红卫兵语言集中体现了“文革”语言的典型特征,以及红卫兵“造反有理”的无意识社会心理。包括准救世主、泛敌意识、迷信领袖、暴力崇尚、道德专政、英雄主义等方面的情结。对红卫兵语言的研究散见于“文革”语言研究专著和论文之中,目前专门研究红卫兵语言的专著极少。
马越细致分析了一张红卫兵小报的材质、内容、主题特征,以语言、词汇为中心,结合对文体、文风的考察,从这篇典型的 “应时之文”中,发掘红卫兵运动时期所特有的时代文化表征。他发现红卫兵语言具有奇特的语汇体系,受到当时的左倾、激进大环境和整体社会氛围的影响,且与派性斗争的紧张程度紧密相关。大量的军事用语、粗鄙不堪的谩骂式语句以及 “流行语”的使用,在客观上造成了紧张、严峻的语义效果,虽然达到了实际功利的目的,但是缺乏审美意义上的美感作用。红卫兵语言具有独特的文体文风,小报采用了 “罪状书”这一攻击性很强的论证形式,分十条列举事实,从不同方面出发列出对立派别的 “滔滔罪行”,措辞十分严厉强硬,处处可见语气强烈的感叹句、反问句。风采独具的遣词造句、犀利泼辣的论证风格,通俗流畅、平白易懂的语言也都是它的显著特征。此类文体最后还演变成了 “文革八股”。红卫兵语言同“文革”中的大多数政论文一样,这份小报也没有作者个人署名,落款的 “八一军团”只是一个含义暧昧不清的代码。小报作者自觉地放弃了对话语的独占权,而化身于抽象的 “集团代言人”,个人独特的生活经历和人生体验都完全消解于现实的 “流血祭礼”之中。马越认为,在“实用”价值上,这篇文章确实达到了 “攻心”的效果。其措辞激烈的行文、咄咄逼人的气势,使文章整体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与煽动性。但是,就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而言,这篇文字相当贫乏薄弱的。尤其是它的语言己经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作为文学材料所应具有的审美作用而流于简单化和单义性,更接近于日常生活用语。马越进一步指出:这不仅是红卫兵小报,也是整个“文革”文学的总体特征之一。[12]红卫兵语言的特色还体现在红卫兵题材的歌曲中,例如 《红卫兵之歌》、《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红卫兵战歌》等。《革命造反歌》歌词以杀气腾腾的革命口号为主。《造反歌》加入了一些粗俗的语言。
(二)知青语言
作为 “文革”时期的一个特殊群体,知青使用不同于 “革命群众”的语言。研究的价值是,考察他们的语言能了解他们的生活轨迹、心理历程和精神状态以及 “文革”和乡村生活对他们的影响。李超、张港的 《论黑龙江的 “知青语”》主要论述了黑龙江的 “知青语”的形成、意义和特点。不足的是该文是漫谈式的论文,且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未能对知青语言问题做出系统的论述。[13]李明华论述了知青和知青语的区别,通过论述知青语言与 “文革”语言和红卫兵语言的关联进一步阐述知青语言。他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主要通过 《知青日记选编》、《知青书信选编》等进行具体的统计分析,以 《中国知青诗抄》、“文革”期间报纸、回忆录等为研究范本,对知青语进行深入的分类研究,并追述其各自的产生根源,分析论证知青语的特点。他以大量“文革”知青时代的知青日记、书信、诗歌等具有真实可信的资料作为研究范本,分析了知青语言不同语体使用的情况。[14]刘起林选择 “文革”时期公开发表的知青题材长篇小说,揭示其话语逻辑与内在意味。他认为文本模式化叙事的双重情节建构、理性主题开掘、人物及其关系设计和矛盾发展演变程式等方面,顺应着违背历史与文学规律为 “文革”意识形态提供合法性论证的目的,显示出反人权、反人性的思想特征。但作品人物形象和情节叙述的具体内涵,以及对地域风情、民间文艺、浪漫抒情气质等审美元素的追求,暗含着后来知青文学合理化发展的道路。[15]知青语言研究的语料还可以结合当时报刊杂志的文章,以及当下口述历史的现场采访进行,从而拓展语言整理的范围。
(三)“文革”流行语
“文革”流行语与上面所提到的 “文革”词汇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重叠,但是流行语不限于词汇,它还指这一时期所流行的歇后语、短语和句子等。目前对这个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资料的整理工作中,如 《“文化大革命”词典》、[16]《历史的细节丛书:正在消失的词语》[17]等。这些成果对 “文革”流行语的特征的研究不多。刁晏斌发现,有大量 “文革”时期的流行词语沿用至今,或者是经过一度沉寂以后又重新启用,他探讨了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以及沿用的词语与重新启用的词语之间的差异。[18]孟国认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些 “文革”词语(包括 “文革”前一段极 “左”时期产生的词语)进入了语言博物馆,还有一部分至今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人们的言语交际中。目前,“文革”词语大都在感情上、词义上或用法上产生了异化,其中相当一部分已被更新,但这一更新和异化的过程是复杂而漫长的。[19]
四、“文革”语言的文化反思
由上述 “文革”语言现象的梳理以及获得的认识,我们有必要对 “文革”语言进行理性反思。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指出,“语言的所有最为纤细的根茎生长在民族精神力量之中”,[20]“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21]所以,人们学习和接受语言的过程,其实是一种文化习得并受其同化的过程。正像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所说:“获得某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某一套概念和价值。在成长中的儿童缓慢而痛苦地适应社会成规的同时,他的祖先积累了数千年而逐渐形成的所有思想、理想和成见也都铭刻在他的脑子里了。”[22]可见语言制造出了一种现实生活,这种生活包含着人类内在的精神结构。 “文革”语言制造的现实生活不仅给当时的人们造成了灾难,而且还在日后带来了恶劣的文化后果,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文革”语言形成了语言暴力现象
“文革”暴力语言充斥公文、教科书、文艺作品以及视听媒介,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话语方式。具体来说,“文革”语言暴力通常在詈词、极端词语以及日常语言的军事化修辞等现象中显示出来。李逊、裴宜理认为 “文革”语言的粗野主要表现在:粗野的红卫兵咒骂语,夸张激烈的修辞方式,泛滥的军事用语。[23]刁晏斌从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这两个方面对当今的语言暴力现象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前者在校园语言、体育界用语、社会用语以及文人用语等中都有十分明显的反映,而后者则主要表现为沿用 “文革”时期流行的暴力词语和大量使用詈骂性言辞这两个方面。刁晏斌呼吁人们同这些现象进行斗争,以求得语言的和谐。[24]“文革”的语言暴力是斗争哲学在精神上的表征。斗争哲学通过教科书、日常语言、社会环境深深植入了人们的头脑。触目所见、充耳所闻是 “批判”、“斗争”、“打倒”、“砸烂”、“横扫”等等充满暴力、威胁、恫吓、火药味的词汇。
(二)“文革”语言造成了人们的精神创伤
周一农认为,“文革”十年给中国人民的语言生活所带来的创伤是深重的。斗争哲学斗掉了言语信任;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限制了言语话题;革文化革命也革掉了汉语规范化。也正因为这场空前的灾难,才深深地唤醒了大众对于语言民主和文化的强烈的重建意识,也才真正迎来了新时期二十年中,汉语发生的令世人瞩目的变化。[25]周荐、李根孝在 《乱世出怪语》一文中总结道:在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怪词怪语,文章的语法错乱,逻辑混乱,文风恶劣,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病态社会导致语言中出现的病态现象。[26]朱逢春、邬忠认为:作为 “文革”政治话语载体的大字报是 “文革”话语的缩影和典型代表。狂热的政治话语向公众话语扩张与渗透,形成话语霸权,严重地影响了当时语言的健康发展。[27]靳彪、赵秀明认为,由于政治的原因,翻译工作在马恩列斯及毛泽东著作的翻译以及对联合国文件的翻译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总体上来看, “文化大革命”使得正在蓬勃发展中的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处于停滞,中国的翻译界只能在曲折中前进。翻译机构被拆散,翻译刊物停刊,翻译大家遇害,翻译被迫停止,翻译稿被毁,翻译理论和实践都被迫中止。[28]总之, “文革”语言与 “文革”翻来覆去的政治运动一道撕裂了人们之间原本和谐的伦常规则。
五、结语
语言是人类保存记忆、交流信息、表达感情的载体,是文化大系统中最重要的子系统,体现了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风俗习惯以及终极关怀。在“文革”历次残酷的政治运动中,语言服从不同阶层、派别政治利益的需要,成为了不择手段打击对手的工具,包括污蔑陷害、罗织罪名、上纲上线、暗箭伤人等等手段。那些被诬蔑、被攻击却无法辩解的人则往往结局悲惨。为了避免这种被动挨整的境地,人们努力打造自己的语言本领,让自己变得伶牙俐齿,随时可以迅速反击别人。因而, “文革”时期的语言暴力成为了一种保护自己、打击对方的武器。
在 “文革”时期政治高压和封闭灌输的环境里,人们不知不觉改变了传统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话语系统。目前的中国社会语言中,“文革”语言与 “文革”思维方式并未完全绝迹。有的词汇消亡了,其影响不复存在;有的词汇依然保留,而保留的词汇其意义未变;有的词汇意义则发生了适应性的转换;有的词汇则意义与用法都改变了。但是,“文革”思维在语言上的政治文化负面影响仍未完全消除。偏狭、僵化的政治理性曾经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健全、自由的人性,因而,我们在今天通过研究来反思 “文革”语言,从而试图重塑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创建和谐自由的语言环境、营构文明健康的语言心理,这是相当必要的。
[1]巢峰.“文化大革命”词典 [M].香港:港龙出版社,1993.
[2]周荐.“文化大革命”词语辞典 [M].韩国大邱:中文出版社,1997.
[3]祝克懿.“文革”元旦社论话语的逻辑语义分析 [J].贵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1 (7):69.
[4]贺晓娟.试析农村标语的演化与功能 [J].文史博览 (理论版),2006 (8):55-57.
[5]林立峰.文革宣传话语的修辞分析 [D].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6]祝克懿.语言学视野中的 “样板戏”[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7]李熙宗.“文革文学”语言研究的一部力作 [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5 (3):122-124.
[8]刘超.样板戏人物语言分析 [J].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05,7 (6):106-110.
[9]钟蕊.革命话语和 “样板戏”中的 “英雄”修辞幻象 [D].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0]邱海珍.“文革”文学女性语言研究 [D].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11]高群.文革诗歌修辞论 [D].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12]马越.红卫兵话语的文化表征——从一张发黄的红卫兵小报说起 [J].中国青年研究,1996 (6):26-28.
[13]李超,张港.论黑龙江的 “知青语”[J].理论观察,2003 (6):70-71.
[14]李明华.文革背景下的知青语言研究 [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15]刘起林.文革时期知青小说的话语逻辑——兼论文革前后知青文学的精神渊源 [J].湖南社会科学,2004 (6):123-127.
[16]巢峰.“文化大革命”词典 [M].香港:港龙出版社,1993.
[17]蒋蓝.历史的细节丛书:正在消失的词语 [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
[18]刁晏斌.“文革”流行语在当今的沿用和重新启用 [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8 (6):101-104.
[19]孟国.“文化大革命”词语的更新和异化 [J].天津师大学学报,1992 (5):76-80.
[20]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 [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7:62.
[21]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 [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7:70.
[22]帕默尔.语言学概论 [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3:148.
[23]李逊,裴宜理.革命的粗野——文革语言浅议 [J].文学自由谈,1993 (4):33-39.
[24]刁晏斌.试论当今的语言暴力现象 [J].辽东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8,10 (6):60-65.
[25]周一农.主权的回归与语用的解放——新时期大众语言主潮 [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9,19 (3):39-46.
[26]周荐[韩],李根孝.乱世出怪语——“文化大革命”时期用语特点简析[J].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17(1):108-110.
[27]朱逢春,邬忠.从 “文革”话语中透析话语霸权——由一张大字报说开去 [J].邯郸学院学报,2008,18 (4):60-62.
[28]靳彪,赵秀明.“文革”十年间的中国翻译界 [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 (1):4-6.
——评张丽军《“样板戏”在乡土中国的接受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