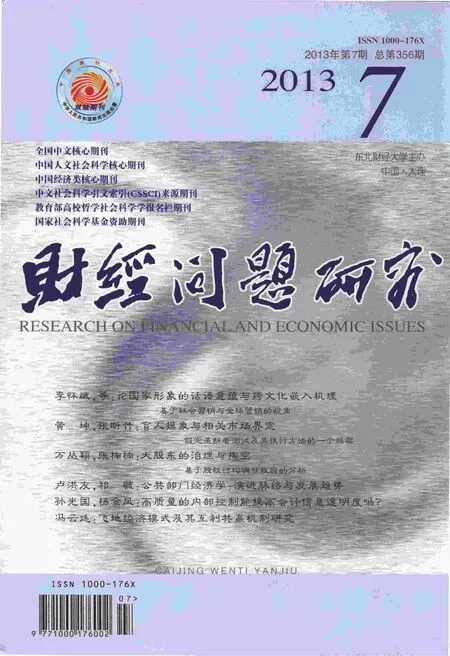我国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创新研究
穆 琳
(天津财经大学 教务处,天津 300222)
主体功能区是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新概念,并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上升为国家战略。主体功能区的划分旨在规范空间开发秩序,优化空间开发结构,提升空间利用效率,构建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可能会导致区域间的利益冲突,这就引发了对生态补偿的潜在需求。本文基于生态产品视角,提出了通过市场化方式,以生态产品交易手段进行生态补偿的初步构想。
一、相关文献综述
1.在主体功能区的理论研究方面
樊杰通过分析地域功能的基本属性提出区域发展的空间均衡模型,阐明资源要素在各区域间的合理流动是实现空间均衡的前提以及主体功能区的形成有利于空间均衡的形成[1]。李军杰根据区域发展的现状,从主体功能区的角度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展潜力和现有开发密度进行了新的阐释,并基于此提出设计功能区划分指数的初步构想[2]。张可云从主体功能区的概念入手,据此提出可能出现的主体功能区规划、管理的操作问题,并给出了这些操作问题的解决方法和区域管理的可能出路[3]。魏后凯从主体功能区的概念界定入手,认为主体功能区不同于综合经济区,而是典型的经济类型区,进而分析了主体功能区的作用及可能引发的问题,最后指出主体功能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分步推进建设,不能急于求成[4]。
杨玉文和李慧明从生态学的角度并运用系统论的方法对我国的主体功能区规划进行了解读,提出优化开发区域应以稳态经济思想为指导,重点开发区域应以生态经济效率理论为指导,限制开发区域应以生态经济和自然资本投资理论为指导,禁止开发区域应以生态环境价值论和公共物品及外部性理论为指导,并分别给出了对应的发展模式[5]。张明东和陆玉麒认为空间结构理论和人地关系理论是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理论基础,并提出通过GIS的空间叠置和聚类等空间分析技术在主体功能区划中的应用,可以较好地解决空间尺度与区域功能属性之间的矛盾给区域功能区的定位所带来的影响[6]。姜安印从空间资源优化配置的视角提出主体功能区从空间资源价值、空间功能互补性以及空间结构极化规律等方面对区域发展理论进行了创新[7]。孙姗姗和朱传耿认为主体功能区规划在区位定位方法、区域衡量发展、区域可持续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具有重大创新,是对区域发展理论的丰富与发展[8]。Friedmann认为, “区域政策处理的是区位方面的问题,即经济发展‘在什么地方’。它反映了在国家层次上处理区域问题的要求。只有通过操纵国家政策变量,才能对区域经济的未来做出最有用的贡献”[9]。
Gualini认为近些年来欧盟一体化过程中,面对各级政府间关系日渐紧张、区域功能的特殊性和将区域定位为联系空间载体的强烈需求,使欧盟各国原有的区域发展规划和政策体系面临创新的压力[10]。Hoover和Giarratani指出区域政策的目标是提高个人福利和促进就业平等与社会和谐。所以区域政策的实施应该有助于促进就业、提高生活水平和避免收入差距过大[11]。
2.在主体功能区的实践研究方面
曾岚根据汉中市的实际情况,提出汉中市应按功能定位把生态环境建设上升到战略高度,并对汉中市面临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的解决进行了探究[12]。徐伟金根据浙江省的实际情况,分析了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对浙江省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提出了浙江省主体功能区划分的初步设想[13]。林凌和刘世庆根据四川省的具体情况,提出四川省划分为五大经济特区的发展战略,从而促进四川省各区域间的协调发展[14]。王潜以辽宁省海城市为例,根据生态功能区规划的内涵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对海城市的国土空间进行了功能区的划分并提出了相应的生态控制方向[15]。胡昕和胡毅诏分析了主体功能区和生态补偿的内涵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甘肃省生态现状的研究,提出了甘肃省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模式与保障措施[16]。
王利等分析了主体功能区划分与空间开发战略协调的必要性与基本思路,以辽宁省在全国空间开发总体战略中的定位和内部空间开发战略为基础提出了辽宁省主体功能区划分的可行性方案[17]。危旭芳总结分析了发达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构建主体功能区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利于我国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制度安排及相关建议[18]。邓玲和杜黎明在分析同质化政府管理下的区域发展不协调的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区域协调功能进行了研究,并从主体功能区区域规划、行政区间合作、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政绩考核标准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19]。
Wheeler认为欧盟区域政策的实施,对各种区域发展规划的探索与制定具有极大的激励,其政策性功能也得到了体现[20]。Branch根据多年来对美国区域规划实践的跟踪研究,认为有效的区域规划应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水平以及提高环境质量,而在实践中美国各级政府间在区域规划的合作上却并没有达到这些目标,使美国目前缺乏综合、有效的区域规划[21]。Twomey和Taylor通过研究英国区域政策与区域间产业转移的关系,得出区域政策对英国的产业转移具有较强的影响,并且与投资激励相比,区域政策更具有效率[22]。Wren和Waterson研究了区域政策对直接就业的影响,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区域政策对就业具有很大的影响,并且在不同的经济周期阶段影响的效果不同,在经济衰退阶段对就业影响较弱[23]。
在上述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的角度对主体功能区的建设进行了探索。通过构建生态产品交易补偿机制,使主体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由政府财政主导的传统的生态补偿机制向由市场主导的生态补偿机制转变,从而提高生态补偿的效率。
二、主体功能区对生态补偿的内在需求
各个主体功能区因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等的不同而被划分为不同的功能定位,这种定位导致了主体功能区之间在发展模式和经济效益上存在较大差异: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区域主要发展经济效益高的工业产业,而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则发展短期内经济效益不明确或者说经济效益无法兑现的生态产业。同时国家根据功能定位的不同而对不同主体功能区提供相应的区域政策、产业政策和人口政策等政策支持也是各有区别,这种政策上的差异对待又进一步加大了各主体功能区间的利益不平衡[13]。
1.功能定位的限制导致某些主体功能区发展机遇的丧失
在我国现阶段,各个地方都把经济发展放在首要位置。而经济发展的实现则要依托于具体产业的发展,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精细化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尚在起步阶段,还不具备大规模发展的条件,对经济发展贡献有限,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主要还是依托于资源开发、化工和钢铁等传统产业。尽管这些产业污染高、对自然环境破坏大,但由于其现阶段利润高,同时又能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增加就业以及带动地方区域经济发展,所以是各个地方区域争先发展的产业。而主体功能区功能定位的划分,使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只能发展生态产业,禁止其进入现阶段利润高的上述产业,使其丧失了在现阶段发展区域经济的最快路径,可以说是对该区域发展机遇的一种剥夺。
2.功能定位的限制导致某些主体功能区承担额外成本
由于功能定位的不同,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区域可以发展对自然环境有一定污染但经济效益高的产业,走的是一条边开发边治理的道路,其开发产生的经济效益远远大于其治理环境的成本,具有净收益。而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发展生态产业,提供生态服务是其主体功能。在实现这一主体功能的过程中,两类功能区不仅要承担丧失发展经济效益高的产业的机会成本,而且还要为修复和维护生态环境支出一笔额外成本。例如,在传统上以木材加工业为主业的大兴安岭和小兴安岭地区,目前,不仅禁止砍伐森林资源,限制木材加工业,而且还要额外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森林防火、林木维护和封山育林等工作,失业的木材加工工人及其家属的安置也需要投入不菲的资金[14]。这些额外成本投入往往是地方经济无力承担,同时也进一步增加了这两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负担。
3.功能定位的限制导致某些主体功能区劳动力资源的流失
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的环境承载能力有限,不适宜发展工业,人们就业途径有限,所以该区域的劳动力比较富裕。国家引导该区域人口向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区域转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该区域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但有一个问题不能忽视,进行转移的劳动力都是青壮年劳动力,存在明显的择优机制。对于迁出区域,剩下的绝大部分都是鳏寡孤儿,生产能力低下,也就是说,该区域由以前的劳动力过剩转变为现在的劳动力紧缺,同时还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这种劳动力的流失又为该区域的经济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虽然各个主体功能区承担的主体功能不同,但根据要求,各个功能区域间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即各区域不论经济是否发达,居民都具有享受与全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共服务的权力。这就需要通过政府财政或其他途径对经济欠发达的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进行相应的生态补偿。
三、我国现有生态补偿机制存在的问题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生态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15]。由于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以及由此产生的外部性问题,不能依靠市场的力量对其实现有效配置,只能由政府来提供。所以在现阶段的认识范畴里,对生态的补偿只能依靠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来进行。但随着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提出,这种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
1.现有补偿机制补偿效率较低,成本较高
生态补偿机制的效率如何,不仅取决于能否产生预期的生态系统服务,而且取决于提供这些新增生态系统服务的成本[16]。我国现有的生态补偿机制是以政府为主导,市场化程度低甚至缺失,这直接导致补偿效率较低,补偿成本较高。按照规划,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地区的功能定位是开展生态产业,进行环境保护,这一功能定位在现阶段不能给该区域带来经济效益,只能由政府对其进行财政补贴或生态补偿。但是这种补偿机制容易产生一系列效率低下和成本高企的问题,不能有效解决改善民生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第一,补偿标准没有体现区域差异性。目前我国的生态补偿采取“一刀切[17]”的标准。例如中国的退耕还林 (草)工程,整个北方地区的补偿标准是统一的,补偿偏高和不足的现象都有存在,忽略了各个地区间在具体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差异[19]。第二,补偿标准如何确定没有明确的计量方法。政府在对补偿标准的确定上主观随意性比较大,没有按照科学合理的方法进行计算确定。在补偿过程中,补偿标准明显偏低,不利于调动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地区生态保护的积极性。第三,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容易产生寻租问题。政府既是补贴政策与标准的制定者又是补贴的给予者,垄断了整个生态补偿流程,难免产生寻租的问题,推高补偿成本。
2.现有补偿机制限制个人发展权
现有的补偿机制主要强调的是对限制开发地区和禁止开发地区进行财政转移支付,这些转移支付主要是用于这些区域的公共服务上,而忽略了这些地区的个人发展权问题。虽然国家鼓励该区域人口向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区域转移 (国家倡导的是主动性的人口转移),但是不可能整个区域的人都选择转移出去,留下的人也拥有自身发展的权力,但该区域现有的功能定位以及产业政策是不利于这些人发展的,对这些个体来说他们为了给其他地区提供适宜的生态系统而付出的机会成本远远大于他们目前的收益 (这里的机会成本是指为确保生态服务供给而放弃的收益[18]),即这些人的个人发展权被变相剥夺了。现有的生态补偿机制显然是忽略了这个问题。
3.现有补偿机制转移支付模式单一
我国现阶段的政府转移支付主要以纵向转移为主,而缺乏横向转移支付。首先,在纵向转移支付中,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占绝对主导地位。在这种模式下,各地区能够合理预期到最后会有政府出面买单,容易使这些地区产生依赖的思想,这不仅与“受益者付费”的原则相背离,而且不利于调动各区域进行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其次,我国生态服务的提供者主要位于西部,经济欠发达,生态服务的受益者主要位于中东部,经济较发达,由于缺乏横向转移支付,导致西部生态服务的提供者无法得到受益者提供的合理补偿。这种单一的纵向转移支付模式显然削弱了财政转移支付实现公平的最初目的。
4.现有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不完善
虽然涉及生态补偿这一概念的法律制度已经存在,但是关于生态补偿的规定主要散见于有关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法律、规章中,目前我国还没有颁布一部统一的关于生态补偿的法律法规。由于这些规定比较零散、不全面以及使用性不强,不仅在宏观上制约着我国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而且也无法满足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在实践中的实际需求。
四、生态产品交易补偿机制的实现路径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导致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出现各种问题的主要诱因是政府权力过大,市场化程度低,所以解决问题的重点应放在对现有补偿体制进行市场化改革上。鉴于此,笔者提出了生态产品交易补偿机制的市场化构想。一个市场的形成需要三种力量:企业或生产者、产品和消费者。在生态产品这一市场中,消费对象为生态产品,消费者是全体人民,政府代表人民进行购买,但生产生态产品的生产者或企业在实际中还无法确定或是否存在。因此,建议政府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构建生态产品交易补偿机制。
1.创建生态产品生产企业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单元,对优化资源配置起着关键的作用。传统的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对自然环境产生一定的破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企业都尽量避免参与环境保护以免增加自身的经营成本,即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与参与环境保护是相矛盾的。这种传统的企业模式不适合提供生态产品。
为了把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与参与环境维护的动机很好地结合起来,实现企业在生态产品市场中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在此建议创建生态产品生产企业。生态产品生产企业遵循一般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原则,通过改善生态环境来提供自己的产品——生态产品的专业企业。其经营范围包括植被维护、保持水土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传统上由政府参与的领域。考虑到市场建立初期,由于缺乏历史经营数据,各种资金参与筹建这种新型企业的积极性不会很高,持有观望态度的概率比较大。在这一阶段,可以先由政府设立国有独资的生态产品生产企业,员工全部面向社会招聘,以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地区的人员为主,实行完全独立于行政体系的市场化运营。待市场相对成熟以及相关政策逐步完善,各种资金,比如民间资本或外资会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进入这一产业。为了避免市场地位不对等,政府可以考虑通过转让股权逐步退出这一生态产品供给市场,实现完全市场化,这将充分调动全社会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
此外,生态产品生产企业的建立,可以为限制发展地区和禁止发展地区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就业途径,享有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机会,避免了产生大规模生态移民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维护了该地区人们的个人发展权利。
2.生态产品交易的市场化实现形式
在生态产品市场的生产者、消费者和产品都具备的情况下,我们进一步探讨生态产品的交易如何来实现。
由于生态产品生产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动机与保护环境的动机是一致的,在通过提供生态产品并出售获利的过程中,既实现了内部的经济性也实现了外部的经济性,也就是说,企业同时实现了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两者之间的实现次序是有先后的,只有在出售生态产品并实现社会利益的前提下,企业才能实现自身的利益。可是生态产品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即它的产权是一种公共产权,不能进行精确分割。在这种情况下,既无法精确确定生产者生产了多少,也无法确定消费者消费了多少,如果由个体消费者与生态产品生产企业直接进行交易的话,估计这一市场是无法维系的。所以,要选出一个全体消费者的代理人——政府来与生态产品生产企业进行交易,政府资金来源与传统的政府主导型补偿机制相同,都来自于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和生态税费收入,不过资金的补偿形式由传统的收入再分配转变成政府购买。
生态产品交易的市场化实现形式,从表面上看与传统的政府转移支付模式没什么不同,但本质上却差别很大,它是一种完全的市场交易行为。通过政府购买的形式紧盯生态产品交易,政府的角色由传统的大家长变为消费者,不必参与生态产品的生产过程,杜绝了政府在生态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寻租行为,提高了生态维护的效率。
3.生态产品的交易方式和利益分配
在生态产品的交易方式上可以借鉴我国的环境权益交易中心的做法,由国家环保部门牵头为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地区设立生态产品交易平台[21]。所有的生态维护和生态修复项目通过这一交易平台公开发表,面向全社会进行招标,在众多潜在生态产品提供者中,依据个体差异,选择最有效的生态产品供给者[22]。这就从源头上杜绝了地方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既是规章的制定者又是政策的实施者的补偿体制漏洞。由于这一交易平台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可以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对整个招投标过程进行监督,保证生态产品交易公开、公平、公正地进行。
生态产品生产企业同样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企业持续经营的前提是企业能够获得合理的经营利润。在对出售生态产品而产生的经济利益进行分配时,可以分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来进行讨论:对于国有生态产品生产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利润可以滚动计入生态基金,并继续用于生态保护;对于私营生态产品生产企业产生的利润,在减税或免税的基础上归企业自身所有,以提高其参与生态产品生产经营的积极性。由于提供生态产品具有正外部性,其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远远大于生态产品生产的成本,所以,对超额完成生态产品生产任务的企业,政府可以给予不同标准的奖励。
4.生态产品交易的实现路径
在生态产品的交易过程中,政府的购买资金来源与传统补偿机制相同,仍然以财政转移支付、生态税费收入以及生态基金为主。由环保部门对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并根据考察的情况确定各个地区的生态项目,然后将生态项目放到生态产品交易平台上向全社会进行招标。在招投标过程中,对于具有同等技术、设备的生态产品生产企业,可以优先考虑选择由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地区的人员为主组成的企业。竞标成功的企业根据所负责的项目进行具体的生态产品生产。根据各个项目具体内容的不同分别由农业、林业、水利和环保的部门对各项目进行定期核查以监督其实施情况。项目完工后由各个相关部门对其进行验收,在生态产品达到合同约定的生态指标后,再对生态产品生产企业进行付款。
五、构建生态产品交易补偿机制的政策建议
在实践中要实现生态产品交易补偿机制的构建,还有赖于国家提供相应的制度政策支持。
1.加大财税政策的支持力度
在生态产品交易市场中,政府是生态产品的需求方,生态产品生产企业是生态产品的供给方。在这一市场的构建过程中必须依靠财政税收政策的支持,实现生态补偿方式由传统的财政转移支付向政府购买的转变以及生态项目的建设由政府实施向企业实施转变。首先,要拓宽政府购买生态产品的资金来源。在传统的生态补偿机制下,补偿资金主要来源于纵向转移支付,即中央拨付的生态补偿资金,缺乏横向转移支付。由于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是生态产品的提供地区,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区域是生态产品受益地区,所以后者应向前者进行横向转移支付,拓宽政府购买生态产品的资金来源。其次,对有志投身于生态产品生产的民营企业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比如,对拥有技术但缺乏资金的民营企业提供贷款担保、低息贷款或无息贷款;对已经生产运营的民营生态产品生产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或其他税费的减免等。最后,对于企业员工主要由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人员构成的生态产品生产企业可以加大财政资助的额度。
2.健全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
在通过生态产品交易来推进补偿机制市场化的过程中,必须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政府与生态产品生产企业的交易规则,规范生态产品市场的运行。虽说在生态产品市场中,政府摆脱了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尴尬角色,但政府还是拥有市场监管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角色,这就可能导致在生态产品交易过程中因部门利益而产生冲突。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必须在法律法规框架内创新管理体制,由利益不相关的部门分别负责生态产品的购买和生态产品质量的检验,从而实现政府双重角色的内部分离。
3.完善生态产品交易平台
要建立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必须以生态产品交易平台为基础,促进生态产品投标主体的多元化,吸引各种力量及企业参与。生态产品交易平台必须秉承公开、公正、公平的理念,从一个第三方的角度促进各个招投标项目顺利进行。对于政府主导的生态建设项目必须通过这一平台进行交易,并鼓励社会公益组织主导的生态建设项目利用该平台进行交易,从而实现生态建设资金的高效利用,以实现我国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
[1] 樊杰.我国主体功能区划的科学基础[J].地理学报,2007,(3).
[2] 李军杰.确立主体功能区划分依据的基本思路——兼论划分指数的设计方案[J].中国经贸导刊,2006,(3).
[3] 张可云.主体功能区的操作问题与解决办法[J].中国发展观察,2007,(3).
[4] 魏后凯.对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冷思考[J].中国发展观察,2007,(3).
[5] 杨玉文,李慧明.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及发展机理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6).
[6] 张明东,陆玉麒.我国主体功能区划的有关理论探讨[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9,(3).
[7] 姜安印.主体功能区:区域发展理论新境界和实践新格局[J]. 开发研究,2007,(2).
[8] 孙姗姗,朱传耿.论主体功能区对我国区域发展理论的创新[J]. 现代经济探索,2006,(9).
[9] Friedmann,J.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A Case Study of Venezuela[M].Cambridge:The MIT Press,1966.
[10] Gualini, E. Regionalization as Experimental Regionalism:The Rescaling of Territorial Policy-Making in German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04,28(2):329-353.
[11] Hoover,E.M.,Giarratani,F.An Introduction to Regional Economics [M]. Regional Research Institute,1999.
[12] 曾岚.关于汉中市按照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实现突破发展的思考[J].宏观经济研究,2006,(10).
[13] 徐伟金.关于主体功能区划有关问题探讨[J].浙江经济,2006,(2).
[14] 林凌,刘世庆.重点推进与协调发展:四川省“十一五”五大经济区的区域发展战略[J].决策咨询通讯,2007,(2).
[15] 王潜.县域国土主体功能区划分及生态控制[J].环境保护,2007,(1).
[16] 胡昕,胡毅诏.基于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甘肃省生态补偿机制初探[J].问题探讨,2012,(1).
[17] 王利,韩增林,关伟.辽宁省空间开发战略与主体功能区划协调研究[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1).
[18] 危旭芳.主体功能区构建与制度创新:国外典型经验及启示[J].生态经济,2012,(3).
[19] 邓玲,杜黎明.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区域协调功能研究[J]. 经济学家,2006,(4).
[20] Wheeler, S.M.The New Regionalism:Key Characteristics of an Emerging Movement[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2002,68(3):267-278.
[21] Branch,M.C.Regional Planning:Introduction and Explanation[M].Praeger Publishers,1988.
[22] Twomey,J.,Taylor,J.RegionalPolicy and the Interregional Move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Great Britain[J].Scottish JournalofPolitical Economy,1985,32(3):257-277.
[23] Wren,C.,Waterson,M.TheDirectEmployment Effects of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Industry [R].Oxford Economic Papers,1991.116-138.
[24] 陈辞.生态补偿的财政政策研究——一个主体功能区的视角[J].经济理论与研究,2009,(12).
- 财经问题研究的其它文章
- 税法的核心价值与纳税人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