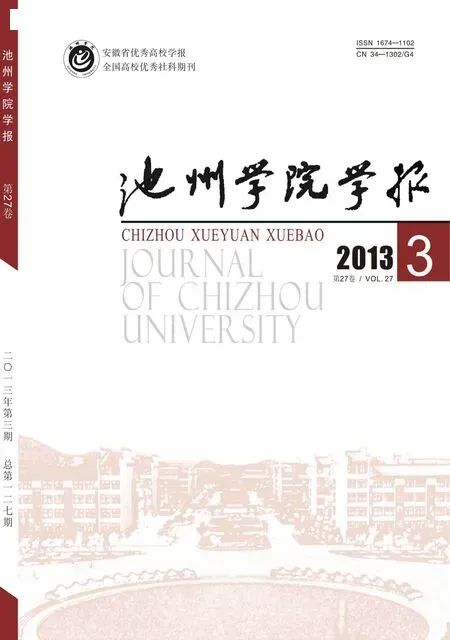湿地土壤有机碳组分研究进展
石小磊 ,许信旺 ,,毛 敏 ,何小青 ,方宇媛
(1.安徽师范大学 国土资源与旅游学院,安徽 芜湖241000;2.池州学院 资源环境与旅游系,安徽 池州247000)
温室气体的增加对气候和各种生态系统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到21世纪30年代,二氧化碳和其它温室气体增加的总效应将相当于工业化前二氧化碳浓度加倍的水平,可引起全球气温上升1.5~4.5℃超过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升温幅度,将导致海平面上升9~88㎝。碳的自然平衡遭到破坏是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的根本原因[1]。二氧化碳作为一种主要的温室气体,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土壤碳形态类型、碳储存、碳循环、碳累积与碳排放方面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也十分巨大。不同的生态系统下温室气体的源和汇就是一项重要的研究任务。
湿地生态系统是地球上碳储量最丰富、碳密度最高的生态系统,尤其是在湿地土壤和泥炭中。我国湿地土壤碳库达8~10 Pg,占全国陆地土壤总有机碳库的约1/10~1/8,过去50 a间的损失可能达1.5 Pg[2]。在研究湿地生态系统中,土壤碳的稳定性取决于土壤有机碳不同组分的构成[3],通过物理技术、化学技术、生物学技术三种方法将土壤有机碳分成不同的组分,而分离出的有机碳的活性组分和惰性组分对于土壤的固碳作用大小又不同,土壤固碳增加对温室气体减排的研究意义也非常重大。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有机碳形态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土壤有机碳组分必将成为研究土壤温室气体排放研究的重点。
1 土壤有机碳的组分分类方法
土壤是仅次于海洋和地质库的全球第三大碳库,有机碳储量1550Gt在全球碳循环中起着重要作用[4]。张国等(2011)研究土壤有机碳中的有一些组分在土地利用方式下发生的变化反应比总有机碳更敏感,这部分碳被称作活性有机碳,可作为有机碳早期变化的指示物,而非活性有机碳表征土壤的长期积累和固碳能力[5]。早期霍连杰等研究,土壤有机碳的类型和组成,分别从化学、物理两个方面对土壤有机碳进行分类[6]。张国等(2011)用生物学方法对土壤有机碳进行了更深入地研究[5]。
1.1 物理分组法
土壤有机碳的物理分组是按照土壤有机碳的密度或土壤颗粒大小进行分类,20世纪60年代,Tiessen等(1983)根据土壤有机碳与土壤有机质结合的各级土壤初级颗粒的大小将土壤有机质分作砂粒(粒径>50μm)、粗粉砂粒(20~50 μm)、细粉砂粒(2~20 μm)、粗粘粒(0.2~2 μm)和细粘粒(粒径<0.2 μm)结合的有机质[7],可分离出有机碳的活性组分和惰性组分。Von LützowM等(2007)按密度分组,将土壤轻组有机碳中的一些新添加的、部分分解且未腐殖化的有机质,而重组分碳则是矿质吸附的腐殖化的有机质[8]。Gregorich EG等(2006)研究,轻组碳主要包括微生物遗留残骸、动植物残体、菌丝体和孢子等,是介于新鲜有机质和腐殖化有机质之间的中间碳库[9]。重组碳主要成分是腐殖质,分解程度较高,具有较低的C/N[10]。用物理分组法可以客观的反映出土壤有机碳的结构和功能。
1.2 化学分组法
土壤有机碳组分是根据化学性质和化学组成进行分类[6],基于土壤有机碳组分在各种化学提取剂中的水解性、溶解性等化学反应性进行分组,提取溶解性有机碳、酸水解有机碳和易氧化有机碳等。溶解性有机碳是生物可代谢有机碳,包括有机酸、酚类和糖类等;酸水解方法可将有机碳分成活性和惰性成分;利用KMnO4模拟酶氧化可分离出活性碳和非活性碳[5]。Logninow和Chan(1987,2001)根据土壤有机碳被三种不同浓度的高锰酸钾或硫酸和重铬酸钾溶液氧化的程度对其进行分类[11-12],分类结果是相似的。Patton(1987)依据土壤有机碳周转速率的快慢将土壤有机碳分成易变碳库和稳定碳库,或分成活性碳库、慢性碳库(缓效性碳库)和惰性碳库,或分成易分解有机碳,难分解有机碳和惰性有机碳[13]。
1.3 生物技术分组法
生物学分组主要是通过一些生物方法测定对已经矿化的生物和被矿化的有机残体的微生物生物量,或根据把有机碳作为一种底物的反应来推断出土壤中生物可利用的有机碳量[5]。土壤活性有机碳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微生物量碳[14],监测有机碳的动态变化就是用微生物生物量碳/土壤有机碳值,可以用来指示土壤碳的平衡、积累或消耗,而且是比有机碳更为敏感的一种动态指示因子,能够准确预测出土壤有机碳的长期变化[15]。通过土壤微生物的分解之后有机碳转化成无机碳的过程就称作土壤有机碳的矿化,在土壤矿化过程中微生物呼吸释放出CO2[16]。活性有机碳是土壤较为敏感的组分,是土壤早期有机碳变化的指示物,而土壤中活性较差的惰性有机碳则可以指示土壤碳固定和积累的能力。
根据以上三种分类法,国内外学者皆研究出各自不同的有机碳分组法。Jenkinson等(1977)把有机碳分成可降解植物、生物有机碳、抗分解植物、物理稳定有机碳和化学稳定有机碳5类[17]。Kucharik等(2000)等,根据有机碳在土壤中的平均驻留时间的差异,综合土壤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子模型,将土壤有机碳分成了活性碳库、受保护的缓性碳库以及未受保护的缓性碳库和难以转变的稳定碳库4类[18]。徐明岗等(2000)指出,土壤活性有机碳根据有机碳组分和测定方法的不同,可分为易氧化活性有机碳、水溶性有机碳、轻组有机碳和微生物量碳4类[19]。吴建国等,(2004)依据物理分组方法,把土壤有机碳划分为轻组有机碳、重组有机碳和颗粒有机碳三种类型[20]。不同的研究员依据不同的方法划分出不同的类别,但大多数研究员都把土壤有机碳划分成活性有机碳、缓性有机碳和稳定性有机碳[13,18,21-23]。
国内外学者在有机碳组分方面的研究也较为火热,主要为了致力于寻找未来CO2排放控制相关的安全途径。国内外研究学者都把土壤活性有机碳作为一个研究重点,国外研究者主要从固碳减排、生态碳循环以及化学燃料燃烧释放等导致的全球变暖问题上较为关注,对于土壤有机碳中的惰性碳的研究相对较少。国内学者多以各种生态系统活性有机碳为研究重点,把土壤有机碳组分的不同分支方向作进一步的研究,以增加农业生产、生态环境和社会效益为目标,大多也是以活性有机碳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有机碳组分的累积研究相对较少。为改善逐渐恶化的生态环境,土壤有机碳组分这一研究方向也越来越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
2 土地利用对湿地土壤有机碳组分的影响
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不仅直接影响土壤有机碳的含量和分布,并通过对土壤有机碳形成和转化因子的影响,而间接的影响土壤有机碳的含量和分布[24]。同时不仅自然环境对土壤有机碳的积累的影响较大之外,人类活动的影响也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如耕作方式、肥料施入等。段正峰等(1998)研究土地利用方式对微生物量碳的影响,试验中土壤微生物量碳含量依次为:菜地>橘林地>草地>灌丛>耕地,其中耕地和菜地的对比中,由于受到耕作活动、种植制度和轮作方式因子的影响,表现出的起伏变化较为明显[25]。土壤微生物量碳是土壤有机碳中所占比例较低但活性最高的部分,对土壤有机碳的动态变化过程具有重要的影响[26]。土壤中微生物量碳库的周转速率更大,周转时间更短,相对于土壤有机碳的变化更为快速[27],而另外一种土壤可矿化碳是对微生物分解土壤有机物质的衡量指标[28-29]。研究表明耕地的可矿化碳含量分别比草地、菜地、橘林地和灌丛低。长期施用有机肥能显著提高土壤活性有机碳的含量;有机肥与无机肥配合使用,能够增加土壤活性有机碳的含量;长期施用化学肥料,可增加土壤有机碳的氧化稳定性[30]。前人研究表明,作为人为利用主要途径,自然土壤的农业耕垦引起了土壤总有机碳库和表层有机碳库的损失[31],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制约着土壤碳库容量和固碳水平,邰继承等(2011)研究不同土地利用下湖北江汉平原湿地起源土壤有机碳组分的变化,从研究结果来看,同是湿地起源的土壤,化学键合组分的差异明显大于物理分离组分的差异,湿地的农业垦殖对湿地土壤有机碳的影响,因不同的农业利用方式而异,研究中开垦为稻田后显著提高了土壤有机碳库[32]。李典友等(2008)研究也表明,长江中游地区湿地土壤开垦为稻田是相对理想的保持土壤有机碳库的土地利用途径[33]。赵海超等对春玉米种植密度对土壤有机碳组分的影响进行了研究,高、低密度均增加土壤 0~40cm土层有机碳质量分数,中密度下促进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增加。随着种植密度的加大土壤中活性有机碳增加,轻组有机碳减少[34]。曾从盛等,(2008)研究,在闽江口区域,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湿地在土层0~50 cm处的易氧化碳平均含量结果显示为天然芦苇沼泽湿地>草地>撂荒地>水田,其中易氧化有机碳的不同组分含量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芦苇沼泽湿地主要以低活性有机碳为主,中等活性有机碳在草地中占有较大比重,而高活性有机碳则是出现在水田和撂荒地[35]。张金波等,(2005)研究表明,土壤DOC含量在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小叶章草甸湿地>耕作后弃耕湿地,那么湿地垦殖为水田的有机碳含量大于湿地垦殖为旱田的有机碳含量[36]。黄靖宇等,(2008)研究表明,垦殖后的小叶章沼泽湿地等一些土地利用方式的土壤微生物碳含量低于未受人类干扰下的天然土壤微生物量碳含量,农田弃耕还湿或弃耕人工造林的土壤微生物量都呈增长趋势,而小叶章湿地垦殖为农田20年后,土壤微生物量碳下降趋势很明显,,但土壤微生物的活性距离恢复到垦殖前天然沼泽湿地的水平还很遥远[37]。以上是对不同的土地利用和管理方式下,土壤有机碳库及土壤活性有机碳形态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土壤碳形态对于土地利用和施肥等措施反应十分敏感,也是当前在湿地土壤呼吸方面的研究热点。
3 不同组分有机碳的固碳潜力
运用物理技术分组法、化学技术分组法和生物技术分组法将土壤有机碳分为不同的形态,从而分离出的活性有机碳、缓性有机碳和惰性有机碳。Parton等(1987,1989)根据有机碳周转时间的不同将土壤有机碳库划分为活性碳库、缓性碳库和惰效性碳库[38-39],土壤活性碳库易被土壤微生物分解矿化,对植物养分供最直接作用。缓效性碳库指介于活性和惰效性碳库之间的那部分,惰效性碳库化学性质和物理性质较为稳定,对于土壤的固碳和积累作用较强,是最具有固碳潜力的一种有机碳形态[40]。
3.1 固碳差异性的表现
土壤碳固存始终与有机碳积累有密切关系,杨丽霞等(2006)模拟结果表明:各土壤剖面的土壤活性碳库一般占总有机碳的0.5%~7.6%,平均驻留时间为41~64天;缓效性碳库占总有机碳的45%~71%,平均驻留时间为3~30年;采用酸水解法测定惰效性碳库的库容,一般占总有机碳的20%~50%,并且缓效性碳库和惰效性碳库从表层到下层其含量锐减[40]。活性有机碳占的百分比越大,说明有机碳质量也就越高,越易被微生物分解,有机碳的稳定性也就越差[41]。缓效性碳库的固碳时间以年为单位,较活性碳库分解慢。惰效性碳库由于它的物理和化学性质更为稳定,分解速率慢、固存时间长达50年乃至几千年[13]。
3.2 固碳差异性原因分析
影响土壤有机碳稳定性及固碳潜力的因素主要有土壤的物理性状,土壤生物,以及人为因素等。许多研究者认为,不同粒径土壤团聚体及土壤基本颗粒中有机碳的含量及质量存在明显的差异[42]。不同的环境因子对土壤的PH值、土壤三相、微生物、土壤温度、水分的影响是研究土壤不同碳形态固碳差异的核心内容。不同的土壤生物对土壤的固碳也较明显,Moore J C等(2003)强调了根际细菌和真菌与各自对应的微型土壤动物驱动有机碳的积累和稳定过程[43]。以上三个主要影响因素造成了不同组分碳的固碳差异性,而最根本的还是不同碳形态本身的抗物理和化学性质。活性碳库又是容易被微生物分解矿化的那部分有机碳,Skogley等,(1994)指出,活性有机碳是作为碳源和能源和能被微生物利用的有机物。因此活性有机碳的固碳时间和潜力要明显低于抗物理和化学性质教强的缓性有机碳和惰性有机碳[44]。
4 活性有机碳组分与碳排放的关系
温室气体是指大气中自然或人为产生的的气体成分,它们能够吸收和释放地球表面、大气和云发出的热红外辐射光谱内特定波长的辐射。湿地在化学元素循环中,特别是在CO2和CH4等温室气体的固定和释放中起着重要的“开关”作用,被称之为“转换器”[45]。二氧化碳和甲烷作为主要的温室气体,它们的增温效应分别占70%和23%[46]。CO2和CH4排放主要受水分和温度变化的控制。当湿地排水后,CO2和N2O的排放量大大增加,而CH4的排放量减少[47]。全球天然湿地CH4排放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22%,稻田CH4排放量占全球排放总量11%[48]。这一部分排放的碳主要是活性有机碳,这种碳形态对温室气体的影响非常之大。
4.1 活性有机碳与CH4排放的关系
沈宏等(1999)研究,土壤活性有机碳是微生物生长的速效基质,其含量高低直接影响土壤微生物的活性,从而影响温室气体的排放[24]。土壤DOC的含量与CH4产生量显著相关,增加淹水土壤活性有机碳含量可以增加CH4生成量[49]。很多研究也表明土壤活性有机碳与 CH4排放量有显著关系,Wang等(1992)研究指出,土壤可溶性有机碳和微生物量碳与CH4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50]。Yagi等(1990)人研究指出,CH4排放量和易矿化碳呈明显的线性关系[51]。
4.2 活性有机碳与CO2排放的关系
湿地土壤有机碳储量与温室气体排放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特别是活性有机碳能够灵敏、准确、真实地反映土壤有机碳的存在状况以及土壤质量变化,提高土壤活性碳库有利于提高土壤肥力从而增加作物产量和实现土壤固碳减排的效果紧密相连。有研究表明,土壤总有机碳与产量关系不明显,进而探索活性有机碳(比如水溶性有机碳、微生物量碳、易氧化态碳),发现作物产量以及大气的固碳减排与土壤活性有机碳显著相关。
5 结语
目前对于土壤碳形态分组的研究较多,大多数都是通过物理、化学、生物技术法对土壤进行形态分类,表述形式各有不同,但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它是由活性的有机碳、缓性的有机碳和稳定性有机碳所组成。而其中活性碳库又是与碳排放温室气体排放等紧密相关的。因此,在研究土壤碳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中,应加强对有机活性碳的研究。在湿地生态系统中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活性碳组分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今后应加强湿地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这一研究方向对土壤活性碳库组分的影响研究,在人类活动下对湿地生态系统的科学管理和合理的农业开发利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与此同时继续加强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有机碳组分与碳排放、碳固定的研究,为农业和生态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1]刘子刚.湿地生态系统碳储存和温室气体排放研究[J].地理科学,2004(5):634-639.
[2]潘根兴,李恋卿,郑聚锋,等.土壤碳循环研究及中国稻田土壤固碳研究的进展与问题[J].土壤学报,2008(5):901-914.
[3]王霞,马钊,樊媛.土壤有机碳组分及农业提高措施的研究进展[J].吉林农业,2011,12(262):93-94.
[4]LalR.Soil carbon sequestration impacts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food security[J].Science,2004,304:1623-1627.
[5]张国,曹志平,胡婵娟.土壤有机碳分组方法及其在农田生态系统研究中的应用[J].应用生态学报,2011,22(7):1921-1930.
[6]霍连杰,纪雄辉,吴家梅,等.土壤有机碳分类研究进展[J].湖南农业科学,2012,(1):65-69.
[7]Tiessen H,Stewart J W B.Particle-size fractions and their use in studies of soil organic matter II.Cultivation effects on organic matter composition in size fractions [J].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Journal,1983,47:509-514.
[8]vonLützowM,Kgel-KnabnerI,EkschmittK,etal.SOMfractionation methods:Relevance to functional pools and to stabilizationmechanisms[J].SoilBiologyandBiochemistry,2007,39:2183-2207.
[9]GregorichEG,BeareMH,McKim UF,etal.Chemicaland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hysically uncomplexed organicmatter[J].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Journal,2006,70:975-985.
[10]John B,Yamashita T,Ludwig B,et al.Storage of organic carbon in aggregate and density fractions of silty soils under different types of land use[J].Geoderma,2005,128:63-79.
[11]Logninow W,WisniewskiW,Strony W M,eta1.Fractionation of organic carbon based on susceptibility to oxidation[J].Polish Journal of Soil Science,1987,20:47-52.
[12]Chan K Y,Bowman A,Oatesl A.Oxidizible organic carbon fractions and soil quality changes an oxic paleustalf under differentpasture leys[J].Soil Science.,2001,166(1):61-67.
[13]Patton W J,Schimel D S,Coleand C V,et a1.Analysis of factors controlling soil organic mater levels in Great Plains grasslands[J].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Journal,1987,51:1173-1179.
[14]周脚根,黄道友.土壤微生物量碳周转的研究方法和影响因素[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06,14(2):131-134.
[15]InsamH,DomschKH.Relationship between soilorganic carbon and microbial biomass on chronosequences of reclamation sites[J].Microbial Ecology,1988,15:177-188.
[16]Haynes R.Labile organic matterfractions as central components of the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soils:An over-view[J].Advances in Agronomy,2005,85:221-268.
[17]Jenkinson DS.1977.Studieson the decomposition of plantmaterial in soilV.The effects ofplant cover and soil type on the lossofcarbon from14C labelled ryegrassdecomposingunderfield conditions[J].Soil Sci,28(3):424-434.
[18]Kucharik CJ,Foley JA,DelireC,etal.Testing the performance of a dynamic global ecosystem mode:l Water balance,carbon balance and vegetation structure[J].Glob Biogeochem cycle,2000,14(3):795-825.
[19]徐明岗,于荣,王伯仁.土壤活性有机质的研究进展[J].土壤肥力,2000(6):3-7.
[20]吴建国,张小全,徐德应.六盘山林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土壤有机碳的矿化度[J].植物生态学报,2004.28(5):657-664.
[21] Elzein A,BalesdentJ.1995.Mechanistic simulation ofverticaldis tribution of carbon concentrations and residence times in soils[J].SoilSciSocAm J,59:1328-1335.
[22]宋长春,王义勇,阎百兴.土壤水热状况动态及沼泽湿地耕作后的N变化[J].环境科学,2004.25(3):150-154.
[23]辛 刚,颜 丽,汪景宽.不同开垦年限黑土有机碳的变化[J].土壤通报,2002.33(5):332-335.
[24]沈宏,曹志宏,胡正义.土壤活性有机碳的表征及其生态效应[J].生态学杂志,1999,18(3):32-38.
[25]王艳芬,陈佐忠,LarryTieszen.中国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土壤有机碳的分布[J].植物生态学报,1998.22(6):545-551.
[26]段正峰,傅瓦利,甄晓君,等.友岩溶区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有机碳组分及其分布特征的影响[J].水土保持学报,2009(4):109-114.
[27]何振立.土壤微生物量及其在养分循环和环境质量评价中的意义[J].土壤,1997(2):61-69.
[28]van Veen J A,Merckx R.Plant and soil related controls of the flow of carbon from roots through the soil microbial biomass[J].Plant and soil,1989,115:179-188.
[29]Marumoto T J,Domsch K H.Mineralization of nutrients from soil microbial biomass[J].Soil Biol.Biochem,1982,14:469-475.
[30]Powlson D S.The effects of biotical treatments on metabolism in soil:Gramm irradiation,autoclaving,air-drying and fumigation[J].Soil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1976,16:459-464.
[31]张付申.土娄土和黄壤土在长期施肥下对土壤的可氧化稳定性研究[J].土壤肥料,1996(6):32-36.
[32]邰继承,靳振江,崔立强,等.不同土地利用下湖北江汉平原湿地起源土壤有机碳组分的变化[J].水土保持学报,2011(6):124-128.
[33]李典友,潘根兴,陈良松,等.安徽六安市表层土壤有机碳的空间分布及尺度变异分析[J]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2008,24(4):37-41.
[34]赵海超,刘景辉,张星杰.春玉米种植密度对土壤有机碳组分的影响[J].生态环境学报,2012,21(6):1051-1056
[35]曾从盛,钟眷棋,仝川,等.土地利用变化对闽江河口湿地表层土壤有机碳含量及其活性的影响 [J].水土保持学报,2008,22(5):125-129.
[36]张金波,宋长春,杨文燕.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水溶性有机碳的影响[J].中国环境科学,2005,25(3):343-347.
[37]黄靖宇,宋长春,宋艳宇,等.湿地垦殖对土壤微生物量及土壤溶解有机碳、氮的影响[J].环境科学,2008,29(5):1380-1387.
[38]Parton,W J,Schmi elD S,Cole C V,Ojmi a D S.Analysis of factors controlling soil organicmatter levels in Great Plains grasslands[J].Soil Science Society ofAmerica Journa,l 1987,51,1173-1179.
[39]PartonW J,Sandford Jr,R L,Sanchez P A,Stewart JW B.Modeling soil organicmatter dynamics in tropical soils[J].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Journa,1989 39:153-171.
[40]杨丽霞,潘建军,阮韶峰.森林土壤有机碳库组分定量化研究[J].土壤通报,2006(4):241-243.
[41]朱志建,姜培坤,徐秋芳.不同森林植被下土壤微生物量碳和易氧化态碳的比较[J].林业科学研究,2006,19(4):523-526.
[42]刘连友,王建华,李小雁,等.耕作土壤可蚀性颗粒的风洞模拟测定[J].科学通报,1998,43(15):1663-1666.
[43]Moore J C.Top-down is bottom-up:Does predation in the rhizosphere regulate aboveground dynamics[J].Ecology,2003,84(4):846-857.
[44]JohnsM,Skogley E.Soil organic matter testing and labile carbon identification by carbonaceous resin capsules[J].Soil Science Society ofAmerica Journal,1994,58:751.
[45]马安娜,陆健健.湿地生态系统碳通量研究进展[J].湿地科学,2008(2):116-123.
[46]NnobyR.Carbon cycle:inside the black box[J].Nature,1997,388:522-523.
[47]潘根兴.中国土壤有机碳、无机碳库量研究[J].科技通报,1999,15(5):330-332.
[48]王明星,李晶,郑循华.稻田甲烷排放及产生、转化、输送机理[J].大气科学,1998,22(4):600-612.
[49]Vermoesen.A.Ramon,H.Composition of thegas phase and hydrocarbons[J].Pedologie,1991,22:119-132
[50]Wang Z P,Delaune R D,Lindau C W.Methane production from anaerobic soil amended with rice straw and nitrogen fertilizer[J].Fertilizer Research,1992,33:115-121.
[51]YagiK,MinamiK.Effectsoforganicmatterapplicationonmethane emission from someJapanese paddy fields.Soil Sci[J].Plant Nutr.1990,36:559-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