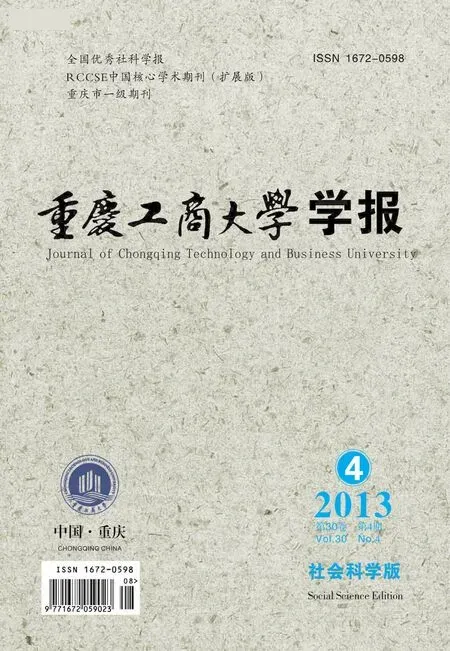传媒商业化下的新闻民工的生成与行为*
商建辉
(河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河北 保定071002)
新闻从业者作为媒体的人力资源,不但是媒体理念的践行者,而且其行为已成为塑造媒体的重要力量。
一、负责任的传播者变为养家糊口的新闻民工
在传媒商业化的道路上,在媒体内外的压力下,“中国新一代新闻工作者正在陷入严重的工作和生活窘地。在一个饥肠辘辘的中国商业化媒体环境里,中国的记者正在变成一个整天为自己生活奔波养家糊口的人”。[1]
(一)工作压力巨大
阿尔·佐丹奴教授认为,美国的许多商业传媒都已经变成了年轻人的“血汗工厂”,年轻人在其中承受着外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2003年《纽约时报》丑闻的调查文章其实只是展示了“商业媒体黑暗海洋上的冰山巨大一角”。佐丹奴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7个月见报73篇文章,平均每个月10篇,每三天一篇。按每周5个工作日计算,在《纽约时报》编辑部,这个刚上路的新手平均两天要发表一篇文章。另外,不要忘了他的特点是到外地频繁出差写“真人故事”。这意味着他要处在怎样的压力之下[2]。《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2010年10月载文称记者成了“奔跑的仓鼠”。文章说:“编辑部的人数不断减少,任务却一直增加。一个NBC的白宫首席记者,一天要做16个出境采访,主持一档节目、客串两档新闻节目,还要在Twitter和Facebook上更新8~10次,写3~5篇博文。和他一样,大部分记者忙碌如转盘上不停奔跑的仓鼠,强调速度,追求数量”。揭开英国报业“窃听”丑闻的英国著名记者尼克·戴维斯在《媒体潜规则》一书中曾披露一名年轻的新闻专业毕业生记录自己在地方报工作一周的经历,比《纽约时报》的记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周一到周五,他的成稿数量分别是11篇、10篇、7篇、13篇和7篇。
这种在西方商业化媒体中存在的现象,在中国媒体中已初露端倪。学者陆高峰2009年在29个省、市、自治区做的报业从业者的调查报告显示:超过八成的报业从业者认为工作压力很大或较大。认为报社工作压力很大和较大的从业者分别为39%和43%,总体达到82%。而认为工作压力很小和较小的只有2%,两者各占1%。只有16%的报业从业者认为报社工作压力为一般。[3]依据同一作者2009年在24个省、市、自治区做的广电从业者调查报告,广电从业者对工作压力的评价指数与报业差异不大。近八成广电从业者认为工作压力大。其中认为很大的占44%,较大的占35%,而认为较小和很小的只有1%。认为很大的人员比例比报业高出5个百分点。[4]。2004年记者节前夕,东方网与《新闻记者》杂志组织并联合千龙网、北方网、红网、大洋网等全国知名新闻网站,进行了“中国新闻记者公众形象”的网络调查。在谈到记者的职业压力时,调查结果显示:93.3%的人认同记者的职业压力是比较大的,仅有6.7%的公众认为压力较小。[5]看来新闻从业者压力大这一点也是被公众认同的。
这一点,从新闻从业者的超时工作现象中可见一斑。2006年,《青年记者》杂志对全国各大报业集团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平均每天工作9~12小时的新闻从业者占到总数的63%,不到8小时的仅占18%,甚至16%的传播者每天工作11~13小时。[6]2009年,在陆高峰的调查报告中这种情况仍在继续,“每天工作在8小时以内的不足三成,而工作在10小时以上的近四成。报业从业者每天工作时间在8小时以内的只有29%,其余71%的从业者每天工作时间在8小时以上。其中,每天工作在8~10小时的占35%,在10~12小时的占24%,在12小时以上的占12%”[7]。广电从业者的状况一样糟糕,超时工作程度总体高于报业。“近八成广电从业者每天工作时间在8小时以上。其中,在8~10小时的占49%,10~12小时的占19%,12小时以上的占7%,而每天工作在8小时以内只有25%。每天工作在8小时以内的人员比报业少4个百分点,而在8~10小时的比报业高出14个百分点。”[8]2010年,周红丰在《上海地区记者生存状态调查》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该文指出:在不少媒体单位中,超时加班成为一种常态。被调查对象中58.4%的记者每天工作8~12小时,甚至还有15.1%的记者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而且61.8%的记者从未领取过加班工资。
《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2010年在谈到工作压力时的话也可作为这种状况的佐证。“对《三联生活周刊》许多记者来讲,压力非常之大。我们的运作非常严格,每周二定选题,把一周的工作全部确定下来,就各自为政,记者从星期三开始飞到全国各地去采访,有三天的时间,星期六回来写稿子,星期天开始发稿,对他们来讲每周的压力都非常大。我们有个年轻的记者,去年入职的,北大新闻系的硕士,到了今年过春节的时候来找我,说他打算要走了,我说为什么年轻轻刚来就走,好不容易办进来解决了户口。他说他实在是受不了压力了,去年一年走遍了整个中国,宁肯去当公务员。这就是《三联生活周刊》的压力。”[9]让我们再看几个调查记者个案。现供职于《瞭望东方周刊》的朱雨晨,常常整月整月地在外出差,“宾馆的标准间都很相似,有时在早晨醒来,竟想不起自己是在哪里?在干什么?”他的女友在另一家媒体工作,他们因此时常遭遇“这个在虹桥机场降落,那个在浦东机场起飞”的“巧合”。李玉霄曾在一年里对七宗灾难事件予以调查报道,钱钢评价说:“别的记者的死亡人数是从公文里抄来的,李玉霄的死亡人数是一个一个地偷偷数尸体数出来的,谁能想象,他要承受多么大的心理压力?”[10]
这种状况也可以从媒体从业者身心疲惫指数中看出。学者陆高峰2009年在29个省、市、自治区做的报业从业者的调查报告显示:八成以上报业从业者认为自己的身心状态是比较疲惫或很疲惫。报业从业者中感到充满活力和较有活力的分别只有1%和7%,而感到很疲惫和比较疲惫的分别为26%和48%。只有18%的从业者对自身疲惫指数的评价为一般。[11]广电从业人员的身心疲惫指数与报业基本接近。超过七成的广电从业者对自己身心状态的评价是比较疲惫和很疲惫,两者分别占44%和30%。感到比较有活力和充满活力的分别为7%和2%,只有17%的感到一般。[12]2007年记者节前夕,《青年记者》联合全国20个大中城市的媒体开展了“记者节业内问卷调查”也展示了同样的状况。当问道“用一两个词来描述您今年的工作状态”时,回答不约而同的是“疲劳”。
(二)收入低、社会保障差
在如此大的压力下工作的新闻从业者,其薪酬和社会保障与其工作压力并不匹配。2003年3月至4月,中国社会保障杂志社同中国传媒网进行了一次媒体从业人员社会保障情况的互联网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目前大概有近百万新闻工作者或者媒体从业人员,其中43%的人没有任何劳动合同、没有工资、没有工作证、没有记者证、没有社会保障。有的干了半年,也没有人发给他工钱,其生活和工作的窘境不比那些在城市打工的弱势的农民工好多少,因此被人称为“新闻民工”。[13]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情况并未改善。学者陆高峰2009年在29个省、市、自治区做的报业从业者的调查报告显示:收入满意度差,对当前收入不满意或很不满意的超过一半。从业者中对收入感到很满意和较满意的只有16%,分别占到1%和15%,而感到很不满意和不满意的占到53%,分别为16%和37%,只有31%的从业者对收入满意度的评价为一般[14]。广电从业者的收入满意度比报业从业者还低,认为很不满意的人数比报业高出5个百分点。超过一半从业者对当前收入不满意或很不满意。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分别占33%和21%。而认为较满意和很满意的分别为11%和2%。其余33%的认为一般。[15]不仅目前的薪酬水平不能让从业者满意,甚至还有下降的趋势。《财经》杂志主编何刚发现,如果以购买力计算,十年前,《南方周末》和《财经》杂志为代表的一批新锐市场化报刊,其核心成员月收入在1万元以上,但十年后,这些媒体的核心人员虽然收入也明显增加,但其购买力缩减了近一半[16]。
不仅薪酬相对较低,新闻从业者的社会保障也不尽如人意。学者陆高峰的调查显示:①近三成从业者不能或基本不能享受到“双休”权利;②不能和基本不能享受到法定节假的近两成;③超过四成从业者从没有享受过带薪休假权利;④四分之一从业者没有与所供职单位签订劳动合同;⑤近四成从业者所在单位没有为其上缴“三险一金”;⑥近三成从业者所在单位没有为其申领记者证。[17]广电从业的情况与此大同小异。
其中调查记者保障最差,除了那些“寄居”中央大媒体的外,大部分还属于“流浪记者”,同“在编记者”比起来,他们没有编制,没有户口,没有职称,甚至也没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记者证。他们的权益常常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一旦出现闪失,马上会被所服务的单位炒掉,成为媒体原始积累时期的牺牲品。[18]
(三)健康状况堪忧
近年来,针对新闻从业者健康状况的调查此起彼伏,甚是热闹,既有全国范围的,也有地域范围的;既有实地调查,也有网络调查。本文以这些调查结果为依据分析新闻从业人员的健康状况。2000年,上海市新闻从业人员健康状况抽样调查报告显示,自认为身体很好或较好者仅为26.5%,而绝大多数(69%)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的身体一般或不好,可见新闻从业人员的总体健康水平偏低。而且被调查者最近一次的健康普查也证明了这一点:健康者仅为18.4%,患病者为8.9%,亚健康者则高达47.3%[19]。
新浪网2003年推出的《媒体从业人员调查》结果显示,超过80%的国内记者认为自己处于亚健康状态[20]。陆高峰2009年的调查显示:近六成广电从业者较多和经常为自己的健康状况担心,两者分别占25%和33%,而较少和从不担心的分别仅为2%和0,其余40%从业者为偶尔担心。经常和较多为自己健康状况担心的广电从业者人数比报业少4个百分点,而较少和从不为自己健康状况担心的人数同样也比报业少4个百分点。[21]报业的状况更为严重,六成以上从业者经常或较多为自己的健康状况担心。从业者中经常和较多为自己的健康状况担心的分别占到32%和30%,总体达到62%。而从不和较少为自己健康状况担心的分别只有2%和4%。[22]
2011年的《法治周末》发起媒体人身心健康调查结果也不容乐观。超九成的受访者表示对目前的工作感到压力太大,近八成受访者长期处于焦虑状态。媒体人的身心健康问题日益凸显,不容忽视:“白发、胃病、颈椎病、失眠、焦虑甚至抑郁”。以上这些调查的结果都为新闻从业人员的健康状况敲响了警钟。
2011年,媒体人接连离世的消息,成为圈中热议话题。“累心”“焦虑”是大家公认的媒体人常态。
一位供职于西南某媒体的同行说:“我们这里同城报纸多,竞争非常激烈。跑社会新闻,忙是种常态。手机24小时不敢关机。见线上联系人的时间远多于见父母的时间。忙还不怕,不忙更焦虑——没稿子啊,但每个月考核既有量的压力,又有质的压力,甚至还有独家新闻的压力——这时候特别焦虑,晚上常失眠,做梦也梦见去扒新闻。”
一位曾供职于北京某媒体的陈小姐因为受不了这种压力而选择离职,“那段日子我快疯了。真找不到稿子写的时候,头发还大把大把掉。心情特别不好,逮谁都想吵架。我都觉得我快抑郁了,去看了心理医生。后来听从医生的建议,干脆选择了辞职。”
媒体记者的压力,演员姚晨也很有感慨。她发了微博说:“一位从事社会新闻类工作的记者老友,最近患上严重抑郁症。我劝他:换个口儿,跑娱乐……他乐:我还是去娱乐那些社会败类吧……挂了电话,心里难过……珍重,朋友”。[23]
(四)新闻从业者的自主性不足
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常常怀抱新闻理想,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使命,所谓“初生牛犊不畏虎”,但在进入媒体后,一方面,新闻从业者必然继续受到行政力量的干涉,主管部门依然牢牢决定着新闻从业者最终的话语权,王家岭矿难事故现场严格的凭证进入,《南方都市报》采访奥巴马开天窗一事,宜黄拆迁案的新闻媒体后期失声都是极为有力的证明[24]。同时,记者的新闻报道活动有着很强的官方烙印,他们常常是依靠媒体作为党的部门的威慑力来完成采访的,也就是说,“很多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往往是待其盖棺定论之后再采访,而不是新闻记者独立观察的结果,是记者根据有关方面的调查结果进行的再报道。”[25]比如,1998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对“建国第一税案”的采访是中组部通知并安排的,《北京青年报》对海南贪官戚火贵的报道事实上是法院判决之后的再报道。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许多贪污腐化大案如周北方、王宝森、陈希同、邓斌、成克杰等案的报道以及其他高级干部的报道也是比较被动的。以舆论监督著称的中央电视台的两大栏目《新闻调查》与《焦点访谈》报道过有关腐败的23件大案曾编成一本书《抨击腐败》出版,但那23件大案无一是媒体首先开始调查的。2000年7月20日《南方周末》头版上刊登的“丽水怪案何时真相大白”,标题上已注明“在调查机关帮助下,本报记者调查‘卢氏黑帮’新闻揭露的是浙江丽水的一个作恶多端的黑社会性质的团伙以及它背后的关系网黑幕”。在文中,记者也多次提到“在检察院的支持和帮助下”,文内大量内容也是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南方周末》2001年2月8日的“民权法院有个造假院长”也是“盖棺论定”后的采访。[26]2001年《新闻调查》播出的《厦门特大走私案》同样是在相关部门对案件进行了查处以后才进行了报道[27]。另一方面,他们又会感觉到“无处不在的经营创收氛围”,在日常的新闻采编中,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常常受到商业主义的打压,“媒介从业者在媒介机构内相对于经营部门的独立性被削弱,这种削弱集中表现在经营部门插手新闻的选材、新闻的处理及对待与媒介有业务往来的广告主的言论态度上”[28]。
2002年针对上海新闻从业者的调查报告显示:上海新闻从业者中,对于在自己所从事的新闻工作中获得的工作自主性,平均自主程度为5.9[29](各项指数1为“最低”,10为“最高”)。这样的结果在调查记者的身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2009年陆高峰的调查表明,超过四成从业者认为当前工作中自主性程度较低和很低,而认为较高和很高的不足两成。其中认为较低和很低的分别为28%和16%,认为较高和很高的分别为15%和1%。广电从业者对工作自主性评价与报业相差不大,总体略低于报业[30]。
与此同时,记者调查的独立性也大大减弱,调查记者群体的表现是更好的试金石。在一次采访中,王克勤是这样描述自己的:“我们的社会就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中的大船,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守望者,要随时发现航行中可能会碰到的暗礁,随时发现船上的哪个螺丝钉可能会坏,把大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及时地向船长汇报”。但王克勤随后的遭遇却是非常尴尬的:他发现了暗礁,但船长却没有转动手中的舵轮;他找到了锈蚀的螺丝钉,但检修工却警告他不要多管闲事。[31]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组,比例太高的选题被否决也令他们疑惑:究竟中国目前是否已经具有了真正做“调查报道”的条件?《新闻调查》还能生存多少时间?[32]
在如此背景下,新闻从业者曾怀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常常被撞击得粉碎,其热情逐渐冷却,其锐气日渐消磨,其理想日渐放下,其烦恼日渐呈现,他们逐渐被媒体塑造为生产线上循规蹈矩的新闻民工。
二、新闻民工的选择
既然沦为新闻民工的处境,那么,他们会首当其冲将“铁肩担道义”放在一边,而将妙笔挣金钱放在首位了。
(一)进行“便宜”的报道
这条规则鼓励简单、容易出活的、容易获得的新闻,也就是说一个新闻能否被报道除了受该题材的精彩程度影响外,还会受到诸如距离、交通、通信以及报道的难易程度的影响,可能后面的因素更具决定力。《洛杉矶时报》记者汤姆·罗森斯蒂尔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上发表文章称:“今天的报纸和杂志的采访越来越多地通过电话进行,记者们搜集来的故事差不多和自己采访的一样多。从电子文稿、数据库和电视资料中收集素材,记者们承认,越来越多重要事件的报道他们都不在现场……”[33]英国记者尼克·戴维斯曾以自身的亲身经历表达了这样一个观念:新闻发生地离舰队街越近,越有可能被报道。他写道,20世纪90年代末,他报道了发生在孤儿院的性侵犯事件。在听证会上,孤儿院的员工、受害者宣誓提供证词,陈述了包括警官、社会工作者在内的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诸如如何对小男孩动手动脚、实施强奸等,并指责官方对此置之不理,以至于此类事件持续发生了很多年。当时的场面感人,但听证席的最后两排留给记者的座位却空着。并非因为这个故事不够好,而是因为听证会在北威尔士举行,这里离舰队街太远,媒体不想费心来报道。[34]
与尼克·戴维斯一样,《鲁中晨报》副总编辑刘成广发出了同样的感慨,“让记者深入下去,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由于有了严格地按工作量考核的制度,年轻记者变得越来越‘功利’,一个稿子如果10分钟能采访到‘足够’的材料,他绝对不会待上20分钟;如果一次能够采访完,他绝对不会去第二次,更不会在稿子见报后给读者一个反馈”。[35]
一位记者的现身说法也证明了这件事。这位记者描述到,“一般来说,现在的节目制作都实行经费包干制度,一期节目制作下来,比如经费是六千元,那么,采访的时间越短,所花的费用越低,落到自己腰包里的钱就越多。这就决定了他们尽可能选择成本低一点的、容易做的题材,于是城市题材占的比重就要大多了。而且,对于外聘的记者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他们制作的节目只有被播出才能报销费用,因此到太远的地方或选择代价和风险太大的题材如舆论监督是不大可能的。”[36]这位记者总结归纳他们选材的标准时提出了距离、交通、通讯、语言、风险等方面的内容,距离、交通、通讯和风险与成本和节目制作难度有关。
(二)进行自我审查
科学家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把跳蚤放在桌上,一拍桌子,跳蚤迅速跳起,跳起高度均在其身高的100倍以上,因此跳蚤被称为世界上跳得最高的动物!然后,科学家在跳蚤的头上罩上一个玻璃罩,然后让其跳动。跳蚤第一次起跳就碰到了玻璃罩,连续多次以后,跳蚤调整了自己能够跳起的高度来适应新的环境,此后每次跳起的高度总保持在罩顶以下。科学家们逐渐降低玻璃罩的高度,跳蚤又经过数次碰壁之后主动调整了高度。最后,玻璃罩接近桌面,跳蚤无法再跳了,只好在桌子上爬行。经过一段时间,科学家把玻璃罩拿走了,再拍桌子,跳蚤仍然不会跳,“跳蚤”变“爬蚤”了。“跳蚤”变“爬蚤”,不是因为已经失去了跳跃的能力,而是一次次受到挫折之后学乖了,习惯了,变得自我设限了。
犹如“跳蚤”跳高的故事,当新闻从业者在内心深处认同“新闻民工”这样的概念,为了更好生存,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利益,避免因触怒各方面而遭降职或解雇,他们可能会“自我设限”——“记者放弃撰写明知不被编辑采用的新闻事件。”[37]
在美国的一份研究中,接受调查的记者和新闻机构总裁中超过40%承认通过进行自我审查来有意回避具有新闻价值的故事或者更广泛的受众,市场压力被认为是在列举的十种解释自我审查原因中最重要的一个。在被调查的人员中有80%受访者认为重要的故事常常看起来乏味,因此有些会被回避;同时有超过50%的人指出重要却复杂的故事有时候或者常常都遭到忽视。超过三分之一的回复者表示他们进行自我审查是因为对于个人事业的考虑[38]。美国评论家戴安娜·欧文这样看待这一问题:“20世纪80年代,在地方性的媒介市场逐渐被垄断式公司经营所排挤后,记者们往往倾向于在报道中采取一种‘谨慎行事’的态度,以避免得罪公司的支持者。”[39]
在英国,面对一些游说集团制造的令人恐怖的气氛时,BBC的一位资深记者说:“如果《今天》的节目主编预料到某篇报道会招致大规模的投诉,他会三思而后行。游说集团肯定起作用,我可以列举出无数的例子”。[40]在国内也是如此,张洁在2003年被任命为《新闻调查》制片人时所面对危机之一为新闻从业者在生存压力下的自我审查,下面这段话是新闻从业者真实生活的写照:
《新闻调查》这个栏目的从业人员90%以上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1996年招兵买马时,这些平均年龄30出头(这个年纪才有足够的阅历、资历和经验,才能应对45分钟市场的挑战)的从业人员考虑的可能更多的是借这个平台实现自己的电视理想。但七年之后,对于这批已经奔40岁的人来说,生活压力日趋沉重,上养老下养小,他们要在北京生存,以前是租房子,现在是贷款买房子。我们的从业队伍经济上的压力或者经济上的需求,这几年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他认为,“在这种背景下,对这些新闻从业者来说,很有可能在做节目的时候首先脑子里想的是保播出,什么样的节目最安全,什么样的节目播出系数最高,我就做什么样的节目,而不是选择最难做的、最艰难的、最承载我们的品质和理想方向的选题。”[41]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个好的调查性报道选题,因为难度和风险比较大,有时候题在题库里放了3个月甚至半年都没人去领[42]。
(三)进行权力寻租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尚未建立完全的市场经济,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仍未完全发挥。权力依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利用权力追求非生产性收益的活动就是寻租活动。最早提出寻租思想的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开创者戈登·塔洛克教授,但其寻租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直到1974年安妮·克鲁格(A.krueger)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以后,才真正启动了寻租理论研究的大幕。所谓“寻租”是指“寻求直接的非生产性利润(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通过从事非生产性活动而获得利润的方法。”
这种寻租活动运用到新闻报道就成为“新闻寻租”。所谓新闻寻租是指,“新闻界或新闻从业人员利用手中的新闻报道权、舆论话语权和媒体传播权转移财富分配,为团体或个人谋求不正当利益,对其他社会主体利益造成损害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43]。这里的新闻寻租特指新闻从业者的行为,而非媒体的行为。
从前文可以看到,一些新闻从业者认为新闻工作“工作辛苦”但“收入低”,于是他们在新闻采访、报道的过程中试图利用手中的新闻报道权、舆论话语权和媒体传播权获取一些经济的补偿。在新闻从业者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的调查中,有23%的人认为是“采访对象的馈赠”。有些新闻工作者把“有偿新闻”视为增加自己收入的一个“正当”途径,即使其认识到搞“有偿新闻”是一种违规行为。[44]正如一位曾在路透社和《21世纪经济报道》工作过的新闻记者所言,“当前中国记者权力寻租现象已经是制度性的,因为对记者收入的设计里或多或少考虑到这个因素,也就是说记者的劳动价值=记者的公开收入+可能获得的红包收入”。[45]
在这种情况下,新闻从业者的新闻寻租活动就成为了家常便饭。一是采编人员采访新闻,被采访的一方要向他们提供“辛苦费”“劳务费”“餐费”“车马费”。二是采编人员参加各种新闻发布会,即使有些活动不具备新闻价值,并且接受以任何名义或形式赠送的礼金和有价证券。三是被采访单位以合适的理由邀请记者赴外地或出国旅游、疗养。四是企业不惜重金,邀请新闻记者参观企业,参与各种产品鉴定会、新产品新闻发布会、新企业开业会等,以试吃、试穿、试用为名,赠送各种各样的纪念品。五是采编人员收受费用将批评稿、曝光稿撤下不发,搞“有偿不闻”。如2002年6月22日山西省繁峙县义兴寨发生金矿爆炸事故后,当地负责人和金矿矿主为隐瞒真相,向采访事故的11名新闻记者行贿,就是十分典型的案例。六是采编人员向被采访对象索取费用,刊登收费新闻。这种新闻内容有两种:一种褒扬性的真新闻或称“广告新闻”,一种是杜撰炒作的虚假新闻。七是采编人员以方便工作为由长期借用或变相接受被采访单位的车辆、房屋、交通工具。八是采编人员以谋利为目的为企业和单位举办新闻发布会或私自组团采访。九是采编人员顶着新闻记者的头衔,超越记者职权,以自己特殊身份在采访过程中拉广告。十是采编人员利用新闻工作者身份的特点和便利条件,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收“好处费”,数额有时大得惊人。[46]
三、结语
在新闻生产活动中,新闻从业者扮演的角色对其行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目前,新闻从业者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在商业化的背景下已经全部或部分的变质。以报业为例,“记者与报社的关系事实上已成打工者与工厂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的记者仅仅只是把记者这一职业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的现状下,除了少部分尚有职业理想的记者,事实上很难让他们不以各自报社的考核、考评目标为追求目标和衡量标准”[47]。在此种状况下,某些新闻从业者的行为难免走形,这是值得新闻界警惕的状况。
[1]李希光,孙静惟.商业化阴影下的中国下一代记者,新闻记者[J].2004(11).
[2]百年名报《纽约时报》自曝家丑的背后故事[J].王巧丽,编译.新民周刊,2003(6).
[3][7][14][17][22]陆高峰.报人从业生态急需“绿化”——报业从业者生态调查报告[J].传媒,2010(8).
[4][8][12][15][21][30]陆高峰.广电从业者生态调查报告[J].传媒,2010(7).
[5]陈洁.公众眼中的记者形象——东方网与本刊联合调查简报[J].新闻记者,2004(12).
[6]新闻从业状况抽样调查数据统计[J].青年记者,2006(21).
[9]朱伟.周刊遭遇新媒体挑战 培养杂志性格是关键[EB/OL].http://www.sina.com.cn 2010-10-13.
[10]苏朝伟.中国调查性报道的现状与前景[D].中央民族大学,2005:34.
[11]陆高峰.报人从业生态急需“绿化”——报业从业者生态调查报告[J].传媒,2010(8).
[13]孜骏.媒体从业人员社会保障状况堪忧[J].新京报,2004年11月15日.
[16]何刚.正视媒体人的“薪酬危机”[J].中国记者,2011(12).
[18]贾国勇,孙新德.关注调查式记者生存状况[J].检察风云,2005(8).
[19]贾亦凡.“无冕之王”安然无恙乎?——上海市新闻从业人员健康状况抽样调查报告[J].新闻记者,2000(6).
[20]邱慧.商业化运营条件下坚守新闻职业道德的方式[J].声屏世界,2006(5).
[23]李珏.郑州电视台28岁男记者猝死6天内3位媒体人英年早逝 心理专家教你“解压七步法”[N].钱江晚报,2011-5-26.
[24]龚君楠.媒介市场化进程中新闻工作者社会责任缺失原因初探[J].现代传播,2011(3).
[25]张威.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J].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449.
[26]张威.中国调查性报道的困境与挑战[J].青年记者,2006(3).
[27]郭雪婷.电视调查性报道在中国的发展与延伸[D].四川大学,2007:29.
[28]黄晓芳.关于西方媒介市场化的逆向思考[J].国际新闻界,1999(6).
[29]陆晔,俞卫东.社会转型过程中传媒人职业状况——上海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之一[J].新闻记者,2003(1).
[31]孤帆.王克勤的孤独是一种危险[J].公民导刊,2004(12).
[32]张威.中国调查性报道的困境与挑战[J].青年记者,2006(12)
[33]约翰·维维安.大众传播媒介(第七版)[M].顾宜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5).
[34]尼克·戴维斯.媒体潜规则——英国名记揭秘全球新闻业黑幕[J].崔莹,译.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76.
[35]刘成广.记者在居委会上班——《鲁中晨报》社区新闻探索[J].青年记者,2004(8).
[36]徐小立.传媒消费文化景观[M].人民出版社2010:165-166.
[37]马丁·李,诺曼·苏罗蒙.不可靠的新闻来源[J].杨月荪,译.台北:正中书局2002:114.
[38]大卫·克罗图,威廉·霍伊尼斯.运营媒体:在商业媒体与公共利益之间[J].董关鹏,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52.
[39]姜江.无形之网:美国调查性报道的制约性因素简析[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40]尼克·戴维斯.媒体潜规则——英国名记揭秘全球新闻业黑幕[M].崔莹,译.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81.
[41]张洁.市场化压力下的专业主义[M].中国传媒经济(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04:140-141.
[42]唐勇林.公关与反公关——编辑部的故事[M].中国青年报,2006-5-17.
[43]梁君,顾江.新闻寻租的博弈分析[J].当代传播,2009(5).
[44]高崇.从越轨社会学解读“有偿新闻”[J].当代传播,2008(4).
[45]张志安,陆晔.记者“权力寻租”中的社会资本转换及其伦理边界[J].国际新闻界,2008(10).
[46]易鸣璇.我国“有偿新闻”现象研究[D].暨南大学,2011:12-13.
[47]黎勇.“真实”掌握在记者手中?——市场化嫌体内部考评机制与新闻失真[J].青年记者,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