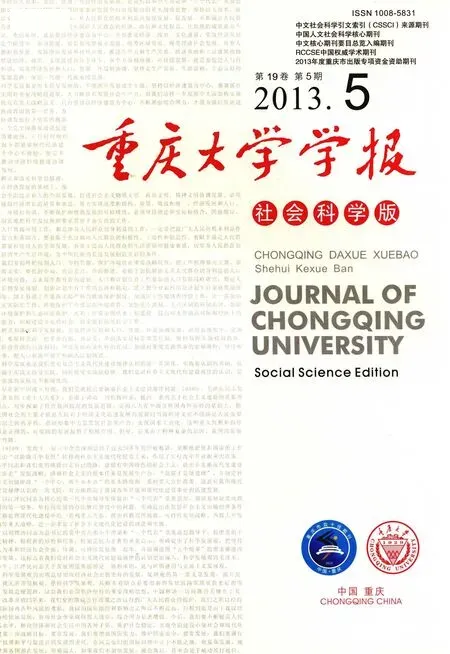土地保障功能下集体林地流转的现实困境与制度完善
秦 鹏,李汝义
(重庆大学a.法学院;b.西部环境资源法制研究中心,重庆 400044)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土地在农民的生老病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保障功能,成为农民最基本也最为重要的保障依托。一方面,广大农民将自身的劳动力与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相结合,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就业保障;另一方面,农民通过对土地的耕作经营所获取的经营性收入构成了农民生育、医疗、养老和丧葬的主要经济来源。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普遍重视耕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而忽视了林地的社会保障作用。实际上,对于“靠山吃山”的山区农民而言,林地在其基本生活保障方面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耕地。在反思林区生活贫困的现实和借鉴耕地承包经营成功经验的基础上,2008年以来,中国各级政府加大力度推进新一轮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将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从耕地向林地延伸。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集体林地划分细碎、林地资源浪费严重、森林生态依然脆弱[1]。要解决集体林地资源利用低效和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不强的问题,需要从制度层面上进一步解决制约集体林发展的问题。
林业作为规模效益比较显著的产业,其资源配置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是目前人类认识到的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方式。只有让森林资源在市场上具有足够的流通性,让更多的社会资本愿意投入到森林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中,才能在整体上激活林业发展潜力,全面提升林业生产力和市场竞争力。
为了加快林业发展,中央要求“加快推进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通过森林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林业的适度规模经营。但是,鉴于中国集体林地所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在坚持集体林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依法将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通过家庭承包方式落实到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并“防止农民失山失地”便成为林权制度改革的基本要求。
可见,集体林地在经济功能的实现所要求的林地集中经营与林地保障功能所导致的林地分散经营之间存在矛盾。这种矛盾也直接导致集体林地流转面临诸多现实困境,林地分散经营的状况得不到改善,集体林业的现代化发展举步维艰。
二、土地保障功能下集体林地流转的困境阐释
从林地流转的过程考察,欲签订有效的林地流转协议:首先,流转双方需要具有交易的动机和需求;其次,需要有方便交易的外部条件和环境;最后,要有规范的交易程序和方式。但从目前的实践情况看,在土地保障功能制约下,集体林地流转面临诸多现实困境。
(一)细碎的林地划分增加了集体林地流转的成本
在土地保障功能下,对每一位农村人口来说,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就成了其基本生存权的体现。而在平等思想指引下,每一位村民所拥有的土地不仅数量要均等,而且土地质量也要均衡,这样农户所拥有的本来就十分有限的承包地,也就被分割成零星的若干小块。有村级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样本村平均每户农民承包林地的面积为1.867 hm2,平均每户承包的林地分为4.5块,细碎化经营特征明显[2]。南方9省(不包括海南省)集体林业用地户均面积0.43 hm2,而且被分成数块[3]。林地划分细碎,单宗林地涉及的转出方就多,要使林地能够实现大面积的集中流转,需要取得各林地转出方的一致同意,这就无疑增加了集体林地流转的交易成本。
(二)固有的保障理念降低了集体林地流转的意愿
目前,在中国由农村集体组织承担其成员的就业安置、病残和养老保险的机制尚未建立,在非农就业岗位不足和就业收入不稳的情况下,广大农民仍把土地作为其安身立命的基本生活资料和外出就业的最后退路。部分林农认为拍卖林地是吃子孙的饭,是“败家子”的行为。这种固有的保障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林地流转意愿。大多数林农宁愿使林地荒芜也不愿意将其流转出去。有研究发现:家庭人数较多且平均年龄较大的农户,其流转出林地的意愿很低。这样的林农往往家庭负担较重,即使林地的产出很低,他们也不愿意转出林地,林地是他们家庭养老防灾的保障[4]。总之,固有的土地保障理念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集体林地使用权人进行林地流转的意愿。
(三)严格的保地政策复杂了集体林地流转的过程
在土地保障功能的制约下,“防止农民失山失地”便成为集体林地流转政策的基本要求。在严格的保地政策下,现行集体林地流转从流转主体资格到流转客体范围,从流转前的审核批准到流转后的经营利用都设置了一定的限制条件。例如,在集体林地流转过程中,集体林地家庭承包经营权的转让不仅需要经发包方同意,而且还要经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有些地方是土地、林业、农业等多家部门审批。这种复杂的流转过程,增加了林地流转的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体林地流转的顺畅进行。学者孟一江等对愿意流出林地的50户进行调研显示,有60%的农户认为流转过程复杂影响了林地流转[5]。
三、土地保障功能下集体林地流转困境产生的制度原因
集体林地顺畅流转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是:集体林地权属主体享有处分权和收益权。然而,土地保障功能下,集体林地承包经营权的处分权能受到不当限制,收益权能又不能充分实现。
(一)集体林地承包经营权的处分权能受到不当限制
现阶段,中国农村土地保障功能的实现主要依靠农民对土地的直接耕种经营,与土地使用权的享有密不可分。因此,在制度安排上,受土地保障功能的制约,对因林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所造成的“失地”持严格的限制立场,林地承包经营权成为一种不稳定、不完全和有条件的物权。
例如,在流转方式上,《土地承包法》第37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3条更进一步指出“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可见,在采取转让方式流转林地承包经营权时,发包方的同意是合同生效的必须要件。
然而,《物权法》和《土地管理法》在赋予村民委员会等组织集体林地所有权行使代表权和经营管理权的同时,对所有权行使主体的权利、义务与责任,林地经营管理主体的管理对象和目的等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从而导致各主体的责权利边界模糊[6]。在实践中,“农民集体所有林”演化成“村委会林”甚至“村干部林”,林业行政管理部门和农村基层政权利用林地管理权和实际上的林地所有权的优势地位,在旅游开发、林地流转等林地权属管理活动中与民争利。
林地承包经营权的处分权能受到不当限制,这一方面过分强化了以发包方为代表的林地所有者的实际控制力,为行政权力和行政手段干预林权流转留下了太大余地;另一方面使得林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属性无法彰显,林权流转的预期收益不明确。林权流转不畅导致林地的规模经营与集约化利用不能展开,林地经营停留在小农经济的低效率程度,严重制约林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的林地使用权制度应以开放自由的流转机制为核心,林地使用权可以摆脱所有权的束缚单独进入商品市场。现存的林地经营效率低下和林农生活依然贫困的问题,表面上看,是因林地担负了农村社会保障功能所致,实际上,是因对林地承包经营权处分权能的限制不当所致。
(二)集体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收益权能不能充分实现
林地是一种特殊资源,既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又能产生重大的生态效益。中国现行立法片面强调林地生态效益保护,而淡化林地经济效益的发挥和林地在民法上的财产属性,致使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收益权能不能充分实现。
随着国家对生态建设的逐步重视,许多地方将属于集体所有的林地或集体所有由农民个人承包经营的林地界定为公益林地,并对其权利行使进行严格限制。此外,商品林地经营者的财产权利也受到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或制度的限制,免费为社会提供生态利益。在这些情况下,国家应该根据物权法规定对林地权属主体的利益损失给予补偿。
中国1998年修改颁布的《森林法》中原则性地规定了生态补偿制度,但是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和系统方法。现实条件下,中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极不完善,具体表现为补偿资金严重缺乏、补偿标准偏低、补偿对象不明确、补偿范围不全面。近年来,中国在“退耕还林”及生态林建设中,仅对生态公益林给予每亩5~10元的低标准补偿,而通过采伐许可证和木材运输管理依旧控制着集体林地上木材的采伐和流通,这种产权约束事实上是社会的生态公益侵占了林农的经济私益,导致集体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收益权能不能充分实现。
从林地生态系统的角度看,林地及其附着物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对象应该是多元化的。除了林木等林产品可以作为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对象以外,还有林地景观等生态利益。因此,一块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应可以通过林木的采伐、林地景观的开发、生态利益补偿等多种渠道获取收益。
然而,在中国现阶段,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收益权能主要是通过对林木的砍伐使之成为木材或获得其他林产品而实现的。未经林地权利人允许,在林地周围发展“农家乐”旅游、建楼堂馆所等开发利用林地景观资源的行为比比皆是。社会主体无偿享用集体林地所提供的生态利益,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收益权能因没有得到法律的全面保障而不能充分实现。林地承包经营的预期收益较低影响了潜在的林地受让方参与林地流转的积极性。
四、土地保障功能下促进和规范集体林地流转的制度完善
在中国目前经济社会条件下,由农村土地承载农业生产与农民社会保障的双重功能还具有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必要性,无视土地保障功能而推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既不符合当下国情也不具备普遍意义,因此稳定现有土地保障的基本架构长期不变是必然的制度选择。在这一制度前提下,既要实现集体林地资源要素向市场的逐步释放,又要妥善解决林农社会保障问题,唯一方法就是将集体林地利用与土地保障相分离,实行集体林地资源有偿使用与自由流转,由集体林地所有权来承担土地保障功能。
(一)由集体林地所有权承载集体林地保障功能
目前,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农村五保供养制度、自然灾害生活救助制度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但是,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基数和低下的农民收入水平决定了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是最大难题。土地是农村最大的财富,如果能够将之转化为市场流通下的土地资产状态,让农民得以以土地所有权收益作为社会保障费用,则有望为各地农民提供长期、稳定、公平的社会保障,同时能够极大地减轻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压力。
就集体林地制度而言,进一步落实农民对农村集体林地的所有权,建立完善的集体林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市场,然后成立农村社区保障组织或者聘请专业化的资产管理机构对所有权的财产性收入即社保基金进行运作,根据安全、保值增值的原则运营,所得收益和利息全部归入基金。农民集体林地所有权的财产性收入包括林地使用权的有偿出让金、林地征收补偿金和森林生态补偿金等一起构成集体林区林农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
只要农民不丧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就能够获得以集体林地收益为支撑的基本生活、养老、医疗和再就业培训等社会保障。如果农民因就业、迁徙、土地征收等因素放弃了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则考虑纳入城镇居民社会保障的范畴。对主动放弃集体成员权的林农,给予其适当的货币补偿,鼓励农民向城市分流。
(二)保障集体林地所有权收益权能的充分实现
凭借集体林地所有权产生的财产性收益来形成集体林区林农社保基金,这是一种间接的、与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价值相联系的保障方式,其实现途径取决于农民对集体林地所有权的价值实现程度。在目前情况下,农民集体林地所有权的实现受到两个方面的威胁:一是来自地方政府借口“公共利益”与开发商相勾结肆意以征地为名侵犯农民林地权益;二是来自村委会无视村民利益主动或被动迎合有关林地流转需求,而林地流转后又肆意截留本来较低的流转价款。
就中国农村目前的现实而言,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实现另行设置一种方式,不仅制度成本过高,而且难以操作。可行的做法是,利用现有的政治资源,将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内容有机地融入其中[7],通过发展民主政治、增强农民集体自决权来消除集体土地所有权实现的障碍,确保农民集体土地权益的真正实现。
当务之急是制定村民自治基本法。该法不仅要体现村民自治的民主精神和自决理念,而且要对村民自治所涉及的基本要素加以明确规定。在诸如集体成员资格的得失变更、自治事务的确定、自治权的内容和救济、自治组织的产生和运行等方面作出更具操作性的规定。当集体林地管理组织的行为偏离集体林地所有权主体的意志和设立目的时,可通过村民自治来纠正;当公权力对集体林地所有权进行不当限制和非法侵害时,也可通过村民自治来对抗。只有这样,集体林地所有权的本来意义和价值才能实现。
此外,集体林地还能够产生巨大的生态利益,承载着巨大的生态价值。长期以来,集体林地生态价值被社会无偿或低偿占用,集体林地所有者并没有得到与林地生态价值相对应的经济利益。因此,通过立法明确林地所有者对森林生态利益的所有权,并构建生态利益市场交易机制,这样既保障了生态建设者的经济利益又满足了社会公众的生态利益需求,还缓解了政府购买生态利益的财政压力,是实现林地经济与生态价值和谐的制度保障。在赋予市场主体经济产权的同时,还必须赋予市场主体对森林资源的生态产权[8]。在德国,通过建立“生态账户”的形式,合法经营产生的生态林效益可以销售[9]。在哥斯达黎加,政府将国内林业碳汇的总量进行统计,将额外的碳汇资源作为国家的碳汇储备,适时地卖给一些外国企业,所得收入的大部分都用来补偿给林主[10]。这些做法,对中国保障集体林地所有权收益权能的充分实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促进集体林地使用权自由且规范地流转
促进集体林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需要修改现行集体林地流转立法中不合理的限制性规定。在目前集体林地流转实践中,地方政府部门以规范林地流转为名限制或变相限制林地流转的现象时有发生。实际上,只要不抛荒林地,农民是否流转,如何流转,以何种方式流转农村林地承包经营权,都应由农民自主决定,农民的意愿必须得到尊重。因此,在集体林地流转制度建设方面,应修改现行立法中不合理的限制性规定,不能通过统一交易市场、评估前置程序、一律实行变更登记等手段加大交易成本,侵害广大市场主体在集体林地流转方面的自由权利。
促进集体林地使用权的规范流转,需要完善集体林地流转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备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林地流转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林地流转中介机构是林地流转双方联系的纽带。只有中介服务机构的建立和健全,才能构建有序的林地流转市场,克服林地流转双方在林地流转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弊端。但目前,集体林地流转的资产评估机构不规范、中介组织欠完善等社会化服务方面的问题严重制约了集体林地的有效流转。为有效保障流转双方的合法权益,必须建立林业法律咨询、技术培训、资产评估、资金筹措担保等林业中介服务组织。目前在利用政策机制培育林地流转中介服务机构的同时,还需要利用法律手段规范中介服务行为,防止因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而影响集体林地流转的效率,也防止中介机构借林地流转之机非法获利行为的发生。
五、结语
现阶段农民集体财产主要体现在集体土地上,对该财产的支配是村民自治的主要内容之一。将林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负载于林地所有权之上,同时促进集体林地自由且规范地流转,既是为了更好地解放林地使用权,体现林地使用权的物权属性,发挥林地的生产要素功能,也是为了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促进集体林地所有权的价值实现。这种变革不是通过诸如“以土地换社保”等将农民土地财产与城市社会保障简单兑换的形式,而是将农村土地制度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结合起来,为农民自身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发展机制。如果能够使集体林地流转既满足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又照顾中国土地保障的现实国情,那么这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就可以说取得了成功,而这种成功又必将为下一轮农村耕地制度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1]黄锡生,本鑫.国后林改时期集体林地承包经营的现实问题与制度完善[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1,32(4):432-435.
[2]贺东航,冬亮,王威,等.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态势与绩效评估——基于22省(区、市)1050户农户的入户调查[J].林业经济,2012(5):-13.
[3]沈文星,范泽华,翁小杰.福建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研究报告[R].中国林业出版社,2008:61.
[4]李彧挥,方苑,陈亮.林农流转出林地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南省安化县为例[J].江汉论坛,2012,(2):14-19.
[5]孟一江,李翔.农户在林地流转过程中的意愿调查与分析——基于对绿水乡农户流转意愿的分析[J].全国商情:理论研究,2010(7):2-74.
[6]邓扶平,徐本鑫.论集体林权流转的制度前提及其立法完善[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33(1):41-45.
[7]胡吕银.在超越的基础上实现回归—实现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理论、思路和方式研究[J].法商研究,2006(6):85-90.
[8]徐本鑫.生态视角下我国集体林权流转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及其实 现路径[J].农业现代化 研 究,2012,33(4):443-446.
[9]中国林业产权制度改革相关政策问题研究课题组.中国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研究进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27.
[10]何沙,邓璨.国外生态补偿机制对我国的启发[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4):6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