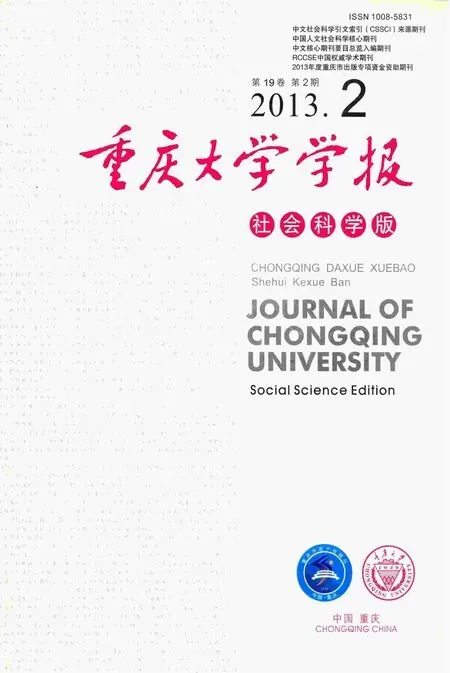中国慈善组织的法律形态及其设立对策
胡卫萍,赵志刚,高志民
(1.华东交通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法学系,江西南昌 330013;2.中国《检察日报》社,北京 100040;3.《人民政协报》社,北京 100040)
中国慈善组织的法律形态及其设立对策
胡卫萍1,赵志刚2,高志民3
(1.华东交通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法学系,江西南昌 330013;2.中国《检察日报》社,北京 100040;3.《人民政协报》社,北京 100040)
近年来,中国慈善活动开展热烈,但“双重许可”设立原则使中国慈善组织的设立平添障碍,慈善组织法律形态呈现单一型设置状态,非法人形态的慈善组织未被有效定位,慈善组织本身存在“非法”现象。而中国政府对民间团体过于审慎的态度和非法人团体立法规定的模糊,更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市场经济下中国慈善组织的发展。为保障中国慈善活动的顺利进行,促进慈善组织规模的扩大、规范,有必要确立慈善组织法人和非法人团体并存的法律形态,并明确设立规则,从多个层面为中国慈善事业法律体系的建构提供良好组织基础。
慈善组织;法律形态;设立对策
近年来,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迅速,慈善活动开展热烈,涌现了不少慈善组织,如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苏州汇凯爱心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李连杰壹基金等。它们在扶贫济困的慈善事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一半以上的救助款项是通过各类慈善组织募集的[1]。但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从事慈善活动的组织却存在注册难、登记门槛高、登记程序复杂、法律地位模糊的现象。有数据表明,目前未经登记的非法人慈善团体在中国至少有几百万个[2],即有相当数量的慈善组织是未经登记的社团组织,未曾拥有合法的身份。2007年6月,山东寿光民政局,就以没有登记的事由,解散了所谓的“非法”团体——“爱心”义工团队[3]。慈善组织在一开始设立就被“非法”的状态,是慈善组织相应法律形态未被依法确认的结果,它不但使慈善组织设立本身存在“非法”现象,亦使慈善活动实施也因慈善组织设立的“非法”而“非法”。慈善组织法律形态、慈善组织设立中存在的问题,不仅直接影响着中国慈善组织队伍的扩展、慈善活动的实施,更严重制约着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一、慈善组织的概念
慈善组织(Charity organization)的涵义,因各国宗教、政体、习俗、文化的差异而各有界定。美国税法将慈善组织界定收入无需交税的组织,且其捐助者也会因为捐赠行为而获得相应的税收减免[4]。俄罗斯《慈善活动与慈善组织法》认为,慈善组织是为了造福整个社会或特定范围的公民才实施慈善活动的,是一非政府性、非商业性的组织。亚美尼亚共和国《慈善法》第11条第2款,则强调在慈善组织的名称中冠上“慈善”的限定语,以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中国学者对慈善组织的定义也存在广义和狭义的分歧。狭义学说认为慈善组织主要是指从事扶贫济困、关爱弱势群体的组织;广义学说则认为慈善组织不仅扶贫济困,还实施环境保护等增加人类福祉的诸多公益行为[5]。但概括而言,慈善组织作为慈善活动的实施主体,是以社会救助为目的,以利他主义、人道主义思想为指导,通过社会公众志愿参与的形式,在宗教、文学、艺术、教育、体育、旅游、民族文化、环境保护、科学与公众事业等多个方面,以非受制于政府的身份独立开展扶贫济困、扶助弱势、保护生态等公益活动,并以其活动的公益目的、巨大的社会效益有别于其他非营利组织,具有自愿性、民间性、非营利性、公益性等特点[6]。
二、慈善组织的法律形态
在慈善活动开展过程中,慈善组织要管理慈善款物,将慈善款项落实到位,以严谨的责任心保障慈善款物不流失,帮助受赠者生存和发展,实现捐赠者意愿[7]。所以,慈善组织对捐赠人而言,是慈善款物管理者、执行者;对受赠者而言,是慈善救助的落实者,它以慈善活动中介者的身份开展慈善活动。但这些活动的顺利开展,又依赖于慈善组织活动实施时自身行为独立性的强调,要求慈善组织能根据社会救助公益目的的需要自主决定慈善款物的使用,自主开展慈善救助活动,不受组织外活动的影响。而这些相应自主权利的享有,则依托于慈善组织法律形态的独立,强调其独立的法律地位。慈善组织法律形态的明确,也就成为慈善法立法活动中首当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慈善组织法律形态的基本类型
根据各国通行做法,慈善组织的法律形态基本类型,包括法人型慈善组织和非法人型慈善组织两类。法人型慈善组织,是以从事慈善救助活动为目的、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无偿地对受益人提供帮助。非法人型慈善组织,虽同样以从事慈善救助活动为目的,但因为没有取得法人资格,只能在法律允许的相对有限的范围内从事慈善活动,自愿而无偿地为受难者提供物质、资金等方面的服务和帮助。这两种类型的慈善组织在一些国家是共同存在的,彼此独立地各自发展,如德国、美国、乌克兰等。但在另一些国家,却只允许法人形态的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救助活动,非法人形态慈善组织的设立则被界定为“非法”,不允许非法人慈善团体的存在和发展,如中国大陆地区。
(二)法人型慈善组织的优势
虽说,目前法人形态的慈善组织是慈善组织法律形态的主流,但实际上,慈善组织最开始是以非法人慈善团体的法律形态存在的,后来随着法人制度在各个国家的逐渐推行,慈善组织逐渐出现了法人形态。法人型慈善组织法律形态一出现,即在慈善活动开展时显示其较大优势,因它取得法人资格,具有更强的社会公信力,而且可以向社会大众募捐;可以以法人的名义行使权利并以其全部财产对外承担有限责任;还可以获得税收上的减免优惠,提高慈善团体从事慈善公益活动的积极性。虽说现在法人形态的慈善组织和非法人形态的慈善团体,均为现代社会慈善组织的法律形态,但因为法人型慈善组织的自身优势,许多国家在确定慈善组织法律形态时,都首选法人型的慈善组织。
(三)非法人慈善组织在大多数国家被界定为合法组织
德国、美国、瑞士、日本、俄罗斯、乌克兰、法国等大多数西方国家,虽也确立了法人型慈善组织,但都普遍承认未登记的非法人慈善组织的合法地位。在美国,人们认为建立一个慈善团体是他们的天然权利,而不是政府赋予的特权;承认非法人慈善团体为民事主体,可以以团体的名义参与民事活动。德国的100万个社会团体中,有一半是未经登记的法人团体[8]。未经登记的非法人慈善团体也是合法社团,称为无权利能力社团。在德国,设立一个非法人慈善团体,只需一个不拘形式的设立行为和由设立人所指定的章程[9],但非法人团体须对团体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乌克兰规定个人及实体,可以通过法律方式登记为某一慈善组织来共同从事慈善活动。瑞士规定公法上的团体组织及机构需要登记,非经济目的的社团、宗教财团、家庭财团则不需要登记。澳大利亚的非法人慈善团体估计有30万个,远远超过了已经10万个登记的法人慈善组织。俄罗斯和法国,不仅承认已登记的法人慈善团体的特殊法律地位,还承认未经登记的民间慈善团体的合法身份。日本在实践中也承认非法人慈善团体,其《非营利活动促进法》以认证的方式确立公益法人,认为满足法律规定条件的组织经主管机关确认即可成立,准入条件大大放松[10]。这些事例说明,在国际上,无论是法人形态的慈善组织还是非法人慈善团体,它们的法律地位都得到了许多国家的共同认可,成为扩大慈善组织队伍、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的举措。
(四)中国现行法律只承认法人形态慈善组织的法律地位
民政部2000年颁布的《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①民政部2000年颁布的《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规定非法民间组织有三种:(1)未经批准擅自开展社会团体筹备活动的;(2)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或者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活动的;(3)被撤销登记后继续以社会团体或者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活动的。,意味着在中国,未经批准、登记的组织开展的活动是非法民间组织活动,应予取缔;慈善团体作为民间组织的一部分,其活动的开展也不例外。但在中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中,只有法人形态的慈善组织才具有合法地位,才能依法获准登记、注册,享受慈善组织的税收优惠,慈善活动的开展才能得到法律的认可;非法人形态慈善团体是没有合法地位的,被排除在现行法律之外。而一些非法人团体的慈善组织,为了能顺利开展慈善活动,只能委曲求全地挂靠在某法人型慈善组织之下,或违心地注册为“企业”。其慈善活动的开展不仅不能享受到慈善组织该有的税收优惠,还处于民政部门的监管真空,让民众不由自主地质疑其社会公信力,且面临随时被取缔的可能。这显然与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要求相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慈善活动的顺利实施。
三、中国慈善组织的法律形态直接影响到中国慈善组织的设立
中国慈善事业处在发展的初期,和慈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非营利性组织数量众多,远远超过许多慈善事业发达国家,但中国慈善组织的数量和这些国家相比却相差甚远。究其缘由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中国慈善组织法律形态的立法限定,只允许设立法人型慈善组织,将许多从事慈善活动的非法人团体排除在慈善组织之外,且在设立条件、规则上也有诸多限制。这直接影响到中国慈善组织的设立现状。
高职教育中,专任教师在实现培养高端应用型人才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项目教学是以典型的职业工作任务来组织教学内容,要实现项目式教学,教师必须通过企业见习、实习等途径了解企业,积累工作经验,了解实际的工作过程和经营过程,将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工作任务作为具有教学价值的项目,胜任项目式教学工作[12]。
(一)法人型慈善组织的单一设置使中国大量民间慈善团体无法获准注册
中国慈善组织目前是法人形态的单一类设置,具体表现为事业单位中的慈善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法人、社团法人等法人类型。中华慈善总会及各地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及各地红十字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以及养老院、孤儿院、残疾人院、孤儿或残疾人学校等扶助弱者的机构,都分别是这几种法人形态慈善组织的典型代表[7]140-141。但在中国要想注册成为一个法人型慈善组织,在资金和人数方面有严格的设立条件。如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10条之规定,全国性社团组织的活动资金为10万元以上,地方性社团组织的活动资金为3万元以上,这使慈善组织设立的资金数额起点较高。在人数上,社团成立必须有50以上的个人会员和30以上的单位会员;个人会员和单位会员混合组成的总数不得少于50。而德国的法人组织登记只需要7个组成成员,一般团体的成员组成只需要3个;香港社团成员登记的人数最少为3人。《基金会管理条例》第8条,对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地方性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800万元、400万元、200万元的要求,远远高于德、美、日等国的设立条件。这些都使那些原本打算成为慈善组织的团体在较高的设立条件面前知难而退。且这种较高的设立条件,也与实践运作相脱离②青岛市有一个“笑姐”爱心助残团队,为了在现有制度下保证公信力,该团队不接受现金捐赠,只接受物资捐赠。该团队没有任何经费,完全依靠志愿者运作,运作中所需费用也由志愿者按AA制分摊。这样的团队在现有制度下是无法获准注册的。[11]。
另外,中国主管机关在慈善法人的设立上还采取有限竞争、抑制发展的思路,在慈善组织的数量和规模上实行限制。如根据1998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13条规定,对同一区域内存在业务范围相同、相近的民间社团组织,登记机关认为没有必要设立的,就可对其设立申请不予批准;必要时还可将相应的社会团体予以撤销或合并。在很大程度上直接限制了慈善组织的规模和数量。
法人型慈善组织的单一设置,以及其过高的原始基金、过多的人数要求和过多的设置限定,都使中国大量慈善组织,特别是大量民间慈善团体无法获准注册。数十万个非法人团体的慈善组织只能以“草根”组织形式长期“非法”存在[12],政府对其采用“不接触、不承认、不取缔”的三不方针[7]160,致使其成为慈善事业发展进程中的“怪异”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慈善组织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
(二)“双重许可”原则亦为中国慈善组织的设立平添障碍
虽说每个公民都有“慈善”的权利、“结社”的自由,慈善法人亦具有“民间性”,是独立于政府、非受制于政府的组织。但中国法人形态慈善组织的设立制度为“双重许可”原则,即法人型慈善组织不仅要取得业务主管机关的许可,还要到民政部门去审批和登记,通过政治上的审批才能获准设立,这是其取得合法身份的前提。
“双重许可”的设立原则大大增加了慈善法人设立成本。因为设立慈善法人首先得找到业务主管机关,得到其许可后方可进行登记。在现实情况下,从“找到”到“得到许可”并不是个可以简单完成的任务。除了层层审查外,可能还要动用大量的私人关系,大大增加了慈善法人设立的人力成本和财力成本。且在实践操作过程中,业务主管部门往往为了减少或避免承担相应的责任,并不愿意成为其主管部门,亦使慈善组织找不到挂靠的单位而根本无法登记注册[13]。如广州慧灵弱智服务机构,作为中国第一家民办弱智教育的民间慈善团体,其下属的抚养中心、幼儿园和学习、职业培训中心等单位,分属于民政局、教育局、残疾人联合会等不同的业务主管部门,其自身却因为无法确定主管部门而无法进行社团登记[14]。这不仅打击公民一心向善的积极性,甚至会使其干脆彻底放弃慈善念头,不再实施慈善活动。
在“双重许可”制下,业务主管机关和登记机关还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业务主管机关在一些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会给与自己有一定联系、给自己以好处的团体当业务主管机关,进行权力寻租。这不但会导致慈善组织的“法人格”与政府人格依附、混同,使对慈善组织的监管变成“操纵”、“掌控”,而且加重了慈善事业的政治干预、提高了监管难度,慈善活动扭曲、变形,最终失去“民间性”属性,酿造新的社会不公。所以,“双重许可”设立原则已成为中国法人型慈善组织设立的一大障碍,大大限缩了民间慈善组织法律地位的获取,约束了慈善组织民间性、多元性发展,影响了慈善事业发展进程。
四、中国慈善组织设立现状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中国法律为何只承认慈善组织法律形态的法人化?为何会对非法人团体的慈善组织以“不接触、不承认、不取缔”的三不方针对待[7]160?要想改变中国慈善组织的设立现状,让更多的慈善组织涌现出来,让更多有慈善热情的人投入到慈善活动中来,须深究慈善组织设立现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一)中国政府对民间团体一直持审慎态度
民间团体力量,事实上是一把双刃剑。引导得好,这个民间团体,特别是慈善组织民间团体,在激发公众慈善热情,发扬公众捐款捐物关爱他人、救助社会的积极性上,将极好地发挥其“民间”效应,有着重要的指引、凝聚作用,将会成为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社会资源第三次分配的重要“调解器”。且这种民间团体引导下、百姓自发实现的“民间效应”,依靠政府的强制作用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如果引导、监管不好,这些民间团体也将成为顶着“民间”面纱的社会和谐的破坏者,甚至成为与政府对抗的组织,威胁政党、政权利益。且其成员人数越多、规模越大,其对社会的危险系数也就越大。再加上一些民间慈善组织成员的法制观念相对薄弱,只是凭着满腔的热情进行慈善活动,在慈善活动开展中出现不少问题,引发一些纠纷,影响到慈善组织的活动质量,更加重了政府对其的不信任。
这种审慎态度,在计划经济年代,在特定历史时期起到了相当的维稳和过渡作用,但在市场经济时代,这种审慎态度则显得有些“过”。因为政府对民间团体的审慎态度、“许可设立”原则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行动模式来塑造民间组织,对合乎自己意志的民间团体赋以合法资格,对不符合自己认同度的民间团体则被排除在生活之外。这种塑造的最终结果是使国家权力延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国家政权极权化的形式来制约整个社会[18]。绝不能因结社自由可能存在的结社风险对政府利益和社会秩序安全的威胁,就否定结社权利本身,将结社权利“统”住、“束缚”住。毕竟市场经济讲求的是公平、自由竞争,讲究的是为万事万物发展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且根据权利义务一致原则,一定程度的放开就是一定程度的约束。所以,这种审慎态度、“双重许可”的强调,实际上是拿计划经济的标准来衡量市场经济的步伐,无法为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性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生存环境。多样化社会团体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不但不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相反会相互牵制、比照,从而更有利于社会稳定。为此,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政府应转变思路,改变对民间团体的审慎态度,承认未登记的非法人慈善团体为合法,并通过免税、信息公开、行政监督、社会监督等各种制度来约束社团组织行为,变主体身份的限制为主体行为的控制,让更多的慈善组织涌现出来,积极实施慈善救助活动。
(二)中国法律对非法人团体的立法定位模糊
非法人团体,在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传统立法上,并不具有民事主体地位。但随着社会发展,在德国的法律实务中,目前已依实际对无权利能力的社团采取灵活的态度,对具备事实法人条件的无权利能力的社团准用社团法人的规定[19];现代美国统一合伙法和各州立法,基本上也使合伙具有类似于法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即西方各国对非法人团体的法律地位,作出了不同于传统民法理论的思考,逐渐承认非法人团体具有主体地位,并在此基础上,从有益社会的角度出发,确立了慈善组织法人形态和非法人形态的法律地位。
中国立法对“非法人团体”的定位也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1987年的《民法通则》根本未曾涉及“非法人团体”;《合同法》第2条规定虽涉及到“其他组织”,但并未对“其他组织”作出“非法人团体”意义上的正式解释;2002年的《民法典》(草案)第89-94条对非法人团体的定义、设立条件和责任范围等作了直接规定,但较为简单,且局限于“草案”范围,未形成有效的法律规定。而通过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非法人团体立法定位上的变化,和中国《民法典》(草案)的设定,可以窥见,“非法人团体”在中国今后民事立法中可能占据一席之地。但在目前,“非法人团体”在中国的法律地位还很“模糊”。
这一定位的“模糊”,不仅影响到慈善组织能否以非法人团体的身份获得承认,关涉到慈善组织法律形态,还直接影响到中国慈善组织的具体设置,更直接导致了百姓对它的了解程度深浅不一。据《中国慈善事业法律体系建构研究》课题组的调研数据显示,有64.8%的人知道中国慈善总会,74.8%的人知道中国红十字会,50%的人知道中国残疾人联合会,39.2%的人知道宋庆龄基金会,32.7%的人知道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38.4%的人知道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20%的人知道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但这些慈善组织大多有着“官办”或“官方”色彩。对于一些民间慈善组织、非法人慈善团体,如李连杰“壹基金”、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苏州汇凯爱心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等,民众的了解程度则相对较低,甚至根本不知道[20]。中国《民法》这一基本法律对非法人团体立法定位的含糊,不仅导致了百姓对慈善组织本身认识上的模糊,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其他相关法律在“慈善组织设立”上的立法困难。
当然,非法人团体法律定位的“模糊”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与法人制度相比,非法人团体制度“模糊”定位的特点,在淡化国家规制、实践“法人实在说”上有其优势体现,能较好地实现非法人团体的结社自由。但是,可能是中国百姓对法律制定、法律执行上的认识习惯,谈及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更为注重的是法律规定的“强制性”,要求法律规范“明确、具体”。认为只有在法律上对某一问题作出了非常明确、详尽、具体的规定,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才能确知自己到底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赋予也没有放得很“开”)。在这一传统的习惯思维面前,法律规范定位的“模糊”,虽然在有些时候是该规定的法律属性使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一“合理性”却不被理解。这种“模糊”的定位不是给了当事者自由选择的自由,反而是增添了其行为实施合法与否的辩驳和确认难度,无形中增加了法律执行的困难,造成了司法认定的混乱。这在慈善组织设立问题上更是显得尤为突出。为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繁荣中国慈善组织,我们需要从慈善组织法律形态的角度,以特别法的思路,针对中国慈善组织的设立现状,思考慈善组织设立的法律对策,确定慈善组织的判断标准,界定慈善组织的法律形态,规范各种形态慈善组织的设立条件、认证机构和设立程序;对慈善组织的注册、内部治理机构、议事规则、财产制度以及慈善组织的变更、撤销和终止等制度作出具体规定,强调慈善组织的独立法律地位,保障慈善行为的独立实施[21],为中国慈善事业法律体系的形成建构良好的组织基础。
五、中国慈善组织设立的法律对策
综上所述,慈善组织的设立对策,须以合理的慈善组织分类为基础。在法人形态慈善组织和非法人形态慈善组织合法分类的基础上,确立合理的慈善组织设立原则、组织层次和设定条件,建立相应的慈善组织监督制度,唯其如此,才能真正解决慈善组织面临的问题。
(一)确定中国慈善组织法人和非法人团体并存的法律形态
2009年12月,国务院法制办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交了《慈善法》(草案)审议稿。该草案内容的立法重点之一,就是着力规范、明确慈善组织的登记管理体制法律规制。北京师范大学法律系教授刘培峰在评述《慈善法》(草案)时表示,“目前慈善的核心问题依然不是监管问题,而是总量不足的问题……要让更多的人参与慈善,让更多的组织成长起来,依然是目前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中国还没有到组织发展已经很多了的阶段”[22]。而要让更多的慈善组织成长起来,首先需要确认多种慈善组织形态并存的合法;要允许非法人形态慈善组织合法存在,而不能压制其进入,压制只能导致非法人慈善团体不能在正常的法律制度中运行,甚至降低慈善组织公信力,模糊慈善事业。所以,在《慈善法》出台制定之际,我们应着力考虑慈善组织法人和非法人团体并存的法律形态。在《民法》等基本法尚未大修之前,根据民事组织的基本原理,在《慈善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先行确定慈善组织的法律形态可以是法人,也可以是非法人团体;承认非法人慈善团体的合法地位,允许非法人团体进行登记备案。当然,前提是该组织活动不违背人民意志、不违反宪法秩序,同时致力于慈善事业、有明显的慈善目的,如此则不管它是官办慈善组织,还是民间慈善团体,均应对其合法地位予以承认,允许其存在、发展。让更多的慈善组织成长起来,参与慈善活动,不仅符合慈善精神,也符合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需要。
(二)取消慈善组织“双重许可”设立原则,合理实现结社自由权
如前所述,中国慈善组织的设立采取的是“双重许可”的设立原则,是一种重身份轻行为的设立原则。不但将大量意欲从事慈善活动的组织拒之门外,也不能有效防范利用慈善团体违法犯罪的现象,更是对公民结社权和慈善权的背离。虽然中国结社自由是一种有限制的自由,但这种“限制”是对该组织设立合宪性与否的审查、限制[23],绝对不能因为要“限制”而漠视该“结社自由”权利本身。而中国正在草拟的《慈善法》(草案),似乎并没有促动慈善组织设立的“双重许可”原则。慈善法人组织的设立,依然依循现有的社会组织登记、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甚至在许可设立要求上比过去可能更为细致、复杂,设立更难。实际上,政府对社团活动有效利用、监管,更多的应是通过对社团行为的管理来实现,尽量减少社团违法行为的出现,而不是在社团准入的“高门槛”上下功夫。
在一个开放和多元的社会中,为激励人们以自愿的方式服务社会,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我们应转变思想,大力扶持慈善组织的发展,取消现行的“双重许可”设立原则,在认清结社自由权的权利属性的基础上,合理实现结社自由权。可仿效英国、日本等国,采取认证设立、单一登记的管理办法,即取消业务主管部门的多头管理,确立由民政部门、税务部门、财政部门和第三方监管机构等认证机构的认证制度,并由民政部门作为单一登记机关予以登记。这也意味着,今后要成立慈善组织,只要能清楚地表明该慈善组织的组织目的、活动宗旨、活动范围、活动场所、资金来源、成员身份以及相应的内部管理和运作方式,就可到民政部门进行直接认证登记,而不必再由某部门出面作为其业务主管部门。民政部门在接到成立慈善组织的申请之后,须核查所申请的情况是否属实,在情况属实的情形下确认其是否满足法律所规定的条件再予以认证,签署认证意见,而后依照法定程序予以登记,承认慈善组织的合法地位,并发给相应证书。对有些设立内容较为复杂,涉及多部门认证的申请,如涉及免税、公募行为等,可采用部门会签认证制度,即申请人直接将材料递交民政部门,由民政部门进行初步审查,定期汇集,并负责与财政部门、税务部门和专门设立的第三方监管机构(慈善委员会或公益委员会)等相关组织联系,让它们在规定期限内根据申请材料作出同意或不同意设立的批复,以会签的方式予以会签认证许可[6]48-49。这种认证设立、单一登记的设立制度,免去了业务部门的多头管理、主管部门的层层审批,将登记、审核认证的权利集中于民政机关,简化了申请程序,同时又允许税务、财政部门和第三方监管机构进行多头会签认证,增加了对申请者慈善行为目的性的把握,使慈善组织在获准登记、取得合法身份的问题上,免去了许多束缚,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慈善组织规模的扩大,并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中国公民结社自由权的合理实现。
(三)确立“四级慈善组织”的认证登记制度
中国慈善组织的认证设立、单一登记的设立制度,将使慈善组织的设立变得比较容易,为慈善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但如此宽松的登记制度,也会让人不禁担心,该设立是不是过于简单了?同中国政府对民间团体一直持有的审慎态度是否相距太远?其实,“认证设立、单一登记”,只是中国慈善组织设立的基本原则,在慈善组织设立制度的具体考量上,还需考虑慈善组织的活动内容、活动规模、资金和人数等条件上的具体差异,分类设立,形成一个相对完善的组织体系。
笔者认为,在认证设立、单一登记的设立原则下,可考虑设立四个层次的慈善组织的组织体系,即“发展备案型慈善组织、注册型慈善组织、免税型慈善组织和公募型慈善组织”[6]47,对不同层次的慈善组织考虑不同的认证条件、登记形态。(1)“发展备案型慈善组织”。针对那些刚刚起步、规模较小、暂不具备注册为法人条件的在农村乡镇和城市社区中开展活动的民间慈善组织,只要到民政部门登记备案即可成立③中国许多地方已有通过备案制管理未登记慈善团体,进行非法人慈善团体合法化的实践。[24]。它不具有法人形式、不拥有免税资格、公募权,但国家对其开展的慈善活动予以认可,不再处于“非法”状态。(2)当一个慈善组织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和实力,则可选择直接注册为“注册型慈善组织”。因为该“注册型”慈善组织只是获得了法人的身份,并不享有免税权、公募权,同时还要接受更加严格的监管,而愿意注册成为这样的慈善组织其慈善活动目的非常明显,可由民政部门直接认证、注册成立。(3)一个注册型慈善组织在发展成熟、运行几年后,如果希望取得慈善组织自身所得税的免税资格,则可以继续向政府申请成为更高一级的免税型慈善组织,由民政部门会同税务部门和专门成立的慈善委员会等会签审核认证。(4)免税认证成功后,那些最为优秀和最有影响力的慈善组织,如果希望取得公募权和捐赠抵税发票的开具功能,可向民政部门递交申请材料,民政部门、税务部门、财政部门、慈善委员会等相关部门采用会签认证的方式,最终确认为公募型慈善组织(对公募型的慈善组织,监管最为严格,公募权和税收优惠等资格每年都要更新一次)[6]47-50。
由此,在慈善组织认证设立、单一登记的设立原则下,确立四级慈善组织认证登记制度,不但使“认证设立、单一登记”的设立制度“立而不滥”,而且明确了不同层次慈善组织的不同设立门槛和相应权利、义务,对不同注册“需求”的慈善组织有了符合他们意愿的注册形式,能较好地满足一般慈善组织的慈善热情,激发慈善组织设立的民间性和多元性,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
(四)进一步降低中国法人型慈善组织的设立条件,简化设立程序
在确定了中国慈善组织法人和非法人形态慈善团体并存的法律地位,明确了慈善组织的认证设立、单一登记设立原则的同时,法人型慈善组织的设立条件也应该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进行相应的调整。如前所述,中国对法人形态慈善组织的设立规定了较为严格的设立条件,慈善组织规模的扩大也因为设立制度的高“门槛”而受到极大的限制。俄罗斯、印度、巴西、日本等国家通过降低慈善组织设立条件来扩大慈善组织规模(阪神地震后日本出台的《特别非营利活动促进法》就是一个很合适的例证)[5],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为了促进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可考虑降低慈善组织的设立条件。《基金会管理条例》第8条原来规定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地方性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和基金会内部的专项基金的原始基金不低于800万元、400万元、200、50万元人民币”的标准都较高;且依据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全国性的基金会中只有一半左右的基金会拥有800万元以上的基金;地方性的基金会中,有近40%没有达到200万元的最低门槛标准[25]。这些高标准的基金数额如在实践中难以落实,高标准的设定则失去意义。应酌情降低,可考虑将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成立原始基金数降低至10万元为宜[26]。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成立社团须有50以上个人会员或30以上的单位会员,也远高于其他国家,实践中亦有弄虚作假的事例。也有必要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酌情降低社团会员人数。同时,取消在同一领域内已有类似组织时不予设立新的社会团体的垄断条款,因为这一条款已构成慈善事业主管机关拒绝设立新的慈善法人的主要理由,也是其滥用许可权的源头,极大地扼杀了人们行善的积极性,限制了中国慈善组织的发展。
在慈善组织设立登记时,应简化其设立程序。只要该慈善组织能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组织章程、出资证明、可实现组织设立目的的计划说明以及收支预算,提交相应的理事和监事名单、固定的工作场所和工作人员等[27],就可予以认证设立,别让慈善组织的设立条件、设立程序,成为阻碍慈善组织规模扩大的因素。
(五)确立慈善组织第三方监管机构,淡化政府对慈善组织的干预
如前所述,政府对慈善组织的有效利用、监管,更多应是通过对慈善行为的监管来实现,而不是在慈善组织准入门槛的设定上。所以,为进一步规范慈善组织的慈善救助活动,减少慈善组织违法行为的出现,同时防范慈善组织申请和注册中可能出现的“环节腐败”现象,需确立慈善组织的监管机构,加强慈善组织活动监管,明确监管程序和步骤。中国慈善组织目前的监管职能基本是通过行政监管来实现的,这种监管模式,使行政监督职能与直接管理职能混淆,年检和年度报告审查流于形式,更凸显了政府对慈善组织的行政干预,慈善组织活动的民间性、独立性被忽略。
为保障慈善组织的民间性、非政治性、公益性,应淡化政府对慈善组织的干预。我们可仿效英国等国做法,考虑设立“慈善委员会”、“公益委员会”这样的第三方组织作为慈善组织的认证和监管机构,监督慈善活动的实施。即各地慈善组织以自觉选举的方式,推选各慈善组织代表、慈善事务的法律工作者和会计人员,以评议员的身份组成慈善委员会,作为慈善组织的自律性监管机构(建议每隔3-5年左右轮换一次委员,以保证其公正、客观)。该委员会之所以称为第三方组织,是因为它独立于政府之外,不受制于政府。不但负责慈善组织设立、消灭和变更登记的认证事宜,还对慈善资金的运营和慈善项目的运作进行监督管理,对慈善组织的救助行为进行评估和控制,以保证慈善组织活动的“非营利性”、“慈善性”。一旦发现慈善组织有违反慈善目的的行为或者打着慈善幌子的非法慈善组织,即可严厉追惩,直至取消该组织的公募资格、免税资格和法人资格,甚至不予认证登记(必要时还可借助政府的强制力量予以打击,确保慈善活动的目的性)。当然,由于慈善事业的民间性决定了政府不能作为慈善主体,不能过多干预慈善组织的细微活动,只能担当规范和监督的角色。所以,在强调慈善委员会、公益委员会等第三方监管机构监管职责的同时,仍须强调淡化政府对于慈善组织的干预,以保证第三方认证和监管活动的有效性。
慈善组织的设立,作为中国慈善事业法律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关涉到慈善组织法律形态、设立原则、设立条件、设立程序、认证机构、财产制度和组织监管等诸多事项,是一个相对复杂的系统。在愈来愈多的国家将非法人形态的慈善组织界定为合法组织的今天,为促进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扩大慈善组织规模,规范慈善组织活动,我们需要明确慈善组织的法律形态,确立慈善组织的设立制度,以慈善组织法律地位的独立来保障慈善行为目的性的实现,为中国慈善事业法律体系的形成建构良好的组织基础。
[1]孔博,燕雁,沈洋.民间慈善组织的"草根"烦恼[EB/OL].[2011-08-01].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7-02/14/content_5738850.htm.
[2]徐麟.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43.
[3]山东寿光民政局解散未注册的义工组织引发争议[EB/OL].[2011-07-21].http://fz.voc.com.cn/view.php?tid-1677-cid-1.html.
[4]贝奇·布查特·阿德勒.美国慈善法指南[M].NPO信息咨询中心,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5.
[5]陈东利.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危机与路径选择[J].天府新论,2012(1):101-104.
[6]民政部政策法规司.中国慈善立法课题研究报告选编[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6-7.
[7]李芳.慈善性公益法人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33.
[8]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M].王晓晔,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84.
[9]王名,李勇,黄浩明.德国非营利组织[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75-76.
[10]王绍光.多元与统一[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216.
[11]杨明清,李丹.笑姐团队爱心助残[EB/OL].[2011-07-20].http: //news.workercn.cn/ c/ 2011/ 01/01/110101050151721779426.html.
[12]杨团,葛道顺.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0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3]胡卫萍,陈世伟.我国慈善义工活动存在的不足及其法律对策[J].江西社会科学,2011(12):156-160.
[14]王名,李勇,黄浩明.中国 NGO——以个案为中心[M].京:清华大学NGO研究所,2001:68-83.
[15]孙静.从非政府组织对社会稳定的消极影响谈结社自由的限度[J].工会论坛,2011(4):152-154.
[16]杜筠翊.结社自由的基本权利属性定位[J].行政与法,2012(4):81-85
[17]刘培峰.结社自由及其限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2.
[18]刘培峰.非政府组织监管制度研究[D].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博士后论文,2006:48-49.
[19]龙卫球.民法总论[M].第2版.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408-418.
[20]胡卫萍,李玉芬,史子浩.中国慈善活动实施现状调研的数据分析[J].华东交通大学学报,2012(2):116-120.
[21]胡卫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态势及其法律体系建构研究[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43-49.
[22]杜志莹.公益领域政策一波三折《慈善法》出台再成焦点[EB/OL].[2011-07-29].http://www.china.com.cn/gongyi/2010-09/29/content_21031343.htm.
[23]何永红.基本权利限制的宪法审查:以审查基准及其类型化为焦点[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24]吴玉章.社会团体的法律问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96.
[25]朱卫国.民间组织法制建设论纲[EB/OL].[2011-07-27].http://www.hnsfzb.gov.cn/Item/3716.aspx.
[26]韦祎.中国慈善基金会法人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146.
[27]牛余鑫.慈善组织法律监管研究[D].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38-39.
The Legal Form of Chinese Charity and Pondering on Strategies of its Setup
HU Weiping1,ZHAO Zhigang2,GAO Zhimin3
(1.School of Humanitces and Social Scienc,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13,P.R.China;2.Chinese Procuratorial Daily,Beijing 100040,P.R.China;3.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Daily,Beijing 100040,P.R.China)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charity is developing hotly,but the principle of double standard has added unnecessary difficultie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charity,there is a single form of Chinese charity, the illegal corporative charity has not been defined effectively, there's an “illegal"phenomenon of Chinese charity.To some extent,the over cautious attitude of the government towards the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and vague legislative rules to the non corporative charity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charity work in China's economy.In order to smoothly develop China's charity and expand its scale and standardize this industry,it's very essential to set legal coexisting form of the corporative and non corporative charity and to clearly set rules,providing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s structure of legal system of charity.
charity organization;legal form;strategies of the setup
D922.182
A
1008-5831(2013)02-0109-08
2012-02-12
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慈善事业法律体系建构研究"(10CFX065)
胡卫萍(1972-)女,江西临川人,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法学系教授,主要从事民商法研究;赵志刚(1971-),男,山东潍坊人,中国检察出版社副社长,主要从事法学、管理学研究;高志民(1973-),男,山东潍坊人,人民政协报编辑,记者,主要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新闻报道。
(责任编辑 胡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