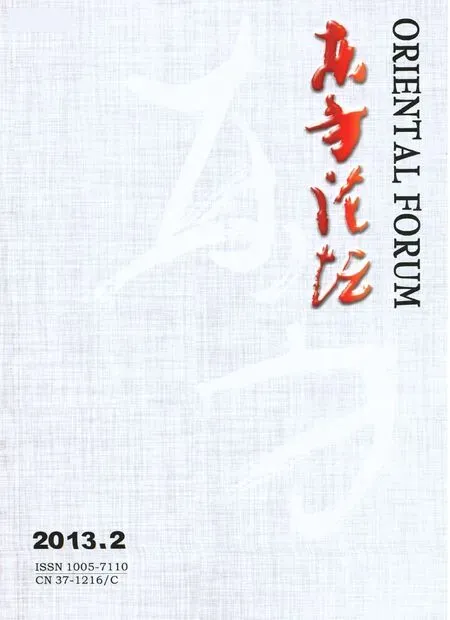弱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另一种论证
杨振华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08)
自环境伦理学诞生以来,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①人类中心主义的概念非常复杂,如我们可以在宇宙论、目的论、认识论、生物学及价值论等多种意义上使用它,非人类中心主义概念也同样如此。墨迪就明确宣称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是价值论的,本文也仅限于在此意义上使用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这一对概念。就没有停止过。两者论争的核心在于提倡环境保护的根本理由是什么:是为了人类整体的、长期的和根本的利益(人类中心主义),还是为了尊重非人存在物或包括人类在内的生态环境的利益(非人类中心主义)?或者说是否应该将独立于人的感受与判断之外的内在价值赋予非人类存在?弱人类中心主义试图超越这种争论,为环境伦理学提供一种“充分”的论证。本文立足于美国环境伦理学家拜伦·诺顿(Byran.G.Norton)的理论展开评述。
一、环境伦理学的两种范式
早在1967年林因·怀特撰文指出,基督教教义表达的是一种西方历史上最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文化价值观,也是现代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1]受此观念启发,环境伦理学创立初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利奥波德和罗尔斯顿等人确立了一种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理论传统,此后更有诸如“动物权利/解放论”、“生物/生态中心论”等理论均主张“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他们认为人类并非——如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价值、意义的唯一源泉;相反,非人存在物也具有不依赖于人的内在价值。这一传统影响深远,以至于有人认为,非人类中心主义彰显了环境伦理学的新颖性,它甚至是这门学科的唯一旗帜。
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主要有:一、从实践上来看,将人视为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或一切价值的源泉,必然会推动人类继续无限度利用或掠夺自然界,使当前的生态危机日益恶化,最终使得人类自身的生存成为不可能。二、从论证角度看,强调人类一个种群的利益而忽视其他物种利益,这可以称为人类沙文主义和物种歧视,它在道德方法论上是利己主义,逻辑上也不能自洽。同时,将“道德”一词局限于人际关系范围以内,是“狭隘的元伦理学(meta-ethics)预设”,将道德关怀的对象局限于人类自身也为道德进步设置了不恰当的限度。在后现代思潮日益兴起的二十一世纪,人类中心主义对于现代主义的本质主义、还原论和绝对理性主义,特别地对于人类力量无限性的迷恋必须加以解构。[2](P20-23)三、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置于自然的对立面,无视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性与整体性关联,这是笛卡尔哲学以来二元论思维方式的延续,它使得人类对自身意义的思考走入困境,生态危机与人性危机陷入恶性循环当中。
立足于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批判,建构自然内在价值理论成为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基本特征。但这种做法与20世纪以来英美哲学界拒斥形而上学、强调“无本体论的伦理学”潮流相悖,也许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诺顿明确反对非人类中心主义者自然价值论的形而上学假设。因为对他而言,环境伦理学需要的论证“并不是直接追问哪些原理为‘真’,而在于对持有特定的共享直觉来说是‘充分’的。”[3]他相信,对于那些具有合理的环保意识的个体和社群而言,在人类的某些活动会严重破坏环境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并不难, 而有些活动的破坏性效应可能并不清晰,它需要相关的科学研究加以确认。重要的是,环境伦理学应确立一些原则并据此推导出人类活动的规则,以限制那些肯定会严重破坏环境的行为。如果一种理论足以承担这种任务,那么这种环境伦理学就是充分的。在特定阶段,一些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尚不确定,我们就没有充分的理由去干预,而且它并不属于环境伦理学的研究课题。
可见,诺顿是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上理解环境伦理学这门学科的。从环境伦理、科技伦理等应用伦理学产生背景来看,它们面对的主要是一些刻不容缓的现实困境,要求逻辑严密、高度自洽的传统伦理学理论及其思维方式无法给人们提供解决复杂现实问题的明确指导。在这个意义上,以环境伦理为代表的应用伦理学实际上是应急的伦理学,虽然它也要求一定程度的逻辑自洽,但指导人们迅速且较为合理地做出行为抉择才是它的根本任务。环境伦理学中非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论争仍然执着于形而上学理论层面,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该学科性质的误解。诺顿试图提供的是一种应对迫在眉睫的环境危机的现实主义解决方案。从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来看,1990年代之后,两种“范式”的形而上学论争逐渐让位于更加关注环保实践中的“环境正义”主题。[4]可以说,诺顿的思路较好地把握了学科特点并与理论发展的趋势呈现了某种一致。
二、“最后一人”与两种人类中心主义
诺顿指出,人类中心主义这一概念本身是非常模糊的,澄清并调整这一核心概念有助于为建构充分的环境伦理学提供可靠的基础。他注意到环境伦理学家经常用“最后一人”的假设情形来区分和验证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这个故事假定S 是面临死亡的最后一个人类个体,那么,应该如何评判他为了宣泄去肆意破坏某物X(X 可以是某一物品,某一非人物种,生态系统,地质构造等等)的行为呢?如果认定破坏行为是错误的话,那么理由一定要在X 或与之相关的自然事物本身中去寻找:因为这种破坏不可能伤害到其他人类个体,也不会影响S 即将死亡的命运。这种围绕非人之物X 做出评判的方式就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反之,如果认为这种破坏行为对他的必死并无直接影响因而是道德中性的,或者满足了他的心理需要因而是有价值的话,那么,这一立场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因为两种评价均是围绕着“最后之人”S 而做出的。诺顿指出,这一检验方法并不令人信服,关键就是对于人的益趣(interest)没有做出很好的界定。
他引入了“感性偏好”(felt preference)和“理智偏好”(considered preference)这对概念来重新评估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感性偏好指的是“当前可以通过某些明确体验来得以满足的个体愿望或需求”,理智偏好则是指“一个人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会表达的愿望或需求,他断定这些愿望或需求与一种可以被理智接受的世界观相一致。”[3]诺顿强调理智偏好的形成依赖于科学理论、解释这些科学理论的形而上学架构以及一系列理性论证的美学与道德信念的充分支持。作为世界观之构成部分的理智偏好并非人先天具有的(在康德主义的意义上它代表着普遍有效性)而且它经常处于变动之中,但仍然可以为限制个体的感性偏好提供指引并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普遍赞同。依据区分这两种不同的偏好,诺顿发现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形态的人类中心主义:强人类中心主义和弱人类中心主义。
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过分强调了对个人感性偏好的满足,这种观念主导之下的人们必然会采取控制、剥夺、破坏自然的方式——正如近代以来,人类借助科技力量所做的那样。因此,这种思维方式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对自然的消费主义态度,不利于环境伦理学的论证与环保实践。但是,环境伦理学不能够也不应该反对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生存的必需去消耗一定的物质资料。非人类中心主义通过假设自然物(界)具有内在价值而强调人类必须履行关爱、保护自然的义务,这种倡导本身当然没有错,但如何在自然物(界)对人而言的工具价值与其独立于人的内在价值之间取得平衡,又如何保障人自觉去履行保护环境的义务呢?诺顿认为非人类中心主义提供的论证无法令人信服。
弱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支持满足部分感性偏好的同时,还强调人们对物质的消耗应该受到理智偏好的限制。这样就在肯定人们利用自然物的天然权利的同时,又为人们消费自然的活动提出了必要限制,还为人们自觉保护环境提供了较为充分的心理动机:保障人类后代生存的权利。相比之下,诺顿的论证思路更为现实合理。
通过区分感性偏好与理智偏好以及强人类中心主义与弱人类中心主义,诺顿试图澄清困扰环境伦理学发展的核心概念,进而在环境伦理学的两大阵营之间寻找一条更为合理、特别是更为现实的路径,这种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他在区分感性偏好与理性偏好时,指出理性偏好取决于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和道德观,这一主张提出了完善片面的现代科技理性、调整对自然的消费主义观念,与今天已被普遍接受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是高度契合的。至于如何确定这些观念的合理性呢?他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判断标准。所以,两种偏好的区分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理论缺陷。但弱人类中心主义提出在消费主义文化盛行的现代社会,对人们无限的欲望进行必要限制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三、超越个人主义的价值观
责任伦理的倡导者汉斯·约纳斯曾说:“所有的传统伦理学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5](P4)伦理学仅关注人类成员内部的事物或只处理人际间关系。而且传统伦理学仅思虑人类活动直接当下的可预见后果,长期的、不可预测的后果则付诸上帝、运气,因而是“近距离的”(short-range)。面对技术文明对人类持久生存的严重威胁,必须建构为千秋万代的人类子孙承担责任的“远距离的伦理学”(long-range-ethics)。环境伦理学的兴起正表明这种远距离、整体视野已经形成:当代人类成员与未来的人类后代之生存被作为一个整体得到了理论关照,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亦成为基本共识。
诺顿指出,立足于个人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的现代西方伦理学各派无力承担起环境伦理学论证的任务。“功利主义和现代道义论在本质上都是个人主义的,它们伦理关注的基本单位是个人的利益或权利。”[3]功利主义的道德评价标准是看一种行为能否维护“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或者将伤害降到最低程度。其理论预设是个体利益可以被量化,功利主义者需要预测不同行为的后果,从而筛选出功利最大化的行为选择。但环境伦理学面对的问题是(尚未出生的)人类后代之生存权利,它能否被量化,当代人的生存利益与未来人类的生存可能性之间又该如何比较呢?功利主义显然无法回答。道义论主张个人的某些基本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如生育权在多数发达国家得到了充分保障,但人口过多就会威胁环境安全,进而威胁到未来人类更基本的权利如生存权,这中间的矛盾又如何破解?面对这样的诘问,现有的道义论伦理学框架也必须加以调整。
因此,环境伦理学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伦理学思维方式。首先,将针对人的伦理视野在时间的维度上拉长。伴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人类活动的影响力可能持续到遥远的未来,如核废料的辐射效应就可长达千年。当代的人类活动(特别是大规模的技术活动)可能会严重影响未来人类后代的生存环境甚至消除他们生存的可能性,因此,环境伦理应该突破个人主义价值观的限制,将人类生存视为一个连续性的整体。责任伦理学表达了在技术文明语境中,“如此行动,以使你行为的后果与真正的人之持续生存相一致”;或者说,“如此行动,以使你行为的后果不至于毁灭这种生存的可能性”;“不得损害人类世代生存的环境”。[5](P18-19)
而且,伦理关注的对象也必须在空间上加以扩展。环境伦理不仅要思考人类成员之间的代际关系,更应该关注人与非人存在物之间的种际关系问题。当代环境伦理学的两种范式分别从上述两个角度对环境问题做出了伦理思辨,人类中心主义强调必须保障未来人类后代的生存环境,非人类中心主义则将自然物(界)纳入伦理关怀的范围。弱人类中心主义调和了两种伦理学论证的方式,一方面它承认人类利益在价值思考中的重要位置:保障当代人的基本物质需求是人类活动的基本目标,不伤害未来人类生存的可能性则是其活动的上限。另一方面,它主张用整体论思维和非个人主义价值观来指引伦理学的论证:将当代与未来人类的整体持续性生存作为价值关注的对象,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作为根本的生存方式。
按照西方的传统观点,伦理学只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只在涉及人的条件下才具有道德意味。而在现代以来主流的自由主义文化中,原子式的个人拥有绝对神圣的先验自由,人类社会(特别是政府机构)则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依据契约而构建出来。在这种语境中,人类整体的延续、自然环境的保护就无法真正成为伦理关照的对象。①实践中,政府在环境问题上的决策机制因此受到民主选举制度的根本制约:自由民主制的政府由当代公民而非未来社会成员授权构成,因而政治力量要保障的就应是当代公民而非后代公民的利益。所以政府的环境保护政策就从根本上成为越权的事件。参见保罗·M·伍德、劳瑞尔·沃特曼著《可持续发展的障碍:越权的环境事件》(载《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 期)。正如诺顿所说,这种植根于个人主义价值论基础的现代西方伦理学无法为环境伦理学提供论证。只有从根本上超越个人本位的价值思维模式,走上当代与未来人类共存、人与自然和谐的整体主义道路才能保障环境伦理学本身的合法性。当然,对当代发展利益的限制又会面临着“生态专制”的指责,而且约纳斯责任伦理的实践机制选择中也确实存在对集权主义政体的偏好,弱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在调和这种紧张关系方面显示了某种程度的优势。
四、弱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效应
弱人类中心主义理论的提出使得学者们意识到,在环境伦理学理论论证与环境保护实践这两个层面要取得良性互动,必须走出一条扬弃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道路。
美国植物学家墨迪(W.H.Murdy)提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与诺顿的“弱人类中心主义”形成呼应。他一方面反对在诺顿意义上的“强人类中心主义”会给最终毁灭人类生存的环境,同时也承认:“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考虑到他在自然中的位置以后可以采取的一种合理与必要的观点”,“它肯定事物之间的普遍相互联系,并且肯定自然界所有事物的价值,因为没有哪一件事不对我们生活其间的整体发生作用”。[6]依照这种“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人并非所有价值的源泉。事实上,反思现代以来的“强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在环境伦理学界已经成为基本的共识。
作为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阵营的一面旗帜,自然价值论具有多种形态,但其基本论证思路是一致的:就是通过赋予自然物(界)以内在价值,从而为人类关爱它们的责任奠定基础,也即通过形而上学为伦理学奠基。这样一来,人的道德义务就根源于人类自身之外了。“如果说,人类中心主义是人为自然立法,那么,非人类中心主义则是用自然为人立法”,依照康德的观点,人的道德性奠基于自由、自律而非必然的自然、他律,“非人类中心主义把人重新限制在自然必然性中,这与人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7]即便如此,墨迪也并不拒绝相信自然之物具有内在价值,只是他强调,“我的行动显示出我评价自己的存在或我的种的延续要高于其它动物或植物的存活。”同时,他也提醒我们,“人不仅是一种生物学实体的发展,而且同时是一种文化实体的进化”,“就是要高度评价使我们成为人类的那些因素,保护并强化这些因素,抵制那些反人类的因素,它们威胁要削弱或毁灭前一种因素。”[6]墨迪呼吁我们参与到人类文化进化的过程当中去,因为“我们并非是在一个毫无意义的舞台上进行荒诞表演的一个个单子,我们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有意义的整体的组成因素,我们每一个个人的行为对于人类进化过程本身的自我实现,以及世界价值的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6]
此外,《环境伦理学》杂志的主编、美国哲学家哈格罗夫(E.C.Hargrove)也是弱人类中心主义的拥护者。他同墨迪一道赞同自然价值论在环境伦理学论证中的重要作用,并从人们对自然的鉴赏与体验当中找到环境伦理学的坚实基础。他批评诺顿用工具价值去表征自然之美所具有的非工具性价值,显示了一定的概念混乱。哈格罗夫在评价中国人喜欢吃狗肉、鸽子肉等现象时说,对西方人来说,作为宠物的动物不应得到这种待遇,但中国人喜欢吃的话他也可以接受。②2011年6月3日,哈格罗夫在南京林业大学所作题为“野生动物与财产权之争”学术报告中回答听众提问时指出,应当允许不同的文化传统中这种价值评判的差异。这里他区分了两种内在价值:自然物基于自身存在的客观的内在价值和基于人的评价的主观的内在价值,只有通过后者,前者才具备道德意义。[8]这样,从价值论角度看,哈格罗夫承认了人的价值主体作用,但也不否认自然客体的独立价值(类似于康德在认识论中预设“物自体”的做法),从而显示了其较“弱”人类中心主义的色彩。
从环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上来看,环境伦理离开人类这一重要种族是不可想像的。诺顿等人的贡献在于,他们察觉到人类中心论是“必要而不充分的”,强人类中心主义的论证方式为环境保护提供了“一个重要但不唯一的理由”。只有将关爱自然、保护环境与(道德意义上的)人类自我完善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地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样,经过墨迪与哈格罗夫等人的发展,弱人类中心主义就吸收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两大阵营的核心要素,从而更好地实现了“充分的环境伦理学”目标。
[1] Lynn White.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 [J].Science,(155) 1967,pp.1203-1207.
[2] 杨通进.整合与超越:走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 [A].徐嵩龄主编.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 [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3] Byran.G.Norton.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Weak Anthropocentrism [J].Environmental Ethics,vol.6,No.2 (Summer) 1984,pp.131-148.
[4] 王韬洋.有差异的主体与不一样的环境“想象” ——“环境正义”视角中的环境伦理命题分析 [J].哲学研究,2003,(3).
[5] Hans Jonas.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In Search of an Ethics for the Technological Age [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p.4.
[6] W.H.墨迪.一种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 [J].张建刚译.哲学译丛,1999,(2).
[7] 曹孟勤.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 [J].学术月刊,2003,(6).
[8] 刘晓华.论哈格罗夫对环境伦理所作的美本体论辩护 [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