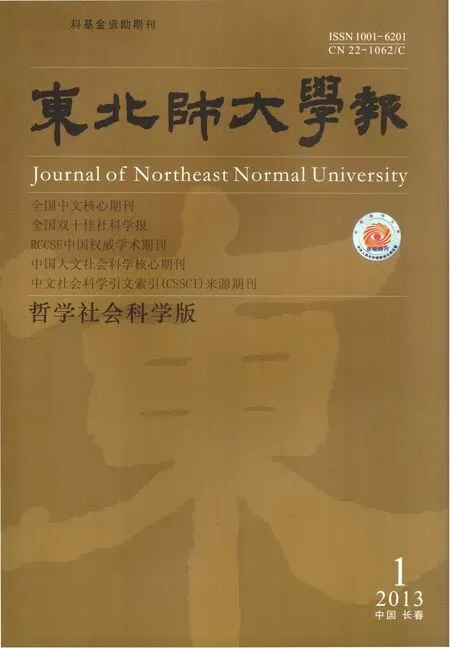商代蹲踞仪式与生殖崇拜
李为香
(济南大学 历史与文化产业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商夷人习于蹲居。正如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由于商夷人所居之处多水潮湿,不宜直接坐于地上,只好两脚触地,以使臀部离开多水的地面[1]。但蹲居的体态在商代的文化传统中绝不仅仅停留于日常起居习惯的层面上,尤其是墓葬出土的呈蹲踞体态的人像或动物像,可能代表着更为特殊的意义。通过系统考察分析,笔者发现,商代蹲踞的体态与史前蛙及蛙人体态特征相似,与鸟图腾亦有着某种渊源,或许可以说蹲踞仪式表达了商代人的生殖崇拜。
一、史前的蛙生殖巫术
商代人为什么会将蹲踞视为象征生育的姿势呢?这还要从具有蹲踞特点的动物及其旺盛的生育力说起。受生存环境和技术的影响,在古代社会,围绕两性关系的生育问题是人们生活的一大难题。除了获取食物之外,自身的生养繁息是原始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了。弗雷泽认为:“活着并引出新的生命,吃饭和生儿育女,这是过去人类的基本需求,只要世界还存在,也将是今后人类的基本需求。”[2]在生产生活技术水平极为简陋粗糙的原始社会,人们对自身的生育能力无法解释,更无法控制。他们最大的依靠就是巫术的力量。生育巫术所运用的原理就是人与动物、植物的相似律,尤其是动物。青蛙无疑是人们所见到的繁殖力最强的动物,一夜春雨之后,青蛙就会产下数量众多的蛙卵。青蛙由于其强大的生殖力而具有多产的意义,从而成为生殖崇拜的象征符号①关于青蛙等动物与生殖崇拜的象征关系可参见,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略论》,《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80-214页;傅道彬:《中国生殖崇拜文化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5-158页;叶舒宪:《蛙人:再生母神的象征》,《民族艺术》2008年第2期。。联系史前文化中刻有蛙纹或蛙人形象的器物,我们发现,青蛙蹲踞的体态与生殖力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关联。
青蛙的显著特征是四肢折曲,如陕西临潼姜寨一期彩陶盆内壁上的蛙纹[3]141、马家窑蛙盆内底部的蛙纹[4]。除了折曲的四肢,青蛙突起的肚腹同样象征着强大的生殖力。青蛙整个身体除去点缀性的四肢和头部,肚腹部分几乎占有全部体积的80%,突起而显见的肚腹与孕妇的形象极为相似。正如赵国华所说:“蛙的肚腹和孕妇的肚腹形状相似,一样浑圆膨大;从内涵来说,蛙的繁殖力强,产子繁多,一夜春雨便可育出成群的幼体,蛙纹上那些黑点表示蛙腹内怀子甚多。”[3]又圆又大的腹部与蜷曲的四肢,这两个显著的生理特征在原始人类的头脑中演变成了一种象征符号,即青蛙的形象与姿势代表着强大的繁殖力。根据巫术中的相似律原则,四肢折曲的姿势运用到人的身体上,便是下肢蹲踞的形象。在象征的意义上,人的蹲踞姿势是人与蛙生殖力量的融合,这种融合对于人来说,将大大地强化生殖力量。这种强化是借助了动物——蛙的生殖力而完成的。
原始人在很多圆腹形器物上绘有蛙形神人形象,简称蛙人,或人蛙,以表达人们的生育愿望。所谓蛙人或人蛙,就是兼具人与蛙的共性,在外形上看是身肢折曲姿势,在内涵上看则是生育力的共有。显然,蛙人折曲的身肢成为生育力的象征符号。如半山时期的一件绘有人蛙(上下肢均蜷曲,尤其下肢像极了蹲踞姿势)的瓦罐嘴[4]85,另如马厂类型的陶壶上的人蛙形象是:陶壶圆口作为人蛙头部,整体呈现出一身多肢形象,而且所有的肢爪均为折曲,状如蹲踞[4]86。在一件核桃庄辛店文化彩陶瓮上同样绘有一身多肢的蛙人纹,中间两条平行的竖线代表蛙人身体,两侧对称折曲的四组折线代表蛙人的肢爪[4]89,也会让人联想到人蹲踞的姿势。在众多的蛙人图像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极为夸张地表现肢爪的折曲与繁多,有的甚至只表现折曲的肢爪。
从青蛙和蛙人的姿势中我们很容易察觉到,青蛙的四肢是折曲的,而蛙人折曲的下肢恰似蹲踞姿势。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青蛙的四肢折曲与多产能力是天生如此,而人的蹲踞姿势与生育能力却并非如此,尤其是生育能力远非人类有限的能力所能掌控。但人们从多产的青蛙身上联想到人类自身的生产,特别希望人能够像蛙一样拥有这种神奇的能力。后者与前者之间的意义关联源于原始人类的象征性联想,“它源于原始人类最初的混沌不分,在人与植物之间,在人与动物之间,都还没有划出严格的界限。植物的生长,动物的繁衍,人类的繁殖,他们也都没有发现多少不同。这导致了他们的相类联想……”[5]394就是这种相类联想,构成了原始人类最重要的生殖崇拜。
在原始人类思维中,生殖的愿望与能力的获得是十分神圣的事情,与此相关的巫术(祭祀)仪式亦充斥于他们的生活当中。根据巫术的力量传递原则,绘有蛙纹或蛙人图像的器物就成为了巫术灵器。巫师在施法时或者将灵器随身携带,通过法术将生育力赐予受法的妇女。或者是由祈求生子的妇女触摸绘有蛙纹的灵器,获得如青蛙一样的多产能力。总之,绘有蛙纹或蛙人形象的器物突出的特征是器物口太小,显然不是实用器物,而是具有特殊的用途,如通神灵器,或者墓葬中的冥器,基本是一种仪式性用器。
随着文明的发展,以肢爪折曲为主要外在特征的青蛙、蛙纹、蛙人图像等生殖象征符号便会突破原始、写实的形式而向更加抽象、符号化的方向转变。蹲踞姿势遂成为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仪式性符号。商代的蹲踞仪式图像实为图腾崇拜与生育崇拜混合而产生的身体表达形式,这一仪式性图像成就了商代人最崇高的生命追求。
二、商代蹲踞体姿的生殖象征意义辨析
(一)正面箕踞:生育力的展现
正面蹲踞石人像主要是殷墟小屯抱腿踞石像与四盘磨箕踞石人像[6]953。这两件石像的姿势为踞或箕踞,其典型的特征是臀部和两脚均触地,大腿与小腿呈弯曲状态。陈仁涛说四盘磨像“袒胸缩腿竖膝两手支地蹲踞而坐之状”[6]951。以脚部着地,臀部朝下,两腿比较放肆地张开,与蛙形姿势有些类似。我们认为,箕踞的放松姿态与史前蛙或蛙人的四肢蜷曲的姿势具有相似的象征意义,即象征着女性的生育力。而根据日本学者林巳奈夫的研究认为,这两个石像的腹部都刻有象征阳物的羊角兽面,显然又在表现男性的生育力[7]154。这表明,在商代,人们已经懂得人类的生育是男女共同完成的事情,所以在生殖崇拜中兼具两性共有的特点。商代出土的阴阳同体玉人表达的同样是这一种意义。按照生育力象征的说法,在石像腹部刻阳物或象征物,其意义再明显不过,是表示两性生育力。在殷墟五号墓还出土有羊头、蹲坐抱膝熊和猴[8]84,可能都与阳性及蹲踞的生育仪式有关。
(二)侧面蹲坐:生育祭祀的神像
玉,在古代被赋予“玉足以庇荫嘉谷,使无水旱之灾,则宝之”[9]楚语下第十八,527的神圣威力,通常作为巫师施行法术时必需的神器,即“祭祀之玉”。考古出土文物中有很多玉器或玉人,按照玉为神器的说法,这些玉器和玉人都应与当时的巫术、祭祀观念和文化有关。王国维在解释“礼”时认为:“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若豐,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10]卷六,144根据玉乃通神之器的说法,商代出土的众多玉像可能是祭祀通神之器。侧面蹲坐玉像主要包括妇好墓出土侧身玉人、江西新赣县大洋洲乡出土的侧身羽人玉佩、侯家庄1550墓出土的蹲踞人形玉佩。除此之外,还有数量众多的玉鹦鹉像,与侧面蹲居人像极为相似,显示出二者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
江西新干县大洋洲乡出土的玉羽人[11]彩色插页二:2是一个“侧身蹲坐”[11]的姿势:臀部明显着地,双膝上耸,双臂蜷曲,双手抱至胸前。从整体看,这件玉羽人既有人的特性,又兼具鸟的特征。众所周知,商夷人以鸟为图腾,商的始祖契就是其母亲“吞玄鸟卵”而生,所以鸟在商夷人的祖先崇拜中应当具有重要的地位。这件蹲踞形的人鸟玉佩,无疑与商夷人的鸟祖先图腾崇拜有关。其中蹲坐的形态、鸟的形状,共同构建起商夷人对人类自身繁育的无限崇拜。羽人“脚底有短榫,榫部有横凹槽,并拢的小腿下部有一斜穿孔”[11],可能是用于商夷人的祖先祭祀活动。这种祭祀活动一方面是对祖先神灵的敬奉,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生者生育能力的获取。
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侧身玉人像有两个[8]82,简报称玉人像“作侧身跪坐形”,“臂拳屈于胸前,脚踵置于臀下”。又称第一个人像“小腿下有三角形榫,上有圆孔”,另一侧身玉人亦是“脚下有短榫,可能作镶嵌用”[8]。若是如简报“跪坐”所言,那么这两尊像是趴伏在地上,面朝下的。但从小腿下有榫及脚下有榫来看,两尊像应该是面朝前,直立插于某处用于祭祀。而且,若是跪坐,双膝、足部与地面应该在同一个平面上,但这两件玉人像的足部与双膝构成的平面与地面是倾斜的,甚至接近于垂直,这显然是一种蹲坐的姿势。所以这两件玉人像是典型的侧身蹲坐像。
侯家庄1550墓的侧身形玉佩也是一个蹲坐形人像[6]952。玉佩上耸的膝和下悬的臀,都显露得很清楚,两臂蜷曲拱于胸前。李济认为这种姿势是“代表日常的生活”,他通过侯家庄蹲形玉佩、四盘磨造像、小屯石像共同的蹲踞形状认为,蹲居与箕踞(我们可以合称为蹲踞)的习惯在商代人的生活中比跪坐更为流行。他认为,无论是人还是神,都习于耸其膝而下其臀的居处方式[6]951。但不足的是,李济先生对蹲踞的意义分析仅停留在居处习惯层面上,未对蹲踞的宗教象征意义作进一步探讨。
侯家庄的这件玉佩与妇好墓中的侧身玉人像很相似,都是下肢蜷曲蹲居的姿势。整个图像集中表现的是手臂于胸前蜷曲,臀部朝下、双膝上耸。刘凤君在《考古中的雕塑艺术》一书中描述妇好墓和侯家庄1550墓出土的蹲踞像“人面向外弧,头戴高冠,臂拳曲于胸前,侧身蹲踞,臀部或小腿部有孔,脚下有短榫,以供穿索和插嵌用”[12]80。联系青蛙与蛙人的蹲踞姿势,我们认为妇好墓和侯家庄墓出土的玉佩都不是简单的装饰品,而是与当时的生育观念与生殖祭祀仪式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前拱至胸的双臂、蜷曲的下肢可能都与多育多产的生殖愿望有关。脚下的短榫就是用来插嵌以备祭祀用的。由此看来,蹲踞人像是用于祭祀场合的,应当是象征接受祭拜的神像。这种侧蹲形的人像与前面所举小屯像和四盘磨造像的正面前向,双腿分开相比,更加摆脱了写实的特征,而只取其蹲踞的生殖象征意义,对生殖器与生殖的直接关联则很少注重。
更值得注意的是,商周时的玉鹦鹉形象与上面的侧身玉人像非常相似。安阳殷墟五号墓出土的20多件玉鹦鹉[8]86以及山东济阳地区出土的西周玉鹦鹉[12]61在整体造型上与这种侧身蹲坐人像很是相似。此外还有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鸟(鹦鹉)形玉刻刀与鱼形玉刻刀[13],这些玉刻刀制作精美细致,显然不是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刀具。事实上,这些被称为刻刀的玉器,应该不是简单的刻画工具,而是用于与神灵相通的神圣空间,有可能是被插于某处用于某种巫术或祭祀仪式的礼器。其作用亦与生育有关。鱼形刻刀、鹦鹉形刻刀与生殖力的关系,大概可以这样推测和解释,鱼自然是取其多子,鹦鹉则主要取其蹲踞的体态,前面我们已经讲过蹲踞体态与生殖力的关系,而且鹦鹉能学说人话,在古人看来,这种鸟身上有一种不可言说的神力。借助这样的神力,人或许可以获得某种超自然的力量,生殖力当然是其中重要的一种。
鹦鹉和侧身蹲踞人像在外部轮廓与形态上的极为相似性,还是使得我们不由得去寻求二者在本质意义上的共同性。笔者认为,鹦鹉作为通神之鸟,最初可能与人的生育繁息没有直接的联系,但由于它能学人话而被认为具有神性。在商周人的观念演化过程中,可能逐渐与代表人类无限生殖力量的女性蹲踞姿势发生关联。如果这种推测正确的话,玉鹦鹉在商周时期与当时的生育观念和生殖崇拜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外部轮廓上看,商周时期的玉鹦鹉与上面所论的侧面蹲像是极为相似的。而从内部情态上看,若将鹦鹉的双翅比作人的双臂,向胸前蜷曲,也是相似的。但最重要的还是蹲踞的体态。鹦鹉的腿特别短,站立时的姿势是双足向下触地,其尾部亦是朝向下的,双翅是贴于身体,从尾部(相当于人的臀部)和脚部来看,它站立的姿势与人蹲踞的形象亦是极为相似。短小的腿使得它看起来更像是蹲在树干上。如此一来,神性鹦鹉与人类之间通过蹲踞姿态联系在一起。人类便向往通过这种与鹦鹉相似的蹲踞姿态而具有通神的性能。根据现代地震科学家的研究,虎皮鹦鹉的叫声频度与地震之间的关系,并由此研制了一种专门的叫声模式识别系统,这种系统不仅可以满足不同叫声的识别,还可以为地震前的监测提供有用的信息[14]。现代科学可以为鹦鹉对地震的感应给出一系列的数据依据,但在遥远的古代社会,人们恐怕只能将这种感应能力看作是一种通天地之神的超自然力量。
侧面蹲坐玉人像与玉鹦鹉像一方面源于商夷人的鸟图腾。人蹲坐的姿势与鸟站立的姿势从侧面看很是相似。所以侧面蹲坐玉像与图腾崇拜和祭祀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图腾崇拜与子孙繁育实为一脉相承,崇拜的目的实际为了生者世界的繁盛与长久。无论是人还是鸟,其蹲坐的姿态成为其显著的身体特征,蹲坐与前述蛙人蹲坐的特征是相似的,且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即从此种姿势中获取强大的生命繁殖力量。
(三)人虎结合图像中的蹲踞:母性生殖力量的传递
关于商代的人虎结合图像,已有诸多学者作过论述,如张光直的巫觋通天工具说[15]333、李学勤的人神合一说[16]37-43、徐良高的虎噬俘虏首级及致厄术说[17]、何新的虎食鬼魅说[18]、谢崇安的血祭献牲礼仪风俗说[19]、熊建华的珥蛇神人戏虎说[20]、潘守永、林 河 等 的 人 虎 交合 说[21][22]118,王震中的商王室祭祀虎方神灵以支配虎方方国说[23],等等。张朋川在讨论此问题时已经注意到人蹲踞的姿势,而且将之与四方夷的日常坐姿结合起来考察,认为这一类的虎人图像艺术实源于西部和西南部少数民族坐姿中的蹲踞样式,虎图像则源于西夷和西南夷虎崇拜的观念[24],却还未能接触到问题的实质。我们认为,虎人图像中的蹲踞人像与上古时期的生殖意识与生殖崇拜观念有着不可分的关系。
商代人虎结合图像中的人一般是蹲踞形象:一种是虎食人卣中虎口之下的蹲踞人像[25];一种是龙虎尊中位于虎下方的蹲踞人像,如安徽阜南出土龙虎尊[15]320、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器物坑出土的龙虎尊[26]89。这两种人像从外形上看,蹲踞的姿势不一致,前者是正面蹲踞,后者是侧面蹲踞。但从蹲踞的姿势看,二者均呈现出手臂上举,双腿弯曲,颇类似于前面所述蛙人形象。所以将虎人结合图像与生殖文化联系起来是必然的。对于这二者的生殖文化意义以及图像中的虎所象征的生殖意义,有很多学者作过相关的论述。比如,日本学者林巳奈夫认为,人虎结合图像中的虎与人具有性交的意义[7]175。潘守永、雷虹霁从人的蹲踞意义与九屈神人的内涵来挖掘此图像的生殖文化内涵,认为人是神人,虎则为神兽。人虎的交合就是借用虎的威力来获得更强大的生育力量。蹲踞即为九屈之态,九屈之态隐含的是交合的情形,是生殖崇拜的象征[21]。林河亦认为此图像意义是人虎交欢,人实为商代的巫女[22]118。户晓辉则从原始社会的虎形象的岩画所表现的突出的生殖内涵来审视人虎结合图像,亦认为此图像反映的是生殖内涵。他进一步认为虎具有母性的意义,人与虎的结合代表的是人虎之间生殖力量的传递[27]。
纵观各家说法,笔者认为,要审视人虎结合图像的意义,必须认清三点:一是人的蹲踞形象;二是虎的意义;三是人与虎的关系。如前所述,商代的蹲踞像实为一种生殖崇拜与生殖巫术仪式,表达了商代人强烈的生育愿望。对于蹲踞的生育仪式意义,持人虎交合说的学者大都注意到了。但若是人虎交合,则必为人虎异性。而蹲踞的形象为女性生育姿势,如阜南龙虎尊中的正面蹲踞人像为裸体,四肢呈蛙状,阴户张开,明显是一个女性形象。四川广汉三星堆龙虎尊中的“人在虎颈下,手臂屈举齐肩,两腿分开下蹲,臀部下垂与脚平齐”[26]89,形象与阜南龙虎尊裸体人像相似。按照人虎交合说,那么虎则为男性。但是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文化体系中,虎却是女、阴、母的形象。《左传·宣公四年》中载云阝夫人丢弃其私生子于云梦泽而虎为之哺乳的故事:“云阝夫人使弃诸梦中,虎乳之。”[28]卷十,405在民间剪纸艺术中也有虎哺养婴儿的故事,如山东胶东地区一种叫做“虎奶”护身符的民间剪纸艺术,其基本构图形象为一只垂尾笑面的慈虎肚腹下有一个仰脸吮吸奶头的小孩[29]。《易·乾·文言》中言:“云从龙,风从虎。”顾炎武释为:“云从龙则曰《乾》为龙,风从虎则曰《坤》为虎。”[30]乾为龙、为男、为父,坤则为虎、为女、为母。所以虎之母性、女性的内在特征也是基本可以确定的。人虎均为女性,二者之间的交合关系恐怕难以成立。
所以卣与尊上的人虎结合图像实为生育力的传递,而且这种力量传递也比较符合巫术感应的原则。即人从虎神的口中获取强大的生育力。虎张开的大口象征着虎的身体内无穷的力量,因为虎口是气息流通之处,虎的内在之气也可以通过口来传递到神人的身体之中。人的头部几乎都被置入大张的虎口之中,可以想见,神人正在通过这种方式汲取虎神的生育之力。
另外还有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所出“妇好钺”上的双虎与人头纹饰[31]、河南安阳西北岗东区出土司母戊鼎柄上的双虎与人头纹饰[15]320。钺及鼎耳上的人虎饰纹呈现双虎共含一人头形象。虎几乎为直立,妇好钺中的人呈夸张的蹲坐形,双臂外张,一副气势昂扬的姿态。双虎张开大口,人头居于大口之间,好像是两虎正在向人的双耳中呼气传力,人与虎似乎是通过口耳传递某种神力。由于此图饰是在武器钺上,所以这种力量可能已经超越了生育力,而成为一种勇猛如神的战斗力。而鼎,在古代是国家的礼器,被视为国家权力的象征,也是王者权力的象征。在鼎上绘以双虎与人头神的装饰,可能是其神圣性的表现,也象征王者至上的权力。
值得注意的是人虎结合图像是刻绘于祭祀酒器卣、尊或权力象征鼎、军事武器钺之上,人汲取虎之生育力可能是最初的具有生殖文化意义的力量传递,随着各种政治军事活动的扩大,生育力可能会被扩展,以至于成为一种无所不能的威力。在鼎、钺上的人虎图像可能就是对生育力的突破与扩展。这种情况恰恰可以说明,生育文化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为基本的文化,其他的文化可能渊源于此。因为生殖崇拜是原始社会人类甚至是上古早期人类的“主要精神文化”,生殖崇拜文化是“当今世界人类多方面灿烂文化的萌芽”[5]389。
三、蹲踞意义再分析
以上我们探讨了商代的不同蹲踞姿势,这些蹲踞姿势因为表达着一致的意义而成为一组特定的象征符号。这些象征符号实为商代人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积累创造出来的文明。它浓缩了那个遥远的历史时刻人们的生活实态与生命追求。与求得食物的丰盛一样,生命的繁衍成为他们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生活追求。这种追求通过习以为见的蹲踞姿势得以表达。透过这一姿势,我们发现任何神圣的东西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它必然来源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但它始终具有超出现实的能力。也正因为此,神圣的东西与现实的距离是最近也是最远的,一旦超出现实,就超出了人力所及的范畴,而进入到一个神圣的领域。但另一方面,日常与神圣的领域亦是不可分离的,因为神圣源于日常,而且回归于日常。
总之,蹲踞,不仅仅是一种日常生活起居的姿势。在出土的墓葬器物中,这种姿势更是不可能只代表当时人的生活起居状态。它更深层的意义应该在于生育力的象征。这些蹲踞的像是祖先、巫抑或是部族神灵?是为了让死去的祖先灵魂(或者巫、神灵)佑护活着的子孙拥有旺盛的生命力,还是为了使死去的人重新获得生命力,也还有再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但可以肯定的是,蹲踞像表达的深层文化意义在于人类对生育力的崇拜,也就是生殖崇拜。它最初是运用了人与动物(蛙)形态相类似的巫术类似律原理。当然由蛙生育崇拜到人自身的生育崇拜,此间经历了无数的变化,以至于到最终可能只保留了四肢、肚腹或其中一部分的相似性,而最典型的就是弯曲蹲踞的下肢。这种整体向部分、写实向抽象的变化,是符合人类早期的观念变迁趋势的。
人虎结合图像则在维持蹲踞之生育姿势的基础上,加入了虎的超人神力,将虎与蹲踞的人结合到一起,实现虎与人之间的力量传递。在生育力上,虎与人均为阴性、女性、母性,其间的力量传递亦是同类之间的力量传递,而非如某些学者所认为的是交合。人虎结合之图像应用于武器或权力象征器物中,则是自生育力延伸出更为强大的神力,或克敌制胜或至上王权。
商代社会中这些丰富多彩的身体姿势向我们说明一个明显而又深刻的道理,即在古代社会,身体的姿势、动作与行为是人们用来表达自身愿望、情感与信仰最直接也是最生动的技术形式。身体中所蕴含的精神技术能量可能是现代社会任何一种技术都无法比拟。
[1]王育济.济南历史文化的变迁与特征[J].东岳论丛,2010(5):5-26.
[2]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50.
[3]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略论[J].中国社会科学,1988(1):131-156.
[4]叶舒宪.蛙人:再生母神的象征[J].民族艺术,2008(2):82-89.
[5]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6]李济.跪坐、蹲居与箕踞[A].张光直,李光谟.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7][日]林巳奈夫.神与兽的纹样学——中国古代诸神[M].常耀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五号墓的发掘[J].考古学报,1977(2):57-96.
[9]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0]王国维.观堂集林[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1]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新干县博物馆.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J].文物,1991(10):1-24.
[12]刘凤君.考古中的雕塑艺术[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
[13]夏鼐.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J].考古,1983(5):462.
[14]陈浩,徐慕玲,张弘,蒋锦昌.地震前虎皮鹦鹉叫声的模式识别[J].地震研究,1991(4):415-424.
[15]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北京:三联书店,1983.
[16]李学勤.试论虎食人卣[A].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37-43.
[17]徐良高.商周青铜器“人兽母题”纹饰考释[J].考古,1991(5):442-447.
[18]何新.诸神的起源——中国远古太阳神崇拜[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278.
[19]谢崇安.人兽母题与神权政治——先秦艺术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二[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科版,1998(3):90-94。
[20]熊建华.虎卣新论[J].东南文化,1999(4):114-119.
[21]潘守永,雷虹霁.“九屈神人”及良渚古玉纹饰[J].民族艺术,2000(1):150-165.
[22]林河.中国巫傩史[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
[23]王震中.试论商代“虎食人卣”类铜器题材的含义[A].中国文物学会等.商承祚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113-124.
[24]张朋川.虎人铜卣及相关虎人图像解析[J].艺术百家,2010(3):98-110.
[25]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104.
[26]陈德安.三星堆——古蜀王国的圣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27]户晓辉.岩画与生殖巫术[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196.
[28](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9]傅道彬.中国生殖崇拜文化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171-172.
[30](清)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0.
[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队.殷墟妇好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