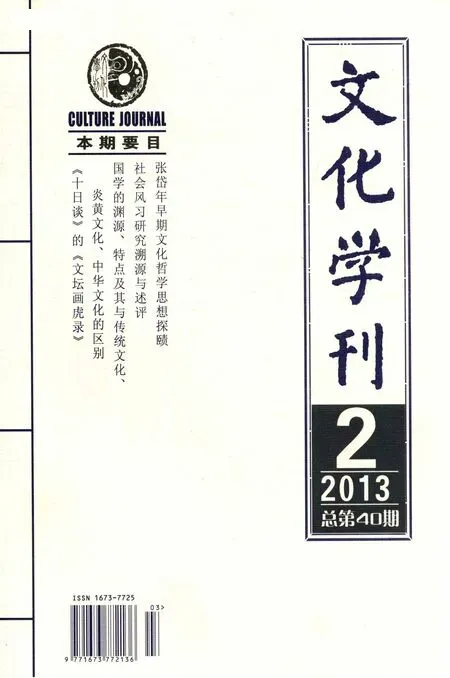告 别
王充闾
(作者系著名作家)
我们来到法兰克福的第二天,参观过国际书展之后,晚间,应东道主邀请,在莱茵河畔的“老歌剧院”,聆听了一场格调高雅且令人心旌摇荡的交响乐。
我原是音乐的“不良导体”,混了几十年,也没有锻炼出来一对“有乐感的耳朵”。特别是对于具有复调性、交响化特点,被人称作“庄严宏伟的音乐殿堂”的西洋交响乐,更是接触不多,知之甚少。什么多乐章的交响曲啦,什么交响诗、协奏曲啦,什么音乐会的序曲、组曲啦,充其量也只能粗加分辨,至于品鉴其所谓“稀世之美”、“味中之味”,则是一片茫然。
记得大文豪肖伯纳曾经说过,一切音乐作品都是标题乐。而且认为,音乐越是向文学靠拢,越是不纯,越好。但他终究不是出色当行的音乐家、作曲家,他的观点并没有得到音乐界的普遍认同。相反地,许多高层次的听乐者,则趋向于追求那种绝无背景、一空依傍的“纯音乐”,他们主张摈弃文学与视觉的干预,宁心静虑地直接倾听本文,以求溶入音乐艺术的化境,窥探其“无形之相”。听说,有人要贝多芬阐释他的一支曲子的意蕴,贝多芬默然无语,只是重新把这个曲子演奏了一遍。这个人没有理会,再问贝多芬意蕴何在,贝多芬泪流满面。一曲奏罢,竟然不能被人理解,这是音乐本身的悲哀,也是作曲者、演奏者的悲哀,进一步说,也是听众的悲哀。在这种多重悲哀的情势下,这位“乐圣”只好用悲怆的眼泪告诉世人:曲外无文,一切都在乐曲里边,并没有什么外在的、需要用语言文字补充和阐释的意蕴。
而像我这类初涉乐趣的“半吊子”,在乐海漫漫、茫无津渡的情况下,倒是喜欢找个入门的向导,觉得如果乐曲能和文学联结起来,比如,借助歌词的导引、标题的提示,理解起来总比直面本文要更容易一些。因此,当听说晚上这场音乐会将有海顿的《告别交响曲》时,情致格外浓烈一些。但是,它的结果,会不自觉地陷入望文生义、以偏概全的泥淖。
即以这个“告别”二字来说,当时我所萦怀的,是“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进而引发我无穷的联想——中国历代的文人骚客,由于长期受农耕条件下生活方式的影响,安土重迁,不惯流徙;加之,古代关山迢递,道路阻隔,正如《别赋》作者江淹所说:“况秦吴兮绝国,复燕宋兮千里”,“是以行子肠断,百感凄恻”。人们往往把背井离乡同生离死别联系到一起,结果是“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因而,从《楚辞》中率先唱出“悲莫悲兮生别离”的哀歌开始,一部古代文学史载满了《别赋》、《感别赋》、《叹别赋》、《离别赋》、《别思赋》、 《惜别赋》……就这样, “告别”的文章足足作了两千余年。
就这样,直到演奏开始之前,我一直在想着惨然长别的场景。
二
这座“老歌剧院”在法兰克福久负盛名,始建于19世纪80年代,于今已有一百三十年历史了。这是一座典型的欧式建筑,两层起脊,中间又凸起一层,上下两层灯柱衬着八扇窗户,放射出雪亮的辉光。剧院通体由石头砌造,显得庄严、肃穆、古朴、大方。
作为巴黎歌剧院的复制品,它是这里最著名的建筑之一,也是一流的文化场所,每年有大批来自国内外的艺术团体和个人到此演出。特别是我们所在的这座可容纳七八百名观众的莫扎特大厅,尤为豪华、典雅。据介绍,在这里演出的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涵盖了巴洛克早期到先锋派时期的各类作品,有交响乐、音乐剧、爵士音乐、摇滚音乐、流行音乐等多种形式,为观众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选择余地。
开场演奏的是贝多芬的交响曲,那种新颖的风格、宏伟的形象,一下子就攫住了听众的心魄。过去听过他的《热情》、《悲怆》奏鸣曲,这天晚上也还想听听他的英雄史诗般的《第三交响曲》、《第五交响曲》、《第九交响曲》,可是,演奏的却是以“田园”为标题的《第六交响曲》——一幅表达乡间情趣的“音画”。听来倒也轻松、流啭,只是后面带上了一点感伤的意味。关于这部交响曲,背后还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大概给它加上一个“告别”的标题,也还大致能够说得过去。
1807年仲春,“乐圣”贝多芬来到维也纳近郊一位伯爵家里,教伯爵的妹妹丹兰士演奏钢琴,没有想到,很快他就坠入了情网。每天早晨,他都要和丹兰士手挽着手,到充满绿色乡风的田园里去散步,还一起参加当地农民举行的舞会,沉浸在浓郁的欢情里。这天,他感到有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奔腾鼓荡在灵府之中,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于是,大步流星地奔回伯爵的府邸,立即用钢琴记下了交响曲前三个乐章的雏形。后来,情况发生了骤变,丹兰士由于抵抗不住母亲的粗暴干预,不得不忍痛离开他的身边,这给贝多芬带来了莫大的苦楚。在一个暴风骤雨、雷轰电闪的秋天,他久久地伫立在窗前,凝神专注地望着滂沱的急雨和利剑般的闪电,心头透露出一种阴郁透骨的寒凉。在这种情况下,乐曲第四章的初稿诞生了。
到了第二年的初夏,贝多芬忆起这一段永生难忘的经历,把春花般艳丽的柔情和激荡胸臆的雷雨连缀在一起,谱写出一支清音悦耳的华章,这就是《田园交响曲》。海顿不愧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尽管是一些细微的表征,也逃不脱他那敏锐的听觉。他告诉贝多芬:人们在您的作品中无疑会发现美丽动人的心音,但是,同时也会觉察到一种特殊的东西,阴暗的东西,因为你自己就有一点特别和阴暗。贝多芬听了,感动异常,把海顿奉为并世的“知音”与“解人”。
海顿之所以有此敏锐的感觉,端赖于他的高妙、超拔的修养。在音乐的欣赏中,与其说是凭借理解,毋宁说是靠的是体验与领悟。作为心灵的感应,欣赏者依赖的是自己丰富的感受;不具备这种感受,是绝对无法达到这种境界的。海顿这样的音乐大师,正是通过心灵感应,领悟到乐曲中细腻而微妙的情感表达。
这天晚上,我们还欣赏了勃拉姆斯的《第三交响曲》。由于乐曲中不同情绪的轮番交替,手法更接近于浪漫乐派,因此,所得印象比较模糊。当然,这和我一心关注着《告别交响曲》的演出,也有一定关系。
三
海顿是奥地利一位多产的作曲家,仅交响曲就写了一百零四部之多。一般地说,他的乐曲充满鲜明的形象,具有乐观、幽默的特征。早期作品中三个乐章的占一定比例,后来,逐步定型为四个乐章,唯有这部《第四十五交响曲 (告别)》是五个乐章。这部乐曲不仅意境动人,而且,演出方式也十分奇特,乐队一登台,就以每人手擎一只点燃着的蜡烛而引人注目。
演奏开始了,首先出现的是精神抖擞的快板,尔后,越来越紧张、激烈,给人一种急管繁弦、慌乱不安的感觉。第二乐章是温和、宁静的柔板,类似抒情的小夜曲,长笛和小提琴温柔、凄惋地奏鸣着。第三乐章是轻盈的小步舞曲,洋溢着海顿的舞曲所惯有的轻松与幽默。第四乐章重又回到急速而慌乱的格调上来,音乐像旋风般地奏鸣着,速度越来越快。当时猜想,整部交响曲大概就要在这种遒劲、激越的和弦中结束了。但我立刻又划了一个问号:若是这样,“告别”的意蕴又从何说起?果不其然,急促的音乐到此猝然中断,接着,转换为温存的、爱抚的旋律,类似第二乐章的柔板。就这样,第五乐章出人意外地开始了。看来,这部交响曲的前四个乐章,原是一部完整的套曲,而其最后的第五乐章,是为着特定的目的与要求补充进去的。
第五乐章是整部交响曲中最具特色的部分。演奏继续进行着,但乐曲的情绪和气氛逐渐地低沉、黯淡下来,节奏也趋于平缓了。这时突然发现,表情有些哀惋的第一双簧管手和第二号手,各自吹熄了乐谱旁的蜡烛,擎着乐器默默地退场了。不一会儿,低音大管的乐师也灭烛而去。紧接着,第二双簧管、第一法国号、低音维奥尔琴的乐师也都相继下场。乐音渐渐寥落,唯有弦乐声部还在持续地演奏着。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先是大提琴手,接着是小提琴手,最后是中提琴手,一个接着一个,也都陆续退场了。乐曲临近尾声,曲调格外哀惋、凄切。台上只剩下两个小提琴手,他们神情寂寞地,用微弱而凄戚的音调,静静地演奏完最末一个音符,随后便吹熄蜡烛,黯然离去。舞台上一片漆黑。过了一会儿,乐师们重新登台、谢幕,演出宣告终止。
想来,所谓“告别”,是和这样一个令人黯然神伤的结尾有直接联系的。可是,问题接着就出来了:这位享誉世界的作曲家,为了什么,或者说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要设置这样一个结尾呢?当日,我们带着一个很大的疑团,离开了这个同样有些迷离惝恍的“老歌剧院”。
四
直到读过海顿的传记,才算揭开了这个谜底。
原来,海顿从29岁的丁壮之年来到艾斯哈特齐亲王府邸,一直到58岁离开,在这个贵族之家足足当了30年的乐长。亲王是一个头号的“乐迷”,他对音乐的酷爱和在这方面的特殊要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决定了音乐成为宫廷中的至高无上的需要。
本来,他的府邸是在维也纳东南八十公里外的艾森斯塔特,但他作为匈牙利最富有的而且权倾朝野的一个贵族,对于当时尚属奥地利统辖的匈牙利境内的萨托更感兴趣。他把这个林木葱茏的胜地更名为艾斯泰尔哈泽,大肆扩建宫室,置备各种豪华设施,每年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此地勾留,自然,他所亲自经营的音乐活动,也在这里夜以继日、无时或息地进行着。
这可就苦了海顿指挥下的管弦乐队。因为大多数乐师都是奥地利人,长年在外从事紧张的音乐演奏,思家恋亲之情与日俱增。但他们受雇于王府,每天都以仆人的身份奉命登场,谁也不敢向亲王贸然提出回家探亲的要求。长期以来,海顿忍受了太多的“俳优畜之”的耻辱,每天穿着绣花的号衣,饭前饭后在客厅里随时听候主人的吩咐;作为乐长,他当然更能理解乐师们的苦衷。于是,他那幽默中又带有几分淘气的性格起了作用,索性以暗示的方式,通过乐曲的演奏,提醒亲王:如果不放大家回去,就将面对“告别”的场面了。
据说,这天听说乐长将有新作面世,亲王率领家族和亲朋好友,意兴盎然地前来欣赏。结果就是前面叙述的那样,乐师们一一退下,最后,海顿乐长也收起了指挥棒,向亲王及贵宾深深鞠躬,示意演出到此结束。亲王不愧是超级乐迷,的确有着一双妙悟的耳朵,第二天就下令:全体人员返回奥地利境内的艾森斯塔特。尔后,人们就给这部《第四十五交响曲》加了一个《告别》的标题。
在欧洲音乐界还有另一种传说:艾斯哈特齐亲王为了减缩府内支出,考虑要解散或者精简乐队人员。30多位赖以谋生的乐师闻讯后,忧虑重重,惶惶不可终日。乐长海顿出于同情,遂谱写了这部交响乐曲,作为解散前的告别演出。亲王听了,深深为之感动,便打消了解散或者精简乐队的主意。
不管是哪一种背景,这场演出和这最后乐章用以结束整部交响曲的特别方式,都给当时以至后世的听众造成了强烈的反响。莱比锡的《普及音乐报》有过这样的记述:“当乐队演奏员开始熄灭烛光并相继悄然退席时,听众的心都收紧了”,“而当最后的小提琴奏出的那微弱的声音终于也消失时,听众深受感动地开始默然散开,好像同他们所欣赏的东西也永远告别了似的”。德国著名作曲家舒曼听过这部交响曲的演奏后也写道:“对此,谁也笑不出来,因为这绝对不是为了消愁解闷而写的。”
五
“对此,谁也笑不出来”,确切地反映了聆听这部交响曲时听众的心态。但是,也仅止于“笑不出来”的苦涩与沉重,却并非如我开初时所臆想的那种生离死别的深悲剧痛,或者临歧哽咽的黯然神伤。我想了一下,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差距,还是和我对于《告别》这个标题的内涵的理解有直接关系。
原来,标题音乐是借助于主导动机来表达特定的思想的。但是,主导动机这种手法,实际上起作用的是语言、文字,而并非乐曲本身具有这样的功能。这里不完全是形象思维,还有很大的抽象思维成份。如果去掉了这个文字的提示,听众有时就很难晓得这种所谓“主导动机”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艺术讲究“通感”,音乐作品所表达的感情,须能唤起听众所经历过的感情体验。而这种感情体验也好,或者音乐作品表现的感情也好,都是间接地反映思想意识的,不可能像语言、文字那样明晰、确凿。这就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作为形象化的乐曲,能否准确无误地表达出这种主导动机呢?也可以把话翻过来说,如果标题是后加的,像海顿的《第四十五交响曲》那样,它又是否能够恰切地把握形象化的乐曲的意蕴呢?即便是它能恰切地表达乐曲的固有意蕴,还有个听众如何理解的问题。这些环节有哪一个解决得不好,都会产生误导的现象。恐怕这也是音乐界许多人对于标题乐不以为然的一个原因。
回国以后,我曾专门找来海顿的《第四十五交响曲 (告别)》的光盘,反复听过几次。由于脱离开了舞台演奏的场面,感觉总不像在“老歌剧院”那样明晰,那样强烈。由此,我又悟出一个道理:虽然我们都承认,音乐是时间艺术、听觉艺术,但是,如果要赋予它表现思想的功能,那就不仅要与语言、文字结合,而且,配合舞台演奏也是必需的。就这个意义来说,它又何尝不是空间艺术、视觉艺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