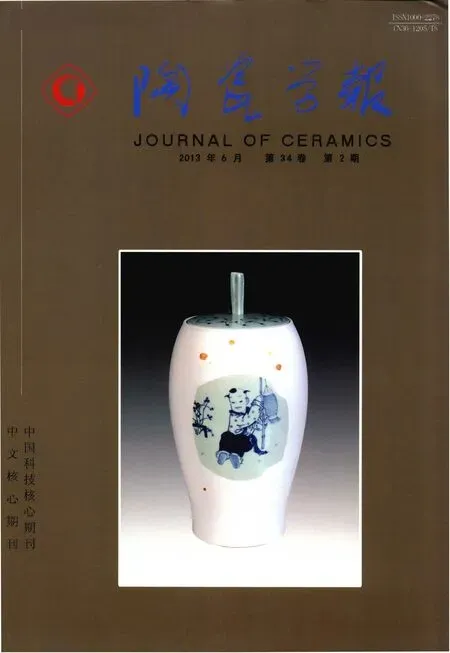论陶瓷文化的自律性和他律性
邹晓松 孙 斌 孙新明
(1.景德镇陶瓷学院,江西景德镇 333001;2.德化陶瓷职业技术学院,福建泉州 362500)
0 引言
自律性和他律性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个对立统一体,在任何事物中自律性和他律性都是普遍存在的,并且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促进该事物的发展。由此可见,自律性和他律性是发生在一定范围内的矛盾的统一体。文化是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社会学范畴,是人类改造自然与完善自身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及其结果的总和,它包括物质和非物质两个方面的内容。陶瓷文化是人类围绕陶瓷生产与利用物质和非物质方面的具体表现。历史上,陶瓷文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深刻的文化内涵既包括自律性,又包括他律性,是自律性和他律性的对立统一体。
1 陶瓷文化的自律性
陶瓷文化的自律性是陶瓷生产所依据的材料及其工艺,与人们主动利用陶瓷为自身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生活服务的历史的发展规律。
从陶瓷文化史上看,陶瓷文化是沿着自身材料及其工艺不断发展的,并利用各种材料的生产与日常生活的规律发展的。远古时代先民们为生存造物发现了粘土的可利用价值,随即发明了陶器。“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最初是用泥糊在编织物上烧成的,后来就直接用泥制坯烧制了”。可以说,这是对陶瓷文化自律性开始阶段的概括性描述。陶器的发明最直接地用在人们求生存、谋生活的造物之上,所以,围绕陶器所产生的文化的自律性首先表现在它受到生存和生活意识的直接支配。
随着陶器制作技术的提高与人们利用陶器为自身活动需要的不断增加,陶文化的自律性也在不断丰富。例如,出于信仰或祭祀的需要逐渐产生了一般的用于崇拜的陶器与用于祭祀的陶器。历史上的陶瓷“明器”实际上就是由祭祀陶器发展而来并专门用于祭祀之用的。在此,由于陶的逐渐多样化,人们开始将用于生活与用于祭祀的材料及器物区别开来,尤其瓷器产生之后,人们更加明确地确立了因材料不同而有所侧重的功能性需要并形成专门化利用陶瓷规则,于是,对陶瓷的材料性能及其可用之处进行着严格的划分。例如,人们用没有含铅的粘土制作陶器作为生活器皿,而利用含铅的粘土制作陶器作为“明器”(唐三彩)。当然,这些都没有脱离陶瓷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没有脱离围绕陶瓷生产与利用所形成的陶瓷文化的自律性。
陶瓷文化的自律性,实际上,就是一个地区的人们客观地遵循生产和生活规律来充分地利用陶瓷进行文化创造的规律。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是陶瓷生产与利用从来都没有间断过的民族,在几乎遍布中国的范围内,陶瓷形成了适合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自律性。就在该地区,陶瓷文化的自律性是不断发展与逐渐丰富的。从实用主义陶瓷文化到功利主义陶瓷文化,再到审美为特色、为主流的陶瓷文化的发展历程,不正说明陶瓷文化自律性发展的规律,它因人们表达文化需要而逐渐发展起来。
2 陶瓷文化的他律性
在任何事物的内部,或一定范围的内部所形成的这一事物或这一环境的自律性,当该事物或该环境受到外来因素影响时,就会发生变化,这种受其他因素影响的规律,就是该事物或该环境的他律性。一般地,以陶瓷文化发展的规律为主线,所有影响陶瓷生产与利用的文化因素,历史地构成陶瓷文化的他律性规律。
从狭义上讲,一定范围内陶瓷文化的发展总是沿着自身的规律进行,尽管在行进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吸收了其他文化因素,可是,它仍然依着自身的因素并以之为主流的发展,这便构成地区陶瓷文化的自律性。例如,宋代的景德镇窑虽然吸收了定窑等多个窑厂的陶瓷文化因素,但是,它仍然没有脱离自身的本质,而是在其它窑厂影响下丰富着自身的陶瓷文化内容。这就是狭义上所讲的陶瓷文化的自律性和他律性。也就是说,陶瓷文化的自律性是围绕陶瓷文化逐渐丰富而展开的。这是在陶瓷文化范畴内,地区陶瓷文化的自律性和他律性互动与转化的规律。然而,在特定情况下,一些文化因素却极大地影响了该地区陶瓷文化内容及其发展方向。诸如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以及宗教等文化因素对陶瓷文化的影响较为深刻,突出表现就是这些因素部分或全局性地打破了陶瓷文化的自律性,而表现出他律性的文化现象,给陶瓷文化的自律性打上了深深的他律性的烙印。例如,在封建政治因素没有影响景德镇陶瓷生产的时候,景德镇纯属于“民窑”陶瓷文化范畴;公元1004 年,宋真宗将昌南镇改为景德镇之后,景德镇陶瓷文化的自律性就受到他律性(政治意识及思维模式)的重大影响,此时,瓷都陶瓷文化的特征开始酝酿并逐渐形成一定的特色。再如,明代德化窑,它的陶瓷文化,原本在自身范畴内发展的自律性特征,是由舶来文化打破的,并鲜明地具有西方文化的他律性特征。因此,相对于封闭的区域而言,陶瓷文化的他律性,就是外部文化因素影响的区域陶瓷文化的发展规律。
随着陶瓷文化范畴的不断扩大,原本在一个地区(一个窑厂,如越窑、定窑、景德镇窑等)陶瓷文化的自律性基础上形成的他律性,逐渐变成区域范围内的自律性。由此可见,陶瓷文化的自律性是相对于一个特定范围而言的,这个特定范围既包括一定的地域空间,也包括一定的时间段。例如,在五代十国与宋代时期,所有受政治因素影响的陶瓷文化,它的他律性就是针对官窑陶瓷文化体系之外的文化因素而言的。尤其五代十国时期,南方越窑陶瓷生产得到相对发展,仍然在全国陶瓷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但是,控制它的钱氏割据政权为了保证“长治久安”,将越窑的青瓷器作为“贡品”,即“秘色器”供奉给中原的强势王朝,这种“秘色器”文化原本不是越窑瓷器的文化内容,而是因为外来的强大的武力威慑,给它披上屈辱的外衣,使越窑陶瓷文化受到他律性文化的影响,明显带有中原王朝的政治色彩。
从历史上,广泛意义上的陶瓷文化的他律性很早就开始出现了。远在汉唐时期,由于对外文化交流,尤其是商业利益的驱使,中国陶瓷文化早已受到了他律性因素的影响。中国瓷器生产不仅受到商业文化的影响打上输出国文化的烙印,而且,还利用外来材料和技术进行生产。例如,青花瓷器的绘料“苏勃泥青”就是外来材料,而用“苏勃泥青”所绘制的青花瓷器,具有明显的外来文化的特征。在中外商业贸易不断扩大的影响下,中国陶瓷生产越来越多的受到他律性文化因素的影响,并表现出舶来文化的特征。这不仅扩大了陶瓷文化他律性的地域空间,也使陶瓷文化他律性的文化内涵,以及具体内容与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彩。
3 陶瓷文化自律性和他律性的关系
陶瓷文化的自律性受他律性影响,同时,在文化内涵上逐渐丰富起来,并为人类文化活动做出积极贡献。
陶瓷文化的自律性是发生在一定的具体范围内的自律性,它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具有各自的个性特征。比如,同样是白瓷文化的自律性,发生在邢窑并围绕邢窑陶瓷生产与利用所形成的陶瓷文化的自律性,明显与发生在定窑的不同:第一,是历史背景和条件的不同,一个是在大唐帝国及其封建文化十分繁荣时期,一个是在宋代封建文化继续发展并商品经济文化开始萌芽时期;第二,邢窑陶瓷文化的自律性是按照当时材料与生产技术发展,并为绝大多数人生活服务的陶瓷文化的自律性来发展的,而定窑是在皇室生活驱使下发展起来的陶瓷文化的自律性。当然,不论邢窑陶瓷文化的自律性,还是定窑陶瓷文化的自律性,都是特定时空范围内的陶瓷文化的自律性。随着文化范围的扩大,陶瓷文化自律规律的范畴也在扩大。在明代,中国陶瓷文化的自律性已经注入商品经济因素,而在此前,陶瓷文化因受经济因素影响而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在当时,经济文化因素实际上是陶瓷文化的他律性因素。
另外,一定空间的扩大,使陶瓷文化的他律性相对变得更加复杂化。对于一个陶瓷产区而言,它生产的陶瓷产品流通范围越广,它的他律性越大,越深入。相反,也就越狭窄,越浅薄。陶瓷文化的自律性是在自身范围内发展起来的并起作用的文化因素,而陶瓷文化的他律性是在外界发展起来并起作用的文化因素。例如,在宋代景德镇窑,影青瓷及其工艺,以及它所涉及的生产和人们的生活等构成了它的自律性,而作为定窑的陶瓷文化因素,是它的他律性因素。随后,在时空变化中,景德镇陶瓷文化的自律性因素在扩大,而它的他律性因素也在扩大,延伸到更加广阔的地域。清代初期景德镇因受珐琅彩装饰这样的他律性的影响,逐渐形成了粉彩瓷器,而珐琅彩是从欧洲传来的一种彩绘技术。因此,从空间范围讲,景德镇陶瓷文化的他律性已经发展到了海外,舶来文化因素成为他律性的重要因素。
在中国历史上,陶瓷文化最为浓重的他律性就是半殖民地时期的陶瓷文化。此时,陶瓷文化的他律性上升到主导地位,而自律性严重下降,下降到从属地位。19 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与中国半殖民地性质的蜕变,陶瓷文化的他律性上升,尤其在东南沿海地区,陶瓷文化发展受到极端的他律性文化的影响而几乎忘记了自我。殖民地文化的影响深刻地为民族陶瓷文化打上外来文化的烙印,甚至成为影响陶瓷文化发展的严重障碍。例如,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德化陶瓷产区,历史上,它是受外来文化所形成的他律性影响较为深刻的中国陶瓷文化的一个典型类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它逐渐恢复了过去的生产,主要从事外来产品加工的陶瓷生产,成为国内较为典型的受他律性影响深刻的陶瓷产区。就现代陶瓷企业而言,设计、生产与销售等环节的紧密结合,是陶瓷文化发展的主流,然而,在德化陶瓷产区绝大多陶瓷企业都依靠订单加工为生产与运作模式。当然,如果分析自律性和他律性在陶瓷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人们很难说清楚伯仲,可是,丧失自律性的陶瓷文化只能受制于人。
综上所述,陶瓷文化的自律性和他律性是陶瓷文化中一个对立统一体,自律性决定陶瓷文化的自我属性,而他律性影响陶瓷文化的自我属性。当自律性处于主导地位的时候,陶瓷文化明显地表现出自我扩张的精神,相反,陶瓷文化就会沦为从属的文化地位。
4 结论
在陶瓷文化的历史上,陶瓷沿着本身材料生产与被利用的方向发展的规律,构成陶瓷文化的自律性,陶瓷文化受到其他文化影响发展的规律,构成陶瓷文化的他律性。在陶瓷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强调它的自律性占主导地位,并灵活地利用它的他律性文化因素。
1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2 冯先铭.中国陶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 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5
——《艺术自律性研究》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