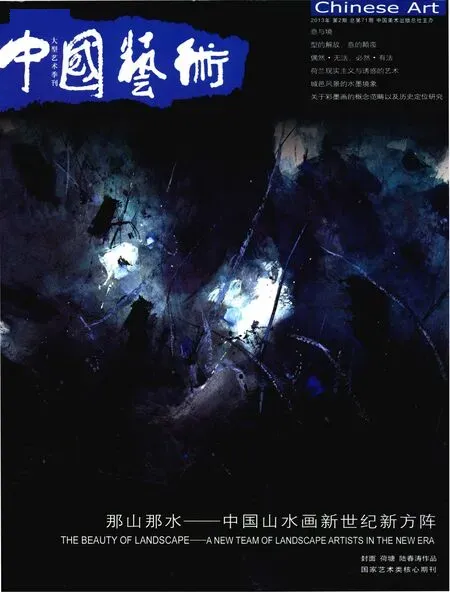民族民间手工艺传承条件的解析——基于香格里拉县尼西乡汤堆村藏族黑陶手工艺的田野调查
刘春/文
民族民间手工艺传承条件的解析
——基于香格里拉县尼西乡汤堆村藏族黑陶手工艺的田野调查
刘春/文
ANALYSIS OF THE INHERITANCE OF ETHNIC FOLK CRAFTS
随着时代精神与社会文化需求的嬗变,特定地区、特定文化环境中的民族手工艺凭借其积淀的内蕴力量,适时抓住社会发展的机遇,与时代精神、社会文化需求形成契合,熔铸了传承的良好条件,得以广泛传承和复兴。香格里拉县尼西乡汤堆村藏族黑陶手工艺就是典型案例。
民族民间 手工艺 传承条件 解析
随着工业的发展,曾经的民族民间手工艺辉煌逐渐暗淡,甚至在工业时代的浪潮中趋向湮灭,只有那些与农耕乡村生活依旧保持紧密联系的手工艺还在狭小的空间中艰难维持。但近年来,一些地区的民族民间手工艺的生存发展空间豁然开朗,民族民间手工艺传承衰微的走向急剧转变。本文试图以香格里拉县尼西乡汤堆村藏族黑陶手工艺变迁为例,进行民族民间手工艺传承条件的研究与解析。
一、尼西乡汤堆村藏族黑陶手工艺状态
汤堆村辖属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尼西乡,位于山林环绕的谷地之中。著名的滇藏“茶马古道”由南向北贯穿村中,214滇藏国道在其东山坡蜿蜒穿行,香格里拉到维西的公路在此转向。该村民小组分布有7个自然村,158户人家,人口共计800余人,民族以藏族为主。处在滇西北交通枢纽上的汤堆村,历来以农耕经济为主,人多地少,村民农闲季节也从事制陶业、采集业、运输业。烧制黑陶是村中长年延续的手工艺,是部分村民的经济收入来源。
汤堆村制陶历史久远,据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香格里拉县的相关研究人员对尼西乡石棺墓的发掘研究以及李月英等学者对尼西石棺墓与德钦石棺墓中的陶器对比分析,认为“尼西陶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民国)中甸县志》记载:尼西和东旺地域皆烧制土陶,并远销他乡。20世纪50年代,汤堆村制陶业曾一度兴盛,60年代又跌入低谷, 70年代后制陶户逐渐增多。至今,汤堆村158户中有88户从事手工制陶,产品销往迪庆州、丽江、昆明、四川、西藏、北京、广州、上海等省市,有的产品远销日本、欧美。近年来,汤堆被称为“土陶村”、“黑陶村”,成为国内外著名的藏族黑陶手工艺村。
二、黑陶手工艺传承的条件
工业时代,民族民间手工艺的总体趋向是衰微或湮灭,但有的民族民间手工艺却顽强地生存延续下来,并显示了强大的传承能力和存在的合理价值。如汤堆村藏族黑陶手工艺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中,积蓄储备了有利于黑陶手工艺延续传承并扩大生存空间的内蕴驱动力,当时代精神与社会需求嬗变之际,其内在驱动力的释放有了良好外部环境,从而保障了其顺利传承。
(一)黑陶手工艺传承的内蕴驱动力
1.藏族农耕传统生活方式的需求
汤堆村处于农耕技术不发达的滇西北高寒山谷,农耕经济收入有限,由于经济能力有限,过去围绕藏族火塘文化、宗教文化生活所需要的器皿就很少采用金属制品而选择价廉物美的黑陶器皿。又由于黑陶在火塘生活中具有吸热慢、散热慢、保温好和色泽越烤越黑越亮的特性,同慢节奏的火塘文化与高寒山区气候条件相得益彰。而在宗教生活中,汤堆村民认为黑陶器皿从火与土中诞生,更具有神圣、庄严、厚重和自然灵性。所以煨茶罐、盛水罐、炖汤土锅、烤火盒、酥油壶、油灯以及祭拜神灵祖先的酥油灯、香炉、净水碗等生活器皿均采用黑陶。汤堆村邻近地区的藏族、纳西族、普米族、傈僳族和摩梭人也喜爱黑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乡村生活与火塘文化的共同需求选择了黑陶,并成为他们传统生活的必需器物。传统农耕生活的需求为汤堆黑陶手工艺传承与生存提供了广阔空间。
2.黑陶烧制原料有保障
汤堆村自古至今未曾中断黑陶手工艺的延续传习,非常重要的条件是当地拥有烧制黑陶所需的足够数量的松柴、陶泥。村中做陶人家都从本村所属山林中就地取材。尼西乡其他村小组也曾有人家烧制黑陶,后因该村缺乏陶土原料,就停止了黑陶的烧制。这说明,汤堆村藏族黑陶手工艺的延续传承得益于陶泥原料和松木原料的保障,没有原料保障的民族民间手工艺是难以维系生存的。
3.工艺师的守望与开放维系着传承的延续
民族民间手工艺能以活态方式传承,关键在于手工艺传承人是否继续操持其所掌握的手工艺,并运用手工艺为当地传统生活提供精神与物质需求的物化支持。民族民间手工艺逐渐消亡,一个重要原因是手工艺师的逝世带走了手工艺。
汤堆村藏族黑陶手工艺传承延绵不绝的原因之一是该村始终有衷情黑陶烧制的手工艺人。他们通过家庭传授、师徒学习、口传心授,根植于传统生活的土壤上,使黑陶手工艺的普遍传承有了人才支撑。据孙诺七林师傅介绍,他11岁学习制陶,村中有5个60余岁的大师傅,他拜大舅农布恩珠为师。此后,孙诺七林一直烧制黑陶,未曾中断,并传授家中男子和收授家外男子为徒,无论亲属或非亲属的徒弟,一视同仁,教授了40多人,其多为本村人,也有外地人。这些人已成师并收授徒弟。又据孙诺江才师傅说,他家已有五代人制陶。孙诺七林曾说:“在汤堆村仅靠农业耕种,不能完全解决生活问题,得寻找别的门路,幸运的是我们有土陶技术。”汤堆黑陶手工艺人为了生活而坚守世代相传的手工艺,以开放的胸怀传承黑陶手工艺,对黑陶手工艺衷情与尊重的信念,终使黑陶手工艺以活态的形式延续传承。
(二)黑陶手工艺传承有良好的外部环境
1.茶马古道维系着黑陶销售的市场
汤堆村处于214国道下方,是香格里拉县到德钦、维西的交通枢纽,经此可抵四川、西藏。历史上走滇藏茶马古道的马帮商队从中甸建塘镇出发后的歇息地就在尼西乡,马帮由此北上德钦或折向维西。汤堆村是马帮商队休息或途径的重要村落,成为马帮商队的集散食宿地。工匠手工烧制的黑陶本与茶马文化浑然一体,藏族、纳西族、普米族、傈僳族等生活中常用的酥油壶、煨茶罐、土锅、茶碗等也就成为茶马古道上的商品之一,被马帮商队带到丽江、中甸、大理、怒江以及邻近云南的四川西藏部分地区。至今,远离尼西乡汤堆村的丽江拉伯山区的摩梭人依然非常喜欢使用汤堆村的黑陶煨茶罐。20世纪90年代以来,汤堆村黑陶烧制产量不断提高,黑陶产品种类从生活、宗教用品中衍生出了旅游工艺品,大量的产品通过214国道、香维线走向村外市场。汤堆村依托古今交通要道的优势,将黑陶产品输运到广阔的市场。市场的需求和交通的节点作用使黑陶手工艺的传承有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2.旅游产业的发展推动黑陶手工艺的传承
旅游作为新兴支柱产业在云南发展迅猛,滇西北已成为富有神秘色彩的梦幻旅游地。旅游使少数民族传统的经济、文化和生活形态融入了旅游产业,成为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伴随旅游产业的发展而进入现代社会。滇西北旅游发展对汤堆村具有直接的积极影响,村民的商品意识得到加强,他们利用交通道路优势,沿路设店开展旅游购物、餐饮服务。村民对黑陶与旅游的关系有了自己的理解,黑陶不仅是自己享用的生活用品,而且是旅游者可以带走的民族工艺品,从而扩充了黑陶品种。村民对黑陶的质朴生活情感得到了升华,形成了崇敬黑陶和以黑陶为荣的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心增强。村镇经济结构的比重发生了演变,黑陶手工艺创造的经济收入逐年稳步扩大,农耕采集业的经济收入比重降低。为了满足游客对旅游工艺品的购物需求,村民已不满足传统的黑陶工艺,开始外出永胜、剑川、建水、景德镇学习考察烧制陶艺,尝试工艺创新和品种创新。在滇西北旅游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汤堆村顺应时代的变化,将具有显著民族特色的黑陶手工艺和产品融入现代旅游业,使传统的黑陶手工艺传承达到空前规模。不难看出,旅游以其特有的文化属性和消费力量推动着特定区域的乡村传统手工艺的复苏与兴旺。
3.民族民间手工艺保护与研究活动成为黑陶手工艺传承的精神支柱
民族民间手工艺赖以生存延续的沃土是农耕背景下的乡村生活方式。自工业革命以后,世界范围内的民族民间手工艺即趋于衰微态势,从此保护民族民间手工业的呼声就未曾绝耳。在当代社会环境中,民族民间手工艺具有的地域性、民族性、独特性、创造性、实用性、工艺性、脆弱性和历史的文化记忆性再次引起社会的关注,出现了保护民族民间手工艺的热潮。尤其是进入21世纪,民族民间手工艺的保护逐渐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轨道,成为国家政府致力推动的政策性、制度性的文化工程,成为文化、学术、教育机构的学术研究活动。在政府性、社会性的民族民间手工艺保护活动中,诸多民族民间手工艺以活态的形式呈现其文化艺术的价值,成为文化研究、传播和旅游的热点,在保护与宣传的热潮中获得尊重与自信,由此建树了民族民间手工艺传承的精神支柱。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尼西乡汤堆村藏族黑陶手工艺就受到了政府和学者的关注。进入21世纪,汤堆村黑陶手工艺走向全国及世界,成为研究、保护与开发藏族黑陶手工艺的著名乡村。无论是政策性、制度性的文化保护项目,还是学术性的调研保护活动,或是民间的关注,都给汤堆村带来了积极的文化影响力。孙诺七林说:“美国、英国、日本都来买黑陶产品,发达国家的人都来参观,说明这是非常有希望的手工技术。”来自外界的肯定,唤起了汤堆村的民族尊严与自豪,由此萌生了黑陶手工艺传承的信心。黑陶手工艺的延续传承,不仅仅是依赖汤堆藏族乡村生活需求的支撑,而且有了来自汤堆村外部的文化发展需求的支撑,由文化、学术、教育、传媒机构和民间研究人员形成的保护民族民间工艺的合力,成为汤堆村藏族黑陶手工艺延续传承的精神支柱。
结语
民族民间手工艺根植于乡村农耕传统生活环境中,乡村农耕传统生活环境的变迁对民族民间手工艺的产生、发展和兴衰有着直接影响。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后,来自于乡村农耕传统生活环境下的民族民间手工艺与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逐渐脱节,与现代生活发展需求渐行渐远,呈现了衰微的整体态势,有的手工艺则成为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或成为消亡的手工艺文化记忆。但同样的时代环境下,特定区域中的特定民族手工艺却由衰微走向复兴,在当代社会寻找到了新的生存空间,获得了现代社会文化的认同,焕发了勃勃生机。这对于民族民间手工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言,无疑有许多有益的启示。
[1]华觉明.《传统手工技艺保护、传承和振兴的探讨》[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7年1期
[2]李月英等.《尼西土陶》[M].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8月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 项目编号:2012XY02
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艺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