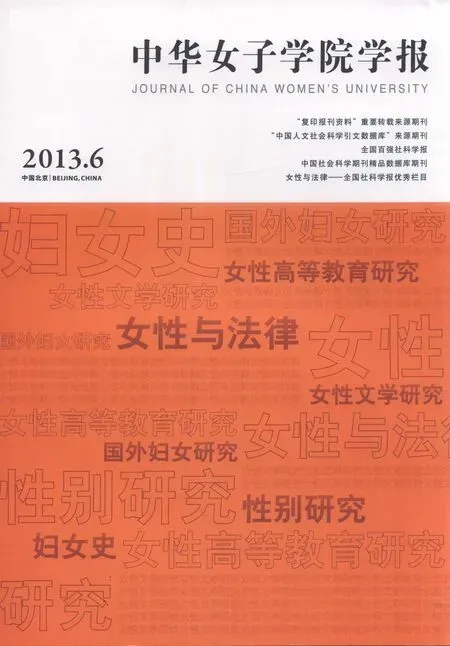从性别对峙走向性别和谐
——以张爱玲作品为例解析女性写作的价值
王灵
从性别对峙走向性别和谐
——以张爱玲作品为例解析女性写作的价值
王灵
张爱玲作为女性写作的代表之一,以其作品为例解析女性写作的价值具有典型意义。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都是一些悲剧女性,但她的写作不是纯粹的描写无良少女、堕落的妇女,而是把她们放在时代的背景下,透射出悲剧人物背后的社会事件和原因,虽然如前文所述张爱玲的大部分作品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但毕竟没有脱离时代和社会。女性写作应当避免单纯的自我言说和一味的身体写作,而着眼于两性和谐的实现,并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关注全人类的终极价值。
女性写作;性别对峙;性别和谐;误区;写作价值
中国的女性写作自产生以来,一直备受关注,与之相关的研究也层出不穷。张爱玲作为女性写作的典型代表之一,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和娴熟的写作技巧,为世人奉献了一个个鲜活的女性形象。对其本人及其作品的研究至今仍渊渊不断。本文将试图以张爱玲的作品为例,来梳理女性写作价值的发展脉络以揭示女性写作价值的终极目标。
根据以往的相关研究,女性写作的价值往往被零散的表述为女性的自我表达、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同男性强权文化的对抗以及性别和谐的实现和对整个人类的价值的终极关怀。诚然如此,但女性写作的价值在各个历史时期,并不是同时存在或同时并重的,由女性自我言说到性别对峙到性别和谐,最后转向对全人类的关注,这四个价值,概括来说实质上就是由描述性别对峙走向追求性别和谐。而女性写作价值的最终极目标在于在性别和谐的基础上,把着眼点放在全人类和全社会的利益上,这样才能永葆女性写作的活力,从而进一步实现女性写作的跨越式发展。
一、女性写作的价值
(一)女性的自我言说
早期的人类历史长河中,女性一直是处于“失语”状态的,这主要是“男尊女卑”的封建制度使得女性一直处于受压迫的地位,沦为男性的附庸,她们在婚姻关系中不是同男人一样作为婚姻关系的主体,而是沦为婚姻关系的客体并成为丈夫的附属物,甚至是被作为丈夫的私有财产,即使是在中世纪的西方情况也同样如此。教会法明确规定“夫妻一体主义”,即夫妻结婚后就变成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男人。妻子没有法律上的人格权,没有社会地位。“在19世纪以前的英国,女人要是写了一本书就可能立即招致很多人的攻击”(包括来自女性自身的)[1],所以女性要想获得发言权,要从这种男女不平等的地位中解放出来,就必须有自我意识的觉醒,而女性写作的价值之一就在于女性开始认识自我、发现自我、表达自我。由于女性自身的特点,她们相比男性更善于书写自己现实的生活和真实的心理感受,张爱玲的很多作品就是以她亲身的生活经历为基础的。由于父母的离异,在张爱玲的生活中父爱和母爱都是不完整的,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缺失的,因此,张爱玲的作品中塑造的母亲形象鲜有比较完整或完满的。比较典型的是《金锁记》中的母亲曹七巧,由于灰暗的婚姻和不幸的一生,她的母爱也畸形化,最终将一双儿女的幸福和前程毁灭在自己手里。同样在她的作品《心经》中,许小寒对父亲许峰仪的爱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父女关系,演变为一种畸恋。这两部作品中对母亲曹七巧和有恋父情结的许小寒两个形象的塑造,实质上是张爱玲对母爱的渴望和对父爱的追寻的自我叙说。张爱玲在很多作品中描写女人的服饰,包括首饰、式样、衣料、颜色等等都有较大篇幅的细节描写,这些也是她自我言说的表现。例如,在散文《更衣记》中对女人服装的描写细致入微,随手摘一小段文字即可见一斑,“穿在外面的是‘大袄’。在非正常场合,宽了衣,便露出‘中袄’。‘中袄’里面有紧窄合身的‘小袄’,上床也不脱去,多半是妖媚的桃红和水红。三件袄子之上又加着‘云肩背心,黒缎宽镶,盘着大云头。”[2]285她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描写葛薇龙的服饰:“葛薇龙在玻璃门里瞥见她自己的影子——她自身也是殖民地所特有的东方色彩的一部分,她穿着南英中学的别致的制服,翠兰竹布衫,长齐膝盖,下面是窄窄的裤脚管,还是满清末年的款式;把女学生打扮得像赛金花模样,那也是香港当局取悦于欧美游客的种种设施之一。然而薇龙和其他的女孩子一样爱时髦,在竹布衫外面加上一件绒线背心,短背心底下,露出一大截衫子,越发觉得非驴非马。”[3]137在《沉香屑第二炉香》中描写克荔门婷时,“她穿着海绿的花绸子衣裳,袖子的边缘钉着浆硬的小白花边。”[4]151在《桂花蒸阿小悲秋》中,描写秀琴“披着长长的卷发也不怕热,蓝布衫上还罩着件玉绿兔子呢短大衣。”[4]200在张爱玲的散文和小说中,像这样对女性服装的详细描写随处可见,这正是女性作家自我经验的积累和对自身生活的切实感受,是女性意识的自我言说和自我表达。
女性正是通过写作来达成自我话语权的实现,通过对女性体验和思想的表达,实现自我价值。
(二)性别对峙,冲破男权文化的突围
英国作家伍尔夫曾经说过:“现有的语句都是男人编造的,它们太松散、太沉重、太庄重其事,不适合女性使用。”[5]182因此,女性写作最初大都是从女性性别立场出发,她们渴望通过写作来冲破父权文化的堡垒,解除男权文化的绑架,完成自我身份的认同,从而反抗流传下来的几千年的封建传统,真正的改变女人“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人生悲剧。现实中,女性为了冲出男权文化的突围,往往将男性置于对立的一方,将男性视为自我解放的障碍。这种将性别对峙的女性写作,相对于女性自我解放的初始阶段而言,是进步的,但放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性别对峙不能充分利用男性在女性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没有让男性参与到妇女发展的进程中来。
在张爱玲的写作过程中,她一方面注重女性内部心理世界的描写,一方面积极探讨男权社会与人的关系,她的写作深刻地揭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的生存困境。但是,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不管是沦落风尘的舞女顾曼璐(《十八春》),还是寄人篱下的葛薇龙(《沉香屑第一炉香》),不管是身居香港华贵大宅的梁太太(葛薇龙的姑姑),还是坚强、独立的顾曼桢(《十八春》),她们总是被张爱玲描写的比男人更弱小,命运比男性更凄惨,她是把女性的悲剧命运放在几千年封建王朝所确立并流传下来的男权制度下来写的。这些女性往往是受生存或感情所迫,要么为找到一张长期饭票,要么是为填补感情空虚而结婚,最终在经济上、身体上、人格上沦为男性的附庸。女性在从属于男性的地位中,难以找到自我的主体身份。《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就是这类女性的典型代表。她为了获得经济上的供养,以自己的青春做赌注,嫁给了一个残废,葬送了自己的一生,且把一双儿女的幸福以母爱的名义毁灭在自己手里。在《红玫瑰和白玫瑰》中,热烈的红玫瑰王娇蕊爱上了丈夫的朋友佟振保,她的爱情给了振保真心的快乐和满足,但是振保却一直在自己所认为的“对”与“错”中挣扎,一会儿他那颗封建的脑袋认为,一旦跟王娇蕊结婚将是错的;一会儿他又认为,顺从自己的内心娶一个相爱的人是对的。最终,他的封建意识战胜了他的内心,他考虑到王娇蕊是有夫之妇,并且是自己朋友的妻子,她的婚外出轨行为就是一种不贞的放荡行为,如果自己娶了她,将会为社会所不齿,会毁了自己的前程。最后佟振保在母亲的安排下娶了个门当户对的白玫瑰孟烟鹂,而为了爱吃尽苦头的王娇蕊,最终还是被振保离弃,被封建的男权制度所离弃。至于白玫瑰孟烟鹂,虽然嫁给了佟振保,但佟振保自始至终对她无爱,烟鹂却“颇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架势,对振保是百依百顺,甚至遭到振保责骂的时候,“烟鹂脸上掠过她的婢妾的怨愤,随即又微笑”。[6]156发展到后来,烟鹂和裁缝偷情被振保发现,导致振保更肆无忌惮地嫖娼,无视烟鹂的存在,至此烟鹂彻底成了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同样,在张爱玲的作品《连环套》中的霓喜,她的身体不断被出卖,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最后当她发现男人和钱都不可靠,只有自己能靠得住的时候,已经晚了,衰老使她不得不屈从于自己的命运。上述作品所描写的女性基本上都揭示了一个主题,女人对自身往往是无能为力的,想要基本的生存和正常的生活,就要依赖于男性。正是这种对男人的依赖,使得女性永远处于卑微弱小的地位,或者说这种依赖某种程度上又反过来加深了女性悲惨的境地。在作品《琉璃瓦》中,姚先生有7个漂亮的女儿,他对已经成人的老大、老二、老三的婚姻费尽心思,但他对女儿婚事的张罗,并不是为了女儿的幸福,而是把她们的婚姻当成一种交易,一种谋取财富和地位的捷径,姚先生的追求就是当时男权主义价值观的体现。
总之,张爱玲笔下的很多女性都是男权社会下受压迫、受束缚的形象,她的某些作品传达出一种氛围,女性如果要从男权社会中解放出来,要追求自由,就要斗争,就要和男人激烈的斗争,她把男性放在了女性价值、女性自由、女性解放的对立面。这与她的家庭、父母的关系以及当时的男权社会是相吻合的,然而其作品中妇女“解放”的斗争几乎都以失败告终。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女性的解放和发展排除了男性这个同盟者。
(三)性别和谐的实现
如果女性写作的价值只是定位在女性的自我言说以及对大丈夫小女人的男权制度的揭露,而不能真正地构建一个健康、和谐的两性关系,那女性写作将停滞不前,陷入困境。
通观张爱玲的作品,很难找到一段美好或正常的恋爱、婚姻关系,她笔下的两性关系往往充满着斗争和算计,也难有完好的结果。比较典型的《十八春》当中,顾曼桢和沈世钧的爱情有过一段短暂的美好时光,但最终因为曼桢姐姐和姐夫的自私与诡计而分开,18年后,这一对有情人再次相遇,却都知道“我们已经回不去了”。有情人最终没有成眷属。小说的结尾,虽然张爱玲刻意成全了顾曼桢和张豫瑾,但作品终究透露出了苍凉、无奈的意味。18年,人生真的被彻底颠覆了。
《心经》中的小寒,一直为恋父情结所苦。文中的父亲许峰仪在明知自己女儿对自己的不正常的爱之后,不明朗的态度实质上纵容了小寒的感情,最终他迫于伦理的压力退出这种感情,寻找婚外恋,对于段绫卿,他只能给这个深爱自己的女子以物质的、金钱的补偿。一个男人以屡次的不忠应对三个女人(妻子、女儿、婚外恋对象)的感情,这种关系透射出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在这些描述中,张爱玲体现的就是性别对峙而不是性别融合。
在张爱玲的另一部代表性作品《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和范柳原的心理战争是典型的男人和女人的婚恋斗争,范柳原对白流苏的感情,不过是想在众多的女性中找个不同口味儿的,以填充他空虚的心,而白流苏的目的更明确,她不过是想跳出娘家人的挤兑,借自己的美貌抓住青春的尾巴来换取一点物质生活,她以性别为资本,来换取一个女人活着的最基本的物质需求。这一对男女各自心怀鬼胎,最终因一座城的毁灭而走向婚姻。但是这种婚姻可以说是非常功利的。小说结局表面上皆大欢喜,但张爱玲实际上对这段感情做了一个巨大的反讽,一场战争可以成全他们,那么战争结束了呢,和平当然也可以拆散他们。所以张爱玲作品中描写的两性关系往往是悲凉的、人情冷漠的、自私的,让人对婚姻和感情充满了恐惧、绝望和无奈。
《桂花蒸阿小悲秋》中的阿小,是张爱玲塑造的一个不太同于其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她代表了安稳的女性的典型,是凡俗人生安稳生活的象征,但实际上阿小的安稳更凸显了女性生命的悲剧色彩。她做保姆,不依赖谁,整天忙忙碌碌,放弃对命运的抗争和努力,让心灵完全被琐事所占据,正是这样才换来了安稳的人生。
张爱玲在作品《有女同车》中说:“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她的很多作品都围绕着这样一个共同的话题:男人和女人。但是通观她的这些作品不难发现,张爱玲的写作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她在作品中所抛出的两性关系,很少有积极的赞美或正面的欣赏,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尖锐地指出了男女两性的对峙。试想,如果所有的女性写作都像张爱玲的很多作品一样,只是宣扬自私、冷漠和充满算计的两性关系,而不追求更高层次的写作价值,那人类将如何构建和谐、健康的家庭,社会将何去何从。
(四)超越性别,着眼社会关怀和全人类关怀
女性写作应当超越自身的立场、超越性别对立,将视野放出去,拓展写作的广度和深度,关注社会发展的热点,在内容上更开放和更多元化,女性写作不能只写女性,也不是只再现简单的两性关系,而是应当向更高层次的价值迈进,关注社会的进步,关注生命的真谛、向着全面提升人的价值的终极目标前进。大家熟知的女作家王安忆的女性立场是竭力改变以男子为中心的文化和社会制度,从而达到改变男女两性的社会性别关系,使两性都能得到全面发展,而非男女对峙、以女性中心代替男性中心。①参见龙梅《论张爱玲、王安忆小说中的两性关系书写》,2008年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用作家张抗抗的话概括就是:“我们将走到外面广阔的天地去,用女人的心去感受除了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之外与现实世界的更为复杂的关系,并将我们的眼光放射出去,传递出女人深切的社会关怀、人文关怀和人类关怀。”[7]但是张爱玲的写作不同于丁玲、冰心等女作家,她并没有写恢宏壮大的社会变革,也没有写高远的志向和人生理想,她自己也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8]175所以张爱玲的作品一般跟政治无直接关系、跟时代的变动大局无直接关系、跟社会发展无直接关系,她所描写的是她所生活的旧家庭和她熟悉的动乱的都市。比如,造成《金锁记》中曹七巧的悲剧命运和扭曲性格的罪魁祸首就是男权社会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张爱玲实质上已经揭示出这层主题,但她也只是抛出一个主题而已,并没有着力去寻找深层答案,或者根本没有想到去解答这个问题。张爱玲的作品对婚恋、家庭的题材涉猎较多,并且她笔下的爱情大都充满了算计,婚姻也变成了无爱的婚姻。在这场关系中,婚姻更像是一种交易,男人从中得到女人这个玩物,女性找到男性这个生存的经济保障。既然女性在物质上依附于男人,那么在感情上以及生活中也要依附于男人。由于当时社会的动荡和物质的不富足,张爱玲无法彻底超越性别立场和当时的现状,也使得她无法着眼更广、更深的政治变动和社会变革。张爱玲的这种女性写作虽是一种缺憾,却也反而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女性写作的特点。
二、提升女性写作的价值,避开女性写作的误区
女性写作的价值是伴随着女性写作的发展阶段不断呈现的,女性意识的觉醒,使得女性有了自我表达的需求,自我言说,这应该归为女性写作的最低层次的价值。然而,如果女性写作仅仅是一种随心所欲、不顾其他的一吐为快,一厢情愿的自我张扬,片面的情感宣泄,那么写出的作品就会陷入庸俗低级的漩涡。女性写作应从关注女人自身转向关注两性,并且从下意识的两性对峙转向两性和谐,最终超越性别转向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
总之不管处在哪个阶段的女性写作,都应向更高层次的写作价值迈进,避开女性写作的以下几个误区。
1.从性别对峙的角度出发,极度地强调“女”字,是女性写作的第一个误区。男人和女人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女性写作时,只有以人的意识代替女性意识、从女性视角去审视男性,从人的角度的写作代替女性角度的写作,增强两性间的沟通、合作,才能使女性写作从狭隘的女性视角转向关注全人类,使女性写作真正达到以人为本的高度。
2.女性过度书写身体是女性写作的第二个误区。随着社会经济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转变,女性写作也变得商业化。为满足消费者、读者的口味及欲望,女性写作不可避免地会写到性,但是如果过于露骨的毫无节制的写性,必然会使作品成为低级下流的色情文学,一味的囿于情色恰是女性写作的大忌。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出版的“70后”女作家卫慧的《上海宝贝》和绵绵的《糖》有大量的性欲望和性过程描写。这两位女作家的身体写作,曾经遭到了一些人的批判,认为她们纯粹是在迎合消费时代潜藏的功利目的和商业目的,迎合大众的口味,而冲出了身体写作的道德底线,进行了过度的肉体写作,毫无艺术的美感。因此,女性写作时即使写性也应写得有美感、有艺术的价值和要素,做不到这一点,至少也要写得恰如其分,既不过分夸张,也不过分遮掩。例如,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红玫瑰王娇蕊是佟振保虽然最终放弃但不能真正割舍的热烈情人。在描写他们的关系的时候,张爱玲并无一句出格的身体动作的描写,却写出了佟振保从王娇蕊那里获得了性的快乐和感情的满足。当振保封建的脑袋开始起作用的时候,他劝说自己应当适可而止,但是“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根本就觉得没有辩论的需要,一切都是极其明白清楚,他们应当彼此相爱,应当爱下去”。[6]149
3.女性写作过度关注在婚姻家庭领域的两性平等,而忽略了政治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的性别公正,这是女性写作的第三大误区。女性写作首先必须把自我言说放到一个艺术性、文化性和社会性的大框架之下。不能单纯为女人而写作,也不能单纯的以与男权对立为目标,应当将性别和谐贯穿到整个社会文化中,从总体上强调女性的尊严、价值和社会存在。通过女性写作引起女性对自身社会地位的关注,不只是在婚姻家庭领域、教育领域取得与男子完全平等的地位,更应唤起女性参政的欲望,引起全社会对女性政治权利的尊重。性别平等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男女完全一样,而是在承认性别差异的基础上追求平等,从而达到更高层面的性别公正,促使两性关系和谐、健康、发展。
4.脱离时代,缺乏社会责任感也是女性写作应竭力避免的误区。一个作家应当具有社会责任感,关注他所生活的时代,着眼社会发展的潮流,反映社会现实,唯有这样才能写出具有时代精神的作品,从而感动读者,影响社会,赢得大众的关注和喜爱。但是当下女性写作往往会陷入一个误区,他们过于关注自我意识、自我体验,她们写作要么蹲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顾影自怜,哼哼唧唧;要么为了金钱和名利,一味迎合大众口味,赚取大众眼球,写出的作品低俗且乏味。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都是一些悲剧女性,但她的写作不是纯粹地描写无良少女、堕落的妇女,而是把她们放在时代的背景下,或置于社会的滚滚洪流中,从而透射出悲剧人物背后的社会事件和原因。虽然如前文所述张爱玲的大部分作品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但毕竟没有脱离时代和社会。张爱玲塑造的很多女性形象,都是可怜、可悲、又可恨的,比如,在《十八春》中的姐姐顾曼璐,她为了赚钱养家不得已做了舞女,这是她的伟大和可怜之处,后来为了拴住老公祝鸿才,她又牺牲了自己的妹妹,这是她的可恨之处,张爱玲对这个悲剧人物的塑造,实质上既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又把她放到当时的社会制度之下的,揭示了世态炎凉以及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制度根源和心理根源。这就使得作品具有了更深意义、更高层次的价值。
总之,女性写作应当走出误区,以女性独特的性别视角、细腻的内心感受和丰富的人生体验,关注全人类的生存和社会发展,唯有这样,才能提升女性写作的价值,实现女性写作的跨越式发展!
[1]王洁群,王建香.实现女性自身的价值——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写作观[J].广东社会科学,2000,(6).
[2]张爱玲.张爱玲精选集[Z].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3]万燕.女性的精神——有关或无关乎张爱玲[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
[4]王光东.沉香与倾城解读张爱玲经典[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5.
[5]弗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随笔集[M].孔小炯,黄梅译.深圳:海天出版社,1995.
[6]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A].张爱玲文集[Z].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
[7]张抗抗.半边风景半边天——漫谈女性写作[N].华读书报.2001-11-29.
[8]张爱玲.自己的文章[A].张爱玲文集[Z].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杨 春
From Gender Confrontation to Gender Harmony:Zhang Ailing’s Work as an Example Analysis of the Value of Female Writing
WANG Ling
Zhang Ailing’s work is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female writing.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the value of female writing.Female writing should avoid simple self-narration and focus on gender harmony.Its responsibilities concern the ultimate value of mankind.
female writing;gender confrontation;gender harmony;misunderstanding;writing value
10.3969/j.issn.1007-3698.2013.06.012
:2013-06-20
I206.7
:A
:1007-3698(2013)06-0070-05
王 灵,女,山东女子学院学报编辑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女性与法律、女性与文学。250300
——细读《孔雀东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