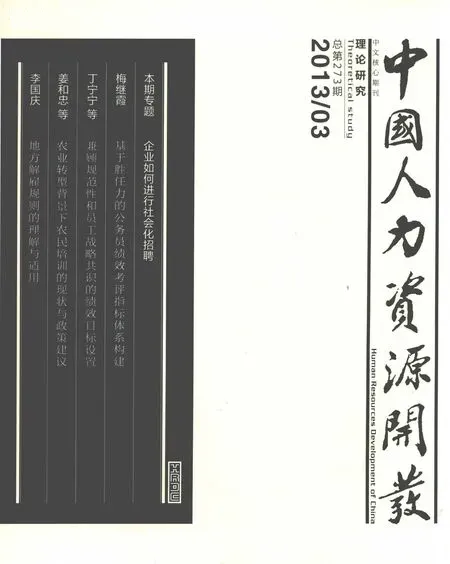农业转型背景下农民培训的现状与政策建议
● 姜和忠 徐卫星
■责编 / 韩树杰 Tel: 010-68345891 E-mail: hrdhsj@126.com
我国是人口众多而耕地等农业自然资源极为匮乏的国家,资源集约利用、内涵式发展的现代化农业转型是我国粮食安全以及农产品稳定供应的迫切需要。为此,政府应通过投资教育提高农民素质,把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但近10年来,我国农民培训供给规模有限,不能满足培训需求,亟需政府从立法、组织规划以及培训体系建设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
一、农业现代化转型与投资农业人力资本
1.自然资源约束下,农业现代化转型是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我国是人均耕地、淡水等农业自然资源极为短缺的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的耕地占用、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人口基数的增加将进一步加剧这一短缺状况,农业发展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明显上升。自然资源约束下,如何实现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是我国长期面临的难题。优化配置农业生产要素,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建立资源集约利用的内涵式发展的现代化农业,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舒尔茨认为,将传统农业改造成高效率的经济部门,出路是引入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其中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关键因素,因为农民的技能和知识水平与其耕作的生产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因而,引入新生产要素,除了机械等物的要素,更要引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能运用新生产要素的人(舒尔茨,2006)。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业科技定位为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出路,而发挥农业科技在农业现代化中的作用,离不开科技最终使用者农民自身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
2.政府通过补偿投资农业人力资本,是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转型的重要环节
引入现代生产要素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也可能增加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但引入新生产要素毕竟需要成本,作为新生产要素需求者的农民,其经济行为也是理性的,如果投入不增加自身收益或比较收益低,将降低农民投资新生产要素的积极性。实际上,农业生产具有显著的公共产品属性,相对于新生产要素引入产生的巨大社会与生态效益,农民耕作获得的比较收益低,承担的外部性成本高,对农民投资新生产要素、集约利用耕地等自然资源的激励不足,农地的粗放经营乃至弃耕抛荒也是农民的理性选择,这会加剧农地资源的隐性流失。农业生产效率以及农地资源集约利用水平,实质上是农民基于其所面临的自然、经济以及制度环境约束条件下,所采取的农地利用行为方式的直接结果(吴郁玲、顾湘、周勇,2012)。因此,探讨影响农民耕地利用行为的相关因素,并根据这些因素提供相应的制度安排才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推动农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农地保护补偿被视为是内部化农户外部性成本、提高农民农地经营激励的有效措施,但单纯的经济补偿对农民的激励效率较低。通过政府补偿投资农业人力资本,内部化农民投资新生产要素的外部性成本,相应提高其农业收益,不仅是农地保护补偿更为有效的途径,也是推动农业现代化转型的重要环节。《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十二五”发展规划》把加强农民教育培训,视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措施和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面临的新任务。
二、我国农民培训的供给现状分析
本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以及《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整理,分析我国近年来的农民培训供给情况,结果发现:尽管我国农民培训机构软硬件条件有所改善,但农民培训供给主体结构与培训内容相对单一,培训规模逐年下降,农民培训的有效供给严重不足。
1.农民培训机构办学条件有了较大改善
2003-2010年的8年间,全国农民培训学校的各项固定资产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增长最快的是现代教学设施。其中,多媒体教室座位数由103669个增加到385128个,增长271.5%,语音实验室座位数由33135个增加到102577个,增长209.6%,教学用计算机的台数由131512台增加到201158台,增长了52.6%,现代教学设施的快速增长也反映了农民培训学校教学方式和手段的巨大改变。同期,学校占地面积以及教学行政用房建筑面积也分别增长了22.0%和60.9%。同期,农民培训学校的注册学生数下降了26.9%,从4684万人下降到的3424万人,在校学员总数的下降与农民培训教学资源总量的增长反映了农民培训学校生均教育资源有了较大幅度的改善。
但是,农民培训学校的办学条件与城镇职工培训学校依然存在较大差距,2010年,代表现代教学设施水平的生均多媒体教室座位数、语音实验室座位数以及教学用计算机台数,农民培训学校与城镇职工培训学校之比分别为8%、9.4%和13%;农民培训学校生均占地面积、教学行政用房建筑面积与图书藏量也分别只有城镇职工学校的60.1%、49.7%和30.8%。①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4-2010)数据计算,其中,源自《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0)的数据为2010年的,而非2009年的;《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等未提供2003年以前的学校资产数据。即便考虑到城乡培训所需资源的差异性,培训资源的城乡差距仍然过大。
2.农民培训机构基本由政府主办,社会化程度极低
2011年,在全国103420所各类农民培训学校中,各级政府部门以及农村集体主办的有102640所,占了总数的99.2%,所培训的学生数也占了培训学生总数的99.5%。2004年,民办农民培训学校数为892所,占农民培训学校总数的0.5%,2011年,民办农民培训学校数下降为780所,但所占比例微升至0.8%。横向比较,2011年,民办城镇职工培训学校占职工培训学校总数的24.2%。②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整理、计算。可见,农民培训的社会参与程度极低。
农民培训具有公共产品性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农民培训也大多由政府主导, 但其政府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政策法规的制定与经费投入保障等方面,基本上形成了政府、行业协会、教会及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等多元化的主体结构以及由高中等农业院校、各级农业科技教育培训和民间各类培训服务机构组成的多层次培训结构(赵正洲、王鹏、余斌,2005)。
3.以初级生产技术培训为主,尚未形成多层次多目标的农民培训体系
农民培训的目标相对单一,基本为初级生产技术类培训,科技文化教育以及系统化的中、高等职业教育极为薄弱。一是相对于农村庞大的文盲半文盲群体,与职业技术教育配套的农民中小学教育规模仍然偏小,2008年③统计年鉴未提供2008年后的农民中小学结业人数。农民中小学结业总人数为310.8万人,仅占该年培训总人数的6.7%。缺乏基础科技文化知识仍是部分农民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的障碍因素;二是系统化的农民中、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严重滞后,2010年,全国农民高等学校毕业学生总数仅为865人④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9,2011)整理、计算。,长期性的、系统化的生产技术培训比例很低。
单纯的技术传授不能提高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教育培训必须注重科学价值观念的培养,忽视观念教育的单纯技术教育是治标不治本的浅层次教育(朱启臻,2008)。实际上,除了初级技术培训,农民教育还应包括针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管理所需的农业经营管理培训、面向市场的农产品销售培训和促进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创业教育等职业培训,参与农村基层组织活动的公民教育以及提高基础科学文化素养的科技文化教育等等。
4.学校数量快速萎缩,年培训人数急剧下降
2011年,全国农民培训学校数量从2001年的49.6万所下降至10.3万所,10年时间约80%的学校被撤并,其中下降速度最快的年份是2001-2003年,从49.6万所下降至21.5万所。在培训学校总数下降的同时,单校规模却有所扩大,校年均结业学生数由2001年的176人提高到2011年的338人;校均专任教师数、校均占地面积以及校均教学行政用房建筑面积等教学资源均有较大幅度增长。从地区分布来看,农民培训学校数量减少速度最快的几个地区依次是湖南、黑龙江、安徽、江西、山西、四川及广西等。
与培训学校数量同时快速萎缩的还有年培训总人数。全国农民培训学校年培训学员数从2001年的8732.3万人下降到2011年的3794.7万人,下降比例高达56.5%。培训人数的快速下降一定程度反映了农民转移就业、农村就业人口减少的现实,但同期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第一产业劳动力从3.6亿人减少至2.8亿,下降比例仅为22.2%①本节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2)和《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2)整理、计算。,统计数据无法支持农业就业人口的减少就是农民培训人数快速下降的主要原因。相关研究显示,近70%的被调查农民有参与培训的需求(陈华宁,2007),参与培训人数少主要是由于开展的培训供给不能很好地满足需求, 培训效果不理想(柳菲、杨锦秀,2009)。总之,相对于目前仍然庞大的农业人口以及农业现代化转型的需求,我国农民培训的供给规模依然太小,有限的供给也不能有效满足需求。
三、提高农民培训有效供给的政策建议
1.加快农民教育培训立法与规划进程
我国目前尚没有一部全面规制农民教育目标体系、功能定位、组织管理以及经费保障等内容的全国性法律法规。在总结各地农民教育实践与地方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加快农民教育立法的进程势在必行,以使农民教育规划、运行管理以及经费保障有法可依。
政府应设立专门的农民教育规划机构。规划机构负责农民教育需求的研究、教育目标和功能的规划,前期为农民教育培训立法提供支持,后期日常工作主要是依据农民教育培训法律法规负责培训内容设计、教学过程指导甚至编写培训教材,提高农民教育培训的标准化与规范化水平,以使培训供给真正满足农民需求。
农民教育的目标体系规划和功能定位应满足农业现代化转型以及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要求。尽管调研显示,生产技术培训最受农民欢迎,但要培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除了生产技术培训之外,农民教育培训目标应涵盖科技文化培训、公民教育培训、创新创业职业培训以及经营管理培训等。农民类型的科学分析与定位,也是制定农民培养目标、培训内容的科学依据。李水山(2009)将农民划分为基础型、骨干型以及先导型三种,三种农民各有不同的教育需求。针对不同类型农民的教育需求,规划和管理部门引导培训机构按规划要求提供不同类型的培训内容及教育模式。
2012年,农业部发布了《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了“十二五”期间我国农民教育培训的主要任务及保障措施等,这无疑将会为我国农民教育培训的发展方向与实施保障产生积极作用,但我国的农民教育资源分散配置于不同的部门,如何优化配置这些资源、发挥其整体效应仍需配套的制度安排。
2.构建统一的农民培训管理组织,统筹配置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资源
我国当前的农民教育分属于教育、科技、农业等多个部门,没有统一的农民教育管理机构。多头管理阻碍了农民教育的资源整合和统一规划,部门之间的各自为政、培训资金的各自使用与培训活动的各自实施,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构建统一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农民教育组织管理网络,有助于农民教育的整体规划、教育资源的整合以及教育活动的指导、监督及考核,以提高农民教育的供给质量和农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
我国职业教育资源分散配置、整体效应较低的情况,不仅存在于农民教育培训领域,城镇职工职业教育以及普通高等、中等职业教育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因而,打通现有普通职业教育与成人职业教育的界限,构建全国统一的职业教育体系与管理机构,提高我国职业教育的整体规划与教育资源的集约利用水平,应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但鉴于我国农村地域分布广,城市职业教育资源服务于农民教育培训仍存在若干障碍因素,职业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仍需分布实施。当前可以对分布于不同部门的农民教育培训资源进行整合,以提高现有农民教育培训资源的配置效率;长期目标应该是将农民教育培训纳入到未来统一的职业教育体系中,统筹发展我国的城市与农村职业教育、普通与成人职业教育,直至逐步消弭它们之间的界限。实际上,加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统筹也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要求。
3.建立以耕地保护补偿基金为投资主体的资金保障机制
近年来,中央政府加大了财政支农力度,政府主办的各类农民培训学校的办学条件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但经费保障问题仍是制约农民教育培训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结合前文分析,除了中央和省级政府继续加大公共财政对于农民培训的专项支持以外,建立以耕地保护补偿基金投资为主、市场化筹集为辅的资金保障机制不仅具有合理性,也可以为农民培训有效供给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2008年,四川成都在全国首创耕地保护基金对农民耕地保护进行补偿,广东佛山等地此后也开展了类似的实践,而耕地保护补偿、农业现代化以及农民培训也一并写进了2008年10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中。从上述两地的实践来看,其资金来源与使用范围并不相同,成都主要来源于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和土地出让金, 目前主要用于缴纳农民的养老保险补贴;而佛山主要来源于财政预算和土地出让金,资金使用范围涵盖农村医疗、养老保险、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管理服务等。通过耕地保护基金对农民进行补偿在我国仍处于探索阶段,建议该补偿机制在全国推广时,通过耕地发展权市场化交易等手段拓宽资金来源,并将农民培训明确纳入耕地保护基金的使用范围。
实际上,通过提取土地出让金的一部分用于农民培训的地方实践早就存在,只是没有使用耕地保护基金这一名称。从2003年开始,浙江衢州市每年从土地出让金拿出一定比例用于农民培训,衢州的农民培训充分尊重农民意愿,通过发给农民培训券,由农民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学习时间,5年内有效,这一实践值得总结与推广。2011年,提取土地出让金的一部分用于农村教育的规定,也出现在财政部与教育部联合下发的《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中。通知规定,从2011年开始,各省级财政部门须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10%的教育资金,该资金目前重点用于农村基础教育, 使用范围尚未明确提及农民培训,但土地出让金的部分比例或耕地保护基金用于农民培训的中央政策支持仍值得期待。
除了资金来源不稳定以外,因部门利益与界限难以打破、管理机构与实施主体不分导致的资金使用监管难、使用效率低也是制约我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的重要因素。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实现农民培训的管办分离有助于提高培训资金的使用效率,培训实施应交由教育相关主体,而地方政府和农业主管部门可以作为资金的管理与使用者,向教育实施主体“购买”教育培训产品,并监督资金的使用情况。澳大利亚众多的技术与继续教育(TAFE)学院也是政府拥有,政府向学院拨款是采用商业化方式进行,即政府作为教育培训商品的“购买者”出现,这样不仅可以破除资金使用的监管难题,也因为学院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有助于激活培训实施主体的活力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4.引导形成多元主体参与、有序分工的多层次农民培训体系
农民培训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理应由政府主导,但政府主导或政府提供不等于政府直接生产。政府垄断公共产品生产往往效率不高,我国现有的农民培训机构基本由政府或准政府主办,没有外部的竞争压力,内部也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官办培训难以满足市场化择业的农民所需。政府主办的各类农民培训学校生源的大幅下降与农民需要的培训得不到满足并存的局面,实质是有效供给不足。提高农民培训的效率也需要引入市场机制,除了实施管办分离,政府通过“购买”培训产品推动现有培训机构的市场竞争之外,还需扶持企业、农民专业协会、行业协会以及民间培训机构的成长,以逐步形成不同培训主体有序分工、公平竞争的农民培训体系,而政府的主导作用应更多地体现在体系规划、标准制定以及绩效考核等政策供给与资金保障等方面。
我国农民培训的市场化运作尚处于探索阶段,规模仍然较小。在当前尚未形成多元主体参与农民培训的背景下,需要通过加强考核与示范激励等方式激发现有公办培训机构的活力,提高培训的质量。但部门利益与农民培训管办不分的局面,加大了考核与监督的难度。因此,打破部门利益,管理机构与实施主体分离仍是关键。
另外,培训层次过于单一,即提供初级技术培训、缺乏中高等职业和学历教育也是我国农民培训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难以满足农业现代化转型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农业现代化意味着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与集约化,这需要一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有创业理念与能力、懂经营、会管理的较高素质的职业农民队伍。按照管办分离的原则,与其在现有农民培训体系内重新或创建中、高等农民职业院校,不如充分发挥现有教育系统农业类职业院校的资源,采用政府“采购”形式,对农村初高中毕业生、村组干部、农业经纪人、种养大户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骨干等进行创业培训、经营管理培训以及学历教育,改善农业劳动者学历结构,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使之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带头人和骨干力量。
5.合理布局农民培训教学点
随着农民培训资源的整合,农民培训资源更多被配置到乡镇一级,村办农民培训机构有弱化趋势,村办农民培训学校所培训的学员数所占比例从2004年的52%下降至2010年的42%,同期,乡办农民培训学校培训的学员比例从40%上升到48%。①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2010)相关数据整理、计算。一般而言,将有限的资源集中配置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益,但教学资源配置的上移也会给偏远地区农民参与培训带来不便,增加这些地区农民参加培训的成本,降低了农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因此,农民培训在资源配置上应当兼顾效益与公平。
1. 西奥多·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2. 吴郁玲、顾湘、周勇:《农户视角下湖北省耕地集约利用影响因素分析》,载《中国土地科学》,2012年第2期。
3. 赵正洲、王鹏、余斌:《国外农民培训模式及特点》,载《世界农业》,2005年第6期。
4. 朱启臻:《农民教育重在提高有效性》,载《农村工作通讯》,2008年第8期。
5. 陈华宁:《我国农民科技培训分析》,载《农业经济问题》,2007年第1期。
6. 柳菲、杨锦秀:《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培训的需求调查与思考》,载《农村经济》,2009年第12期。
7. 李水山:《我国新农村新农民培养目标与模式研究》,载《职业与教育》,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