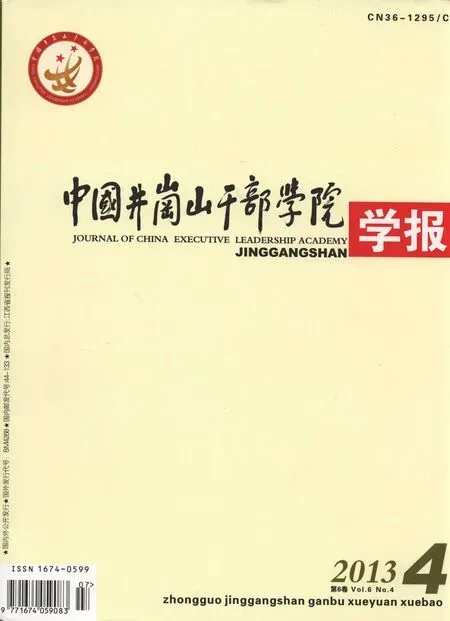女性解放与政治解放的互动
——以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村妇女动员为例
□戴 超 李永刚
(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女性解放与政治解放的互动
——以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村妇女动员为例
□戴 超 李永刚
(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女性是政治的绝缘体。在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如何动员占总人口半数左右的农村妇女参与革命是个难点。本文运用政治动员的视角来梳理共产党动员农村妇女参加革命的社会背景与方法路径:将女性解放与政治解放相结合,一方面使前者依附于后者,另一方面,女性解放并非处于完全被动的局面,二者之间形成的良性互动使农村妇女的革命动员顺利实现。
女性解放;政治动员;农村妇女;土地革命
毛泽东曾说过:“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1]P44传统社会中,农村妇女是男性的附庸,受教育程度低,基本是政治的绝缘体。在中国革命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如何对农村妇女这一群体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妇女的政治动员有何特点?正如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指出:“女性是在具体话语中被界定的,女性身份是多样性、流动的。”[2]P303也就是说,女性性别身份的构建是通过文化、意识形态的运作实现的,女性解放的问题不能够从社会进步、国家发展这一总体情势中剥离出来而孤立地解决,每个妇女的个体命运都与国家、社会的整体命运息息相关。本文尝试以观察共产党的农村妇女革命动员的社会背景和方法路径,研究在中国革命语境下女性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
一、共产党开展农村妇女革命动员的历史背景
我国的女性解放运动是在民族革命、社会革命的大背景下进行的。马克思曾经这样说过:“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包括丑的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3]P586
具体到中国的革命情境下,随着五四以来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城市女工运动的迅速勃兴,中国妇女阶层在革命中的表现和作用,妇女解放运动不断发展。但在中国这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结构下,妇女解放运动仅仅单靠女工的力量来进行斗争是无法实现的。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妇女,她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承受的痛苦和磨难更深重,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豪强地主之间的矛盾也更加尖锐,她们革命起来的斗争性也更加的坚强。共产党在经过不断的探索与调整之后,确定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农妇是妇女群众的一大部分,且她们同受着一般农人们的生活压迫的苦痛,并操作那无报酬的长久劳动,是一般妇女群众受压迫最深的妇女……因此,农妇运动与国民运动,就有很大的关联。”[4]P400中国共产党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中,把妇女解放纳入到国民革命的斗争中,特别是把农村妇女发动起来,壮大了革命的力量。
二、共产党开展农村妇女革命动员的方法路径
政治动员有三大要素:一是意识形态的宣传劝导,即对动员客体的意识形态说服、灌输,旨在从心理意识和价值观的引导和塑造方面获取动员客体的支持与服从,体现着迈克尔曼所说的意识形态的权力;二是人际联系网络的构建,即是将原本处于分散无序状态的动员客体联结起来,整合为某种结构的人际联系网络,置于动员主体的领导和支配之下,成为后者随时可以利用的群体资源;三是特定旨向的集体行动,也即在动员主体的激励、组织和指挥下,动员客体集体性地参与执行动员主体所赋予的任务与目标。这种集体行动如果呈现为民众大规模、协同式的群集状态,通常便被称之为群众运动,但也可能以较为分散化的共同参与形式进行。
(一)意识形态宣传劝导:农村女性教育的普及
美国学者约瑟夫·罗西克(Joseph S.Roucek)将意识形态定义为属于某种特殊社会集团的思维方式,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是“表明一种关于社会生活的理论,这种理论从理想的角度接近事实,证明其分析的正确”[5]。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是一套解释体系,这套解释体系构成一个认知框架,并提供行动指南。中国传统社会中,“女子无才便是德”,农村妇女大多并未受过教育,这为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宣传提出了挑战,也是重大机遇:把意识形态的宣导融入农村妇女的教育中,农村女性教育普及之时,即共产党意识形态宣导成功之日。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说过:“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6]P200在革命战争年代,教育的目的就是为革命战斗服务。教育为着战争就是去满足战争的需要,帮助实现战争的动员。共产党在农村普及教育是革命文化建设的基础和前提。发展教育事业,使广大贫苦工农享有受教育的权利,通过教育使苏区军民扫除文盲,逐渐提高文化知识水平,这不仅是进行苏区各项建设的必备条件,也是共产党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要手段。
1932年6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关于保护妇女与建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的训令》。《训令》指出,为了提高妇女的政治文化水平,各级的文化部应该设立妇女学校,组织妇女识字班,也可办家庭临时识字班、田间流动识字班。教员由政府干部、群众团体干部和当地学校教员担任。于是俱乐部、妇女夜校、问字所、识字班、读报团等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为妇女们提供了学习的机会和场所。赣南、闽西苏区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规定6岁以上的女孩同男孩一样实行免费教育,19岁至30岁的青年要参加夜校学习,妇女要占一定比例,并且打破了童养媳不上学的陋习。每村建立一个妇女夜校,以屋场或街道为单位,组织妇女识字组,每晚识字1-2小时,利用识字竞赛的方法,提高妇女识字的积极性。每位妇女每月要认30至50字,并能写出来,开展个人与个人、村与村、乡与乡的识字竞赛,并定期评奖。在俱乐部,每位妇女都要贴出墙报,每10天出1期,张贴在热闹的地方。读报组每五天读报一次,政治讨论会和各种研究会,每月举行两次,妇女们都要发表意见,相互讨论和研究如何加强妇女政治认识能力和工作经验总结能力。根据地的妇女把学习文化看作同打土豪一样的头等大事。为了动员妇女们学习文化,他们用通俗易懂的歌谣来号召,如《劝妇女读书歌》等。[7]P409
在苏维埃政府的号召下,青壮年妇女在紧张的劳动之余,拖儿带女到夜校学习;年老的妇女也不落后,她们婆媳同学或是祖孙同上校。字识多了,妇女们慢慢能看书报,可以讨论国家大事。据统计,当时闽西苏区的2053所夜校中,妇女夜校就占60%。
作为意识形态的有力宣传手段,农村妇女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接受了共产党描绘的共同愿景,普及教育为共产党发掘农村妇女的革命性提供了有效的平台。
(二)人际联系网络构建:农村妇女组织广泛建立
亨廷顿(Huntington·Samuel·P)在《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中曾经指出:“弗赖在1966年说,‘没有组织就没有权力,没有权力就没有在国家生活中的表现。’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从而也是政治自由的先决条件。在进行现代化的世界里,谁组织政治,谁就控制了未来。”[8]P496如他所言,对组织的强调已成为共产党运动区别于其他民族主义运动的关键标志。共产党可以把“支部建在连上”,亦可以把共产党组织辐射到广大农村妇女中,使妇女组织成为共产党组织的延伸。
党的“六大”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决定,“党必须在劳动妇女中作系统的、经常的指导,自中央直至支部,必须至少有一人负妇运之责,或视相当情形组织妇女委员会”。“农民组织之中要有妇女委员会,妇女必须参加苏维埃政权。”[9]P521930年11月,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的工作计划中就苏区的群众组织与群众工作对妇女组织问题有指示:“妇女群众在苏区中,不需要独立的组织,应按照她们各自的社会地位分别加入各种社会团体。她们在这些团体之中,与男子享有同等的权利,并且党团在这些团体中,尤其在公会贫农团中,应特别注意推举女工农妇的积极分子到指导机关中参加实际工作,以培养她们的做事能力”。[10]P327
在党的高度重视下,中央苏区的妇女组织普遍建立起来。当时妇女组织大约有三种类型:党内恢复重建的妇女部或妇女委员会,包括农村系统的妇女委员会、工会系统的女工部等;政府内部具有咨询协调性质的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群众性的女工农妇代表会议。
1.土地革命时期的妇女委员会、妇女部的建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中央到地方都没有单独成立过妇女群众团体。但是在党内,各级组织(中共中央、省委、特委、县委、区委)都设有妇女工作委员会(或称妇女部)。设有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支部设有妇女工作干事。贫农团等群众团体中,也设有女工部或妇女部,其职能负责各团体的妇女工作。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公布《苏维埃政府组织法案》,规定各级政府组织妇女委员会和妇女部,统一对妇运工作的组织和领导。
2.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
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为使劳动妇女能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彻底解放,更好地参加革命斗争和政权管理工作,改善和提高妇女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各级苏维埃政府需组织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至少由三人至五人组成之,党的妇委书记及群众团体妇女部主任都可以加入该委员会为委员”;“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设主任一人,以总揽该委员会的工作,不分科。主任及委员会由人民委员会及各级政府的主席团委任之”[11]P55。
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既不是妇女部,也不是政府的具体工作部门,而是各级苏维埃政府关于妇女工作的咨询部门。其任务是:“调查妇女的生活,具体计划改善妇女生活的办法,向人民委员会或各级政府的主席团会议提议,得该项会议通过后才发生效力。”[7]P551932年6月20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出第六号训令,明确规定:“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是政府组织中一个关于改善妇女生活的专门委员会,与土地劳动文化等部都不同的,他不是政府的一个行政部分,他的一切计划和意见须提交同级政府主席团讨论和批准,决定后由该级政府用命令来实行。但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不能自己命令下级政府执行,仅限于上下级委员会对于工作之指导。”[12]P4
3.农妇代表会议
1933年初,中共中央局决定在中央苏区设女工农妇代表会议,其任务是传达党中央关于妇女群众工作的布置决议、指示,收集和反映妇女的意见和要求。农妇代表会并不是一种常设的妇女群众组织,没有独立的系统,但是又定期地召开会议(一年一次或数次),每次农妇代表大会何时召开,均由各级党的组织决定。自1933年后,各根据地普遍建立农妇代表会议,农妇代表会议作为“传达共产党及工会的影响到农妇群众中去的最好组织形式”[13]P302,有力推动了苏区妇女运动的发展。1933年11月,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指出,苏区妇女在查田运动等各种群众斗争、经济战线、文化战线、军事动员、苏维埃组织等方面明显地表现出她们的英雄姿态与伟大成绩,而“女工农妇代表会的领导与推动,是紧要的关节”[14]P314。
(三)特定旨向的集体行动:政治经济的全面参与
1.农村妇女参政不断扩大
苏维埃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妇女参政地位,最大限度地发挥妇女对革命事业的支持。临时中央政府指出,“各级苏维埃政府应承认妇女在革命战争中有力的作用”,同时批评了那些很少注意或轻视妇女权利的倾向。指出:“苏维埃政府之下男女是一律平等的,不但劳动妇女在政治上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且应吸收妇女参加政权机关的一切工作,使广大妇女群众团结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积极来为实现她们自己全部权利而努力。”[15]
第一次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明确规定:在苏维埃区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苏区妇女与男子一样,凡年满16周岁以上,都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召开各级党代表大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及各群众团体代表大会时,妇女代表都占有一定份额。1933年8月在进行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时,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发布的关于选举运动的训令中,特别指出:“这里应提出劳动妇女的成分,至少要使有占百分之二十五的劳动妇女当选。如果过去乡苏市苏全无妇女代表的地方,这点尤为注意。”[16]P129
2.广大妇女参加农业生产
土地革命初期,中央苏区的广大青壮年大部分都当红军或支前去。因此,发动妇女参加生产,既是妇女解放本身的需要,也是发展根据地农业生产和各项经济建设事业的需要。毛泽东同志指出:“有组织地调剂劳动力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是我们农业生产方面最基本的任务。”[17]P132当时中央苏区无劳动力或劳动力不足的占四分之三。男劳动力少了,妇女们就把家乡的生产等重担勇敢地挑起来。为了推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1930年党和工农民主政府对妇女制定了新政策,即加强党在农村妇女中的领导。在1933年5月14日的《红色中华》写道:“更令人钦佩与称赞的,则全区(指闽西)生产的劳动工作,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妇女做的,而全区会耕田的妇女同志占百分之五十以上,才溪区妇女真是一支有力的产业军。”[18]P19
至此,共产党的政治动员包括了意识形态、组织、集体行动三个方面,全面而有力,成为农村妇女参与革命的有效杠杆。农村妇女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领域热情高涨地加入革命的队伍。
三、共产党开展农村妇女革命动员的特点:女性解放与政治解放的二元互动
(一)突出女性解放
在中共六大通过的妇女问题决议中,对过去忽视劳动妇女群众作用的特点进行了批评,并充分肯定了女工农妇是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的主力,特别是“在乡村经济中,妇女之异乎寻常的困苦状况,过分的劳动,在家庭习惯及社会风俗上完全没有权利等,成为吸收一般农妇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及夺取她们到革命方面来的条件”[9]P16。在中共六大通过的《农民问题决议案》中也肯定“吸收农民妇女群众加入斗争有极大意义”,“农民妇女乃斗争着的农民中最勇敢的一部分,轻视吸收农民妇女到运动中来必然会使农村革命减少力量”[19]P212。在中共六大上妇女作为重要革命力量的地位被确定下来。
女工农妇运动工作路线的制定,关系到妇女运动是否能够蓬勃开展。1929年12月中共中央第58号通告中指出:一是将农妇组织在农民组织中,在农民斗争中开展农妇工作;二是动员妇女参加苏区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项工作;三是在不与农民整体利益发生冲突的前提下,为农妇的特殊利益要求斗争。在苏维埃政权内,为保证妇女运动能够在正确的方针指导下开展,共产党在苏维埃区域颁布了一系列贯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利益的法律政策。
(二)女性解放从属于政治解放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在革命时期,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随着我国的政治解放运动不断发展。与世界女性解放运动不同的是,它不是女权主义的结果,而是社会革命的直接产物。从意识形态到行动选择,妇女组织的建立、发展女性教育、妇女参政、经济生产等“解放妇女”都是民族觉醒的产物,也是民族主义革命的重要内容。正如阿伦特所言,革命的目的过去是而且一向就是自由。[20]P2自由平等的个体解放诉求是革命的奋斗目标。但是在革命过程中需要的是统一的意志而非自由的个体,妇女解放必须服从于革命的基本要求,在革命的视域下妇女运动的总要求是反对敌人,而不是专门掀动两性间的仇视与倾轧。理解革命时期的女性解放应该从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观念出发,女性解放的路径与措施都应适应于革命的斗争形式。
1931年12月11日,《中央关于扩大劳动妇女斗争决议案》明确指出,共产党在苏区妇女工作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妇女参加土地革命的斗争,强调妇女的特殊要求不能超出本阶级范围之外,指明农妇只有在农民斗争中才能获得真正解放的道路,从而纠正了偏重恋爱婚姻问题的偏差,将农妇运动引入土地革命。因为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始终融在世界性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它以社会革命的形式与世界发生关系,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与西方的女权运动不同,它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框架下进行的,与西方女性主义是以个人为核心的“女性主体觉醒不同,中国妇女的觉醒总是伴生着民族的觉醒,民族群体意识超越性别主体意识”;与西方女性主义主动向已经足够发达的男性中心社会要求权利不同,在中国,妇女的运动总是伴随着社会改革或社会革命。[21]P132
结语
在任何时代,女性都在历史中扮演一定的角色,无论是被动员或是自我觉醒,女性的思想与行动都在历史的洪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与传统中国相比,当代中国女性的地位逐步提升,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不断取得成就。共产党革命时期的成功经验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但对于当代的我们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对妇女的动员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虽然各个时期妇女动员的目的不同,但是很多社会动员的理念、方法具有相通之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妇女动员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认真总结学习这些经验对当前动员广大妇女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建设和谐社会与进一步实现妇女自身解放都有深远意义。同时,在借鉴和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还要与时俱进,根据新时期的新国情进行新探索、新创新。
[1]全国妇联.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妇女解放[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美〕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女性主义与批评理论[A].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C].孟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1937)[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Joseph S.Roucek.A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Ideology[J].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ume 5, Issue4(Oct., 1944)
[6]〔苏〕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谢济堂.中央苏区革命歌谣选集[Z].厦门:鹭江出版社,1990.
[8]〔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9]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A].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1937)[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顾秀莲.20世纪中国女运动史[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8.
[1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组织纲要[A].江西省妇女联合会、江西省档案馆.江西省妇女运动史料选编[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12]萧茂普.赣南妇女运动史料选编:第2册[Z].1997.
[13]苏区中央局关于女工农妇代表会议的组织暨工作大纲[A].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1937)[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14]毛泽东.长冈乡调查[A].毛泽东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5]毛泽东,张国焘.临时中央政府文告人民委员会训令第六号[J].红色中华,1932(26).
[16]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二十二号——关于此次选举运动的指示(1933年8月9日)[A].厦门大学法律系、福建省档案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
[17]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1933年1月23日)[A].毛泽东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8]龙岩地区妇联妇运史资料征集小组.闽西妇运史资料:第1册[Z].1986.
[19]农民问题决议[A].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20]〔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7.
[21]李小江.解读女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胡硕兵)
TheInteractionbetweenFemaleEmancipationandPoliticalLiberation:theMobilizationofRuralWomenduringtheAgrarianRevolution
DAI Chao LI Yong-gang
(SchoolofGovernmentManagement,NanjingUniversity,Nanjing,Jiangsu210046,China)
Women are political insulator in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ocieties.During the process of revolution,it is a difficult to mobilize rural women,who account for abut a half of the total population,to participate in the revolution.This paper,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mobilization,analyzes the social background and channel for the CPC mobilizing rural women to participate in revolution.The CPC combines female emancipation with political liberation.The former is dependent on the latter,but female emancipation is not in a completely passive position.The goo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makes the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 of rural women be realized successfully.
female emancipation;political mobilization;rural women;agrarian revolution
K263
A
1674-0599(2013)04-0073-06
2013-04-08
戴超(1989—),女,汉族,江苏常州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性别政治。李永刚(1972—),男,重庆开县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副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治学基础理论、互联网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