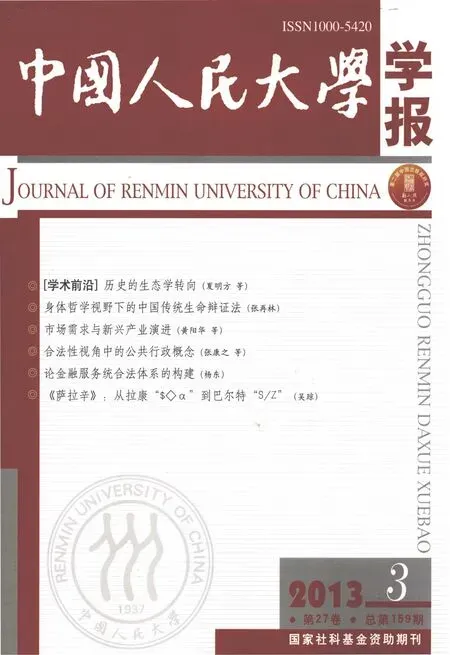合法性视角中的公共行政概念*——20世纪后期公共行政概念建构中
张康之 张乾友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我们思考行政改革的方向和路径时,西方20世纪后期关于公共行政合法性问题的探讨可能会成为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视角。显然,中国的改革开放在30多年的历程中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社会公平的问题已变得越来越突出,各种各样的矛盾迅速积聚,而种种社会问题的存在都会将人们的视线引向政府,进而会对政府及其行政的合法性发出追问。尽管当下中国社会的问题集中表现为政府及其行政的信任危机而不是合法性危机,但是,如果我们不从合法性的视角去看问题的话,信任危机就会日益加重,甚至会有一天演化为一种合法性危机。本文所探讨的虽然是西方 (美国)20世纪60年代之后研究公共行政合法性问题的思想历程,但是,它关于公共行政合法性建构的几种思路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尽管中国的行政改革将走向服务型政府建设这一伟大目标,但是,在此过程中,甚至可以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无法摆脱合法性问题的纠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如果能够在前进的道路上每一步都处理好合法性的问题,也就能够顺利地走向服务型政府。
一、公共行政的合法性问题
“合法性”是现代社会科学语汇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作为一种关于存在之理由的追问,它总是与某种危机的呈现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每当人们想到合法性的概念时,往往是意识到了某种危机状态的来临和呈现。所以,如果在我们社会生活的某个领域中出现了热衷于合法性问题探讨的现象,那就意味着这个领域可能已经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20 世纪后期的公共行政领域便是这样。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人们往往较多地在政治领域中审查合法性,而在政府及其行政的合法性问题上,特别是在相对而言较为狭隘的公共行政领域中,并未对合法性加以严格的追问,人们事实上是默认了政府及其行政的合法性。就公共行政这门学科来看,如果没有对政府及其行政合法性的默认的话,也就根本无法建立起来。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向人们发出了一种信号,似乎合法性的问题被留给了政治学,在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中,则不需要去关注合法性的问题。所以,在早期的公共行政研究中看不到关于合法性问题的探讨。直到20世纪较晚的时期,“新公共行政运动”才把合法性的概念引入公共行政的研究中来。因为,新公共行政运动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对公共行政的存在价值的追问上,它要求公共行政正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并希望从合法性的角度提出增强公共行政的代表性与回应性。然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尽管针对公共行政的各种怀疑情绪开始蔓延,但 “行政国家”的实践仍在不断地扩张其版图,从而压制了对公共行政合法性的追问。到了80年代,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特别是 “政府失灵”这一提法的流行,公共行政陷入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之中。随着危机的出现,合法性的概念也逐渐地被更多的公共行政学者提及,进而,一场关于公共行政合法性的探讨为公共行政的概念注入了新的内涵。
1984年,在 “公共行政理论网络”的非正式出版物 《对话》上,文特里斯 (Curtis Ventriss)指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远不止是理论问题。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公共行政所面对的最为迫切的是合法性问题。”[1]根据葛德塞尔的描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官僚机构成了人们对公共问题不满时随手可及的替罪羔羊,不停地被人们攻击着。包括总统在内设法要进入官僚机构的候选人,在竞选时都声称政府里存在着大量的浪费、欺诈和滥用职权……与此同时,媒体、立法者、社论作者和企业领导们想尽各种办法痛击官僚,蔑视政府雇员的话语铺天盖地地存在于周日的杂志增刊、动画片、报纸、广播节目和其他流行文化的载体中。”[2](P11)此时,“在最好的情况下,公共行政被视为满足公众——通过其民选代表而得到表达的——对于服务的需求的一种必要的恶,在最坏的情况下,则被视为能够有效提供这些服务的一种自私自利的障碍。不同于我们的民选官员以及法院,公共行政官员往往被认为不能合法地在行政过程中施加任何独立的影响。政府观察者都承认或经常接受独立行政行动存在的必要性,甚至认为这种独立行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们却很少在规范基础上去捍卫它或为之辩护”。[3](P2)
事实上,在斯派塞 (Michael W.Spicer)看来,这样的辩护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无论如何努力,公共行政官员都无法获胜。他们处于一场意识形态的枪林弹雨之中,其中,媒体辩论经常类似于一种合法的猎杀,而不是一种开放、文明的观点交流。由于缺乏关于政府角色的共识,官僚机构越来越被视为是某些集团用来谋求利益与特权的工具。许多20世纪80年代的保守主义者往往将公共行政官员视为他们努力增进自由、削减税收和政府规制的一个障碍,并导致了经济的低迷。相反,许多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公共行政维护并强化了既有的社会与经济不平等,并使经济压迫得到了永久化。”[4](P3-4)公共行政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之中。也就是说,20 世纪中期的严重社会分化以及社会不公平问题都被认为是由公共行政的失误引发的,人们把所有社会问题的存在都看做是公共行政合法性危机的证明。
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中,与合法性 (legitimacy)相关的另一个类似的概念是合法律性 (legality)。合法性具有更多的主观性,体现了人们对于合法化对象的一种主观上的认同,或者说,意味着对于某一对象的存在表示了同意或认可。与之相比,合法律性则具有更多的客观性,它反映了对象与法律的客观依据之间的一致性。在某种意义上,合法律性也是一种合法性,但它是一种浅层的合法性,一般说来,满足了形式上的与法律的一致性要求就可以被认定是具有合法性的。而前一种合法性则意味着深层的合法性,虽然必然有着客观基础,却是根源于人们的认识和认同的,并不具有稳定的和明确的判定标准,即使采取定量分析的方式,所呈现出来的也只能是一种含糊的判断。在很多情况下,从定量分析所提供的证明到作出合法性的判断,需要有一个逻辑断裂意义上的飞跃,这种证明可以使人相信,然而,能否真正信服,则取决于人们再一次的理性判断。所以,合法性的问题应当被理解成一个行政哲学问题。在这方面,西方国家20世纪后期的探讨提供了几种具有经典价值的思路。
二、公共行政的宪法合法性
在工业社会的法治条件下,合乎法律是社会治理行为必须满足的基本要求,但是,仅仅合乎法律并不能保证社会治理行为是具有合法性的。因为法律本身可能是与民意或者说主权者的意志相悖的,也同样有一个合法性的问题。一些被认定为 “恶法”的法律本身就不具有合法性,更不用说与这些法律相一致的存在以及行为。因此,合乎法律的社会治理行为也可能是不具有合法性的,在现代语境中,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一种不符合民主之要求的行为。近代以来,民主制度以及文化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同,仅仅合法而与民主制度、民主精神相悖,是不能够被视作具有合法性的。在现代社会中,合法律性的社会治理行为如果是违背民主原则的,就可能得不到民众的主观认同,虽然具备了合法律性的一切特点,也可能是不具有合法性的。反而,合法律性会把人们导向对法律的怀疑,会要求审查法律的合法性。可见,现代社会治理在合法性的问题上反映出了两个层次:第一,浅层次的合法性是指合法律性,即特定的社会治理行为必须合乎法律,要有明确的法律授权。这在理论上可以理解为,法律自身的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或者法律自身的合法性已经经受过审查而得到确认。第二,深层次的合法性是指社会治理行为必须得到民众的认同与同意,必须贯彻主权者的意志。一个健全的社会治理体系应当同时具备这两种合法性,具体来说,既要体现法治,又要贯彻民主的原则。如果一个社会治理体系以及社会治理行为只体现了法治而没有贯彻民主的原则,那么,就必然会出现政治输入不足的问题,就会受到民众的质疑,甚至会被民众所抛弃。反之,如果一个社会治理体系只贯彻了民主的原则却没有体现出法治的特征,其社会治理行为就会失去理性的指引而蜕变成一种激情的 “暴政”。
关于政治部门的合法性问题,现代政治学往往从上述两个层次进行细致的分析,事实上也提出了许多政治合法化的方案,但在公共行政学中,关于合法性的话题则显得相对陌生。这是因为,从进步主义时代开始,公共行政就一直是受效率驱动的,或者说,合理性追求主导了公共行政的研究。同样,在实践中,关于行政行为的评价标准也是基于合理性的要求而制定的,至于合法性问题,则很少有人给予关注。新公共行政运动虽然从回应性的角度提出了公共行政的合法性问题,但在卡特政府的文官制度改革中,新公共行政运动所要求的行政官员对于公民的回应性却被篡改成了行政官员对于政治官员的回应性[5],这既剥夺了行政官员的直接的民主责任,也使回应性以及回应性意义上的合法性变成了加强政治控制与复辟政治分肥的一种说辞。这表明,作为一个非民主机构,公共行政要与作为民主机构的政治部门争夺合法性资源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主动承担民主责任就等于向政治部门夺权,而这又可能威胁到政治部门的合法性,显然是政治部门所不能允许的。另一方面,公共行政又的确陷入了合法性危机,尤其是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之后,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受到了舆论的广泛质疑。对此,公共行政的支持者们必须作出回应。但是,这种回应必须注意的是:既要谋求合法化,又不能与政治部门争夺合法性资源。所以,在20世纪后期,公共行政学者们开始了寻找合法化其他途径的努力。根据罗尔 (John A.Rohr)的看法,这种寻求公共行政合法化的途径应当是诉诸美国独特的 “政体价值”(regime values),也就是要求美国的公共行政体现美国的宪法价值。
罗尔认为: “如果公共行政理论在根本上与构成宪法主要基础的美国思想不一致,那它将很难被有效地整合进美国政治思想的宽广范围之内……如果希望在行政国家合法化的问题上取得进步,我们就应当努力与宪法的浪潮共泳,而不是反对它。主权在民的宪法原则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出发点,它教会我们将公共行政看成宪法本身的工具,而不是根据宪法规定产生的民选官员的工具。这意味着,行政官员变成了依据宪法而与控制公共行政的行为进行持续斗争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无名小卒。”[6](P383)我们知道,美国宪法并没有对公共行政作出规定,甚至没有使用过“公共行政”这一表述,要想在宪法文本中寻找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依据,显然是非常困难的。所以,罗尔强调的并不是宪法的文本,而是宪法所蕴涵的价值以及 “构成宪法主要基础的美国思想”。通过对宪法的这种转换,罗尔相信,可以使宪法成为公共行政的一个合法性依据。同时,我们在罗尔的这段话中还看到,他通过对 “主权在民”这一政治原则的重新解读明确了公共行政与宪法之间的联系,从而否定了行政官员需要通过民选官员的中介来承载宪法价值的观点。这样一来,既为公共行政找到了宪法上的依据,也赋予了行政官员以宪法行动者的角色。也就是说,罗尔为公共行政找到了宪法上的合法性,使公共行政获得了合法律性的特征。进而,考虑到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特殊地位,考虑到美国宪法之于其民主制度的意义,这种合法律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第二层次的合法性。
1984年,罗尔等五位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学者在 《对话》杂志上发表了后来被称为 “黑堡宣言”的著名论文,重申了关于公共行政宪法合法性的主张。在罗尔的分析基础上, “宣言”进一步主张:“如果公共行政接受与坚持其道德权威,并正当地主张行政官员是治理过程中的在宪法上合法的参与者,将有益于对宪法中一个重大缺陷的矫正,即矫正宪法对代表问题的那种令人不满的解决。”[7]这样一来,公共行政的宪法合法性就得到了提升,它不仅具有了宪法上的合法性,而且可以弥补宪法文本的不足。具体来说,在(美国)宪法文本生成的时候,利益集团政治尚未出现,宪法关于代表性的规定没有考虑到利益集团的问题,因而无法解决利益集团政治条件下的代表性不平等的问题。 “考虑到这一宪法缺陷,公共行政作为一种政府制度,拥有一种与一个被终身任命的法官、一个由东南内布拉斯加的少数公民勉强选上的国会新手或一个来自罗德岛的参议员一样正当的主张,可以在社会职能的意义上成为人民的代表。就此而言,公共行政作为一个整体可以与总统——他是由在少于51%的全民选票和29.9%的合格选民即将近19%的人口总数的基础上宣告胜利的选举团体和利益集团的联盟选举出来的——一样代表人民,而不是像政治评论家们那样,仅仅在民选官员身上寻找代表性。”[8]
显然,黑堡宣言汲取了人事行政探讨中的代表性官僚制思想,倡导通过行政职位的开放而帮助那些在政治代表过程中没能得到代表的群体去重新被代表,从而增强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宣言”将它表述为宪法秩序——的代表性与合法性。反过来,既然公共行政起到了增强整个宪法秩序的合法性之效果,那么,公共行政本身的合法性也就不成问题了。人民意志并不仅仅体现于民选官员那里,而是体现在一种可预期的宪法秩序之中,在这种宪法秩序中,各种各样的参与治理过程的合法权利得以实现,基于宪法秩序的条款建立起来的公共行政也就同时拥有了其中的某些权利。因此,公共行政不应在一个拥有主权地位的立法会议或民选官员面前表现出退缩……相反,公共行政的任务是分担对由宪法制定者所制定的、作为人民——其本身就是主权者——意志之表达的宪法秩序的明智而良好的治理”。[9]
黑堡宣言的发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1988年召开的第二次明诺布鲁克会议上,英格拉汉姆与罗森布鲁姆等人就表达了对宪法合法性主张的支持:“美国公共行政能够合法地建筑在其之上的唯一基石就是宪法。公共行政不能仅仅是 ‘一个事务领域’或社会公平的一个独立的促进者,而且应当是合宪的,在行政文化方面也可以是民主的……联邦制度现在已更具有代表性、更分权、更灵活,比过去更注重参与和权利导向。然而,公共服务长久以来的合法性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显然,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一个行政上的 ‘第四部门’只有在被完全融入这个国家的宪政框架之后才不会继续受到质疑。如果公共行政满足于管理或社会公平行动的价值,就无法实现融入宪政框架的目的。”[10]因此,“未来的实质性挑战在于巩固与整合权利、代表、参与和分权,以使公共服务——行政国家的支柱——变成真正合宪的与合法的……第一次明诺布鲁克会议的文本终止于对公务员教育的呼吁。第二次明诺布鲁克会议及其之后的文本也许会好好考虑公共服务的现实,应当更多地考虑其合宪性及其合法性如何能够被传达给公众和民选官员,特别是应当考虑公共行政如何能够被完整地植入政治文化之中”。[11]也就是说,公共行政必须从合宪性的角度重新得到建构,以使权利、代表、参与和分权等宪法价值都能得到体现。在这里,传统公共行政对于管理的强调以及新公共行政运动对社会公平的追求,都在宪法合法性的追求中得到了超越,宪法取代了管理主义而成为公共行政的基本精神。
三、公共行政的民主合法性
向宪法求援,或者说,提出公共行政的宪法合法性问题,可以使行政部门避免直接去与政治部门争夺合法性资源,可以使公共行政的合法化获得一个比较有利的环境。但是,我们也看到,尽管罗尔等人在宪法中所寻找的并不是文本上的依据,而是寻求宪法中所包含的一种价值因素,因而就宪法合法性的思维逻辑来看,依然是属于合法律性意义上的合法性。这也就是我们已经指出的,黑堡宣言在公共行政合法性问题上所追求的境界只是合宪法性,依然属于合法律性的范畴,并不包含与公民互动的内涵,也不意味着公共行政包含着主权者同意的原则。所以,合宪法性并不必然意味着公共行政能够满足公民的公共服务期望,甚至不能真正避免公共行政因官僚主义等问题而变异为公民的对立物。至少,宪法合法性是一种片面的合法性,仅仅拥有这种合法性是无法使公共行政从根本上获得合法化的。因此,寻求宪法合法性的设想一经提出,便受到了诸多批评。
登哈特的批评意见是: “在所有这些论述中所缺失的,无疑是对公民——他们的公共的与私人的价值可能通过政府过程而获得——的忽视。如果公共行政领域存在一种合法性危机的话,那么,这种危机显然不能通过对行政国家宪法基础的一种模棱两可的申述而得到解决。相反,我们必须让公民们相信存在着这样的机制,它既能保证公共机构在政府过程中担负起负责任的角色,又能保证这种角色的履行能够回应更普遍的公共利益。毫无疑问,在像我们这样的复杂社会中,公共官僚机构必然扮演着一种重要的角色。但是,当官僚机构的决策似乎是以一种等级式的而非参与式的方式作出,当官僚机构优先考虑私人(机构)而非公开界定的价值时,这一官僚机构就会持续地经受疑问与质疑。如果我们仅仅遵循黑堡处方,这一点将变成现实。”[12]斯派塞也指出: “合法性不只是合乎法律。无疑,如肯尼思·沃伦 (Kenneth Warren)所说,行政国家是合乎法律的。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联邦法院再未严重质疑过国会向行政机构的各项授权的合法律性。然而,合法性所蕴涵的远不只是遵从法律,它还意味着遵从在一种既定的政治与社会秩序中得到广泛接受的原则、规则与习惯。在这一广泛的意义上,我们是很难断言美国人普遍相信行政国家的合法性的。”[13](P2)根 据 这 一 意 见,即使确认了公共行政的宪法合法性,也不可能真正解决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危机问题。
如前所述,现代社会治理在合法性上包含法治与民主两个层次,在某种意义上,民主是高于法治的,或者说,民主本身是包含着法治的,而不是相反。法治与民主的关系可以这样来认识,如果仅有法治而没有民主 (尽管这在实践中是不可能的)的话,那么法治就是反民主的;如果民主不是建立在法治前提下的话,那么它就不是制度化的民主,也不可能持续存在下去。一般说来,在现代社会,一个特定的社会治理体系只有在同时符合法治与民主两大要求的条件下才能被认为是具有合法性的。就公共行政而言,尽管“民主行政”的提法早在20世纪40年代便已出现,但是,从1978年文官制度改革来看,由于存在着强调行政中的民主会造成与政治部门争夺合法性资源的可能性,并可能遭遇来自政治部门的阻力,因而没有明确的民主行政宣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学者们去为公共行政寻找合法性的时候,选择了法治层面的合法性,即试图确认公共行政的合法律性。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对宪法原则的追溯,代表性、分权以及参与等政体价值,都被视为对公共行政合法性追求进行理论证明时需要援用的基本要素,而落实到实践的层面时,则转化成更多的关注法理支持的方面了。所以,罗尔从宪法价值 (constitutional values)的概念中精心区分出来的政体价值 (regime values,罗尔是在polity的意义上使用regime一词的[14](P3)),虽然这被学者们视为公共行政获得合法性的可行路径,但是,他们又不满足于此,而是要求在民主行政的意义上去追寻公共行政的合法性。
显然,法治与民主所代表的是两种虽然有联系却又有所不同的思路,事实上,在学者们的理论建构中,它们一直是彼此冲突的两条路径。不过,就西方国家的现实政治运行来看,法治与民主又都属于基本的政体价值。这样一来,如果说公共行政的合法性是蕴涵在政体价值之中的话,那么,法治与民主也就都应当成为公共行政合法性的来源。公共行政不仅需要具备宪法合法性,而且也需要具备民主合法性。特别是当学者们认识到作为政体价值的民主高于法治的时候,也就不再满足于合法性问题上的合法律性了。所以,随着政体价值的概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们的接受,黑堡学派关于公共行政合法性的探讨也逐渐突破了罗尔所设定的宪法合法性的界限,走上了追求民主合法性的道路。这可以看做是一场来自于罗尔又超越了罗尔的思想运动,也是黑堡学派所实现的自我超越。
1990年,经过扩充后的黑堡宣言以 《重建公共行政》为名出版。在这本书中,尽管罗尔的观点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随着倡导公民参与的斯蒂福斯 (Camilla Stivers)的加入,转向民主合法性的趋势已经得以展现。1996 年,黑堡学派又推出了他们的第二部集体作品—— 《重建民主公共行政:现代悖论与后现代挑战》,把寻求公共行政合法性的努力真正地转向了对民主的求助,从而使 “民主行政”的概念确立起来。在这本书中,黑堡宣言的两位执笔者瓦姆斯利(Gary L.Wamsley)和沃尔夫 (James F.Wolf)明确宣布他们的观点已经发生改变: “考虑到美国政治制度所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它需要一种不仅可以作为政策的有效执行者而且作为治理过程的合法行动者的公共行政。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但这种合法性最终还是建立在民主性之上。”[15](P21)
瓦姆斯利和沃尔夫的这种观点上的转变,显然对 “宣言”的基本主张再一次提出了挑战。正如邓纳德 (Linda F.Dennard)所说:“事实上,一种公共行政民主身份的发展,多多少少受到了那些支持其合法性的论点的阻碍。宪法合法性可以充分地支持公共行政在政府中的地位,并赋予其权威以效力。但是,如果不承认某种可以制约公共行政官员裁量行为的民主身份,那么,黑堡宣言就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另一种关于政府权力的主张。”[16](P313)因此,仅仅具有宪法合法性是不够的,公共行政还必须获得一种民主身份。 “一种更民主的身份将会让公共行政官员发现,在他们与公民间充满冲突的互动中,所消耗的能量会更少,而产生的知识和力量则会更多。在这一点上,公民与他们的政府是共同进步的,并在承认相互依赖和个体性的基础上创造并再创造着社会……然而,要做到共同进步,则意味着公共行政必须感知到它与公民之间有一种比单纯的政策指令更紧密的联系。”[17](P307-308)也就是说,公共行政需要鼓励公众的参与,并通过公众参与而使行政过程变得更加民主。从理论上看,民主行政其实应当更加提倡一种积极的公民角色,从而改变传统的一切关于消极公民的假定。 “事实上,利益集团政治和内城暴乱的病理现象如果说有什么潜在含义的话,那就是公共行政的现代身份使它寻求改善消极公民的角色的做法反而使消极公民得到了永久化。作为混权系统的产物和疏导者,公共行政必须选择一条道路。它可以选择继续作为权力政治四处受敌的同谋,也可以选择成为民主转型的自觉代理人。”[18](P310)在黑堡学派成熟的主张中,是要求选择后者的,即要求公共行政按照民主的原则重建,让行政人员能够成为公众的代理人。
所以,在 《重建民主公共行政》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新的宣示: “我们的视角需要一种积极的公民,以获得一种对于责任的理解,这种责任既不依赖于等级式的行政管理范式,也不神化行政判断,更不会将责任翻译成 ‘顾客满意’。”[19](P276)也就是说,行政责任在本质上是公共行政对公民的责任,包括培育积极公民的内容,只有培育出了积极公民,公共行政才算承担起了促进民主转型的职责。反过来,如果实现了民主转型,在公民积极参与行政过程的条件下,行政权力又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约束,从而维护宪法中的分权制衡原则。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也能够达成相互促进的效果,公民参与或者说民主合法性可以成为公共行政宪法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支撑因素。在这个意义上,转向民主并不意味着否定黑堡宣言,反而是黑堡学派合法化努力的进步。这就是斯蒂福斯所说的: “重建计划最基本的规范基础在于它忠诚于一种根源于持续合宪性的重建,其中也包括对公共利益的开放性理解,并坚持认为公共利益在本质上是不可定义的,而在特定情况下——在行动可以通过参照它而始终得到合法化的意义上——又是可以达成的。黑堡宣言的批评者们有理由担忧行政权力太容易将他们自己的利益合理化为 ‘公共利益’。然而,只有通过与公民的对话,行政官员才能建构起一种 ‘代理人视角’ (agency perspective),从这一视角出发,才能获得对公共利益的正确理解,因为积极公民可以使行政免于将官僚政治等同于政治。正是在与积极公民的关系中,公共行政才合法地获得了政治含义:不是通过几乎从不可能达成的共识,或通过寻求更接近于友谊而非公民角色的亲密关系,而是通过对进行中的具有公共精神的对话的维护,使行政官员和其他公民共同 ‘创造一个世界’,即使这种对话是以最激烈的形式出现的,仍然是获得公共行政合法性的唯一手段。”[20](P273-274)由此可见,黑堡学派为公共行政寻求合法性的努力走过了一个从宪法转向民主的历程,相应地,公共行政也从合乎宪法的行动转变成促进民主参与和公共对话的实践过程。
四、公共行政的专业主义合法性及其他
黑堡学派的最大贡献就是使合法性的概念在公共行政领域被广泛接受,而且也逐渐使之成为人们观察和思考公共行政问题的一个独特视角。随着合法性概念被引入公共行政之中,学者们逐渐突破了政治学关于合法性的传统二分法 (即合法性与合法律性),开始对合法性的概念作出更加宽泛的理解。一个积极的结果是:由于合法性概念外延的扩展,使学者们可以对公共行政的合法化问题提出更多的意见和建议。
1988年,在一本深受黑堡宣言影响的著作中,斯蒂弗 (James A.Stever)表达了这样的意见,由于受到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美国社会中存在着一种对公共行政普遍怀疑的情绪,而且,当这种怀疑以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治理方案出现的时候,也没有带来什么积极的结果。斯蒂弗认为:“只要公众对为了公共利益而行动的公共行政的前景仍然持怀疑态度,就肯定会助长私人控制的行政组织将人力、资源和技术越来越用于私人而非公共目的。谁都无法想象,私人控制的强大的行政技术还能够继续服务于公共或集体性的目的多久。维持对公共行政的美国式怀疑的传统,阻碍了朝向一种真正的公共行政的进程。在此,一种 ‘真正的公共行政’ (truly public administration)被定义为一种将不断增长的行政权力用于促进广泛的公共利益而不是法律目的的公共行政。”[21](P6)因此,要使真正的公共行政得以生成,首先就需要对公共行政进行合法化,特别是需要为其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斯蒂弗认为,长期以来,在公共行政的合法化问题上,学者们主要采取了三种途径: “1.通过立法进行监督,以确保公共行政的行动符合民选官员的意志;2.促进对公共行政官员专业技能的尊重;3.发展允许公众中的适当部分 (个体的或集体的)参与行政决策的程序。”[22](P13)具体说来,第一种途径是:“民选官员对公共行政官员的监督是保证行政行为与政策合法的一种方式。这一合法化策略的直接依据是:民选官员因为他们是选举产生的事实而具有合法性,因此,只有在受到了这些民选官员的严格控制的情况下,公共行政官员与机构才能得到合法化。”[23](P13)第二种途径是: “那些主张通过诉诸公共导向的公共行政专业主义合法化的人则倾向于强调以下的术语和观念:权威、领导、判断以及行政裁量。这一主张认为,由于(1)长期的教育、 (2)服务的传统、 (3)获取信息的途径以及 (4)接近其他专家的途径,往往假定公共行政官员在其选定领域中拥有卓越的专业技能。这一合法化策略将服务于普通公众的文官与在利润动机下服务于特定客户的其他专业人员区别开来。”[24](P14)第三种途径是: “关于合法性的程序途径聚焦于程序本身的性质。 ‘程序主义者’认为,当它们不遵从适当的法律/宪法原则时,行政程序本身就是不合法的。因此,公共行政合法化的方式就是检查与发展合法的程序。这一观点强调,公共行政官员在形成与执行公共政策时应当遵循 ‘正当程序’。”[25](P15)
在某种意义上,斯蒂弗所归纳的公共行政合法化的三种途径与罗森布鲁姆所归纳的公共行政的三种研究途径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也就是说,如果使用罗森布鲁姆的表述,那么,斯蒂弗所说的三种合法化途径就变成了政治途径、管理途径与法律途径。[26]其中,政治途径与法律途径都是通过控制——不同之处在于是政治控制还是法律控制——来保证公共行政的合法性,管理途径则是通过专业化的服务供给来获取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斯蒂弗将政治途径和法律途径称作消极的合法化途径,而管理途径则被认为是积极的合法化途径。他说: “监督和程序主义者的策略在性质上是消极的。这即是说,这些策略关注的是限制与控制公共行政,以使其得到合法化……相反,选择公共导向的专业主义就是选择一种积极的合法化策略。这一策略选择所强调的是公共行政内在的积极品质。它寻求发展一种与美国基本的价值和需要相一致的专业主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对消极的合法化控制与策略的需要是极少的。与那些把公共行政视为对美国式自由民主的一种威胁的新韦伯主义怀疑者不同,那些诉诸积极的公共专业主义的人则相信,在一个自由民主制度中,公共行政官员因其技能和承诺而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27](P17)
显然,从 “消极的”与 “积极的”措辞中,斯蒂弗已经表达出了他对公共行政专业主义的偏好。在他看来,公共行政的专业主义是进步主义时代留给公共行政的遗产,正是这一遗产奠定了公共行政在20世纪前期的繁荣。随着进步主义时代的终结,学者们在公共行政的合法性问题上失去共识,从而导致了一种 “默认的多元主义”——意指没有更好选择,因而只能默认其存在的多元主义——状况的出现,从而使公共行政进入一个漫长的后进步主义时代,陷入一场持久的合法性危机之中,甚至面临着走向终结的危险。因此,要实现公共行政的合法化,就必须重新求助于专业主义的合法性力量。不过,事实也许并非如此,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公共行政从进步主义时代走向合法性危机的路程,将会发现,仅仅诉诸专业主义也是不够的。因为,公共行政的合法性还根源于时代的要求,也就是说,还需要在专业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一种能够适应自由社会之需要的公共文化,才能使公共行政获得一种较为稳定的合法性。 “鉴于后进步主义时代的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都承认文官在促进公共文化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从而可以使公共行政成为一项公共导向的专业。文官体系的合法性取决于这一专业是否促进了公共文化。一个合法的、公共导向的专业应当是有自信心的,应当相信它所提供的服务与产品能够对公共文化产生积极的影响。回避公共文化的问题就等于是将文官贬低为执行他人意志的技术走狗。通过应对这些棘手的问题,公共行政可以无愧于进步主义遗产而成为一种充分发展的政体专业,并对自由社会中的公共文化有着合法而卓著的贡献。”[28](P178)
黑堡学派在公共行政合法性的问题上存在着宪法合法性与民主合法性两种意见,而且在争论中实现了对这两种意见的综合。与黑堡学派关于公共行政合法性的论述相比,斯蒂弗关于公共行政专业主义的论述虽然也植根于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传统,却显得有些晦涩,因而,这一关于公共行政合法性的建构路径并没有在学术界产生广泛的影响,或者说远逊于黑堡学派关于公共行政合法性问题论述的影响。但是,从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史来看,斯蒂弗是应当被提及的,因为他为我们理解公共行政的概念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除了斯蒂弗,在公共行政合法性问题的探讨中,还有几位学者也是应当给予关注的,其中,斯蒂福斯和西蒙在公共行政合法性问题上的意见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斯蒂福斯是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获得的博士学位,显然与黑堡学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她在公共行政合法性问题上的观点可以说实现了对黑堡学派的超越。在 《公共行政的性别角色》等作品中,斯蒂福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阐述了一种关于公共行政合法性的不同见解。她认为,公共行政历史上最重要的二分并不是政治与行政的二分,而是 “机关男人”与 “社区女人”的二分。根据这种二分,女性作为一种 “社区”动物而被排除在了 “机关”这一男人的世界之外,结果, “公共行政像其他公共部门的活动一样,在结构上是男性的,尽管它表面上是中性的……因此,为公共行政的合法性辩护可从以下两点着手:(1)对女性一系列义务的分配,不管多么必要,通常都被认为是没有价值或不重要的,这与对女性的这种次要位置的看法是一致的;(2)限制女性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或者她们必须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状况”。[29](P5)根 据 斯 蒂福斯的看法,在公共行政的传统中,男性化往往被视为公共行政合法性的基本标志,而一旦公共行政表现出了女性化的特征,就会被人们认为出现了不合法的状况。所以,传统公共行政所推崇的都是具有男性特质的价值——如专业知识、领导与美德,而其他更具女性化特征的价值——比如服务——则一直不受重视。“我们看到历史上公共行政中价值观 (善意、民主、公众)和技巧 (效率、管理)之间的核心冲突到处都有性别的影响,正如在改革中女性牺牲了她们从事慈善工作时独特的女性方法,以便达到公事化实践的标准,因此,公共行政为了效率至上也牺牲了民主。”[30](P148)
在斯蒂福斯看来,这种男性至上的合法化策略有着内在的矛盾,因为, “公共行政的政治角色的其他方面是类似于女性特质的,例如服务的规范。在文化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是女性服务他人,而男性是被服务的对象;女性无私地奉献以帮助不幸的人,而男性追求自我利益,尽管有时候也有很多变数。如果说公共行政人员不同于其他专家的是他们的服务责任和回应性,那么,他们作为一个团体也像女性一样,并不很符合职业的角色:职业主义对公共行政的女性化方面而言,太男性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宣称公共行政的价值在于职业性的、舵手、代理人、客观的科学家和匿名的专家这些术语,其本身就是获得男性化、压抑女性特质或将之排除在外的一种努力。在这种意义上,公共行政不只是男性化和家长化的,它从根本上否认了自己的本质,结果从概念和实践上使自身枯竭 了”。[31](P59)也就是说,在性别形象上,公共行政不同于其他实践领域的根本特征恰恰在于那些被视为女性特征的价值,因而,当它出于合法化/男性化的需要而排除了这些价值时,反而造成了自身的合法性危机。所以,要重塑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就要从根本上摒弃 “机关男人”与 “社区女人”的二分,使公共行政能够同时包容男性与女性的不同文化特质。虽然作为女性的斯蒂福斯是以公共行政研究中的女性主义形象出现的,但是,她关于行政文化的上述分类却是引人深思的。在我国当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中,显然包含着新的文化建构,当我们思考服务型政府的文化形式时,把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相结合的主张也应当成为一种可以参照的意见。
需要指出的是,前面这些合法化的方案都是从规范的角度进行论证的,所表明的都是让公共行政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中获得一种规范意义上的合法性。实际上,在关于公共行政合法性问题的探讨中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在试图寻求公共行政合法性建构的学者那里,都试图从规范的角度提出合法化的方案,而在那些分析公共行政合法性危机的学者那里,基本上都从技术的角度看问题,认为公共行政由于不像市场那样拥有效率而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如此一来,在关于公共行政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中,理论对话其实并不是在同一个平台上展开的,甚至在公共行政合法性问题的探讨中就根本没有形成真正的对话。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公共行政的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也都是处于一种各说各话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公共行政合法化的所有规范性努力都无法解决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危机,因为它们并没有正面回答关于公共行政陷入危机的质疑与批评。要真正解决公共行政的合法性问题,学者们还必须证明公共行政是有效率的,而作出这种论证的人,正是早年因为倡导公共行政的效率取向而备受批评的西蒙。
1997年,淡出公共行政研究多年的西蒙在ASPA 年会上发表了题为 《为什么需要公共行政?》的演说,对20世纪80 年代以来私有化的支持者们一直鼓噪的批评性意见作了有力的反击。次年, 《公共行政评论》与 《公共行政研究与理论学报》分别在当年的第一期杂志上摘登和全文刊登了这篇演说,为关于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争论提供了一种新意见。西蒙指出:“近年来,我们的社会与其他某些西方社会已经被一种通过完全依赖于市场和私人企业来提高生产率的前景晃花了眼。它的口号是 ‘私有化!’组织,而对政府组织在一个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却根本不去作出充分的理解,特别是没有认识到组织忠诚和组织认同的过程在塑造人所应扮演的组织角色时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经济自利是一个社会运行中唯一重要的人类动力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组织中,组织认同需要得到至少与自利同等的关注,这是一个可以简单观察到的事实。”[32]也就是说,如果说个人的自利本性在市场中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生产力的话,那么,组织成员对于组织的忠诚与认同也同样是一种生产力,甚至可能是一种更高的生产力。因而,市场并不必然比组织更有效。在这里,西蒙通过重申自己早年在组织认同研究中的发现而反驳了私有化的支持者所作出的政府必然低效的论断。其实,在 《企业的性质》中,通过对交易成本与行政成本的比较,科斯早已得出过与西蒙相同的结论。但是,科斯关于交易成本与行政成本的比较研究还不足以说明公共行政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即使政府是有效的,市场也可以通过竞争而对它进行局部或者大部分的替代。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政府及其行政是必要的呢?在回答这一问题时,西蒙这位沃尔多的论敌 (也是 “沃尔多奖”的获得者)给出了一个沃尔多式的答案: “一个社会仅仅卓有成效地运行当然是不够的。我们同样期望一个社会公平地分配物品与服务,无论我们关于公平的标准引发了多么激烈的争论。除非这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在分配过程中得到了代表,否则我们将无法期望分配的公平——无论以何种标准进行衡量。”[33]这显然是市场无法做到的,市场绝不可能使一个社会公平地分配物品与服务,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唯有公共行政。所以,西蒙也学着黑堡学者的样子,大声呼吁: “是时候停止对公共服务的诽谤了。”[34]
我们发现,与关注公共行政合法性的其他学者相比,西蒙在这篇演说中所作出的也许算不上是一种论证,而更多地像是一种表态。但是,西蒙却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市场的效率并不是公平地分配物品与服务的效率,公共行政应当拥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效率观,而这种效率观恰恰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等所不理解的。所以,从市场效率的角度对公共行政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是没有根据的。的确,从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的角度看,不可能找到比公共行政更有效率的方式。考虑到这一点,西蒙对 “我们为什么需要公共行政”的回答,无疑是一种对公共行政合法性的辩护。值得注意的是,西蒙在认识公共行政的合法性的问题时,既不是从是否合乎法律的角度,也不是从是否反映了民主价值的角度,更不是从是否拥有女性的服务特质的角度,而是从效率的角度。这样一来,虽然西蒙没有对自己的意见作出充分的论证,却代表了一种在公共行政合法性建构问题上启发人们思考的新思路。从西蒙的意见出发,也许可以把公共行政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导向规范与技术相统一的方向上去。回观中国的现实,近些年来,也许我们产生了某种对市场经济的迷信,特别是把一些市场无法调节的项目交给了市场,因而出现了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在下一步的改革过程中,如果我们注意到了西蒙的这些意见,也许会对行动方案作出慎重的选择。
[1]Curtis Ventriss.“The Current Dilemma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A Commentary”.Dialogue,1984,6 (4).
[2] 查尔斯·T·葛德塞尔:《为官僚制正名——一场公共行政的辩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3] [4] [13] Michael W.Spicer.TheFounders,theConstitution,andPublicAdministration:AConflictin WorldViews.Washington D.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1995.
[5][10][11] Patricia Wallace Ingraham,David H.Rosenbloom,Carol Edlund.“The New Public Personnel and the New Public Service”.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1989,49 (2).
[6] John A.Rohr.“Professionalism,Legitimacy,and the Constitution”.In Willa Bruce(ed.).ClassicsofAdministrativeEthics.Boulder:Westview Press,2001.
[7][8][9] Gary L.Wamsley,Charles T.Goodsell,John A.Rohr,Orion F.White,Jim F.Wolf.“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Governance Process:Refocusing the American Dialogue”.Dialogue,1984,6 (2).
[12] Robert B.Denhardt and Edward T.Jennings,Jr..“The Futur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Dialogue,1984,6 (3).
[14] John A.Rohr.EthicsforBureaucrats:AnEssayonLawandValues.Second Edition.New York:Marcel Dekker,Inc.,1989.
[15] Gary L.Wamsley,James F.Wolf.“Can a High-Modern Project Find Happiness in a Postmodern Era?”.In Gary L.Wamsley,James F.Wolf(eds.).RefoundingDemocraticPublicAdministration:ModernParadoxes,PostmodernChallenges.Thousand Oaks:Sage Publications,1996.
[16][17][18] Linda F.Dennard.“The Matur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The Search for a Democratic Identity”.In Gary L.Wamsley,James F.Wolf(eds.).RefoundingDemocraticPublicAdministration:ModernParadoxes,PostmodernChallenges.Thousand Oaks:Sage Publications,1996.
[19][20] Camilla Stivers.“Refusing to Get It Right:Citizenship,Difference,and the Refounding Project”.In Gary L.Wamsley,James F.Wolf(eds.).RefoundingDemocraticPublicAdministration:ModernParadoxes,PostmodernChallenges.Thousand Oaks:Sage Publications,1996.
[21][22][23][24][25][27][28] James A.Stever.TheEndofPublicAdministration:Problemsofthe ProfessioninthePost-ProgressiveEra.New York: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Inc.,1988.
[26] 罗森布鲁姆、克拉夫丘特:《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 (第五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9][30][31] 斯蒂福斯:《公共行政中的性别形象:合法性与行政国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32] Herbert A.Simon.“Why Public Administration?”.JournalofPublicAdministrationResearchandTheory:J-PART,1998,8 (1).
[33][34] Herbert A.Simon.“Guest Editorial:Why Public Administration?”.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1998,58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