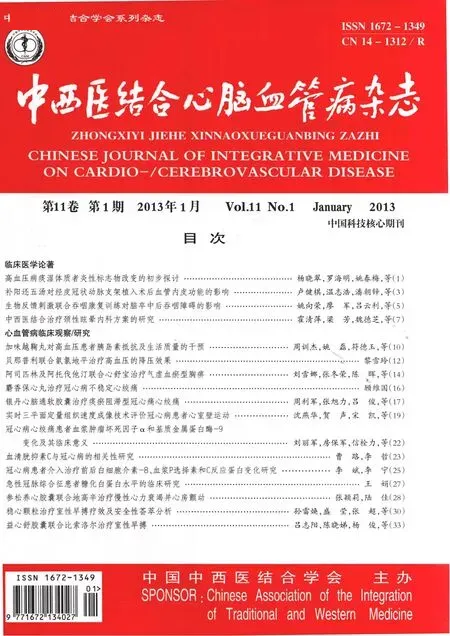出血性中风病因病机新认识1)
张根明,周 莉,崔方圆,陈 颖,陈 红,岑 锴,孙纪伟
出血性中风好发于中老年人,其病因病机有别于缺血性中风,根据中风病定义[1]“血溢脑脉之外”者为出血性中风,其发病前阶段、急性期、恢复期和后遗症期的病机均呈现自身特有的演化规律,重新认识出血性中风病因病机及其不同发病阶段的病机特点,有利于澄清模糊认识并为出血性中风不同阶段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1 发病前阶段
发病前阶段即“血溢脑脉之外”前的病理阶段,此阶段发生的一系列病理变化构成了出血性中风的发病基础。概言之,由于禀赋薄弱或多种致病因素的长期作用,导致人体正气内虚、内生之邪形成,当正虚邪实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在诱因作用下就会发生络破脉损、血溢脑脉之外的出血性中风。
1.1 内伤积损 出血性中风发病前有一个正虚、邪实日渐积累的过程即张景岳所谓“内伤积损”,系先、后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禀赋薄弱和人体自然衰老均属先天不可控因素,是正气虚损和伏火、暗风等邪气产生的内在条件;饮食偏嗜、情志失调、劳逸不节等均为调摄不当而属后天因素,它加速了疾病发展进程,成为“内伤积损”的外部成因[1]。而后者作为直接影响出血性中风发病与否的可控因素理应得到充分重视。嗜咸则伤肾伤血,伤肾则肝阳不敛而内风暗煽,伤血则“脉凝泣”使脉道失于柔润而菲薄易损;情志内伤,疏泄失职,伏火渐生,久则损及血脉;过逸形盛,必致气衰,并发气滞,气衰气滞,津血不行,久亦伤及血脉。在先后天因素共同作用下,正气渐亏、内邪渐生、终致脑之络脉菲薄、易于破损,从而形成了出血性中风的发病基础。
1.2 诱发因素 凡能扰动气机使气机逆乱上行者均可构成出血性中风的促发因素,常见有气候骤变、情志相激、烦劳过度及用力不当[2]。天气寒冷或气候骤变是重要诱发因素之一[3],春秋和冬季发病率远高于夏季,春秋寒热交替而身之阳气亦随之动越,冬季寒冷收敛使血脉收缩而阳气上逆,均可致脑脉挛急而使细小脑脉薄弱之处“络破血溢”;情志过极也是诱发出血性中风发病的主要因素,肝主疏泄并调畅情志,肝在志为怒,大怒最易气机逆乱、迫血上冲而使络破血溢,所谓“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烦劳过度是出血性中风发病的又一促发因素,“阳气者,烦劳则张”即指过于劳顿易使阴血耗伤而阳气鸱张,阳化风动上冲脑脉则致络破脉损、血溢脉外;用力不当作为诱因,多见于临厕努挣或突然用力使气机逆乱,气血上冲脑脉菲薄之处而致血液溢出脑脉。
在先、后天诸因素共同作用下,正虚与邪实日渐累积为祸,脑之络脉失去柔和通达之性,部分细小脑络变得脆硬而菲薄易损,出血性中风的发病基础就此形成,一旦遇有气候、情志、烦劳或用力等诱因鼓动阳气,气血逆乱,上冲脑脉会发生“血溢脑脉之外”的中风。
2 中风急性期阶段
“血溢脑脉之外”标志着出血性中风急性期的开始,此阶段发生的一系列病理变化使得中风症状迅速出现并达到高峰。这些病理变化包括:①瘀停脉外、脑髓受压,②津行不畅、痰水形成,③诸邪胶结、化毒伤脑。这三个病理过程共同构成了出血性中风急性期脑髓损伤的病理基础。
2.1 瘀停脉外、脑髓受压 “血溢脑脉之外”最先出现的症状系由瘀血所致。离经之血不能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因此虽然清鲜亦称为瘀血,瘀血停于脑脉之外成为压迫脑髓的有形之邪。脑为髓海而位居天位,是至高至贵的清灵之脏,喜静恶扰而不能容邪,邪犯则病。离经之血停于局部脑髓,一方面压迫脑髓使其不能发挥司运动、统感官,主明辨等作用,出现半身不遂、偏身麻木、口舌歪斜、舌强言蹇或不语等症,严重时甚至会出现窍闭神匿的危候;另一方面瘀血内停还可压迫其周边脑络,阻碍其气血运行使得周边脑髓得不到气血的渗灌滋养,亦不利于其发挥应有功能。一则受到离经之血的压迫、戕害,二则不能得到气血津液的濡润充养,瘀血周边脑髓甚至全脑功能都会迅即发生紊乱,瘀血较少者病情尚轻浅而可见在络在经之症,离经之血重者则直中脏腑而呈神昏窍闭之证。
2.2 津行不畅、痰水形成 血与津均为液态且都源自水谷精气,二者关系极为密切,从不同角度发挥滋润和濡养作用,素有“津血同源”之说,津液渗注脉中即成为血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津液和调,变化而赤为血”。在病理情况下,津血之间亦互有影响,对出血性中风而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瘀血停于脑脉之外致脉道不利,脉内之津液渗出于脉外,在局部形成异常水液,轻者化生痰浊、重者尚可化水为肿,阻碍气血津液对脑髓的渗灌滋养;二是离经之血停于脑窍之内,久而不去则亦可转化为痰水,正如唐容川所说:“血积日久,亦能化为痰水”。如此,瘀血不能速祛而痰水又不断产生,痰水生成后反过来又进一步妨碍血行,使得病程进展,中经络轻证甚或转为中脏腑。
2.3 诸邪胶结、化毒伤脑 诸邪胶结、化毒伤脑是上述两个病理过程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脑髓损伤不易修复的重要原因。由于瘀血、痰浊、水肿相继形成,诸邪聚于脑脉之外阻遏气机,气行不畅则郁而化火,瘀、痰、火热诸邪胶结于局部脑髓,迅速发生转化而生成一种致病力很强的邪气即内生毒邪[4],它秉承火热之性,兼寓痰瘀之形,胶固难除,势盛难安,最易败坏形体、攻伐脏腑、扰神闭窍,所以其一旦生成,即成为损伤脑髓的剧烈致病因素。此毒有别于机体其他部位产生的疮毒、疖毒等内生毒邪,它居于天位,在元神之都,具有喜善变、状多端、攻脏腑、扰神明的特点,而临床则呈现出“内风”旋动之征。毒邪形成之后迅速对脑髓构成损伤,重则发为中腑、中藏之危候,而毒邪下攻脏腑又可致变证丛生,临床可见五脏受损的症状如肺热、心悸、便秘、遗溺、呕血、淋证等。
上述三个病理过程是在“血溢脑脉之外”后相继发生的,先是瘀血内停,继则痰水形成,终而化毒伤脑,每个环节均可造成脑髓损伤,而以瘀血为急性期病机之本、痰水为加重因素、毒邪为损伤难复之因,三者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脑髓损伤的病理机制。
3 恢复期和后遗症阶段
病情趋于平稳后即进入出血性中风的恢复期,偏瘫、麻木、言蹇等症不再进一步加重,轻症患者肢体功能可有部分甚至完全恢复,重症患者往往会留有各种功能障碍的后遗症,本阶段病机主要涉及脑髓空虚和内邪伏藏两个方面。
3.1 脑髓空虚 在急性期脑髓为瘀血、痰浊、火热及毒邪所伤,其后诸邪虽渐渐消退,脑髓及全身正气亦有所恢复,但局部受伤之脑髓却因得不到完全复原而呈现脑髓空虚状态,轻者可暂无症状,重者不能发挥“主任物、司明辨”功能。脑髓为奇恒之腑,其生成有赖于先天之精所化、后天肾精和水谷精气所充、脑脉传输之气血津液所养,进入恢复期和后遗症期,受损脑髓局部瘀化痰消,重者可留下空洞,轻者通过周边脑络渗灌作用使肾精、气血达到脑髓受损之处,聚而成形使脑髓空疏之处得以填补。由于脑髓神机禀自先天之精,先天之精受损不复则神机亦不得施,故脑髓空虚虽有后天肾精和精微物质的补充,肢废、言蹇、口喎等亦能得到部分改善,但因其无先天之精而有别于脑髓,是不能发挥神明机巧之用的。
3.2 诸邪伏藏 导致中风发病的致病因素在恢复期及后遗症期依然存在,禀赋和老龄作为固有病因将伴随终生,后天因素虽可通过调摄而减少其对人体的侵害,但业已脆弱菲薄之脑络在短时间内难以修复,而暗风、伏火等邪气亦无法完全消除,当再遇气候骤变、大怒劳烦、用力不当等诱因时则可导致又一次出血性中风的发生。另外,中风后新的致病因素不断产生使得“积损正衰”进一步加重,一则脑髓受损、五脏失调、肢体痿废,气血周流不畅,易致内生邪气包括痰、瘀等邪的生成和积蓄,二则肾精、气血聚而成形,虽可填补脑髓空疏之处,但亦有部分与局部痰瘀相结、形成伏痰死血为祸,在肝风引动之下可发为痫证[5],原有诸邪与新生致病因素共同为患,久之既可损伤脑络而致出血性中风复发,亦可闭阻脑脉发为缺血性中风或呆傻之证。
恢复期阶段病情日趋平稳,肢体功能或可部分恢复,但受损脑髓则不能再生,多数患者会留有偏瘫、言蹇等后遗症,同时由于原有致病因素和新生致病因素的共同作用,也为再次中风和中风痴呆的发生埋下隐患。
4 结 语
出血性中风发病机制复杂,其发病前、急性期、恢复期及后遗症期的病机存在差异,有必要详加辨析。发病前积损正衰为其本,气机逆乱为诱因,脑脉破损为其果;急性期离经之血为脑髓损伤之主因,痰浊水肿则为加重因素,而内生毒邪则阻碍病情向愈;恢复期和后遗症期,脑髓空虚和诸邪伏藏则增大了中风病再发和呆傻之症形成的风险。
[1] 王永炎,张天,李迪臣,等.临床中医内科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585-589.
[2] 王永炎,严世芸.实用中医内科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432.
[3] 张根明.关于换季输液预防脑梗死的思考[J].中国临床医生,2010,38(5):60-62;
[4] 张根明.对缺血性中风急性期病机的再认识[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中医临床版),2010,17(3):37-39.
[5] 胡文立,刘艳伟,焦俊杰,等.中风后痫性发作及癫痫的再发因素[J].现代诊断与治疗,2001,12(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