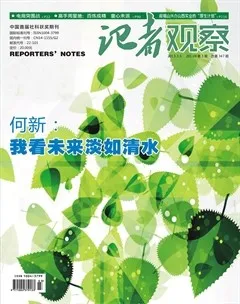一餐一世界
民以食为天。
我们每个人,各自头顶着一片天。有的艳阳高照,有的乌云密布,有的风清月白,有的灰霾浓重。饭碗如苍穹,苍穹如饭碗,倒扣上空,走哪跟哪。虎不辞山,人不辞碗。
在这个时代,绝大部分人,不是缺少食物,而是缺少食欲。
吃好喝好,是最实在的祝词。吃什么喝什么,却一直是困扰我们的难题。怎么吃怎么喝,则更是上升为一个映照三观的态度问题。
饥肠辘辘让人愤世嫉俗,酒足饭饱让人厌世消沉。太饿或太饱,都让人充满了负能量。
全世界70亿人,一天吃掉的食物达1400万吨。仅仅按照重量匡算,全世界人的嘴巴拼成一个超级大嘴来吃汽车,一顿饭就吃掉北京天津的所有汽车,因汽车尾气排硫量超标而导致的灰霾天,就会烟消云散,重新迎来蓝天白云。
美国著名摄影师彼得·门泽尔和费丝·德鲁休夫妇,是摄影界了不起的实验者。他们耗资100万美元,用3年时间访问了30多个国家的100人,记录他们每天所吃的食物。并统计这些食物所含的热量,在当地的价钱。
无论是清汤寡水,还是高热量的垃圾食品,摄影师都仅仅是静态地展示,并没有多说一句话。
然而。通过各地人们的食物大博览,读者却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经济、文化和民俗的巨大差异,更直接揭示了贫富之间的财富鸿沟。
《我的食物》是继轰动一时的《饥饿星球》之后,这对摄影师夫妇的又一部震撼人心的新作。
在摄影师的镜头下,乍得布里德金难民营的一家人,一个星期的伙食费只有1.23美元。他们全家人的梦想,就是饱饱地喝一锅鲜羊肉汤。而意大利西西里的一家子,一周的伙食费高达260.11美元,他们喜欢吃热狗和冻鱼。
211倍的贫富差距,让我们更加明白:不同的家庭,不同的食物,不同的世界。所谓食糜与吃菜的悬殊,是无法弥平的鸿沟。人世间的多元化,不仅仅是你在河东他在河西,而且还包括他在天上你在地下。
饿死人的施政,就是暴政。饿殍遍野,易子而食的惨象,则更是无道至极。好在,那些苦难深重的人间惨剧已成历史,做梦都在吃东西的饥馑年代也随风远去。
全世界的博爱者、慈善者,都在为局部地区的难民饥民走向温饱而努力。比如摄影师门泽尔夫妇,他们的这些图片,展示世界各地人的食物,同时也默示他们之间的差距。让温饱成为基础,让健康得到保障,在很多地方,依然任重而道远。
以中国为例,尽管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财政收入突破11万亿元,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依旧在世界百名左右。中国还有1亿多贫困人口,还有几千万城市低保人口以及为数众多的其他困难群众。
有的人,一顿饭耗资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有的人,一日两餐,豉油捞饭已属奢侈。在追求安全营养的健康食品之路上,我们看到的是,one dream,twoworld——同一个梦想,不同的世界。让饥馑者得到温饱,让罹病者重获健康,在饭碗里找回生命的尊严,在餐桌上体现活着的意义。
数月以来,一阵倡导节俭抵制浪费的新风气,正在席卷中国的各大酒店、各家高端会所,节俭光荣、浪费可耻的美德重回正道。
“人人有资格享有吃饱吃好的权利,不分种族、肤色、性别、国籍或出身,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这正是摄影师门泽尔夫妇最想表达的。
民以食为天——除此之外,几乎没有独立存在的真理了。
一餐一世界,一汤一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