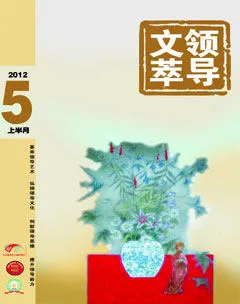官员和人民都自私 谁主导改革谁获利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不仅经济迅速增长,立法体系也初步形成,法治理念深入人心。然而,近年来,改革也出现了不少问题,甚至某些成就本身就是产生问题的原因。
未来改革之路怎么走、如何保证改革越改越好而非越改越糟,是整个中国社会面临的根本问题。
一项改革的“好”就在于其促进人民的利益,所谓的“糟”即意味着损害人民的利益。问题在于,什么决定了改革的“好”或“糟”?绝大多数人都是“理性自私”的,官员有官员的理性,百姓有百姓的理性,任何理性人都首先会做对自己有利的事,因而谁是改革的主导者,改革就对谁有利。因此,要让改革对人民有利,人民必须成为改革的主导者,至少是参与者。只有在人民的主导和参与下,改革才能越改越好;反之,如果官员主导了改革,人民不能通过宪政制度有效防止官员滥用公权和贪污腐败,那么官员就难免利用改革为自己谋利,而这样的改革只能越改越糟。
政府主导改革的危患
然而,近20年的改革恰恰是由政府主导的。1993年起实行的干部考核体制将官员命运和改革力度巧妙结合起来,GDP成了评价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作为客观经济数据,GDP确实和地区经济发达程度及人民生活水平相关,但是一旦成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GDP增长不仅未必等同于社会财富增长,而且可能成为社会畸形发展的代名词,进而蜕变成各级官员为自己谋利的工具。
GDP思维表面上看是重视社会发展,实际上由此带来的盲目“发展”和公权滥用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在经济发展成为“硬道理”的前提下,各级干部想方设法、不择手段提升本地GDP数字,其诀窍除了招商引资,就是城市改造和农村城市化。各地政府大肆征地拆迁,美其名曰“发展”,实质则常常是扰乱社会正常生活秩序和经济自由发展规律,结果不仅造成环境恶化、资源浪费,而且因为滥征乱拆、克扣补偿而产生大批失地农民、城市“钉子户”和未安置移民,由此引发大量“上访”和群体性冲突。
从这个角度看,2001年施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就是一次缺乏人民参与下发生的制度倒退;它在没有广泛征求民意的情况下,将原先的实物补偿改为货币补偿,取消了先安置、后拆迁的原则,并授予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不受控制的征地拆迁权力,形成了根深蒂固、难以撼动的地方既得利益堡垒,同时造成全国成千上万唐福珍式的个人悲剧和群体冲突。这些冲突和悲剧充分验证了一条简单道理:一旦人民缺位,那么改革必然停滞甚至发生倒退。在没有人民参与的政府主导下,即便良好的制度改革也会变形。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被普遍认为是对中国税制的重要完善,有人甚至将其誉为中国的“财政联邦主义”。但是,分税制不仅没有像通常的财政联邦主义那样强化地方自治,反而一举扭转了国家财政总收入占GDP比例以及中央财政占总财政比例逐年下降的双重趋势,开启了这两个比例逐年上升的“国进民退”时代,成为强化中央财政和国家作用的制度基础,为“土地财政”埋下了祸根。这次良性的税制改革造成了不少地方入不敷出的分配后果,促使地方政府以“发展”的名义通过征地拆迁、压低补偿等途径再次向人民伸手。
事实上,如果没有人民参与,整个公共财政必然沦为政府官员的私人“小金库”。
我们看到,政府该投入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生产安全、环境保护、食品卫生等民生亟需的诸多领域远没有达到适当投入,大量资金却流向了“维稳”、“三公”消费、豪华办公楼乃至官员个人灰色收入等制度缺陷本身造成的问题“黑洞”。即便对于公开的财政预算和开支,也很难弄清那些粗线条的数字究竟意味着什么——医疗开支是用在了缓解看不起病的农民们的疾苦,还是用在了离休干部疗养上面?政府财政支持的经济适用房是帮助了城市低收入家庭,还只是为特权阶层获得二套甚至多套房产提供了方便?在财政预算不受人民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取之于民的税钱自然不会用之于民。人民为国家财政付出了成本,但是并没有尝到充分的好处;在退休、下岗、看病(有时是因“结石奶粉”、艾滋输血或环境污染致病)、为子女教育缴纳学费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再次透支在还贷和通胀后所剩无几的积蓄。如果经济改革不完善造成的盲目发展、社会不公或资源浪费会使我们失去和谐生存的物质环境,那么教育改革的退步会使我们失去这个国家的精神和希望。作为计划经济思维的“最后堡垒”,中国教育体制更让我们看到一幅越改越糟的直观图景。不仅基础教育水平在全国各地千差万别,尤其是在城乡之间天壤之别,广大农民工子女也无法和城里的孩子分享同等质量的义务教育,而且大学招生地域歧视使高等教育机会本来就极其稀缺的许多欠发达地区雪上加霜。由于国立名牌大学大都集中在京沪等大城市,而这些大学一直对本省市考生实行特殊录取标准,其录取本地考生的比例比外地高几十倍甚至数百倍。由于农业比重高、考生基数大的省份是首当其冲的地域歧视受害者,而这些地区吸收本地考生的高等教育资源尤其稀少,知名大学农村学生数量连年下滑便成了自然现象。近年来,一些发达省市实行的“自主命题”改革,以及一些重点大学实行的“自主招生”改革,在地域歧视的招生考试体制下,很可能加剧地域歧视乃至本地不同高中之间的歧视。而地域歧视、“高考移民”以及特权阶层加分舞弊等乱象愈演愈烈,而究其根本原因,仍然是深受歧视之害的全国人民不能有效参与招生考试制度改革。
让人民有效参与改革
由此可见,凡是进步的改革都离不开人民的有效参与。事实上,1978年启动的经济改革本身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近年来,少数地方的公民积极要求参与影响地方民生的重大决策,促成了官民良性对话并取得了良好效果。政府对民意的尊重多少是被“逼”出来的,而事后都应该庆幸事件的圆满结局;虽然官民对话乃至对峙看上去有点“不和谐”,但是总比自焚、群体暴力冲突、大规模上访或事故发生后被迫“引咎辞职”和谐得多。
然而,在更多的地方,公民主动参与的动力和压力都还远远不够,以至地方官员在决策过程中依然我行我素、独来独往、闭门造车。如此在政府主导下形成并强力推行的政策自然未必符合多数民意,而更可能只满足官员自己和少数特权集团的利益。这样的改革之所以不仅没有越改越好,反而越改越糟,以至最后闹得民怨沸腾、悲剧丛生、冲突四起,实在是改革的性质本身就已先天决定的。
要使中国今后的改革越改越好,人民必须能有效参与改革进程。要让人民参与,首先要让人民讲话;无论是否是官员爱听的话,都得让人民说出来。否则,人民如何表达民意?执政者又如何了解真正的民意?因此,要让人民畅所欲言,就要尊重人民受《宪法》第35条保障的各种言论自由。
其次,还要通过各种渠道保证民意受到政府的重视。当前,要做到这一点更难,因为各级人大的选举和运行尚不规范,各级官员都唯上不唯下。尽管如此,中央也还是可以采取诸多措施促进公民参与,至少应废除造成中国社会非正常发展的GDP考核制度。即便仍维持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体制,也应该从考核指标中删除“地方GDP”这个中国发明的概念,并让当地人民的实际收入和满意程度发挥更大的作用。(摘自《中国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