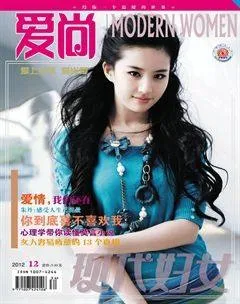为什么中国人喜欢怀旧 等
2012中国男人调查之没钱别谈感情
原始社会,靠狩猎为生的时代,只有强壮的男人才能生存下去,所以,那时候,优胜劣汰法则就开始了。时至今日,男人之间的竞争从体能转化为大脑,优胜劣汰的法则愈演愈烈,特别是在中国,马太效应更加明显,强者恒强,毫无背景的男人想要脱颖而出难上加难。
为什么现在的男人压力这么大呢?除了自己给自己压力,其实更多的是竞争压力。竞争什么呢?资源。生存资源和女人资源。
正因为压力太大,所以男人渴望自由、渴望放松、渴望旅行,可是大都是房奴、车奴,她们根本就没有财务自由。为了生活,他们可能会做不喜欢的事情违背初衷,只为生存和赚钱。
除了生存上的压力,其实爱情上的压力也不小。所谓“丈母娘推高房价”,“嫁人先有房”,这都加大了男人的压力,就好比催化剂。如果男人经济上不强大,那么可能就娶不上老婆,甚至原本有的女人也会被抢走。所以,没钱别谈感情,就算谈了感情也是白谈,这是多么残酷!
归根结底,男人的压力还是源于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这是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这是一个以“财富和地位”为面子的社会。只要主流价值观改变不了,男人就会永远忙下去、累下去。所以,身为女人,大家也要多多理解男人的不易。
——赵格羽,作家、编剧
砸日系车的蔡洋是怎样蜕变的
砸穿西安日系车主李建利颅骨的嫌犯是21岁的泥瓦工蔡洋。这个小学五年级辍学、从老家来到西安的“90后”,已经吊在空中刷了两年墙。他喜欢看抗日剧、上网玩枪战游戏,还在项目经理的奥迪车上撒过一泡尿,为此“感觉很爽”。他想证明“我很重要”,于是喧嚣的游行队伍给他提供了宣泄的机会。喧嚣过后,这是一个让人唏嘘的时刻:日系车主李建利因颅骨被砸穿仍然躺在病床之上,蔡洋也必将因其打砸行为受到法律的制裁。一场偶然的交集,就这样改变了两个人乃至两个家庭的命运。
蔡洋的人生历程更像一棵野草,无人理会,独自伸展。即使在打砸事件之后,他仍旧自认“我是爱国,抵制日货”。什么是爱国,怎么爱国,他浑然不知。当这样一种让人痛彻的事实摆到眼前,所有的人都应当追问,我们的社会、教育或公益、制度或政策,到底在这个群体身上疏失了什么。国民人格,说起来那么虚拟,但一旦展露却这般深重。蔡洋必将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借此看到一个有关国民人格的命题。它包含着今日中国必须面对的艰辛。
——杨耕身,媒体评论人。
莫以文学名义消费莫言
当一个本名叫管谟业的作家在50多岁的年纪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笔名、真名、作品和各类传闻轶事都开始被人津津乐道,甚至连小时候“掉过粪坑,相貌奇丑,喜欢尿床”等也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
如今,一切与莫言相关的东西都在升值。有报道称莫言10年前的手稿飙升至120万元;签名书在网上加价售卖,例如《透明的红萝卜》要价已达10万元;家乡要重修莫言文学馆,发展红高粱文化旅游……更多跟他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和事也在借他炒作。
消遣无害,消费既然是“费”,则必然带来损耗。经诺贝尔奖包装过的莫言,被强行拉进偶像的流水线,被加工、被装扮、被想入非非。事实上,消遣与消费莫言正成为一种“自觉”。媒体除了反复追问莫言“你幸福吗”之外,大众压根不关心莫言为什么不幸福,至多反问你都得诺奖了还有什么可不幸福的,然后自忖即使你不幸福又关我什么事。
也许是出于作家的敏锐,他在获奖后就表达了莫言热不如文学热的态度。然而,面对非常想通过“透支”他的声誉和价值为自己谋利的人与机构,不知莫言能够“无语”到何时?
——蒋芳,新华社记者
为什么中国人喜欢怀旧
一条诨号为“国民床单”的老牌床单,最近忽然为微博和媒体所关注。这种图案笨拙、手感粗糙的床单,意外地裹住了世人的记忆神经。随后,茶缸、脸盆、水壶、毛毯、缝纫机等旧物,均成为网民钟情的对象,更有媒体卷入这场器物怀旧的狂欢,试图罗织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业名牌的清单。尽管这还只是一个初级的开端,却足以展示工业器物怀旧的基本方向。
引发这些怀旧思潮的动因,第一次是基于文化饥饿,第二次缘于消费主义,第三次则较为复杂,其动力不仅来自市场消费,更是针对当下现实的一种柔软抗议。在一个物质膨胀和精神瓦解的时代,怀旧就是一种记忆疗法,它要借助“从前乌托邦”的有限时空,修理被现实灼伤的普遍心灵。
旧器物中的大多数已无法被当代年轻人所使用,并自然地融入日常生活经验。它只能被悬置在装饰架上,犹如一个孤零零的存在,照亮了脆弱而破碎的记忆。但是,怀旧终究只是一种颓废的辅助疗法,它只能产生短暂的安全幻觉,而改变现实的最佳途径,就是越过“国民床单”和“国民怀旧”,径直投入“国民变革”的伟大潮流。
——朱大可,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研究员
(责编 子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