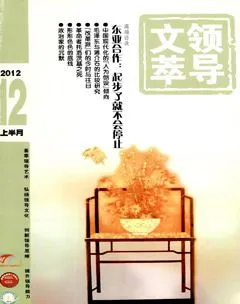公民“政策参与”层级亟待提升
“中国民众的‘政策参与’认知水平远高于实际参与水平,低水平的实际参与对政策参与客观状况总分起了重要的‘拉低’作用。”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合作发布的政治参与蓝皮书暨2012年《中国政治参与报告》如此评价当前民众“政策参与”的实际状况。
该报告显示,民众对“权利与参与途径认知”、“政策重要性认知”的得分率均超过50%,而“实际政策参与”的得分率仅为11%。
在该报告主要执笔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史卫民看来,公民“了解和接受公共政策的参与”水平大大高于公民“实际政策参与”水平这一特点,显示当前中国的公民政策参与,是“接受型的政策参与模式”,而不是“博弈或改变型的政策参与模式”。
“目前公民的政策参与基本停留在‘解决问题’和‘增进政策接受性’的水平上,较难提升到‘增加民众对政策尤其是决策的影响力’的水平。”史卫民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如此表示。
公众政策参与层级低
在2012年的这份报告中,一个最重要的基本结论是,当前中国民众在政策过程中以“接受政策”为基本特征的参与,可以称之为“接受型的政策参与模式”。
“通过这个基本结论,我们解释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公民政策参与到底是针对什么的?从这个模式来看,我们的政策参与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而不是为了改变政策。”史卫民解释说,一个通俗的理解是,例如医保,公众普遍认为医保政策是好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各种问题,公众对医保政策的参与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
形成这个特点的原因何在?在史卫民和课题组团队看来,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前的顶层制度设计和老百姓的参与有相当大的距离。“当前一些重大政策,都是由中央层面来制定,在这些制度设计和决策方面,公众的参与是非常少的。”
报告认为,这种制度建构的模式,对公民的政策参与,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优点是政府对于民众了解政策和执行政策提供了保障作用,缺点是把政策参与层级压的很低,真正在决策层面的参与比较少。
课题组研究认为,这种消极影响最主要表现在,缺乏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尤其是影响决策的制度安排,或者已有的制度安排(如政策听证会、政策方案意见征求)实际作用不大。
“例如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制定相关就业、社保、教育等政策时,缺少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史卫民表示。
而目前的各类听证会流于形式也早已广受诟病。一些参加听证的代表可能是事先安排好的,听证后总是绝大多数同意政府的方案。
“听证会走过场,预先设置议题,实际上是为保证政策过关。如果以此为前提,公众参与很大程度上就是个形式。”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种思路背后的大背景是,当前各级政府头号任务还是求发展,而百姓更关注民生,两者之间产生了差异,体现在政策上,如果更多引入百姓和社会的参与,发展速度势必会受到影响。
实际操作更重要
在此次调查中发现,对某项政策不满意时,被调查者可能采用的表达意见方式,排在前列的分别是“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向政府有关部门(包括信访部门)反映”、“找熟人帮助解决问题”或“向媒体反映”,而“参加听证会反映意见”则排在倒数第二的位置上。
对于这样的现状,课题组得出的结论是:已有的制度安排(如政策听证会、政策方案意见征求)实际作用不大,在一定程度上强化而不是弱化了政策过程(尤其是决策过程)的“模糊性”。
史卫民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任何政府在整个政策过程中,都有一个模糊区间,“在中国,由于存在中央和地方的博弈、资源分配的问题以及行政效率等原因,政策有一定模糊性是客观存在的。但有一种模糊性是要消除的,就是利益集团在操纵政策的制定。”
在他看来,模糊性本身可以用公开性的制度设计来减少不良后果,公民政策参与要求的“开放性”,与中国目前政策过程较强的“封闭性”确实有一定的矛盾。
而在课题研究团队看来,近年来,政府改变“封闭性”决策过程的努力也在显现。如在医疗体制改革的政策方案选择等方面,就大量采用了“开放性”的做法,经过四年的各界大讨论最终形成了目前的医改方案。问题是,这样的尝试还太少,还难以起到改变中国既有政策模式的决定性作用。
“政策民主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政府来说,要通过比较形式化的方式,走向比较有实际意义的方式。”史卫民指出,相对完善的政治参与既需要理性的政府,也需要理性的公民,尤其是政府,需要大量的政策学习,“学习什么呢?在决策中不能拍脑袋,在执行过程中不能强行推,在评估过程中要科学,不能想当然。”
课题组成员、中国社科院政治所博士郑建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政策参与的种种不足,一方面是个阶段性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与政府的行政效率考量相关,“政府要预先评估收益和损失,在这个过程中,会找到一个他们认为稳妥的点去推进。”
“制度的建成是个漫长的过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一直在推进,尤其这十年发展比较快,已经开始建立相应的制度。”史卫民指出,政策参与制度的形成,和选举制度一样,形成之后,从不规范逐步走向规范,就会对整个社会产生作用,“不过,关键的问题,不在文本的制度,往往在实际操作。从文本意义上说,每个公民都可以对任何政策发表意见,但问题是,发表了有用吗?这就是机制问题,而不是制度问题。”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