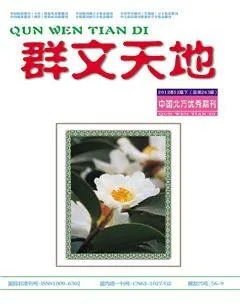司法调解的另外表现
一、案例的提出
案例一,申请执行人张某与被执行人李某在诉讼过程中达成调解协议,约定由李某归还张某人民币110000元,于2011年3月23日归还人民币50000元,2011年5月15日归还60000元。2011年3月23日李某归还张某人民币40000元。其余未给付,申请执行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剩余款项人民币70000元。本案在执行过程中发现,本案虽为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但实则是张某委托李某为其购房,李某也为其找了房源,张某支付李某人民币110000元,同时搬进了房屋,但一直未办理过户手续。后因房价上涨房主不同意卖房,于是李某出具欠条给张某欠张某人民币110000元,但张某一直居住该房。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李某提出要求张某搬出房屋,否则余款不支付;申请执行人则提出,其基于对李某的信赖而损失了很多期待利益,若搬出所居住房屋则需要另外补贴对方人民币20000元。经执行法官的多次协调,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由李某给付张某90000元人民币,张某同时搬出所居住的房屋。
案例二,申请执行人邓某与胡某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经诉讼判决由胡某赔偿邓某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人民币41435.35元。因胡某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本案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查无可供执行的财产,通过执行法官的多次工作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由被执行人胡某一次性支付邓某人民币12000元,邓某放弃余款的执行。
二、案例的分析
两起案例均以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且履行完毕为结案理由。两案从其表面上看是当事人就自己的民事权利所做的自愿处分,但法官为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强制执行并不如外界所描述的——当事人拿到了人民法院或其他机构作出的裁判文书就意味着进入了保险箱。事实是,当事人进行诉讼有败诉的风险,而申请执行则也有执行不能的风险——即被执行人无履行能力的风险。上述第二个案例中,被执行人已年满65周岁,且其交通肇事的工具为农村拖拉机,经调查其确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作为执行法官在告知申请执行人存在执行不能的风险前提下,告知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是每个公民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双方当事人能够本着互谅互让、通情达理的原则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其次,执行过程中的和解并不如外界所描述的——一味地使被执行人让渡其权利。债权人放弃部分权利是达成和解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绝对。上述案例一恰反应了申请执行人多获得了利益。从和解协议的表面上看,双方当事人是自愿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愿意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数额及履行方式,但却是执行法官在深入了解双方的矛盾焦点,向双方当事人进行释法明理后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
最后,执行才是最终的案结事了。案例一中,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达成调解协议,但被告却只部分履行,原告据此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诉讼过程中并没有真正的案结事了,且也未真正深入了解双方矛盾的焦点,只是按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案处理。该案中当事人或许是为了方便而在诉讼过程中未向人民法院阐述其真正的目的。而在最后的强制执行过程中,当事人为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最终的保障,往往向执行法官“坦露心声”,当事人也知道这是其保障自己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关口。因此,执行法官在处理案件过程中为了能彻底的案结事了,需要也应当介入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之中而予以化解。
三、司法调解的另外表现—执行和解
在现有的对司法调解的研究中,大多集中于诉讼调解以及其余非法院调解,研究均认为调解更有利于当事人矛盾纠纷的解决;但调解案件申请执行比例高,调解案结事未了的现象仍然存在 。实则上,强制执行才是真正的体现能否案结事了的阶段,执行阶段法院实质性介入和解可以视为“二次调解”。执行和解应当纳入司法大调解的范畴。
从上述两则案例可看出,成功的执行和解案件大多与执行法官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说服教育方法分不开,与其说是纠纷当事人之间自愿对其民事权利的处分,不如说是执行法官为了化解矛盾纠纷而对当事人进行的执行调解,其内容客观上包含了法院的意志。然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 ,执行员所做的工作只是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法院意志撤身于外,蒸发于无形之中,形成了当事人一种自动和解的表象,这种过程与结果的矛盾,与法理不符,在司法实践中也引发了许多问题 。
究其原因,一法院实质性介入执行和解过程将愈加使得法院失去被动、中立的态度,不符合司法权的中立性 ;二是法院实质性介入否定了执行依据的既判力。
执行中法院实质性介入执行和解过程是司法能动主义的体现,强制执行的过程不仅要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也要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并不是法院的强制和解,并非是前置程序;正如诉讼调解,仍然是以自愿、平等为基础要件。执行权的能动性不仅在于使生效的法律裁判文书得以尊重和实现,更在于化解矛盾与纠纷。执行依据的既判力是指确定纠纷当事人之间的最终判断,执行中法院实质性介入执行和解是在执行依据确定的权利义务前提下,根据客观情况促使当事人行使民事权利的处分,并没有损害执行依据的既判力。在我国台湾地区法律规定,当事人在强制执行程序或破产程序中,或其它场合成立之和解,纵在法官劝谕下成立,亦属诉讼外之和解,非所定之执行名义,亦无阻止原执行名义之效力 。
“和解是最适当之强制执行”“瘦的和解胜过胖的诉讼” 。执行中的和解更有利于纠纷当事人矛盾的化解、有利于缩短执行周期,也避免了就案论案、机械执法,充分体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执行法官为了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付出了许多努力,而这种努力不亚于调解,且是为了真正案结事了的调解。
(作者简介:王建军(1974.10-),男,大学本科,江苏省金坛市人民法院执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