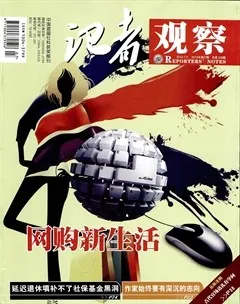顶层设计绝非“改革计划书”
“摸着石头过河”,可以说是对中国改革最形象的描述,30余年来,中国社会通过“摸石头”跨过了一条又一条的改革大河;近一段时间,中国社会对改革又有了一种新的期待与呼唤——“顶层设计”。应该说,提出改革的顶层设计,表明中国社会对改革的认识与实践更加深化,但如果片面理解顶层设计的意蕴,并据此而简单否定“摸着石头过河”的意义,对更进一步推进中国的改革是很不利的。
改革从不忽视理论指导的重要,更不否定统揽全局、统筹兼顾的必要性。改革需要设计,改革也可以设计,尤其是顶层设计。但是,顶层设计不是成立一个什么权威部门在办公室、会议室里闭门造车,拿出什么“一揽子计划”“终极方案”,然后发一道“红头文件”要求全国各地照此改革,这样的行为是要出大问题的,这样的思维是要犯大错误的。尤其是现在一些人提出的一些改革方案不是从教科书上照抄下来就是从外国人那里照搬过来,这样的设计不仅与中国火热鲜活的改革实际相差千万里,还可能把中国的改革引到歧路上。在进行顶层设计的时候,一定要避免两个误区:
第一,不能把顶层设计理解为是“方案设计”。我们的改革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就是看到在鲜活的实践面前,任何“计划”都是苍白无力的。市场经济最神奇也最让人敬畏的地方,就是市场中各怀心事的主体通过自发的博弈与磨合而各得其所。对所谓完美、超然、成熟改革方案的信奉与膜拜实在是典型的计划思维,指望用一套方案通吃改革打遍天下更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第二,不能把顶层设计理解为是“用好制度代替坏制度”。有的同志讲,我们现在的改革之所以好像人人都不满意,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好制度”,只要设计出“完美制度”改革便可一劳永逸。其实不是这样的。制度研究告诉我们,“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在实践中往往是一句空话,甚至是谎话。任何制度都有其偏好群体和优势策略,这是由“制度非中性原则”决定的,从来没有不偏不倚、一视同仁的制度存在。
真正管用的改革方略和真正靠得住的制度,像中国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小岗村的田野里长出来的,不是在办公室里鼓捣出来的;从南海边上小渔村变成国际大都市的特区深圳,也是自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杀出一条血路,并不是对会议室里所谓规划的照猫画虎。
现在改革中遇到困难、出现问题,表面上是缺乏有效的实施方案,其实根源是我们在事关改革方向性的一些根本问题上没有搞清楚。有了科学改革观,改革的动力、改革的共识、改革的方略等这些具体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所以说,顶层设计为改革明确方向,“摸着石头过河”为改革探索道路,两者相辅相成。摘自环球网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处长、教授、博导)
什么叫真正的“逆城市化” 郎咸平
“逆城市化”这个概念是美国地理学家波恩在1976年提出来的。它指的是西方国家的“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人口增多、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城市病”越来越严重,大量城市人口开始往郊区或者农村流动。美国“逆城市化”的第一步是,富人先搬出去。他们搬出去之后,由于有足够雄厚的财力支持,附近的一些基础设施就逐渐建起来了。第二步是,中产阶级搬出去。因为富人搬出去之后,他们附近的相关配套设施建起来后,一些工厂也搬出去了,到最后形成一个具有多项功能的小城镇。这小城镇交通不拥挤,环境优雅,治安良好,工厂、公司又都在附近,慢慢就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依附于大城市的小城镇,这就是一个富裕社会发展到最后的必然结果。
而中国的“逆城市化”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逆城市化”其实是基于严重的分配失衡,它是由利益或者是土地诱惑所催生出的,并不是真正的“逆城市化”。土地现在越来越值钱了,透过土地可以拿到很多高额的回报。这也是中国城市化的另一个注脚,就是由于城市的不断扩张,需要不断地征用土地,所以你有农村户口,就能够享受土地增值的红利。
在今天整个大的城乡二元结构之下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有两个制度是亟待突破的:一个是户籍制度,其实户籍制度要解决的不是户籍本身,而是户籍背后庞大的利益集群;另一个是土地制度,因为土地能生钱,而且越来越值钱,土地就是财富,在这种情况之下,拆迁、征地过程中就出现越来越多的跟土地相关的案件。
在“逆城市化”的潮流下,很多白领已经害怕了城里的高房价、高成本、交通堵塞、高污染、能源不足这些问题,开始“逃离北上广”进入二线城市,追求更加舒适的生活。之所以说要逃离北上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的“城市化”有很多病,而且有很多的误读。其中一个很大的争议就是,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把“城市化”简单理解为“工业化”。这是非常糟糕的。根据研究显示,中国经济80%的增长来源于钢筋水泥,20%来源于劳动力的投入,到最后我们发现,城市没有任何技术进步。更可怕的是,只要“城市化”一停止,什么都停摆了。这种“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思维是非常可怕的。
目前中国正处于大城市发展的阶段。大城市发展并不是说光盖高楼大厦,用工业化拉动城市发展,而是要解决老百姓的困难,譬如治安、环境、垃圾,还有上学、住房,让大城市更完美,让城市居民的生活更美好。一些有钱人像欧美国家的富人一样逐渐地搬到郊区去住,郊区的配套设施也就起来了,然后中产阶级再搬出去住,接着就会有很多的公司、工厂搬出去,最后形成一个配套完善的城镇。这才是真正的“逆城市化”阶段。
摘自中国经济网
复杂性社会的积极管理 孙立平
人类社会生活是一种群体生活,群体生活必须以基本的秩序作为保障。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管理对于任何社会都是必需的。与传统社会相比,我们现在身处其中的是一个更为复杂、更具风险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世界。
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趋势主要源自于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经济带来的不仅是资源配置的多元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调控机制的间接化和复杂化;而且,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和利益群体的分化。二是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民族国家由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变成一个开放的体系,外部因素“楔入”内部结构,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由此变得更为复杂。三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每一次重大的技术突破都会对现有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带来强烈的冲击。四是大众消费社会的来临。新的消费品、消费方式和消费理念导致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与分化,其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增加是显而易见的。五是快速的城市化。与简单的乡村社会比,城市是一个更复杂的社会,无论是城市生活还是社会结构都是如此。与此同时,社会生活的风险在明显增加。复杂的社会生活本身就意味着系统风险的增加,而社会的转型,无疑又为社会风险增添了新的因素。
简而言之,上述几方面因素使得我们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变得空前复杂。所以,将社会管理区分为消极社会管理与积极社会管理是很有必要的。消极的社会管理是以被动防范为手段,以维护现状为目标;而积极的社会管理则以主动的建设和变革为手段,以改善社会的状况、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为目标。虽然在积极的社会管理中也要努力应:对和化解现实中某些消极因素,但它的目标更具有进取性。这里之所以提出消极社会管理与积极社会管理的概念,是为了避免一个误区,即在种种问题和矛盾的压力之下,片,面地从消极社会管理的意义上来理解社会管理,并在实践中将社会管理变成片面的社会。控制。
在面临加强社会管理的现实因素面前,选择什么样的社会管理模式至关重要。积。极的社会管理旨在改善社会,推动社会进步,以建设一个好的社会来实现社会管理要实现的目标。换言之,管理本身不是目的,管理只是一种手段。社会管理的真正目的是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一个好的社会最重要的含义是实现公平正义。维护公平正义、政通人和、人们心情舒畅、社会生活井然有序,无疑是增进人们幸福感的重要前提。维护公平正义,也是目前我国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社会要立基于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之上;一个什么样的基础才能让我们这个社会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
摘自《北京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