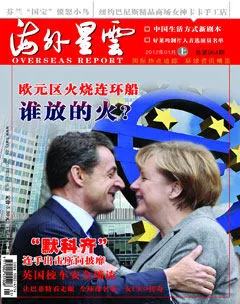重庆大厦演绎另一种全球化
香港重庆大厦有120多个不同国籍的人同住,文化多元、民族平等,商品与资金经此进出南亚、非洲及第三世界,展现另一种全球化现象。
香港另类知名地标
重庆大厦是香港另类知名地标,门牌号码:弥敦道36号至44号,坐落于香港市中心黄金地段。大厦楼高17层有920个单位,有廉价宾馆160家共1186间客房,有香港住宿最便宜的小旅馆。最低的4层是商场(包括地库一层),共有商铺300多个。大厦住了4000多人,主要是香港少数族裔,南亚和非洲裔人士最多,华人反而是少数。每日平均有1万人出入重庆大厦。
跨进重庆大厦,两边厢都是货币兑换店。再深入一点,就会闻到咖哩的飘香,目光所及尽是棕色皮肤的面孔,仿佛身处加尔各答;转一个角落,就进行了一次时空穿越,狭窄的过道里,黑色的面孔簇拥而至,恍如站在开普敦。这里的住客以第三世界人士为主,他们大多提着行李带一笔小钱从金沙萨、阿克拉或卡拉奇等地买一张机票飞到香港国际机场,然后直奔重庆大厦,把自己勾连上全球化的网络。安顿下来后,他们会通过人际网络打听商贸情况,接触中国货品的供货商或亲自到中国内地找货源。采购的货品小至几百部包扎起来的手机或几个装在大袋里的衣物,大至要用货柜船运。
另外的住客多来自第一世界地区如欧美或日本,他们以旅游为目的,很多是背包客,带着一本自助旅行手册《Lonely Planet》;近年,随着中国大陆自由行的开放,住在重庆大厦的中国内地旅客越来越多。
重庆大厦如一个中央车站,小股商品与资金经此进出第三世界国家,是一种“低端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现象。一些小商人每趟商贸活动可以赚取400至1300美元不等。来自珠江三角洲一带的中低端手机是重庆大厦这里最能体现低端全球化意义的商品,也是最大宗的商品。商场里有近100家店铺从事手机批发和零售生意,店主大多是华人,其次是南亚人,最主要的客户则是非洲人。
其来有自
重庆大厦的旧址是名为“重庆市场”的一个商场,一批菲律宾华侨买下该处土地兴建大厦,1960年开始卖楼花,一个1000平方英尺的单位售价约3万元(港币,下同)。重庆大厦当时是三面环海的豪宅,外墙有阳台,其商场是当年香港最大规模的。到上世纪80年代,附近英兵营房的印度士兵开始在大厦低层开餐馆和电器店;楼上被改建成廉价宾馆,原有的阳台被封住。重庆大厦渐渐变旧,墙身斑驳,外墙冷气机滴水严重,下面的人行道热天时经常湿漉漉的。
在香港人心目中,重庆大厦外型老土,是第三世界穷人聚居之地,人流复杂。在重庆大厦某个单位里,戴着金色假发扮演杀手的林青霞杀了几个印度毒贩,然后在逃跑时遇上失恋的扮演警察的金城武,但最终两个人擦身而过,这是王家卫1994年上映的电影《重庆森林》中的情节。电影以重庆大厦为故事背景,影片里大厦的通道和走廊阴暗昏沉,空气里潜藏着惴栗与危险,不同国籍的人往来穿梭,怀着不同目的赶往不同地点。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前,重庆大厦罪案频发,盗窃、抢劫屡见不鲜,毒贩、妓女常以这里为大本营。加上年久失修,电线铺设杂乱,大厦时常发生火灾,又被港人称为“火警大厦”。一般香港人过其门而不入,视为“他者”集中地。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重庆大厦慢慢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伴随着中国内地经济崛起的大环境,重庆大厦的旧故事逐渐被改写。
明星钟楚红曾住这里
香港人林惠龙的人生故事,和重庆大厦一样具有传奇性。
她最早在重庆大厦开旅馆。她一存下钱就买重庆大厦的单元房,把生活重心转移到宾馆经营方面。“B座五楼B一室是钟楚红家,这里很多老居民是看着她长大的,她去选香港小姐后她家人就把单元房卖掉搬走了,后来被人买来做宾馆。”林惠龙笑说:“可是做得不怎么样,我就租来自己做宾馆,留一个小房间和女儿一起住。”
“1993年的时候,王家卫申请来重庆大厦拍电影,当时我做法团主席,担心拍电影引起混乱,于是拒绝了他。他就进来偷拍,把旁边的另一幢大厦也拍了进去。这部《重庆森林》反而让重庆大厦名声变大,多了不少外国客人。”
其实重庆大厦并非是一座大厦,而是5幢大厦在一、二、三楼商场部分连接而成,4楼以上是分开的,因此重庆大厦的英文名Chungking Mansions是众数(复数)。踏入2000年,在林惠龙领导之下大厦管理团队着手改善治安问题。招揽一批有警务工作背景的人参与管理,设立先进的保安控制中心,陆续安装了300多个闭路电视镜头,外围小巷亦被覆盖。
“我们通过监控屏幕看到可能是贩毒或吸毒的,就会立刻通知警方派人来;至于在商场大堂的妓女,会派保安人员去查问她,让她不胜其烦,之后就不想到这里来拉客了。”林惠龙谈到她的另类管理方法。重庆大厦里从事贩毒、卖淫的给驱赶出去,加上更新了照明系统,整座大厦氛围为之一新,一扫以往的阴暗昏眩。有时,警方侦查刑事案件时也要借助重庆大厦的闭路电视录像。
2007年,重庆大厦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亚洲“最佳全球一体化例子”,认为其环境充分体现了文化多元、民族平等、和平共存。从这种意义看,重庆大厦不只是一座大厦,而是一个小小区。
第三世界梦想之地
在重庆大厦出入的人肤色不同习俗也不同,不时有小摩擦,但在有效的大厦管理之下大都能做到和谐共融,以赚钱致富为目标。Mike就是一个成功致富的例子。他是印度人,1967年来香港。9年多后累积了第一桶金,开始在重庆大厦开设自己的店铺,从中国大陆进口手表出口到南亚和非洲。Mike起初在重庆大厦帮人做跑腿,现在已有过亿财产,住在半山。他有18个单元房,是重庆大厦其中一个大业主。Mike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同时有香港和印度身份证,但他说:“我不是香港人也不是印度人,我是重庆人。”
其实,由贫变富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来到重庆大厦只是跨出成功的第一步。这是一场竞赛,有很多人落败而回,在供应链和销售链的其中一环出了错就有可能血本无归。当然并非所有住在重庆大厦的第三世界来客都是为了做生意,不少人是为了找工作。他们有的被迫返回家乡;有的签证已过期但冒险留下来打零工;有的则以申请政治难民为由住在重庆大厦。前一阵子其中一些人收取港币1000元帮人排队抢购iPone 4s,曾被香港一家传媒追踪报道。更有一些做妓女的,所得维持生活之后主要汇回家乡接济亲人。
“做生意赚到钱的,都会在家乡建大屋。”香港非洲人团体副主席Steve说。Steve、37岁、西非加纳人,现租住重庆大厦一个房间。他2005年来香港,主要把中国内地的成衣和电子产品运回非洲出售。“非洲那边对手机、电脑、二手车、电单车、成衣等有很大的需求,一部手机来价港币200元,在非洲可以卖到1000元。”
重庆大厦亦因此声名远播,尤其在非洲和南亚。Steve说:“我们加纳那边都知道Chungking Mansions,他们以为是一座城市,来到一看才啊的一声说怎么只是一座大厦。”(编辑/唐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