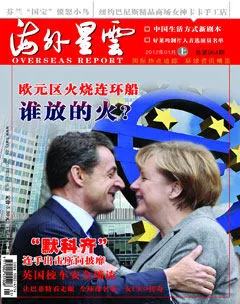中国生活方式新剧本
2012-12-29 00:00:00
海外星云 2012年1期

电视剧的逃避主义是一种升华,让现实色彩投射在想象的画布上,绘出中国生活方式的新剧本。
观看中国电视剧的感觉,已经不是娱乐,而是与中国理想的生活方式互动,浸淫其间,不知不觉地改变了自己。
都市人的童话
去年中国最流行的电视剧之一《步步惊心》是一部穿越剧:美丽的女主角——一位当代都市的办公室女郎,神差鬼使地回到清朝, 参加了“九王夺嫡”的惊险游戏,以丰富历史知识“预知未来”,但又可以用现代的眼光去超越时代的局限。这当然是一种遐想,作者桐华甚至说:“如果武侠是成人的童话,那么穿越小说就是都市人的童话。”
恰恰是这样的童话,带来了现代中国人的独特享受。
而那些以都市恋情为主旋律的戏剧,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与期盼。从《男人帮》到 《双城生活》,从《蜗居》到《裸婚时代》,都可以看到中产阶级上升的身影。他们不甘于平庸与贫穷,力争上游,也因此在生存策略上开拓新的智能,也记录了这 一代中国人的思想状态:要精明也要高明,要晓得如何博弈,赚取最大的利益。
这些电视剧不约而同地展示中产阶级的世界观:要活得自由,崇尚精神的解放,也要物质的滋润。他们都会用电脑,实时的视频联系。但最“雷人”的是他们都住好的房子,就像《男人帮》孙红雷饰演的顾小白住在浦东的现代公寓,比香港的豪宅更强,而他只是一名自认为中产阶级的作家。而《双城生活》的郝京妮虽然只是旅行社OL,但也和当公司警卫的父亲住在北京豪华的四合院,更开一部进口的吉普车。
这在观众的眼中看来,肯定是都市的神话,但这样的逃避主义却发挥了一种“标准设定”的意义:中产阶级就应该这样生活,大丈夫、小女人,就应该这样活得滋滋润润。也就是从这样的物质生活开始,才有对爱情的追求,也才有对情感与人生纠葛的反思。
因而这些都市电视剧不但反映现实,也启发现实。如果说多年前那些红军长征剧在唤起革命的情怀,今天的都市剧却在不断呼唤一个现代化的生活长征。剧中的一些插曲,往往都对时代的弊端做出无情的批判。如《蜗居》的主角海藻的姐夫就被卷进案件,要靠贪官宋思明来解救摆平。当然,《蜗居》中的情节描述拆迁老城区房子所引起居民的抗争,也紧密反映残酷的事实,也肯定引发广大观众的强烈共鸣。
也就是在这样的虚虚实实中,中国的电视剧创造了一个让观众上瘾的世界。它真中有假,也假中有真,让观众体会:中国现实的戏剧性,往往胜过想象的剧本。电视剧的逃避主义,反而是一种升华,让现实的甘苦色彩,投射在想象的画布上,绘出中国生活方式的新剧本,也绘出一幅又一幅激荡人心的历史画卷。
2011年中国电视剧的整体风潮,已彻底走出前两年铺天盖地的“谍战”重围,受众主体偏向年轻化、都市化,更结连80后的需求与口味,进行类型尝试。但在这些热播剧集大获成功的同时,是否意味着本土电视剧产品对社会现实做出了更多关照?年轻的中国电视观众群,又究竟为何而看剧、为何而共鸣?
本土特色造梦
中国电视剧观众主体日趋年轻化、低龄化,而上一代合家聚在客厅守候黄金档剧集的观看方式,也早已不适应于如今的大陆观众群。今天,人们有无数种便利、高效的方式“煲”剧——电脑、iPad、手机,随时随地可通过各种视频网站与软件在线观看,而剧集被消费的速度与价值则成反比。像《步步惊心》这样一部全长35集、每集平均时长45分钟的电视剧,每天夜晚归家已十分疲累的年轻白领,自然没有耐心追随电视每晚播出两集的进度,他们会选择在一个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周末,对着计算机一口气全部看完,为若曦与雍正无疾而终的苦情怅然一番。然而第二天、第二周,怅然便迅速淡去。当红剧集的风头不出3个月,已被下一部替代。观众一方面高速消费着剧情提供的实时想象,另一方面也在高速抛弃着自己所“看”到的。电视剧本身已不及电影般有相对的完整性,而在观众可以充分进行自主选择的观看过程中,它便越加趋同于这个碎片化传播时代的其他媒介——能透过零散的剧情、信息与讨论议题,吸引观众关注一时,便算圆满。
电视剧的价值传播能力,与受众内心的欲望投射紧密相连,因而当下中国电视剧所提供的,其实也是观众所渴望看到的——即使“裸婚”,名牌服饰、奢侈品、最新款电话也一个都不能少,都市80后们诚然正是追求着这样一种既贫穷又有能力消费的生活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以不同类型造梦的本土剧集,也日趋形成了具本土特色的消费生产系统,以向观众兜售不同形式的共鸣。
作为一种娱乐产品,中国大陆电视剧的类型成功正源于它的内在矛盾。如中国其他传播媒介一样,它承载着年轻受众在物质与精神层面的难以同步,也为他们弥合着生活现实与生活想象间的巨大落差。尽管观众在剧集中永远不会看到自己的真实生活,但却诚然可以看到自己所渴望实现的生活 ——爱情、自由、逃离,而这才是电视剧与时俱进的功能与能量所在。(编辑/唐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