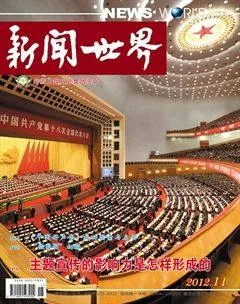新公共领域的出现与权力的位移
【摘 要】清末时期,随着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大众掌握了新兴的政论报纸这一渠道,中国也建立起初具规模的公共领域。以《时务报》的创立为开端,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开始了短时期的扩张,这带来的是统治阶层的权力向公众位移,清政府的权力开始摇晃瓦解。
【关键词】《时务报》 公共领域 权力位移
在哈贝马斯看来,在17、18世纪的欧洲,出现了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过程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有弹性的交往网络。通过私人社团和学术协会、阅读小组、共济会、宗教社团这种机构的核心,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等为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①这些早期的公共空间逐渐沿着社会的维度延伸,并且在话题方面也越来越无所包:聚焦点由艺术和文学转到了政治。在公共领域大规模兴起之前,中国的公共领域只是存在于某些私人聚会等一些形成公共团体的谈话中,但这些谈话中仅仅只存在一部分公共领域生活。当一些公民以不受限制的方式进行协商时,他们就成为一个公共团体来进行社会活动,在大的社会公共团体出现时,这种为了公共利益进行的聚会或结社或发表言论就会出现新的特殊的公共领域,与之伴随出现的就是特殊的手段用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公共领域的发展程度是和社会的民主发展程度是息息相关的,民主的程度决定着公共领域的合法性的程度,决定着公共领域发展的程度。
政府(统治阶层)、媒介、公众,这三者以一种角力的形态出现,统治阶层利用媒介为手段对公众进行意识形态的控制。而这三者的权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科技的发展,新的公共领域的出现,新的权力中心的兴起是和新的传播渠道连接在一起。这种由新的渠道产生的公共领域从总体上来说加剧了社会权利结构内部的紧张关系,使得权力在这场角力中开始位移。我们将从考察以下问题来说明这一点:中国知识分子怎样通过组织也就是新的公共领域使得批判过程(议政)得以运作,并推动权力的位移的?现主要是从维新变法中的《时务报》来阐述。
一、《时务报》创办之前,知识分子的启蒙变法之路,使清政府开始动摇
中国的近代报刊始于外国传教士所办的报刊,而在戊戌变法之前社会的意识形态受到了传教士报刊以及清政府封建思想的禁锢。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了中国知识分子沉重的一击,有觉悟的年轻人开始纷纷寻找富国强民之路。相对于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的铁板一块而言,晚清存在着有限的自由,主要是因为很多城市的列强租界成为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庇护所,同时,内忧外患的清政府迫于压力开始政治经济改革,统治专制集权受到削弱,地方势力相应扩张,民间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近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开始出现,以上条件,均为近代的公共领域的出现起到了推动作用。
以“公车上书”为起点,登上历史舞台的维新派开始了变法图强的维新运动,他们将组织学会创办报刊作为开展维新运动的两种主要手段。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这场运动中一共创办了30多种报刊,②在扩大变法影响、推动改良运动的开展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1895年8月17日,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倡导并出资创办的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第一份报纸《中外纪闻》,同年成立强学会,也是国内第一个具有政治性质的政治团体。但受到顽固势力的反对,于1896年,出版了五个月后,便停刊了。而1896年1月创立的强学会机关报《强学报》同样受到顽固派的绞杀,出版了三期就被勒令停刊。这两份报纸虽然很快夭折了,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努力并没有白费,这两份以官僚士绅为受众的报纸,宣传变法的内容,托古改今制的思想,启蒙了不少官员和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光大了维新,为改良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那时的政论报刊的出现,对于国人来说依然是新鲜的传播渠道,这个新的传播手段的出现,影响了清末的社会权力结构,加重了社会内部权力的紧张状态,并通过新的公共领域达成的。
二、《时务报》一纸风行,清政府迫于压力,开始让步,清政府开始瓦解
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创办的《时务报》一纸风行,发行到全国十八省乃至海外,派报处多达200多个,发行量最高时达到1.7万份,创下了当时报刊发行量的最高纪录,也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维新报纸,“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③《时务报》的出版,惊醒了许多中国人的迷梦。报纸的内容载有论说、上谕、奏折、中外杂志、域外报译等。梁启超一个人就在《时务报》上发表了60篇文章,梁启超论政的时代开启了,依他主张,《时务报》主要分为两个板块,一是政论板块,他自述“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文各报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④24岁的他以那支“笔锋常带感情”、“别有一种魔力”的笔,写下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政论,其中《变法通议》全文7万字,连载了21期,热情地喊出了“变亦变,不变功;变”的时代最强音,提出了“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等具体措施。这些“务求平易畅达”的议论,使海内耳目为之一新,舆论为之大振。《时务报》因梁启超而风靡全国,梁启超因《时务报》而名动一时,“上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⑤《时务报》在主张变法的同时结合维新思想,宣传对象由“少数王公大臣”发展成“中上层官吏和士大夫”,⑥逐步建立起一个代表着共同利益并且独立的公共领域。《时务报》所统率的文人论政的风气,“向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生活领域迈出了可贵的一步”。⑦第二是新闻报道板块,梁启超在《时务报》第一册上发表了《论报馆有益国事》一文,首次把报纸比作耳目、喉舌,认为它具有“去塞求通”的功能,有了报纸“待以岁月,风气见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渐备矣。这在当时不可不说是一大创举。《时务报》的新闻报道板块所引用的材料,大多带有新闻评论性质,这成为发表政治意见的另一种手段。新闻报刊与政论的相互补充,成为共同传播意识形态,宣传变法的“信息流”,创造了“天地间最大之势力”的公共舆论。⑧梁启超的办报主张以及他的政论文章的宣传,不仅启天下人之智,并且代表了知识分子利用了新的传播手段,创立了独立于统治阶级的新的舆论中心,并使中国近代文化系统和舆论空间在大众媒介的引导下营造出民间化的舆论形态。⑨中国近代媒体的信息,已经“演变出一种相对独立、贴近下层市民社会的公共品格。”⑩并且,由于《时务报》学会、学堂、报纸“三位一体”的模式,培养了中国知识分子论政的批判精神,“直接地扩展了公共舆论空间,承担起了哈贝马斯关注的‘沙龙、咖啡馆、俱乐部’等‘对话场所’的角色。”(11)《时务报》的创立是近代一个“规模较小,但已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形成的标志。(12)
三、《时务报》受到绞杀,但统治阶级的权力开始向人民大众位移
《时务报》推动了整个维新运动的发展,在《时务报》的宣传影响下,改良派政治团体在全国纷纷建立,维新运动也在各省市开展起来,各地的维新报纸也纷纷创刊。中国的公共领域,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了些许扩张。这些,通过新的报刊和其他传播渠道而产生的公共领域,真实的表达出自己的政见,彰显了自我的个性,启蒙了公众。在清政府、新兴的报刊以及大众的这场角力中,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群体,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拿起手中的笔,利用报刊这一媒介,宣扬变法精神,启蒙了民智,开始唤醒被统治的人民,构建出新的公共领域,撼动了清政府。但是,封建政权和文化开始对追求自由和理性批判并构建新的公共领域的仁人志士进行扼杀,在顽固势力的压迫下,具有变法思想的梁启超被排挤出去,汪康年将《时务报》私改为《昌言报》。这时《时务报》完全变质,成为了洋务派的喉舌。
参考文献
①杨芳,《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的当代价值》,《贵州社会科学》,2007(12)
②方晓红:《中国新闻史》,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9
③④张之华编:《中国新闻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⑤傅国涌:《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⑥⑧吴果中,《〈时务报〉与中国近代公共舆论空间的建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6)
⑦方汉奇:《中国新闻史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563
⑨⑩(11)刘增合,《媒介形态与晚清公共领域研究的拓展》,《近代史研究》,2000(2)
(12)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史林》,2003(4)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责编: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