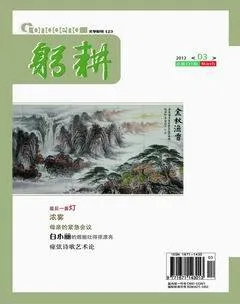梦回故园
奶奶和树
初夏时节,我到浙江奉化溪口镇游览。在参观蒋介石故居丰镐房时,听导游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丰镐房的“报本堂”前原有两棵桂花树,花色一黄一白,开黄花的人称金桂,长在西厢房——蒋介石的原配夫人毛氏的卧室一侧;开白花的人称银桂,长在东厢房——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卧室一侧。两棵桂花树一直长势茂盛,丰姿绰约,特别是到了金秋时节,枝叶繁密,花香满院。然而在2003年,东厢房一侧的银桂却突然日渐枯萎,植物专家虽多方救治,但终无法救其生命。见此情景,有人说“莫不是宋美龄女士也大势去也?”不久,宋女士真的驾鹤西行了,令人唏嘘不止。现在挺立在东厢房门口的银桂树是后来人们重新补栽上的。
是不是真有这么“邪乎”?没有亲眼所见,没有亲身经历,断不敢枉加评论。但不管怎么说,我仍希望这个故事是真的,因为它寄托了人们的一种幽思在里面,况且名人逸事向来是俗人如我者茶余饭后最好的谈资,何必去较真呢?
这个故事也让我想到了我的奶奶和奶奶的树。只不过,上述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代“国母”,千古丽人,而我的奶奶则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乡下小脚女人;这个故事的主体是名贵的金桂银桂,而奶奶的树则是乡下常见的杏树、枣树、柿树、李子树和花椒树。但奶奶和她的树的故事却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千真万确。
打小时候开始记事起,我就记得在我家的房前屋后,生长着各种树木。因为少小贪嘴,对于我,记忆最深的莫过于其中的果树了:
杏树一棵,长在房屋后面,树干有五六尺高,春天来了,花开烂漫,惹得蜂蝶为之群舞,只是一夜风雨过后,便落红遍地。
柿树一棵,长在西山墙外面,每到秋天,果实累累,特别是大年,秋风吹尽黄叶后,只剩下红红的柿子,像燃烧的灯笼,一串串挂在树枝上,煞是好看。
枣树三四棵,散落在没有围墙的院子里,其中一棵大的,是我迄今见过的最大的枣树了:树干又高又粗,高过三丈,粗到两个人合围才能勉强抱住:整个树冠像一把巨伞,覆盖着大半个院子,无论刮风下雨,秋霜冬雪,年复一年地屹立在院子中间。
花椒树九棵,是当年奶奶亲手栽下的。我至今清楚地记得,这九棵花椒树,高约一丈五左右,茎枝疏生,向上斜刺,多少年如一日,在我家房子南侧的空地上站成一排,像哨兵一样,日夜守护着我们的家园。每当春天来了,带刺的枝条上就会吐出嫩芽;初夏时节,树上便开出团团鹅黄般细碎小花,大约十来天的光景,这些花就落了,随即就可以看到比米粒还小的果实;入秋后,果实由小变大,颜色由绿变红,一粒粒,一簇簇,像晴朗夜晚天空中的繁星,掩映在苍绿的叶子中间,浓烈的麻辣香味在我家院子的上空飘荡着,一直飘进大人、小孩的心里。
最多的要数李子树了,大约有二十多棵,只不过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它的学名,大伙都叫它灰(音)子树,至于为什么这么叫,就不得而知了。我曾猜测,许是果实未成熟时颜色灰暗的缘故吧。其实,这些李子树并不是我家的,只是紧挨着我家宅基地生长着,高矮一致,树干几乎一般粗细,树龄看起来有二十来年。这些李子树原是临村一个地主家的,解放后被收为公有,成为生产队集体财产。因为是果树,又长在村边儿,就需要派人专职看护。看护员是一对老夫妻,男的原是地主家的长工,懂得一些果树的技术活,所以才能得到这样一个大集体时社员们看来极好的差使。奶奶的外婆家恰是临村的,和男看护员是本家,从辈分论,奶奶应该叫人家“舅舅”,父亲叫人家“舅爷”,到了我们这一辈,当然就叫“老舅爷”了。老舅爷天生一副好身板,一米八的个子,腰板笔儿直,大嗓门,说话如洪钟,从不拖泥带水,老远就能清晰地听到。据说当年在地主家干活,几十个长工、短工里,他吃得最多,干活也最多;老舅奶一副慈眉善目的模样,见人就笑,而且和自己的男人相反,永远不会大声说话,大人、小孩儿都喜欢她、亲近她。李子园里老俩口安身的窝棚,常常是来来往往,人迹不断。李子园紧挨着我家,我是奶奶的宝贝孙子,看护员又是奶奶家的亲戚,我到果园里的机会自然比村里其他孩子就多,吃的果子当然也就多得多,以至错认为那些李子树就是我家的了。大约是在我即将上小学的时候,这些李子树就全部被生产队挖掉了,理由很简单,社会主义集体不能有副业,地里种庄稼是天经地义的事,长着果树那可不行。后来,想起这些李子树,留在我记忆里的除了那香甜的果味外,就只有老舅爷、老舅奶面对零乱倒地的李子树时悄然落泪、满脸无助的样子……
上面说到的这些树,都和奶奶有关。那时候,在我们家里,奶奶虽然是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却是名副其实的“当家人”。爷爷天生好脾气,从不和奶奶争什么“权力”,特别是爷爷过世后,奶奶理所当然地成了“大家长”,家里的大事小情一般都由她说了算,家里的一切物品也都由奶奶支配,当然也包括这些生长在自家宅基地里的树和它们结的果实了。所以说这些树是奶奶的树(李子树除外),一点也不为过。
奶奶喜欢她的儿孙们,也喜欢她的树。在我的印象中,年迈的奶奶,经常是一手捂着肚子(胃病的缘故),一手拄着木拐杖,扭着“三寸金莲”,在宅基地里转来晃去,就像是一个女王巡视着自己的领地,一会儿抬眼望望这棵树梢,一会儿低头看看那棵树根,脸上写满满足的笑意,就像看到孙儿时的模样。奶奶为什么这么爱树?她活着的时候,没有人问过,成了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命题了。但奶奶为什么会亲手栽下那九棵花椒树,我却知道原由,那是后来父亲告诉我的。
我家祖上世代为农,靠种地为生。到了爷爷这辈,日子依旧过得紧巴巴的,直到1949年解放后,我家的生活才和其他农家一样,慢慢好起来。父亲说,1950年春节刚过,奶奶便从十多里外的娘家拿回来九棵花椒树苗,在她的几个孩子的帮助下,亲手一棵棵栽在刚刚划分得到的宅基地上。奶奶说,花椒成熟后是红色的,预示着日子红红火火;之所以种九棵,取其“久久长远”之意。总之,缠着小脚的奶奶,虽然说不出更多的大道理,但内心却像任何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中国的老百姓一样,渴望过上好日子,对未来充满希望。
但我觉得奶奶喜欢花椒树,还在于它较高的使用价值。在我们北方农村,花椒是最为常见的佐料,味麻辣而持久,有了它,饭菜会变得有滋有味。每到秋天,花椒成熟变红之后,奶奶便会亲手拿起剪刀,小心翼翼地剪掉每棵树上的串串果实,一颗花椒粒也不会拉下,然后放在干净的被单上,晾晒待干,再除净枝叶杂质和黑色的种子,取其果皮,用棉布袋子装起来,以备常年之需。
奶奶是个过日子的好手,逢年过节改善生活,都少不了要亲手采来花椒叶子,或者用干花椒,放在炒菜或者面条锅里,那独特的辛麻芳香便立刻扑鼻而来。记得奶奶最拿手的菜就是花椒炝锅青菜了:那个年代物质贫乏,白菜、萝卜缨是最常见的蔬菜了,炒这些菜时,奶奶一定会投入几粒花椒,待炸至变黑时捞出,留油炒菜,菜香可口诱人。现在,生活好了,家里备用的各种调料应有尽有,但再也吃不出原来奶奶用花椒做出来的饭菜的味道了。
和其他村妇一样,奶奶在日常生活中积累了不少医疗常识,知道花椒不仅是上等的佐料,还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散寒除湿,止痛解毒。家人头疼感冒时,奶奶一定会在饭菜里多放花椒,病人吃了就会出一身大汗,病情随之减轻不少;要是有个牙疼什么的,奶奶又会拿来花椒粒,放其嘴中,用牙咬着,立马见效,等等,诸如此类。后来,我长大看书才知道,花椒富含人体必须的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确实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本草纲目》对其早有记载:“其味辛而麻,其气温而热,入肺散寒,治咳嗽,入肺防温,治风寒湿痹,水肿泻滴,入右胃补火,治阳衰。”
最让我记忆深刻的还有奶奶每每采摘花椒时哼唱的欢快小调:“姐姐窗前有棵椒,扎着馋猫汉子腰。瞪着两眼四下瞧,红的多来绿的少,绿的是叶子,红的是花椒。花椒花椒一大篮,拿回咱家好过年……”呵呵,多有情趣!
1979年农历正月初四,年还没有过完,奶奶便因病去世。就在当年,她亲手栽下的这些花椒树便不再发芽、不再开花、不再结果了,一棵棵相继干枝、枯萎,直至死去。
莫非,树和人真有相通的情脉?
三哥的心事
原以为这辈子不会再见到三哥了,没想到国庆节回老家,第一个见到的人就是他。
那天天下着小雨,当我踏着泥泞赶回村子里时,天色已近黄昏。刚走到村口,风雨中一个模糊而又熟悉的身影在前面晃动,仔细一看,是三哥!我的心不禁一颤,激动地喊了一声“三哥!”同时,加快步伐,赶到他跟前,顾不上地上溅起的泥水打湿了裤腿。
三哥闻声扭过头来,用手揉了揉眼睛,“哦,是老六啊,回来了!”“三哥,没想到进村第一个就能见到你!”我一边从外衣口袋里掏烟,一边仔细打量着眼前的三哥:苍老荒芜的脸上堆满了皱纹,一顶被雨水湿透了的破旧草帽压在头上;弯腰躬脊,前心贴后心,几近九十度;左胳膊上挎着一个竹篮子,里面装了大半篮的青菜,一把沾满泥土的镰刀放在上面;右手拄着一根没有剥皮的疙疙瘩瘩的树棍,显然是随手捡来的。
三哥用挎着篮子的左手接过我递过去的烟卷,嘿嘿一笑,算是表示谢意。他没有点燃烟卷,而是用手摸摸索索地把它夹在左耳朵上面——这是农村常见的烟民们的动作,只是三哥的这一动作比起他人来要笨拙得多,因为他一辈子只用旱烟袋抽烟。
“六弟啊,想不到还能见着老哥吧?听说‘五一’你回来看过我,还给了钱,只是那时候我躺在床上一直昏迷,不知道你来过。”三哥的声音显然有些沙哑。
“是啊,今年‘五一’节回来,听说你病得厉害,我就去家里看你,你躺着不见动静,听孩子们说已经四五天不醒人事了,不吃不喝,想着你急着要去那边见三嫂呢!”我故意轻松地说着玩笑的话,想逗他开心一点。
三哥又是嘿嘿一笑:“昏迷那阵儿,我还真见着你三嫂了,可她不让我过去,说是任务还没有完成,又把我推回阳间了。”想不到一向木讷的三哥还能说出这么幽默的话来,我便打趣道:“老家伙,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你还有什么任务要我做啊?”
“大孙子今年二十五了,还没有对象啊!”像是对我说,又像是对他自己说。然后,木然地自顾自向前晃去,和着风雨留下一路的叹息。
“操心的命,啥时候才是个完呐!”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在心里说。
我和三哥并不是亲兄弟,他是远房的堂哥,在家族里同辈份众多兄弟中,他排行老三,所以我叫他“三哥”。而实际上,三哥和我父亲是同岁的。听父亲讲,小时候上学,三哥学习很差劲,经常是“茶馆里的模范——倒查(茶)第一”。每当先生讽刺挖苦时,他总是憨憨一笑了之,从不顶嘴,过后,成绩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大家都说他是“软废物”。一直到后来,几个孩子也陆续上学了,却像他一样,一个个早早辍学回家了,割草、拾柴、做家务,下地、干活、挣工分,没有一个上到初中毕业的。要是有人好心劝说三哥让孩子继续上学时,他就会不温不火地丢过去一句:“都去当官儿,谁来抬轿?”把人噎死!心甘情愿当“轿夫”,当然就做不了“官儿”了。
俗话说“能处不在一路”,别看三哥读书不行,可人家种菜却是一把好手。当年大集体时期,我们生产队有一个四面环水的寨子,面积不大,一公顷的样子,但土质肥沃,种啥长啥,生产队五百多口人吃菜全靠它了。而三哥是当时生产队的三个“菜板儿”(对专职种菜人的称呼)之一,无论是白菜、芹菜、韭菜,还是大葱、土豆、白萝卜、红萝卜什么的,只要是我们这里适合种植的,样样在行。逢年过节,队里分菜的时候,是全队社员最高兴的时候,也是三哥等几个“菜板儿”最得意的时候,因为这时候他们听到的奉承话最多,见到的笑脸最多。试想,一个普通老百姓,还有什么比群众抬举更令其开心的事情了?也正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后来生产队划分给自家的自留地全部被三哥用来种蔬菜了,而且他种的菜色正、好吃、品种全。隔天一逢集,三哥一定会把自己种的能够上市的蔬菜用架子车(后来是自行车)拉到集市上出售,天长日久,四邻八乡赶集的老百姓都认识他,也都认他的菜。所以,三哥的菜不愁卖不出去,当别人摊位上的菜还没开市时,他早躲在小酒馆的一个角落里,用手指蘸着口水,一遍一遍数着当天的收获了,面前的酒碗里一定是最便宜的散装白酒,而且永远是二两。也正是在三哥的影响和带动下,我们村里家家户户都在自家的自留地里种植蔬菜,成了远近闻名的蔬菜村,近几年蔬菜大棚更是成了村民们的营生地儿了。
所以,我赞成三哥的“轿夫”心态,因为它源于一种实事求是的率真、平凡的境界,绝没有一点点做作的成分在里面。人生一辈子,不管做什么工作干什么活,乐在其中就行,何必宁知不可为而为之,使自己徒添烦恼呢?但是,即便如此,三哥依然有他自己的苦恼和烦心的事情,其中最令他头疼的就是儿子们的婚姻大事。
三哥和三嫂一共生育了六个孩子,三男三女,老大、老二、老五是男孩儿,其他三个是女孩儿。在农村一家有女百家求,女孩儿大了自然会有人主动找上门提亲,不愁嫁不出去。可男孩儿就不一样了,要是家境赤贫、门风不正什么的,想找到媳妇,做梦去吧。
三哥在我们农村也算是能人了,种菜卖菜虽然不能大富大贵,但毕竟带来的是活收入。只是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超越时代,加上孩子多,那些年日子过得并不比别人强,家庭生活水平在我们村里属于下等。“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因为穷,三哥性格中固有的吝啬的特点就愈发显得突出,在外人眼里一个十足的吝啬鬼形象:会种菜却吃了一辈子的干酸菜,爱抽烟却几乎不知道卷烟的味道,有酒瘾却永远只买散酒喝。对自己尚且如此,别人就更别想沾他一点点光了。听说有一次,三嫂娘家唯一的兄弟生病来他家串亲戚,想带点韭菜回去,就自己到菜园里找姐夫。谁知三哥的脸一下子阴沉下来,没搭理人家一句话,蹲在地头只顾抽自己的旱烟。小舅子自觉没趣,当即抽自己一个嘴巴,晌午头上饿着肚子步行十几里回家去了,从此就和他家断绝来往,直到三嫂去世时吊孝才又来了一次。
农村居家过日子,崇尚礼尚往来。但在三哥家,由于上述的原因,开门迎客、出门朋情的事几乎没有,他家的人缘用一句俗语讲,叫作“四面净,八面光”。加上几个儿子相貌平平,生性顽劣,书也没读成,找媳妇自然成了老大难。尤其是大儿子,个子低矮,五大三粗,尽管有一把子力气,干活是“上鞋不用锥子——真(针)中”,但有那样的“门风”,快三十岁了还一直说不上媳妇,成了“老光棍儿”。“病急乱投医”,只要有人上门提亲,三哥、三嫂一律当爷敬。因此,他家自然成了“撇子客”们(我们老家对以说媒拉纤为幌子骗吃骗喝人的称谓)的最好去处,几年下来,把他们大半辈子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大部分钱财生生给骗走了,可连儿媳妇的一根头发丝儿也没见着。为此,大儿子埋怨爹妈没本事,怄气闹情绪,躺家里不下床,甚至有时候不吃不喝好几天。三哥三嫂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求爷爷、告奶奶,人前人后没少低眉下眼说好话、哭鼻子。直到后来,在一个亲戚的说合下,以牺牲大女儿的婚姻为代价,三家转亲,算是解决了大儿子婚姻问题。那天三家同时举行婚礼,临上轿前,大女儿伤心欲绝,哭破了嗓子,发誓再也不回娘家来了。三哥三嫂觉得对不起闺女,躲在房后不敢露头,直到转亲换来的儿媳妇的轿子到了,才蹩出来招呼为数不多的客人。
三哥一辈子几乎没有什么朋友,但临村一个姓罗的却和他有过命的交情。据说还是在修焦枝铁路时,三哥和姓罗的同在一个施工队,有一次下雨塌方,把三哥压在下面,是姓罗的用手把他从泥堆里刨出来,救了一命,从此俩人成了好朋友。由于家传,罗姓朋友后来成了“巫师”,经常走村串户,装神弄鬼,三哥和三嫂都信他。听说三嫂那时候生病,没有去看医生,而是请这个“巫师”朋友来家“免费治疗”,驱鬼辟邪,结果把病情耽误了,算是还了人家一命。今年“五一”期间,我去看望病榻上的三哥,一走进他家院子,就见一个老男人,跪在地上嘴里念念有词,身边是燃烧着的香纸。这个老男人就是那个“巫师”朋友。要不是后来,村干部逼着几个孩子把他拉到县医院,三哥这条老命怕是早就像三嫂一样,还给老朋友了。不过,三哥这位“巫师”朋友也不是什么好事都没干过,除了早年救过三哥一命外,还帮三哥的二儿子解决了婚姻大事,女方是“巫师”的外甥女,和深信巫术的三哥家也算是“门当户对”了。当然,像大儿子的婚事一样,其中弯弯曲曲、反反复复的事情多了去了,花费开销几乎要把老俩口的最后一个钢蹦儿挤出来,只是没有再让其他闺女去转亲,也算是进步了。
“起五更,推磨盘,娶了媳妇起祸端。”这是三嫂的一句口头禅,没想到日后竟成谶语。就在老二媳妇娶进门不到仨月的时间,被榨干了的三嫂终于支撑不住了,生病倒下,再一个月,到她“信奉”的鬼神那里报到去了。死后多时,三嫂一直闭不上眼,直到在外打工的小儿子赶回家里。
三哥几十年如一日,像牛一样地劳作和生活,永远有忙不完的活、做不完的事、操不完的心,任凭岁月磨去脸上的光泽,重担压弯挺直的脊背,但只要有三嫂的陪伴,心里总有着落,身上总有劲头,生活总有盼头。可三嫂这一去,使本来已过花甲之年的三哥一夜之间变得更加苍老,生活的热情也被带走了。听说三嫂走的时候,三哥抱着她的遗体,哭喊着:“天啊地啊,舍不得我的箩头系啊!”围观者无不为之动容。三嫂埋葬后的第二天,三哥就搬出了原来他们共住的屋子,一个人住到村外菜园里搭起的简陋窝棚里——高矮、宽窄、大小只能容纳一个软床(竹子编成的凉床,供一人居,可以折起),无论刮风下雨,无论夏热冬冷,就和他的菜作伴,一住就是多少年,谁劝也不听,直到今年病倒不能动,才被孩子们抬回家里。
记得“农业学大寨”时期有一句流行语,叫作“住在虎头山,胸怀全天下”。三哥没有大寨人那么高的觉悟、那么大的胸怀,只是身处窝棚里、心想儿孙事,因为,儿孙在他心中永远是天。这时候,三个闺女全部出嫁,大儿子、二儿子也早已分灶另过,只有小儿子和他一起生活。小儿子的婚事便成了三哥的头等大事了,心头那沉甸甸的石头依然天天悬着。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令三哥没有想到的是,像其他人家一样,自己家的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日子越过越红火,一年更比一年好。小儿子进城务工,走南闯北,学会了拿瓦刀搞建筑的手艺。几年前,回到老家拉起一支建筑队,自己做老板,挣了不少的钱,比老父亲一辈子卖菜得来的钱不知要多上多少倍,用这些钱家里盖起了二层小楼。“没花一分钱,媳妇主动找上门来了”,这是后来三哥常在人前说的一句话,也是他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
牛老了也该歇槽。按理说,不管怎样,孩子们一个个成了家,里孙外孙一大堆,操劳了一辈子的三哥总该歇歇了吧?可他天生的操心命,儿子们的事情刚完,又开始操孙子们的心了。你说,他是不是很“贱”?
俗话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但愿大病过后,三哥能够把背了一辈子的心理负担轻轻放下,使不能承受之重的生命以一种新的方式延续,在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中安度自己的晚年。
这,也是我对天下所有老人们的美好祝愿!
豌豆多多
清晨,一阵清脆悦耳的鸟鸣声把黎明叫到我的窗前。
侧耳谛听,声音是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咕咕,咕咕,豌豆多多……”
哦,是布谷鸟儿,我久违了的朋友!
我喜欢布谷鸟儿,因为布谷鸟儿在我们豫西老家是吉祥的象征,“布谷鸟鸣,万物催醒”。
可事实上,我喜欢布谷鸟儿,却是因为我喜欢豌豆花的缘故。每到初春时节,布谷鸟都会伴随着和煦的春风不期而至,在蓝天下,在麦田里,不停地唱着:“咕咕,咕咕,豌豆多多……”听着这欢快的歌声,小麦发黄了,豌豆花开了,我也慢慢长大了。
小时候,我最喜欢的花就是豌豆花了。史书记载:“其苗柔弱宛宛,故得豌名。”豌豆属一年生或越年生攀援性草本,是一种粮食、蔬菜、饲料兼用作物:干豌豆子含大量的蛋白质,具有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可用作主食。我们老家有用豌豆粉制成粉丝和凉粉的传统,均属同类食品中的上品;豌豆苗、嫩梢和嫩荚富含蛋白质、胡萝卜素,均是优质蔬菜;籽粒和豆秸为优质饲料,可喂耕牛。因为豌豆和麦子的生长期大致相同,所以在我们老家,人们又叫它又麦豆。
记得那时候,我们老家种植豌豆特别多。豌豆开花一般在3、4月份,那时的气候春暖乍寒。豌豆花实在是太普通了,在我们老家的田野里随处可见,就连它的花香也是淡淡的,不像牡丹、梅花、荷花那样高贵,可人们却是那样地喜爱它。除了豌豆花能够孕育出人们需要的实物外,主要原因是欣赏它那洁身自好的品格:豌豆属自花传粉,而且它的自花授粉是一种严格的自交,不等到花瓣张开,雄蕊上的花粉就落到雌蕊的柱头上,完成了授粉作业,花瓣裹得很严实,不让别的一朵花的花粉有侵入的机会。豌豆通过这种严格的自交传种接代,各种不同品种都能保持自己的独特形状,成为纯种。这和几千年来人们追求的忠贞的爱情和婚姻观是一致的。
当然,这些知识小时侯我并非真懂,只是偶尔听大人谈起,懵懵懂懂知道一点。我喜欢豌豆花,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有漂亮的花朵。你看,每到豌豆花开时节,广阔的田野里到处是雪白的、粉红的、淡紫的花瓣,像一只只蝴蝶,五彩斑斓,美丽动人,在暖风中笑得你挨我、我挤你地摇摆着,引得你不由不去亲近她。蜜蜂来了,蝴蝶来了,小朋友也来了。这时,我们小孩总爱三个一堆、五个一群,结伴到豌豆地里玩耍,闻香捉碟,好不惬意。
喜欢豌豆花的另一个原因,说出来不怕大家笑,就是能够满足像我一样的孩子们的“偷食”欲望。豌豆花开之后,便慢慢长出豆荚来,由小到大,由薄变厚,由青转绿,到了六、七成熟,就可以食用了。豌豆一般是和小麦一起套种的:外面是高高的麦秧子,里面是低矮的豌豆苗。农民伯伯们这样套种的一个目的就是让麦秧挡住视线,以防止像我这样的小孩儿去偷摘豌豆荚。但实际上这也为孩子们作“小偷”起到了隐蔽作用,因为有高高的麦秧子作掩护,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在里面捡那些饱哼哼、甜丝丝的豌豆荚摘食了:先开膛破肚,吃了里面鲜嫩可口的豌豆籽,再剥去豆荚外面的一层薄薄的丝皮,厚实的肉皮便又可大快朵颐了。不过,食用豌豆荚也得掌握好时机,太早了,糖分没下来,不甜;太晚了,皮老籽硬,味同嚼蜡,难以下咽。
但是,“常在河边走,不怕不湿鞋”。偷食豌豆荚也有失手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我们同村的几个小伙伴,午饭后便向家人说要去上学,大人们还高兴得不得了,说我们懂事,知道自觉学习了。其实,一背过大人脸,我们几个撒丫子跑到河西的豌豆地里,去摘豌豆荚了。
哇,这片地里的豌豆荚可真喜欢人,长得又大、又饱,又鲜、又嫩。我们忘了是刚刚吃过饭,一顿痛快淋漓的采食,个个肚皮儿滚瓜溜圆。
“好啊,小崽子们,敢偷队里的品种豌豆,欠揍!”突然,一阵凶神恶煞般的吼叫从不远处传来,吓得我们浑身哆嗦。扭头一看,原来是生产队护青(就是看庄稼)的李老三,手里拿着桑叉,正向我们跑过来。这个李老三,听说抗美援朝时到朝鲜打过仗,脑子负过伤,脾气有点“二蛋”,退伍回到老家后一直找不到老婆,重活也干不了,所以,生产队让他作护青员。这倒是人尽其才,他不仅六亲不认,而且干活从不计较报酬,大人小孩都对他敬而远之。平时,小孩子不听话,大人就吓唬说:“李老三来了”!孩子便立马变得乖乖的。这要是让他逮住,那还有个好?我们几个吓得站在原地不会动,过了一会儿,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快跑啊!”大家这才如梦初醒,四北五下乱跑,跑得慢的,只恨刚才吃的豌豆荚太多!
因为李老三刚刚崴了脚,所以他并没有真的追我们。虽然逃脱了李老三之手,但他还是把我们告到了学校和家里。老师罚我们几个在太阳底下整整站了一下午,回到家里,又免不了挨大人一顿揍。可不管怎么说,只要没落到李老三手里,那就算是我们的运气了!
我们是有运气的,可有人却没这份运气了。那个年代,天天讲阶级斗争,我们这偏远的农村也不例外。如果出身不好,那你就只能老老实实干活,规规矩矩做事,不能出半点差错。可邻村里的郭龙昌家却犯了忌。他家是富农成分,平时谨小慎微,从没有做过出格的事情,邻里口碑一直不错。可是有一年夏,他家7岁的小姑娘雪梅在豌豆地里薅草时,误薅了几棵豌豆秧,被人告发到大队。大队干部便上纲上线,给扣上“破坏社会主义青苗”的大帽子,那还了得?按当时的规定,要游街。因为雪梅太小,父亲就得抵罪。郭龙昌头上带着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着一个硬纸牌,上面写着“富农破坏分子”几个大字,左手拎着一面破铜锣,右手拿着锣锤,走几步,打一通:“哐!哐!哐!”嘴里还要大声喊:“我叫郭龙昌,我是富农分子,破坏社会主义青苗,我罪该万死!”7岁的雪梅则低着头,跟在父亲后面,身上背着那几棵豌豆秧。他们父女二人,在整个大队整整游了三圈,当然身后有民兵押解着。雪梅那时上小学二年级,是我的同班同学。当他们经过我们小学时,大家都出来看热闹。我清楚的看见雪梅满脸都是泪花!老师、同学,还有我,都忍不住哭了。
20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成为永远也挥之不去的阴影。也就是这件事以后,我再也没有去偷过豌豆荚了。
我也永远忘不了1987年那个遍地金黄的夏季。经过十年寒窗,在豌豆收获季节里,在布谷鸟儿的歌声里,我义无返顾地走进了高考考场……
后来,我上了大学,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故乡,来到了这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男女老幼比肩接踵的繁华的都市。多少年来,尽管每年都要回乡省亲,却都是来去匆匆,似乎再也没有见到过豌豆花开了,再也没有听到过布谷鸟儿唱歌了。
而今,“豌豆多多……”这熟悉的歌声伴着黎明一起来了,令人太欣喜了!此时此刻,我感觉,晨光,是如此明媚;气息是如此清新;窗外的无花果叶子是如此的深绿迷人。我真想对着窗外的天空,大声喊:布谷鸟儿,我心中永远忘不了的朋友!豌豆花儿,我心中永远最美丽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