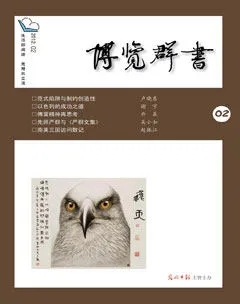古体诗词有可能再现繁荣
当今时代,文化艺术呈现多种样式,使得大众的文化需求有多种选择。在诸多的文学形式中,诗词不再是文人必须掌握的,也不是最时髦和最有冲击力的。然而,我认为诗词很有可能出现新的繁荣和普及。虽然不是独领风骚,但也是传统与现代谐和、风流独具的角色。
诗词当随时代
“笔墨当随时代”,一种文学艺术样式有无生命力和能否为大众接受,在于能否反映时代生活。诗词亦当如此。
1955年台湾诗人节,于右任就说,诗词“一、发扬时代的精神,二、便利大众的欣赏。盖违乎时代者必被时代抛弃,远乎大众者必被大众冷落……此时之诗,非少数者悠闲之文艺,而应为大众立心立命之文艺”。其实,诗词与时代、大众紧密相连,是一切开明的前瞻的文化工作者和诗人的共识与共同追求。一部文学史或诗词史,实际上也是在时代不断演进中适应时代的历史。
我们看到,在世纪交接的时代,作为传统文化精粹的中华诗词,经历复苏,走向复兴和初见繁荣。深厚的传统和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令诗词展现出空前的活力和时代精神。在创作题材和内容方面,国际国内大事、社会生活、个人经历、艰苦磨难、日常情趣、旅游咏物、田园风光、哲思感悟、朋友酬答、内心独白、相思爱情……纷纷入诗,各具风采。
近年来,每逢大事、节庆、纪念日都有大批诗作产生。在纪念香港回归诗词大赛中,贺苏老人“七月珠还日,百年雪耻时。老夫今有幸,不写示儿诗”的五绝,短短20字,形象、深沉、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沧桑老人对香港回归的喜悦;还有,一些反映农民和基层的诗作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吕子房的“浪淘沙·巴山背哥”写道:小子走巴山,踏遍渝川。背星背月背朝天。呵嗬一声忙拄地,仰首岩悬。日夜顶风寒,脚破鞋穿。为儿为母为家园。苦命二哥背不尽,背起人间。写小人物的环境艰窘和拼命生活,画面生动,跃然纸上。
爱情是诗歌的永恒主题。红豆大奖赛一首获奖诗“南国春风路几千,骊歌声里柳含烟;夕阳一点如红豆,已把相思写满天”,形象、概括、洗炼,有很高的美学价值,是公认的佳句。
反映社会各层面的作品如生活本身一样色彩斑斓。请看一则“打工老汉·鹧鸪天”的叙述:
幼女辍学卖豆芽,老父打工走天涯。日背砖块汗如雨,夜宿工棚霜似花。
停烟酒,不喝茶,分分积攒寄娇娃。偶闲也作登楼望,万户千灯不是家。
短短数语,包含相当大的信息量:农村孩子辍学,贫困,进城打工,城乡差别,民工情绪等,表现得生动、真切、委婉、深刻,且娓娓道来,怨而不怒,把握得体。
再如李申写“双枪老太塑像”,“远离战火久。事理乱成堆,老太双枪在,不知该打谁”,反映了时间推移、社会变迁中观念的碰撞和演变。亦庄亦谐!而一首“送儿出国”题材的五绝,更道出天下父母的心声:“叮咛千百遍,默默理征衣。天下爹娘愿,盼飞还盼归。”
重要的是,诗人们没有放下批判谕讽的传统武器。《中华诗词》的“刺玫瑰”专栏,就以专门发表讽刺诗博得各界好评。一则“下马石”:独立皇陵侧,端居孔庙前。干官皆下马,一石冷无言;一则《读西游记》:一路西天遭劫灾,百般请得救兵来。神仙摆下玩猴阵,那个妖精没后台!或冷峻机警,或诙谐深刻,各有千秋。
此外,关于哲思和感悟心路历程的诗句,也时见光芒,如宋晓梧的佛魔:魔为偏执佛,佛是端正魔。细数千秋史,佛魔一纸隔!哲思、彻悟于平白之间。
总之,孔夫子说的“兴观群怨”的功能于当代诗词都有表现,且更见广泛、深刻。由此表现了中华诗词深伟的蕴力和活力。
有了时代精神。诗词可能繁荣
构成诗词时代精神的要素,大略是三个方面。
一是相当的数量与质量。当代诗词同历史上的诗词高峰相比,究竟怎么样呢?首先,诗词尤其是词,以毛泽东为代表,呈现一大高峰。当代诗人聂绀弩、刘征等的创新与作品,庶几与过去的高峰比肩。出现了一批具有新的意象、新的视角、新的语言、新的哲思的好诗词、诗句,如珠似玉。如刘征(水调歌头·中秋赏月)“我谓月,且欢笑,勿神伤。管它阴晴圆缺,只当捉迷藏”的豁达奇语、(卜算子)“且莫叹荆榛,毕竟多芳草。检点人间万古愁,一点丁丁小”的哲思、彻悟……
总之,对于当代诗词的基本估计是,数量绝对超过以往;精品亦有相当篇章。当然,当代的大家、名家不及以往那样耀眼,精品的比例尚远不如唐宋。下大力气提高质量多出精品,是首要任务。
二是显著的特色优势。精短、典雅、押韵、上口,便于记忆,易于流传,诗词原有的这些优势,在快节奏的当今环境中充分展现,更能契合社会氛围和大众需求,显示着蕴力、魅力、耐力。我们不妨做个比较。关于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首名篇,茅盾1923年译本是:
我一生最宝贵:恋爱与自由。为了恋爱的原故,生命可以舍去;
但为了自由的原故,我将欢欢喜喜地把恋爱舍去!
而殷夫1929年的译本是:
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同一作品,都是名家。由于形式不同,效果和社会影响显然不同。
优势在诗词方面。
三是空前的社会支撑。从实践论的角度看,大众的认同和流传,是检验文化艺术包括新诗旧诗重要乃至唯一的标准。
如果要问。当今,什么文化艺术形式离我们最近、接触最早?答案是诗词。以儿童普遍学习“鹅,鹅,鹅”和“床前明月光”为例,孩子的父母和祖父母、外祖父母等,无疑要对此有最简单和基本的接触。特别是,随着社会成员文化水准的普遍提高,更多的人(全国以百万计)接触、了解和喜爱诗词并且提笔写作。这种认同和普及,使得诗词获得前所未有的社会支撑,具有广阔的复兴和繁荣前景。
诗词的流行或传诵,有赖于内在质量和外部环境的契合。
当今社会环境对诗词的影响表现为两重性,一方面,社会发展有利于诗词复兴;一方面,文化的丰富多样约束和限制了诗词的独尊。
封建社会,诗词长期处于尊贵地位。科举考试必有诗词,清朝甚至明确由皇家钦定用韵。兼之诗词形式短小精悍,概括力强,有韵律,易传播,没有其他艺术形式与之匹敌、并列,使之成为独领风骚的艺术形式。
当今时代,文化艺术呈现多种样式,且平面媒体和电视广播以及网络的兴起,使得社会大众的文化需求有多项选择。在诸多文学形式中,诗词不再是文人必须掌握的,不是最时髦和最有视觉冲击力的。精品佳句不少,流行传唱不多。然而,我经过分辨、思考发现,诗词能够融入社会而不被排斥,很可能出现新的繁荣和普及。虽然不再是独领风骚,但也是传统和现代谐和、风流独具的角色!
总之,与时俱进,继承创新,求正容变,众多社会成员参与,大批量较高水准的作品反映丰富多彩的时代生活,就是诗词的时代精神。
如何医治“盛世诗病”
时代与大众,普及与提高,继承与创新,复兴与复古,是当代诗词面临的主要课题,亦有误区和偏颇。我以为突出的是两个方面。一是脱离现实,盲目复古。有一种主张,回避社会,远离大众,完全置身于个人天地,自我陶醉,对社会一概采取冷漠置疑排斥和批判态度,甚至提出“回到唐宋”的口号。
其实,历史上任何成功的复兴或复古都是改革,而不是倒退、回到原来。清代叶燮指出:“诗词正变几千年,盛衰之所以然。”诗词同其他文学艺术一样,不可能回到唐宋,不可能脱离现实生活。
另外,就是故弄玄虚,生僻艰深。别人看不明白,自己说不清楚。
无疑,民众了解、广泛流传的当然是通俗晓畅的作品。艰难用典,佶屈聱牙,何以欣赏?“细数流传千古句,皆从平白语中来。”
二是标语口号,盛世诗病。
如今国泰民安,节庆多。有关节庆和纪念题材的诗,易将事件和政策术语人诗,易生豪言壮语,搬用标语口号和套话,成为“伟大的空话”,姑且称作“盛世诗病”。政论可以如此,报告可以如此,外交辞令可以如此,但诗词则断不可以如此。毛泽东早就说过,“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遗憾的是,当前这类作品较多,甚至包括一些大赛中获奖的作品。
如何解决诗词较为突出和普遍的问题?从写作的角度是大处着眼、细部着手。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方是功夫,更是古来诗人成功的要诀之一。
诗词的美妙和感染力得之于细节的描写。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写初春;刘禹锡“朱鹊桥边野草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写变迁;辛弃疾“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写春夜;尤其是孟郊的“游子吟”,以细线、寸草寄情,以“密密缝”写母爱,朴实真挚,深刻动人,千百年来为人们喜爱。
毛泽东的词作,小到“忆秦娥·娄山关”的“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大到“沁园春·雪”,其中不曾有“革命”、“红军”等政治词语,但其间饱含着浓烈的革命和光明的内涵,是用艺术形象而不是用概念说话。就写诗而言,立意高、气魄大和具体描写非但不矛盾,反而是依赖于具体、鲜活的描写。如获建党90周年大奖赛一等奖的徐绪明的“鹧鸪天”:合是梅花清秀姿,生来不怕雪霜欺。一从亮相南湖后,九十年来放愈奇。勤管理,莫松弛,务防虫蛀干和枝。植根大地春长驻,花俏花香无尽时。作品以梅花喻党,着力细节描绘,摆脱大话套话,得奖理所当然。
诚然,我们不排除豪言壮语和大气魄,而是要大得有理、适度,有奇思妙语。主要着力点是描细节,塑形象,用艺术的形象的语言写诗。
需要指出的是,诗词创作与其说具有理论的品格,不如说更具实践的品格。诗人成功的要义在实践。融入时代,重在磨练,终究还是以作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