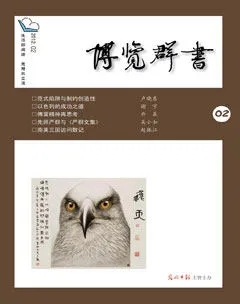傅雷精神再思考
傅雷从少年时代起就受到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后来留学法国,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亦为他所熟悉。在受西方影响的同时,他也强调儒家与老庄思想中的安于平静,洒脱高蹈等的性灵特征。他认为“富贵不能淫”是为人处事的最高境界。
“虐待”孩子的傅雷把艺术看得比生命更重
1954年1月17日晚,20岁的傅聪登上北上的列车,将从北京再赴波兰参加第五届萧邦国际钢琴比赛,并留在那里学习。父亲傅雷从次日开始,就连续写了两三封信给儿子,在诉说离别之苦同时,几乎都是自责、忏悔、道歉的话。他说:“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就是在家里,对你和你妈妈做了不少有亏良心的事。”这是《傅雷家书》第一、二封信中的主要内容。很难想象,教子有方的傅雷怎么可能会虐待天才的儿子呢?
傅雷的检讨是指他对傅聪日常教育过于严苛,甚至有时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包括一年前为了艺术见解不同父子间发生严重的冲突等。他的暴烈和固执,在亲友中间也是有名的。他的挚友楼适夷亲眼看到孩子们在傅雷面前怎样“小心翼翼,不敢有所任性”,说他的“严格施教,我总觉得是有些‘残酷’”。(《傅雷家书·代序》)另一位挚友柯灵也说他“对许多事情要求严格而偏激”。(《柯灵散文选集》P107、108,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黄苗子说他“性格急躁”、“性急言直”。(《洁白的丰碑——傅雷百年纪念·序》,北京图书出版社2008年版)他的夫人朱梅馥更是为此“精神上受折磨”,说他“主观固执”,“他一贯的秉性乖戾……”如果仅从这些评语来看,傅雷不只是一位严父,甚至似乎有点专制家长的味道。
但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他的坏脾气是有原因的,甚至是有道理的。楼适夷说看到的是“为儿子呕心沥血所留下的斑斑血痕”。柯灵说:他执拗,但他“耿直”;固执,但“骨子里是通情达理的”。朱梅馥说:他“嫉恶如仇”,“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因此,对他的“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
这是亲人、挚友对傅雷的深深的理解。他们从他的固执中,“发现它内在的一腔热情……具有火一般的爱心……”(黄苗子:《怀念傅雷》)从他的“桀骜不驯”,他的“宁折不弯”,看到他的个性中“构成一种强烈的色彩”,那是属于傅雷所特有的色彩。
傅雷夫妇给傅聪的信中,几次谈到他们父子性格相似之处。爸爸说:“你我秉性都过敏,容易紧张。而且凡是热情的人多半流于执着,有狂热倾向。”妈妈说:“你的主观、固执看来与爸爸不相上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父子的狂热和执拗很多时候竟都是在于对艺术美、性灵自然和自由的痴心追求。
傅雷说:“我始终认为弄学问也好,弄艺术也好,顶要紧是human(人),要把一个‘人’尽量发展……”又说:“艺术家最需要的,除了理智以外,还有一个‘爱’字!所谓赤子之心,不但指纯洁无邪,指清新,而且还指爱!……热烈的、真诚的、洁白的、高尚的、如火如荼的、忘我的爱。”
他们经常探讨音乐,从这些伟大的音乐家身上,寻找到了与他们内心最契合的精魂和神髓。贝多芬的力量和意志,与命运搏斗的非凡的气势,歌唱每个人的痛苦和欢乐,晚年趋于恬淡宁静的自由境界,尤为傅雷父子所喜爱;萧邦的感伤温柔和忧郁似乎是有一种“非人世的”气息,具有浓郁的诗意和神韵。舒伯特则与沉思默想、遗世独立的哲思相融汇。这一切都使他们如醉似痴地倾心其间。
在绘画中,傅雷最欣赏的是希腊雕塑、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19世纪的风景画。吸引他的正是其中的自然之美。这种自然美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许多诗歌是相通相似的。傅聪说他身在异乡,“精神上的养料就是诗了。还是那个李白,那个热情澎湃的李白。……念他的诗,我会想到祖国,想到出生我的祖国”。
傅雷特别喜爱《世说新语》,就是欣赏魏晋文人的风流文采,追求独来独往、自由自在。他推崇《人间词话》,因为王国维倡导“境界说”,认为境界为最上,自成高格。诗歌艺术有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优秀诗人都应有“赤子之心”,即有真性情,血肉铸成,甚至“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这正是自然之美的极致了。他对于黄宾虹的画给予极高评价,就因为黄主张“尚法变法及师古人不若师造化云云,实千古不灭之理……”中西艺术“亦莫不由师自然而昌大,师古人而凌夷……倘无性灵,无修养,即无情操,无个性可言”。
所以傅雷希冀傅聪成为把艺术看得比生命更重的艺术家,保持独立的人格,性灵的自由,才有真性情和新的独创。音乐本来就是抽象、空灵、飘忽的艺术,更视追求自由甚于一切。他“热切期望未来的中国音乐应该是这样一个境界”。傅聪则说:“人能够有自由幻想的天地,艺术家是不能缺少这一点的……”从傅雷父子的审美情趣和艺术理念深深感受到他们对自由和自然本真的渴望和强烈的追求;他们个性中的“固执”与对艺术美的执拗和痴情常常是浑成一体的。
种好自己的小园子
关于傅雷的译著,翻译家罗新璋认为:“从译笔来看,似乎可分为四九年前后两个时期。”他是从语文翻译水平以及翻译风格变化等着眼的。鄙意认为,如从个人创作心态而论,就如罗新璋论述傅雷在1949年前写的文艺评论特点是:“张扬生命主义、力的哲学与激情主题,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论说精辟,予入耳目一新之感。”文风是“踔厉风发”。(《江声浩荡话傅雷》P193、255、256,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傅雷的翻译也有类似特点,前后期的变化也是很值得玩味的。分期的时限似可稍推迟到50年代初。他的前期最重要的代表性译作应是罗曼·罗兰的三大伟人传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他读这些著作时,“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此实余性灵生活中大事”。所以他曾说,他的译著中“自问最能传神的是罗曼·罗兰”。就是说,那时他从事翻译没有功利目的,没有外在因素,完全是因为与自己的思想性情相吻合,借泽作宣泄内心的激情和喜爱,希冀与读者分享精神上的冲击和收获。这是白由选择的结果,选择的是追求“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这样的工作状态在50年代初终于有了变化。
从此,傅雷翻译工作受到社会诸多的制约:一是出版社的制约:译著选题要听从出版社的计划,连印数、发行、版式设计等都得由出版方决定。书店里已经买不到傅雷的译著,出版社不再印,译者毫无办法。其次,意识形态的制约,如《约翰·克利斯朵夫》在反右中被指责对青年思想起毒害作用,后来就不再重印。巴尔扎克的作品因为是马克思、恩格斯等赞赏的,所以出版社要傅雷继续新译,后来傅雷觉得不宜多译,其实也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问题的。再次,还有一个实际问题即经济来源受到制约。1949年后,各色人等成了公家人吃“皇粮”,唯有极个别的如傅雷等,没有归属某个单位领取固定工资,完全靠稿费收入为生,更谈不到什么医疗住房等的福利保障。他还想像过去那样做一个自由职业者。但是,出版社是清一色官办的,只要不出他的书,他的生计就成了问题。
更关键的是,傅雷从内心深切感受到社会环境对自己的思想、精神和生存的束缚。这对一个把追求自由、自然和艺术美视为生命的人来说是极痛苦和难以忍受的。但这种痛苦和压抑又不能与人明说,连对妻儿都不便轻易透露。我们只能从他不经意处或实在压抑得不吐不快的时候泄露出来的点滴就足以感受到他的苦闷了。1950年6月他致黄宾虹信中说:“方今诸子百家皆遭罢黜,笔墨生涯更易致祸,栗栗危悚,不知何以自处……”那种惶惑不安的情绪再明显不过了。十数年后,他终于感叹说这个社会“可是十年种的果,已有积重难返之势;而中老年知识分子的意志消沉的情形,尚无改变迹象……”他从当时戏曲改编和演出的混乱情况,竟无人提出异议和批评一例,“可知文艺家还是噤若寒蝉,没办法做到百家争鸣”。尽管他与社会已经疏离很久,但他的观察却是相当准确。四年后,“文革”爆发,证明了他的预言不舛。
所以,他的后期翻译工作一方面不能像年轻时完全按照自己的激情和想法自由选择进行;另一方面他又托庇于相对中性的(也是当政者能够接受的)自己喜欢的如巴尔扎克、丹纳等著作的翻译工作,包括倾情于书法、摄影、养花、欣赏音乐等来安顿自己的灵魂,遨游于艺术美的世界里。他说:“我所以能坚守阵地,耕种自己的小园子,也有我特殊的优越条件……”
对于这样复杂矛盾的生活环境,他是非常清醒的。他说:“我们从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辈,多少是怀疑主义者……可是怀疑主义者又是现社会的思想敌人,怪不得我无论怎样也改造不了多少……”怀疑主义是现代哲学的起点,即理性主义的出发点,就是对什么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包括对上帝都会有质疑;就是独立思考不盲从现成的结论,坚持自由的思想,对真理追根究底。1932年他就说过:“自由思想与怀疑这两种精神,在所谓‘左倾’或某个阶级独裁的拥护者目中,自然地被严厉地指斥,谓为‘不革命’与‘反动’……无异是宗教上的异端邪说……”正是这个社会最不能容忍的。20年后,他仍还坚持声称不想退却即改造(变)自己。这样,他的“小园子”也很快就被打得粉碎了!
“三无”的自由职业者
“三无”指无文凭、无单位、无党派。
傅雷多次强调自己是五四精神培育起来的,他借议论法国学术界喻示自己属于“在恶劣的形势之下,有骨头,有勇气,能坚持的人,仍旧能撑持下来”。
人们习惯概括五四精神是科学与民主。如果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皇权,争取政治自由的权利;那么五四运动则是反对专制礼教文化、争取思想自由的革命。那时各种新思想广泛传播,差异虽多,但几乎都呼唤自由,追求人性的尊严和个人力量。18世纪美国政治家帕特里克·亨利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是许多年轻知识分子表示自己决心时爱用的话,文艺作品也常引用宣扬这种精神。后来殷夫翻译的裴多菲的诗:“爱情诚可贵,生命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也是被广泛传诵为人熟知。无疑,争取思想精神文化信仰的自由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为人们所争取。
傅雷是从少年时代起,就受五四运动新思潮影响成长起来的。后来在法国留学,自由、平等、博爱等当然是他熟悉的。傅雷早期翻译过莫罗阿的《服尔德(伏尔泰)传》。傅雷的“小园子”比喻就是从伏尔泰那里引用过来的。伏尔泰在小说《老实人》中曾说,不管世界如何疯狂和残酷,“种咱们的园地要紧”。据杨绛先生说:傅雷曾把自己比喻为“墙洞里的小老鼠”,也是从传记作者比喻伏尔泰为“躲在窟中的野兔”脱胎而来的。伏尔泰就是远离宫廷教会等所在的权力中心巴黎,避居在日内瓦湖附近的法尔奈20年,自由地写了大量重要著作。傅雷曾说伏尔泰作品中描写的那种境界,影响他对现实多少带着超然的态度。凡此可见影响之大。至于受罗曼·罗兰等的思想熏陶,更是人们所熟知的了。傅雷热爱自由的思想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
傅雷的自由也还表现在对待学校教育上。他自幼除接受家教外,曾上过两个小学,两个中学,一个大学,每个学校都只读过半年一载,或因“顽劣”,或因“言论激烈”,或因参加学生运动等,被开除或转校。后又留学法国四年。如此经历十多年的学校教育却始终没有领得一张文凭。这绝不是说他学习不好,而是他有意无意对这些世俗规矩并不在意。当他为人之父后,有一段时间,他就不让傅聪上学校受教育,而是留在家里亲自选材教课。他对文凭、分数、学位一类并不重视,认为这类东西作为谋生手段未始不好,“但绝不能作为衡量学问的标识,世界上没有学位而真有学问的人不在少数,有了很好听的学位而并无实学的人也有的是”。人们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学识渊博中外文化学养深厚的大学问家竟然没有一张文凭和一个学位。
傅雷一生从事固定的社会职业时间极少,总共大概没有超过三年。他在上海美专、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等二三处也都只工作了一年半载,因和同事相处不合而辞去。他几乎没有参加什么政治文化团体活动。他曾参与发起中国民主促进会不久就退出,后来有朋友再三劝说动员回民盟或民促并许以“高官”之称,他都以自己脾气急躁,缺少涵养为由坚决辞谢。五六年后开始因政治气氛松动活跃,他听了毛泽东鼓动鸣放的讲话十分感动深信不疑,再加中共文艺界领导的固请,当了两年上海政协委员和两三个月的上海作协书记。但是他的不合时宜的个性和思想,与一般委员代表们不同的是:不是不投反对票不提批评意见不说上面不爱听的话,只以代表或委员的身份为荣誉,说些歌功颂德的空话套话(他对此有强烈的不满);相反的是放下手里的译著,停工脱产,无偿地(如今称义工)从事调查收集民意的工作,写了十几份详细充实的关于出版、音乐、翻译以至农业方面的意见、建议或调查报告,里面讲的都是问题、不足和建设性的主张,他满怀希望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帮助政府做些有益于改进知识分子工作的事,结果“忙得不可开交”,却落得一顶右派帽子,受到莫名的打击和批判。这次参与社会活动给他带来的伤害是难以估量的,又一次证明他那种特立独行、讲真话的自由精神是不适应世俗社会中虚与委蛇的生活的。
忧时忧国与人生如寄
傅雷只能在书斋里,做一个自由职业者,种好自己的“小园子”。这绝不意味是逃避;相反的是坚守在学术文化的岗位,继续创造美的世界,是清醒地自觉地保持知识分子的尊严和人格,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承续。如陶渊明不愿“心为形役”,“委屈而累己”(《陶渊明集》,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P135、158),就是这样的精神。所以,当老友楼适夷写信责备他用心于书法是“逃避现实”时,傅雷很生气回答:他研究书法是为“探学吾国书法发展演变与书法之美学根据,并与绘画史作比较研究,对整个文化史有进一步的看法”,绝非是为雕虫小技旷时废日。至于对于现实社会,“弟虽身在江湖,忧时忧国之心未敢后人;看我与世相隔,实则风雨鸡鸣,政策时事,息息相通,并未脱离实际……”只不过不愿放弃独立思考、自由思想而已。
傅雷早年受西方思想影响同时,就强调儒家与老庄思想中的安于平静,洒脱高蹈等的性灵特征。他说:“我始终是中国儒家忠实的门徒。”儒家思想当然是入世的,积极的。但是,他最看重的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正气和节操,这与现在那些把《论语》说成“心灵鸡汤”的浅薄之说大不一样。他更认为第一句话“富贵不能淫”最难做到。陶渊明的“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样的文化传统在傅雷心中是生了根的。所以他叮嘱傅聪不要奔走在权贵之门,认为这点傲气是中国艺术家应有的传统美德。他自己被打成右派时总不肯低头;上面摘掉他右派帽子视为恩赐,他却淡然轻蔑地说我本没错。40年代为亲苏还是亲美之争,他发表了超越党派偏见的公道话遭到左派的狂攻他也不在乎。无论政治上打击,还是生活艰难,他都保持尊严不屈服。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应该承续张扬的气节。想到当年和今日社会都有一些所谓学者专家大师沉迷于蜗角虚名,乐于做权力的臣仆,金钱的婢女,奔波献媚于二者,说一些违背科学事实专业的话来站台当托,真是斯文扫地,与傅雷精神相比判若云泥。
傅雷的性格和思想追求与世俗社会完全相悖,所以他总要碰钉子。这是他的悲剧。从社会来说,不能容纳善待这样一位杰出耿直的作家学者,则是荒谬和耻辱。但是,傅雷思想精神的深刻还在于他对这样的悲剧的超越和升华。就是说,他把艺术、美、真理都看成比生命更重要,更可贵;但他又非常清醒地认识到真正达到完美的艺术境界,完美的世界是不可能的(包括他对自己的译著经过多少次用心重译还是不满意),除非到了“上帝”那里才有可能。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仍然一往直前,积极地痴迷地执着地追求不止,总想尽可能离完美更近一些。他有时幻想自己像伏尔泰小说里描写的那样,好像活在另一个星球,来看眼前这个星球上的一切,感到失笑,茫然。总是世俗社会不理解不容他,他就只好构筑他的“小园子”,那里有翻译、音乐、书法、贝多芬、李白、《世说新语》……
一方面,他热爱生活,热爱生命,恋念人生,为现实世界创造新的精神文化积累。他在没有任何外来逼迫委派任务的情况下,尽管身体多病,仍然坚持每天八小时工作,甚至更长时间。即使风和日暖,草长莺飞,他也不舍得离开书桌去放松片刻,说:“要做的事,要读的书实在太多了!”工作对他成了一种激情,一种狂热。外界的事物也仍然会不断吸引、影响着他,发生强烈的波动和反应,“忧时忧国不能自已”。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转眼之间随时可以撒手而去,飘然远行。他自认中国读书人的气质太重,看人生一世不过“白驹过隙”,人的生命“格外渺小”,因此而“超然物外”,“洒脱高蹈”。还说,哪怕自己喜欢的东西,不过是“社会暂寄在我处的,是我向社会暂借的”。古诗就有“人生忽如寄”之说(《昭明文选》卷第二十九)。这样的情绪和思想,他对儿子以及别的亲友都曾许多次流露说及。
傅雷从中西文化着重吸取的是中正和平、清明高远的精神。就如贝多芬的搏斗的人生和大勇主义精神曾给他震撼,但后期他却更接受贝晚年的恬淡安详。人们熟知他深受罗曼·罗兰影响,其实他接受伏尔泰的言行生平思想影响更在潜移默化中。他受中国文化中老庄哲学、佛教教理的影响也都不亚于儒家思想。这不等于他没有苦闷和烦恼,也不是不曾想过要适应这个信仰的时代。但他无法强使自己屈从,而是选择了佛教教理中以智慧达到自然而然的醒悟,化解成活泼生机的力量和健康超脱的心情;认为信仰更易使人沦为偏执和狂热。这样他的精神升华了,超越了任何束缚和羁绊,无论生还是死,他都能豁达洒脱,进入到一个自由的境界。傅聪也说过:“我父亲认为人有自己的选择,有最终的自由去选择死亡……”(《江声浩荡话傅雷》P51)这时,我们对他最后的殉难可能有了新的悟解:尽管是在那个疯狂邪恶的年代发生的悲剧,是那样惨痛恐怖;但想到他生前多年的思考和遗书,他却以异常平静、从容和庄严的气概走向炼狱,几乎像是涅槃。这正是傅雷精神特有的色彩——一个视人生如寄、襟怀坦白、挚爱艺术美的赤子,一个追求自由、坚持独立思考、坚守气节和操守的文化英雄。他和这个世俗社会那么不合调,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但又是那么热情真诚想把自己所有的思想艺术创造传达给别人,造福人类,是我们这个世界引以为骄傲的长者、文化巨匠。
我们缅怀前贤,想到他们用生命换来的进步时,除了感恩,还更应想到责任;现实世界缺少的前辈那样可贵的精神应该重生,把薪火传递下去!
注: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傅雷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