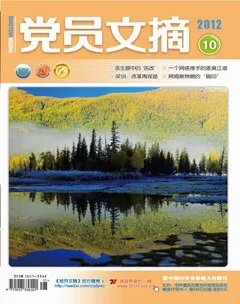深圳:改革再探路
深圳为全国“先行先试”,这里孕育了市场观念最初的种子,并向外输送改革成功的经验以及制度创新的样本。如今,当市场经济的框架在中国确立后,深圳的历史使命是否已终结?
我们通过考察今天的深圳,得出的结论是:NO!
市场经济的框架虽然早已在深圳建立,但其细节仍需继续锤炼,相应的配套改革更需完善。仅有框架而没有细节的制度是靠不住的。市场经济改革30余年,容易改的基本上都已完成,剩下的都是“硬骨头”。
随着新的社会格局形成,改革重心日益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文化、政治领域。深圳已经不仅仅是经济特区,更是综合配套改革的试验区。这也意味着,在社会、文化、政治领域,它依然肩负着“先行先试”的使命,需要在更广阔的改革层面为中国探路。
全国在发展,深圳怎么办
在即将迎来30岁生日的时候,深圳需要交一份答卷。
提问者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2010年,他参加广东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深圳团分组讨论时给深圳人出了三道题:过去30年深圳立起了什么?迎接特区成立30周年深圳能做什么?未来30年深圳再干什么?
“随着扩大开放,深圳的地缘优势不那么突出了,政策优势也几乎没有了,那么我们还靠什么?”汪洋说。
深圳并不是第一次面对这个问题。
1992年,当这个城市还作为全国学习的明星时,《光明日报》头版刊发题为《全国在发展,深圳怎么办?》的文章,深圳本地媒体以《深圳还能再领风骚吗》为题全文转发,引发一场讨论。
人们反应最热烈的话题之一是,在讲求时间与效率的特区,竟然出现了这种现象:深圳一个高科技项目从提出可行性报告到竣工投产,要经过13个部门审批,递交15个报告,收取30多项费用,盖54个公章,用时最少1年。
一些企业不满意深圳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迁到东莞这样地价、人工便宜的地方,深圳一时间出现了大量的空置厂房。
对于这座城市来说,更具有危机感的一个信号或许是1998年3月特区办撤并到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有人悲观地将这一举措解读为:虽然深圳仍以特区立身,但在中央政府实际的决策体系中,已经没有它的位置了。
最终给深圳人“一闷棍”的,是一个名叫呙中校的28岁年轻人。这个来自湖北的小伙子在互联网上发表了一篇1.8万字的长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彻底戳痛了深圳人的心。
这个改革试验场
还有没有新东西
对于汪洋的提问,深圳市委书记王荣的回答是,继续履行先行先试的历史使命。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曾在一篇文章中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如果说‘特区不特’了,那就是你自己放弃了‘特’,这如同深圳只可能被自己抛弃是一个道理……如果说前30年是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后面的改革则是要关注市场经济的细节。”
市场经济的细节指的正是综合配套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改了30年,难度小的都改完了,剩下那些‘硬骨头’,不是经济本身的事情。”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所所长杨立勋说。
2005年,深圳开始向国务院提出申请“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经济特区相比,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改革范围更加全面,包含经济、文化、政治等多个方面,又被称为“新特区”。直到2009年,《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终于获得国务院通过,深圳成为全国第五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拿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把“尚方宝剑”后,深圳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行政体制改革,一下砍掉15个局,按照政府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实行委、局、办并行的行政运行机制,几个月内完成挂牌。
深圳仍被寄希望于破冰全国层面的改革。2009年,民政部与深圳市政府签订“部市合作协议”,鼓励深圳探索建立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的制度。
在此背景下,被称为“没有身份证的孩子”的壹基金,最终落户深圳。要做教育界“蛇口”的南方科技大学也选择了深圳。
从权力走向权利
在杨立勋眼中,近几年,深圳经济发展的速度放缓了,社会层面的改革却提速了。
遇到内地干部来深圳学习,这位社会学领域的学者喜欢趁机给他们上上“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堂课。他觉得,一些省市如今还像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那样,“饥不择食,全民招商”,政府介入到经济活动中,却没有履行好服务型政府的职能。
“不要重蹈我们80年代的覆辙,只看到GDP,结果政府该做的事情反而没有做。”他毫不客气地对台下的“学生”这样说。
事实上,深圳也是经历了高速发展和改革焦虑后,才摸索到了政府的边界。1997年,它挥起第一刀,开始“革自己的命”。四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后,窗口式办文在深圳政府部门广泛推行。一位记者在深圳市民中心行政服务大厅记录下这样一幕:一字排开的“行政超市”里,一家外贸公司负责税务办理的人直奔税务柜台,半个小时搞定所有手续。
“以前去政府办事比陪老婆逛街还累,至少陪老婆逛街只需要在华强北或东门,一条街逛完拉倒。但要跑手续,就要跑多个部门,要盖的公章一大堆,而且不在一起,腿都跑断了。”说到这里,杨立勋仍然忍不住直摇头。
正是通过这四次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一些政府部门官员才真正清楚自己的管辖范围,以及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该管的怎么管。某部门审批人员说:“过去我们总把审批看成一种权和利,抓住不放,批不批由我说了算,较少考虑审批责任和义务。”
在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任周为民看来,这种权力与权利的区分,正是今天的深圳应该为全国提供的种子,“今天的中国最需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在全社会树立起权利的观念”。
一次,一位网民在深圳市人大法治办公布的立法草案中某一条款的最后一个角落里,发现“累计缴费年限满××年退休方可不再缴费享受医保待遇”中的数字从15变成了25。他的这个发现引发了网上大范围的讨论。社保局领导为此很苦恼,他们找到某门户网站的工作人员,“每天都有人骂,你们帮我们整理整理意见”。
“深圳是民间力量比较发达的一个城市。”深圳市改革办主任乐正说,“深圳市民公共意识非常强,特别是在网络上,议政、问政、评政,市民批评监督政府已经成为一种自觉的生活方式。”这些权利意识的汇集,正在促成深圳公民社会逐步形成。
深圳再出发
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深圳,如今追求的不再是单维度的GDP增长,而是每万人病床数和职业医生数、每千户籍老人机构养老床位数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甚至还包括人均公共图书馆藏量这种“小事”。
2011年8月15日,胡锦涛主席在深圳考察时,饶有兴致地走到一台自助借书机前,说要借一本跟深圳有关的书。随后,他在屏幕上轻点两下,一本名叫《深圳之路》的书很快从自助借书机里吐了出来。在深圳,这样的便民借书机有160台。这个在全国率先实施“文化立市”战略的城市,把享受文化视为市民的一种文化权利。
“深圳经济特区肩负起中央赋予的新使命,不仅要带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且要在社会建设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这句话,被写入深圳市政府的文件。
2010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考察深圳。温家宝说:“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在深圳,这样的政治文明土壤已经出现。按照规定,一个深圳外来务工者,只要在辖区内居住满一年就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管有没有户口。2004年,深圳福田区选举人大代表时,出现了四位毛遂自荐的非正式候选人,其中一位名叫王亮的深圳高级技工学校校长最后意外地高票当选。在其他选区,有贴海报为自己造势的,有向选民发公开信的,还有一位候选人在《南方都市报》上以10700元刊登广告,为其12条涉及“建立公平社保、打破管道煤气垄断、降低出租车起步价”等建议内容寻找“婆家”。
这个城市现在已有35万名注册义工。每年,深圳市政府向他们购买服务。“深圳已经完成了从运动式的志愿者团队到固定化的、专业化的志愿者服务队伍的转变。”深圳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说。
深圳人总喜欢讲述袁庚与四分钱的传奇,那是属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鼓声。再过30年,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会不会是深圳的一个普通义工,或者一位高票当选人大代表的非正式候选人?
(胡世民、王景义、邱宝珊荐自2012年8月1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