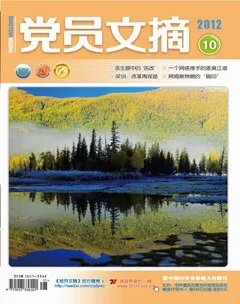医生眼中的“医改”
编者按:医改无疑是中国老百姓目前最关注的话题之一。经过三年攻坚,这项关乎每个人的改革进入深水区。在这个关口,医生的努力和配合显得至关重要。诚如卫生部部长陈竺所言,中国要想破解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离不开数百万医生的理解和支持。
然而,在过去三年中,医生多数时候更愿意沉默以对。即便是在允许多点执业等“利好”措施面前,他们也显得有些被动消极。唯有在受到舆论指责和误解时,他们才愤而疾呼、痛陈心曲。
百姓眼中“看病贵”,医生认为贵在哪儿
讲述者:北京同仁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杨建林
医改正在积跬步。其中,“看病贵”是当前百姓印象中的医疗沉疴之一。有媒体统计,2011年中国住院人均花费6632元,相当于农民一年的收入。
但在抱怨背后,你是否了解“看病贵”究竟贵在哪里?
在北京同仁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杨建林眼中,“看病贵”主要不是贵在挂号和诊疗上,而是贵在手术耗材和进口药品上。
“普通病人的看病流程都差不多,基本上是挂号—诊疗—手术—买药等步骤。在这个过程中,挂号费不应该是导致看病贵的主要原因。”他指出,“挂号费再高,也不会高到让患者承担不起的程度。”
既然如此,为何有医院的专家号卖出“天价”?杨建林认为,有需求才有“黄牛”市场,而一部分患者没必要非得找专家看病不可。另外,一些医院试图以调高专家号来避免医疗资源被浪费,抬升了“看病贵”。
杨建林告诉记者,医护人力成本也不高,手术耗材的成本却高,好一点的进口耗材价格更高。“我国的医疗设备和耗材使用不统一,各地医院采用的耗材都不一样。医保不能报销医疗设备和耗材费用,患者若自费负担,很容易导致一部分人无法承受”。
在杨建林看来,药品也是造成“看病贵”的一方面,尤其在不需要做手术的诊疗中,它占了大头。“一些常用药、普通药,比如吡哌酸等是很经济实惠的,但在很多医院已经买不到了”。杨建林感觉,从2000年开始,药品开始越来越重包装、轻质量,过度包装背后是药品价格的翻番。
而新一轮医改的一大亮点,就是在公立医院中推行基本药物“零差价”制度,即不再让被医院加价的15%助推老百姓的看病负担。
目前,该制度已在山东、陕西、安徽等全国多个县(市、区)的基层医院试点,效果不错。据媒体公开报道,在一些基层医院,百姓购药价普遍比大医院便宜了30%。
杨建林所在的北京同仁医院,也是试点医院之一。在他看来,药品“零差价”可以解决一部分“看病贵”问题,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医药费用高的主要因素,不在于末端的这15%,而在于药企和中间环节”。
据杨建林介绍,药企的逐利特性和臃肿的中间环节正在“逆向淘汰”一些经济实惠的药品,药品“零差价”与它相比是小头。“同一种药,牌子越来越多、包装越来越精,效果不一定好,几元一瓶的药已经很难找到了”。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每种药品从研发、生产到上市,都要经历生产商、采购商和经销商等环节。在定价部门、招标部门、医院药事委员会面前,一家药企要在“同伴竞争”中脱颖而出,经常要以高额投入来“打通”这些环节。有的投入,甚至能占到药品出厂价的十几倍。而最终这些中间花销,肯定要由患者埋单。
“按病种付费”破了大处方,能保证“疗效好”吗
讲述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核医学科主任医师 李春林
从去年8月1日起,“按病种付费”已悄然取代“按项目付费”,在北京六家医院开始试点。这个旨在控制“大处方”、“过度医疗”的医保支付方式,被卫生部部长陈竺形象地比喻为给病人“吃套餐”。
“套餐”怎么吃?
通俗地讲,就是把108个常见病种“打包”,根据病人的年龄、疾病诊断、合并症、并发症、治疗方式、病症严重程度以及疗效等多种因素,分成若干组,每组确定一个报销“上限”。同组的病人从入院到治好出院,治疗费用不能超过这个“上限”,否则由医院“埋单”。
既然定了“上限”4/Mq2Xtt11Wjsvvcj/7ddEog0Pyw2PgaXU3gutNgNu4=,是否会牺牲患者的治疗效果?李春林所在的医院,为了“扬长避短”,采用的是DRG诊疗规范化路径管理,即把治疗一种病的标准化诊疗规范全部列出来,按标准化流程走,不能更改或省略,以保证每位病人“该做的检查、治疗项目,一个都不少”。但此举在他看来,又过于机械。
“像做汉堡包一样,两片面包的中间,是先夹肉还是先夹生菜?顺序不能变。一旦变了,要在电脑上一一填写变了什么,为什么变,很繁琐,加重了医生的负担”。李春林的一位在北大人民医院的同行也表示,“更重要的是,看病不是这么机械化的,流程上写着第三天换药,但病人吸收很快,第二天就需要换药;流程上写着用一个注射器,结果用了两个注射器;再加上很多并发症是难以预测的,这样试图用一个框子来‘框住’花费,能适应千差万别的病人和千变万化的突发情况吗?”并且,“上限”设置后,如果费用不足以使用先进技术,这时医生就会采取保守治疗方案,对患者不利。
权衡以上利弊,李春林认为目前按病种付费还不足以完全代替按项目付费。“如果要实施这一方案并根治‘看病贵’,第一步就是全面、高水平地落实医保”。
“三甲”医院该用来治疗,基层医院该用来养病
讲述者:北京积水潭医院骨科住院医生 李毅(化名)
医改专家早已提出,“看病难”现象说到底,是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造成的。大医院有好医生、好设备,这在根本上决定了患者“宁愿协和蹲一天,不愿回县医院”。相应地,大医院的医疗资源被浪费,小医院的医疗资源却没用上。
但在北京积水潭医院骨科医生李毅看来,原则上,“三甲”医院应该只负责治疗,不负责养病,养病更多应该是县级医院、社区医院的事。
一所医院的医疗器械数量和专家人数是有限的,大家都等着专家看病,实质上是患者与患者间在争抢医疗资源,在抢医生。小病占去了专家的一大部分时间,他能留给真正需要的患者的时间,就被大大压缩了。
据卫生部《2011年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用是81.5元,住院病人人均医药费用是2315.1元,住院病人日均医药费用是228.1元;二级医院的这三项费用分别是147.6元、4564.2元、489.0元;三级医院则是231.8元、10935.9元、912.0元。
此外,在基本社区医疗服务中,采用中药、针灸、火罐、刮痧等手段来处理康复问题,往往“物美价廉”。在李毅看来,在基层医院养病,对患者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国医改“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争取到2015年,实现“大病不出县”。
怎么做到这一点?
李毅认为,首先必须提高基层医护人员的专业水平。只有专业水平能满足病人的需要时,才会有更多患者到社区医院、县级医院就诊。其次,政府要加大投入力度,提高基层医生的待遇。待遇是引进人才的重要保障,人才是提高医疗水平的重要前提。
医生“多点执业”,很多条件不成熟
讲述者: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 朱同玉
所谓“多点执业”,是让好医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到县级医院甚至社区医院里定期坐诊。按照设想,此举既能让老百姓节省路费,在家门口看上病,也能提高好医生的收入,缓解医疗资源配置不均的现状。
但在医生群体眼里,“多点执业”现实吗?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朱同玉告诉记者,至少在他们医院,目前还没有医生尝试“多点执业”。“个别去其他医院做手术的情况,也仅仅限于朋友邀请,正式开始‘多点执业’的相关条件还在探索中。”他说。
在朱同玉看来,相关条件至少包括:执业医生的工资怎么算?是否要在这个医院注册?社保怎么办?人事编制到底属于哪里?
“此外,单位领导怕耽误本职工作,发生医疗事故如何分担责任等一系列问题,都亟待解决。”朱同玉说,“其中,最大的困难是人事编制问题,它决定了社保的办理,医生的待遇等,并且能针对一旦出现的医疗事故,作出正确的责任分担。”
此外,县级、社区医院的设备是否合适,也是朱同玉担心的难题。他说:“很多大型手术是需要高级的医疗平台和设备的,这样的设备只有大医院有。社区医院、县级医院的设备缺陷,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治疗结果,甚至导致医生‘下去了’也无法开展工作。”
在朱同玉看来,真正的“多点执业”范围应该更广,不仅是允许医生下到县级、社区医院中,还可以跨城市、跨大小医院。“医生以后应该成为一个‘自由人’,像律师一样开展工作”。而要实现这些,必须在医生编制方面建立相应的制度。
对于如何缓解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的问题,医改专家一直在探讨。在朱同玉看来,虽然“多点执业”可以缓解这种现象,但治标不治本,要想真正解决问题,还有待“健康守门人”——家庭医生制度在国家层面建立。
由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导致的“看病难”,困扰着很多患者,短期内又难以扭转。而在欧美国家,由于实行预约就诊制,患者除非急诊,否则要在预约之后才能来医院找医生。在预约时段内,医生“如约守候”,为患者提供专属服务。
此举一可保证患者的时间不被无谓的等待“耗掉”,二能让医生提前对患者的病例“做功课”,保证治疗效果,被一些人视作我国医改可供借鉴的方向。
但在朱同玉副院长看来,欧美国家能够实行预约就医制的前提,是完善的家庭医生制,“而当前,我国缺乏这个配套制度的支撑。”他举例告诉记者,“家庭医生是全科医生,常见病、多发病甚至妇产科和小儿科,都属于他们的服务范围。如果家庭医生认为有必要,才会建议病人‘转诊’到专科医院,并出具转诊单。病人取得转诊单之后,一般才能给专科医院打电话预约就诊。”
舆论环境苛刻加剧医生流失
讲述者:天津某三甲医院住院医生 钱江(化名)
频发的“伤医”案不仅令一些医生心寒,也导致不少医学生不愿从医。一项媒体调查显示,八成医生表示不愿让后代从医,未来的优秀医生可能正在“流失”。
在天津某三甲医院的年轻医生钱江看来,职业悲观情绪在他身边的同事和实习学生中比例非常高。
谈起当下的医患关系,钱江认为,医患关系紧张不是单方面的原因。“我承认,确实有一部分医生的工作态度和方法有问题,但多数医生主要是因为工作负荷量太大”。
在钱江看来,另一个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是老百姓对医生的收入存在误解。
“医生这一行,对专业素质的要求非常高,并且所需的学历越来越高。多数医院都要求医生有硕士、博士学历,尤其是三甲医院。从医学院毕业到真正开始工作,即独立值班、管病人,我们都在三十一二岁以后。”钱江这样向记者解释。
“在天津,我刚工作时的工资也就2000元左右。高收入的医生,差不多都是45岁以上的年龄了。”他说,“比较而言,其他行业可能本科毕业就能去工作,干到30多岁,或许已经是中层,收入可观。医生的投入和产出,在很大程度上不成正比。这也是我和我身边的同事,不愿让自己的后代从医的原因之一。”
钱江认为医生的流失现在还显现不出来,但十年后,恐怕医护行业的人才流失会让人震惊。“那时就不是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了,是没有人看病了,花多少钱也没有医生看病了”。
要解决医护人才流失问题,钱江认为,国家加大投入是首要的。“公立医院既然有个‘公’字,就应该具有公益性质,由国家出面扶持,而不是医院去追逐利润。现在,国家对医疗方面的投入偏低,医院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以药养医’”。
“舆论环境也很重要。现在很多人质疑医生、为难医生,一大原因是公众不了解这个行业,而个别媒体的‘挑动’、‘渲染’,又造成医生形象下降。”钱江说,“我觉得医患关系整体上是好的。在最容易形成‘医患冲突’的急诊室,我遇到的绝大多数人都明辨是非。其实到了医院,病人对医生的尊重与依赖是很明显的。个别不通情理的人肯定有,但各行各业都会遇到这样的人,几率差不多。只是医患矛盾被渲染得多了,让人特别注意了其中‘冲突’的一面。”
(摘自2012年8月24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