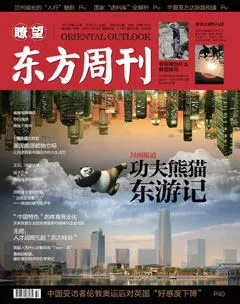鲁朗的秘密:藏东南生物多样性考察记
2012-12-29 00:00:00彭茜
瞭望东方周刊 2012年32期

在林芝的鲁朗地區,有着藏东南最好的原始森林。这片自然秘境广泛分布着青藏高原特有的植物、昆虫、鸟兽,还有世代栖息于此的工布藏族
从拉萨沿318国道一路往东至林芝地區,沿途是低矮灌丛、高山草甸到蓊郁森林的景致变换。植被愈丰,空气渐润。不时有骑行川藏线的驴友和运送物资的卡车经过。
翻过海拔5012米的米拉山口,便是林芝地界。尼洋河从山口发源,绵延309公里汇入雅鲁藏布江。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水汽通道效应在米拉山已是强弩之末,雨水大部分降到了米拉山以东,造就了藏东南的林涛花海。
据统计,藏东一林芝地區林地面积达374万公顷,森林面积264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46.09%,是我国第三大林區,也是我国保护最完整的原始森林之一。
在林芝的鲁朗地區,有着藏东南最好的原始森林。这片自然秘境广泛分布着青藏高原特有的植物、昆虫、鸟兽,还有世代栖,息于此的工布藏族(工布是林芝地區的古称)。
2012年7月,一项针对鲁朗地區生物多样性的科学考察展开。来自“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IBE)”的生态摄影师和公益机构“西藏生物影像调查(TBIS)”的科考人员历时半个多月,从海拔4500米的德木拉山口行至海拔3000多米的东久沟,徒步穿越考察了鲁朗五寨花海,以影像的方式记录了鲁朗特有和珍稀濒危物种的分布范围、生态习性,以及这块土地上的人类生活。
“希望此次拍摄和考察能给当地保护區、林业局一些有益的建议,更希望通过这种视觉化方式把鲜活的自然之美展现给公众。”此次科考队队长、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IBE)负责人徐健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在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副所长杨永平看来,过去,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多停留在科学家和政府层面,缺乏生动的表述,而这次科考以影像记录的形式让科学走出象牙塔,使大众可以感受到科学家的研究之美,有利于生态保护事业的持续发展。
植物:“侠女”绿绒蒿及其他
“乱抹鎏黄染对山,孤芳桀骜扯裙蓝eqhterl3JFW/uH12MKO99dW/kr5CLZFqdvEuyfM3tN4=,杜鹃碎梦限风寒。急雨常聆新叶语,垂虹喜妒彩花妍,流云奇色舞阑珊。”
这阙暗含塔黄、绿绒蒿、高山杜鹃等高原植物名称的《浣溪沙•到鲁朗拜峰台》,是生态摄影师王辰的即兴之作。从海拔4500米的德木拉山口拜峰台一路下行至海拔3500米的鲁朗花海,适应不同海拔生长的各种奇异植物让这位痴迷传统文化的植物学硕士诗兴大发。
这一路,几乎涵盖了北半球的所有气候带和植被类型,是高山生态研究的典型山區。海拔梯度的剧烈变化提供了藏东南生物多样性的完整序列,因此成为此次鲁朗科考的主要路线之一。
拜峰台是高山草甸地带,空气稀薄,终年气温寒冷。雅鲁藏布大峡谷的通道效应使大片水汽一波波向山口涌来。云雾飘渺中三座白塔矗立,经幡翻飞,这是藏族在高山垭口处祭祀神灵的传统。低矮处则是灰背杜鹃的海洋,紫色的小花若隐若现。
王辰一眼便在碎石和灌丛间发现一株傲然挺立的蓝色花朵——似多刺绿绒蒿,是林芝地區的特有物种。
这种绿绒蒿往往生长在海拔4000米以上,蓝色的丝绸质地的花瓣挂满雨滴,身披褐色的小刺。在王辰眼中,这正是金庸小说里“青衫磊落险峰行”的侠女。
“藏地相传有绿绒蒿生长之地,流出的水清澈圣洁,喝了能医病。”王辰说。
垭口处高山草甸两侧的山坡是流石的汇聚。大块岩石被风霜雨雪侵蚀成碎块,石块从陡峭的山体滑落,形成流石滩。灰色的碎石堆中玉树临风般挺立着数十株亮黄色塔形植物,多有一人多高,基部叶片很大,向上渐小。这就是分布在藏东南的高山植物一塔黄,其醒目的外形是为满足高海拔地带吸引昆虫传粉之需。
“塔黄因为形态独特,在当地被称为‘山神的礼物’,即便要食用它时,(人们)也会留下柱头部分。”王辰边说边用相机记录拍下周边环境和塔黄的植株细节。
沿着遍布落石和倒木的小道继续下行,海拔4000米处出现一大片高山杜鹃灌丛,拳头大小的淡粉色花朵在雨中顾盼生姿,面积和密集程度之大让王辰惊叹不已。
海拔3800米附近则是林芝云杉和冷杉的海洋。
海拔陡降500米,来到接近山脚处的鲁朗花海。这里曾是一片森林,由于人类上百年来的放牧活动,逐渐演变成一片开阔的林间亚高山草甸。
盛夏时节的鲁朗百花盛开,黄色的杂色钟报春垂着铃铛般的脑袋,覆盖了大片草甸。紫色的金脉鸢尾也成群地生长,还有散落在草地中的马先蒿、金丝桃等花儿作为点缀。
“与雅鲁藏布大峡谷各种物种基因的交流汇集不同,各个物种在鲁朗变得很稳定,典型物种变成了优势种群,形成了大片的植物群落。”王辰说。这种植物群落构成的景观为以后发展生态旅游提供了契机。
本次科考共拍摄了200多种高等植物。高原四大花卉之中的三种:报春花、杜鹃花、绿绒蒿均被记录。
拍鸟:相机就是我们的枪
为了更方便地记录山地垂直带的动植物,科考队在海拔4500米的拜峰台扎营,夜宿于此。
垭口受水汽通道影响,气候变化极快,一场倏忽而至的地形雨让队员们纷纷躲进帐篷,吃起牦牛肉和土豆炒制的路餐,却迟迟未见鸟类摄影师郭亮归队。
毕业于北大生物系的郭亮是IBE的核心成员,师从著名动物学家、大熊猫研究专家潘文石。保护區的鸟类是他的拍摄主题。
科考队员们戏称郭亮为“特种兵”,因为他总是身着迷彩服,背着600ram的“大炮筒’迷彩镜头,在清晨或傍晚出去“打鸟”,他那本枕边书《中国鸟类野外手册》已被翻得破烂。
雨停之时,众人才见郭亮满身挂着水珠走进帐篷,难掩脸上的兴奋:“终于拍到了黑胸歌鸲!”
黑胸歌鸲是分布于西藏东南部的一种高山鸟类,夏季栖于亚高山林至林线以上的灌丛和矮树丛。因为其上体全灰,眉纹白,腹部雪白,被称为“乌云盖雪”。此鸟喉部还有一抹宝石红,叫声婉转,优雅可爱。
“7月是鸟类育雏的季节,黑胸歌鸲习惯把巢筑在垭口处的灌丛下。”郭亮说,他用望远镜确定了它的活动范围后,便在十多米外静静蹲守。
守了两个多小时后,骤雨初停。黑胸歌鸲跳上灌丛晾晒羽毛,郭亮抓拍了一张特写。
在垭口的灌丛中,郭亮还偶遇一个蓝额红尾鸲的巢,里面还有四枚小小的鸟蛋。但是他只看了一眼便匆匆离开。
“在鸟类的繁殖季节要特别注意,不能刻意寻找它们的巢,如果被鸟儿发现有人类干扰过它们的巢,就会弃巢而去。”郭亮说。
海拔越高,鸟类的繁殖季节就越晚。高海拔的鸟类还在孵化,低海拔的小鸟已经可以随着鸟妈妈出去觅食了。除了垭口处的灌丛,鲁朗广袤的原始森林由于较少受到人类活动干扰,为鸟类栖息提供了极好的生境。
每日,郭亮都扛着“大炮筒”沿山路而下,如独行侠般避开众人去找鸟。在他看来,对该區域鸟类的搜寻要多次重复同一条线路,直至发现鸟类的数量经历一个倒‘U’型曲线的变化,才是对生物多样性的科学记录。
靠听声辨位和目力搜寻,他又记录到了黑鹎、白颈鸫、灰腹噪鹛、白眉朱雀等多种林中鸟类,它们翱翔于天际或伫立枝头的瞬间都被定格在相机中。
“涉及鸟类的生物多样性调查曾经或用气枪、或用粘网捕鸟鉴定。如今相机就是我们的枪,先记录下鸟儿的美丽,让公众喜爱,然后再慢慢渗透保护的意识。”郭亮说。在此次科考中,他共拍摄到60多种鸟类,其中有藏马鸡、四川雉鹑等国家级重点保护动物。
“微观之美”:昆虫记
这片原始森林也是昆虫的乐土。
科研结果显示,藏东南山地自第四纪以来有过多次冰期,但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水汽通道使得很多低海拔區域成为昆虫的天然避难所。在林芝地區的墨脱、波密、林芝、米林四个县及周边區域,有20目206科1985种昆虫;昆虫科目主要集中在鳞翅目、同翅目、鞘翅目和膜翅目,占总科数的56.31%。
鲁朗林海中有很多横生的倒木。揭开树皮上厚重的苔藓,就会发现一个微观王国:腐木上生活着大量的植食性昆虫,同时还栖息着很多它们的天敌。
生态摄影师雷波是位发现“微观之美”的高手,带上100mm的百微镜头和自制闪光灯,他记录下了50多种昆虫图片,昆虫的复眼、腿脚绒毛、翅膀上的纹路都纤毫毕现,极具质感。
“除了相机,不带走任何东西。”这是他一直遵循的生态摄影原则。在生态环境极为脆弱的青藏高原,不采标本、带回拍摄产生的垃圾都是对当地环境的保护。
一次拍摄过程中,由于昆虫爬行太快而无法拍出细节。一旁的协作急了,一把抓过虫子,放在雷波面前让他拍摄。
雷波连连摆手,在他看来,“每个角落都有漂亮的场景,需要发现自然的美,而不是通过人为去布景”。
“物种的多样性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拍摄题材,自然总带给你无法想象的惊喜,仅仅是那些变幻莫测的自然光线就值得你研究七八年。”雷波说。
遗憾的是,科考队此次没有拍摄记录到兽类。
“冬秋季节拍到大型动物的可能性更大,夏季它们会躲到海拔更高的地方。”科考队长徐健说。考察地离公路和人类居住區相对较近也是一方面原因。
鲁朗的人:工布藏族
对于世代生活在鲁朗林海的工布藏族人来说,“靠山吃山”是从祖辈沿袭至今的习惯。
千百年来,当地人都有狩猎的习俗,林中的獐子、熊、血雉、野山羊都是猎手们的枪下之物。彼时进入林中总要十二分小心,因为不经意间就会遇上猎手设下的陷阱或猎夹。
如今,禁猎令实施17年后,尚能从家家户户保存的弓箭中觅得当年狩猎的痕迹。只不过当年的“射猎之箭”已经变成了“竞技之箭”。流传千年的“工布响箭”——圆锥形的木制箭头上有多个小孔,射出后会因气流作用发出尖锐的哨声——已成为当地节庆时的一项竞技活动。
有趣的是,越来越多的工布人家开始持有韩国产的弓箭,制作精良的专业弓箭可以帮助他们在射箭竞技中取得佳绩。
1998年,西藏自治區政府对林區全面实施禁伐,昔日以贩卖木材为生的“木头财政”也开始淡出藏东林區。曾经的猎手成了今日的护林员。当地农牧民组成护林队,每日背着干粮上山巡逻,阻止乱砍滥伐、盗猎等行为,消除森林火灾隐患。
山脚下的工布藏族村落,多就地取材,以木石结构搭建居所。由于气候湿润多雨,这里的建筑与西藏其他地區的民居不同,多是尖顶,利于排水。尖屋顶之下即为通风的储藏室。曾经这里堆满动物毛皮、干肉和擦得锃亮的猎枪,如今则多成为晾晒藏药材的场所。
工布藏族人正以另一种方式获取这片山林的馈赠——采集林下资源。
几乎每个工布藏族人心中都有份采药月历:五月采野草莓根,六七月采绿绒蒿、手掌参,八月采红景天、桃儿七。
在鲁朗镇东巴才村,科考队员们遇到了20岁的藏族姑娘达娃卓玛。她刚刚参加完高考,暑假几乎都是在山林里度过的。
早晨9点,她开着摩托车载着妈妈上山挖手掌参。这种长相酷似手掌的参类既可入药,也是制作鲁朗美食“石锅鸡”的主料。她们用小锄头从地里挖出根部,装满一袋,晚上八点才归家。
对达娃卓玛来说,绿绒蒿、红景天相对更易采集,直接连根拔起后晒干,然后等待拉萨藏药厂一年一度的收购。
一场大雨过后,鲁朗广袤的林海中青冈菌、大脚菇、松茸等菌类纷纷露头。达娃卓玛的奶奶总会在此时提着口袋出现在林中。她认得五种食用菌,捡回的蘑菇一部分被她熬制成鲜美的菌汤,一部分被达娃卓玛的妹妹拿到南迦巴瓦峰观景台卖给游客。
对于这样的一户家庭来说,除了以放牧和农耕维持生计,采集藏药材和菌类是补贴家用的重要手段。尽管一天辛劳换来的是看起来并不丰厚的收入:松萝一斤卖5元,绿绒蒿一斤20元,红景天一斤30元,菌类一斤50至60元。
东巴才村和邻近的五个村子几乎家家采药,曾在东巴才村当了22年村长的达瓦正在担心一些不恰当的采集方式将给当地生态带来危害。在他的记忆里,祖辈采集绿绒蒿等植物时只砍去地上部分,而保留地下的根茎使其继续生长。如今,村里人多采用连根拔除的采集方式。
“高海拔植物年生长量很低,不像水稻一年一季。‘斩草除根’的采集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副所长杨永平对本刊记者说。
鲁朗的原始森林中有着多达1046种的植物,达瓦说,必须尽快找到保护它们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