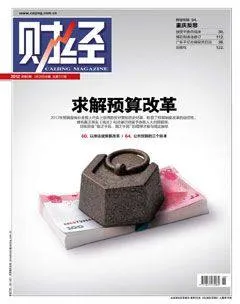亚洲银行模式的未来
这周是去年12月的洪水之后,我第一次访问曼谷。这个城市似乎已恢复,经济正在好转。
国际金融研究所(IIF)测算,2011年泰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0.1%,并预测2012年将有7%强劲的增长复苏,这得益于一项多年期的财政刺激方案,预计将使2011/2012年度的财政赤字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5%。这一财政刺激计划包括从4月起最低工资标准上调40%,企业所得税率从当前 30%大幅削减至23%,在2013年将进一步降至 20%。这将使泰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更接近周围国家。
曼谷之行的目的是就亚洲银行商业模式的未来进行探讨。核心问题是使亚洲的储蓄在亚洲内部循环使用。由于其人口形态和保守的消费习惯,东亚国家的经常项目通常是净盈余,不断积累的储蓄大部分投放在了发达国家市场。为什么不能把其中的部分储蓄用于资助东亚内部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
2003年,迈克尔·杜利(Michael Dooley)、戴维·福尔克茨-兰多(David Folkerts-Landau)和彼得·加伯(Peter Garber)将当前这种跨太平洋的平衡命名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II),亚洲将储蓄再投资到发达国家市场,弥补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这一平衡也被称为“双赢大买卖”(Grand Bargain)。实际上,亚洲是用青年劳动力的工作和自然资源的开发来换美元。双赢大买卖即将结束,因为亚洲人意识到,他们持有的美元可能面临未来贬值的风险,且亚洲的劳动人口及天然资源不应该永远廉价下去。
双赢大买卖对发达国家的银行业务模式造成了影响。逆差国家很快发现,其银行体系的贷存比高达100%以上,因为过度消费必须由信贷提供支持。亚洲的平均贷存比低于100%,因为储蓄高于负债。
美国的银行体系不得不从零售银行转到批发银行体系,依靠资产(按揭和贷款)证券化并向全球市场销售来为其贷款融资。相当多被包装成AAA级的证券最终被欧洲人购买了,因为谨慎的亚洲人大多坚持购买美国国债。因此,在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时,欧洲银行是比美国更大的受害者之一。
美国和欧洲的银行演变成由衍生品市场强劲推动的杠杆型批发银行,确有其道理。因为20世纪80年代,在日本银行的竞争下,它们的净息差业务(即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之差)变得更少且难以赢利。
从传统零售银行业务转移出来的另一原因是,自由市场理论认为应通过降低交易成本 (如交易税和佣金)将市场摩擦减小到零。在过去,经纪人通过丰厚的佣金挣钱,他们愿意为客户提供好的投资研究。当进入息差接近于零的电脑化交易时代后,证券公司必须从事更多的自营交易和杠杆交易才能赚钱。高质量的研究变得稀缺。通过向零售投资者兜售衍生产品,银行可以从预付费用及杠杆交易向客户发放的信贷中赚更多的钱。
自营交易和杠杆化的衍生金融工程,使银行业务从一个实体部门的信托代理人演变为一个可能从事违背客户利益的交易竞争者或委托人。金融部门成了一个为自己谋利的委托人,其总资产远远超过了实体部门,因此“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
因为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陷入赤字,银行体系没有偏离其零售银行业务的根基。经历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后,对于是否允许亚洲银行走衍生品路线,亚洲监管机构已变得更为谨慎。
随着竞争的加剧,亚洲的息差也开始受到挤压,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一些亚洲银行向客户销售不恰当的财富管理产品,其对客户适用性的忽视已受到强烈谴责。因此,亚洲银行是否应更多从资本市场业务赢利,也是当前争论的问题之一。
这就提出了当前全球监管改革没有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指出“如果金融工程师挣的钱远远超过了环保工程师的收入,我们是先实现绿色经济还是泡沫经济呢?”同样,如果要让银行更好地为他们的实体部门客户服务,什么样的政策能激励他们更多地通过实体客户服务而不是杠杆式自营交易来赚钱?
这意味着,监管者应少研究“银行不应该做什么”,多研究“什么样的商业模式能使银行更好地为实体部门服务”。这显然需要监管者和银行,在当前的接触层面之上,进行更好的对话。
作者为中国银监会首席咨询顾问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香港证监会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