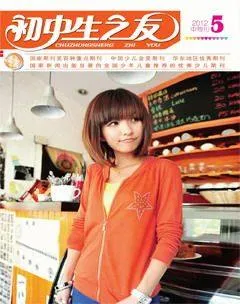马友友:从逃学顽童到音乐大师
他出生在法国,生活在美国,但每次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总是坚持用汉语。他得过16次格莱美奖,却从未出席过颁奖典礼。他是20世纪后半叶古典乐坛最耀眼的明星之一。他5岁就超越了古典音乐界许多名人,9岁登上纽约著名的卡内基音乐厅,23岁获享誉全球的艾维费雪奖,36岁被哈佛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51岁被联合国任命为和平大使……他用琴艺征服了全世界,他的笑容也让身边的人如沐春风,他就是德艺双馨、蜚声国际乐坛的大提琴家———马友友。
4岁时,父亲问马友友除了钢琴之外还想学什么,他没有挑姐姐学习的小提琴,而是指着音乐会上的低音大提琴说:“我要那个大家伙。”可是,父亲实在找不出适合小孩拉奏的低音大提琴,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让他学了体积稍小的大提琴,未料这个乐器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
回忆小时候学琴的经历,马友友说:“父亲教小孩拉琴很有一套。他知道小孩子不容易专心,或者说专心的时间很短。因此,他很注意把握小孩子专心的那10分钟到15分钟。”他说,父亲每天只要他练琴15分钟,但必须集中精神,全心全意地练,这种训练方式让他受用不尽。时至今日,他还是认为:练琴时间在精不在久,逼孩子练琴绝不可能练好,只有在孩子有意愿要练,而且全神贯注练琴时,才可能有好成绩。马友友还提到练琴最重要的要素,他说:“你必须不断地问自己问题,再想办法回答自己的问题,这个过程非常重要。比如,你问自己,为什么这儿要这么拉?你必须回答自己,那是因为作曲家当初写作时,希望产生这样的效果。如此反复地问,反复地答,答不出来的去找相关资料,想不出问题时也要努力去想,这就是自我锻炼的最好方法,也是我自己这么多年来练琴的心得。”
6岁时,马友友来到美国,和著名指挥家斯坦恩同台演出。3年后,在斯坦恩的劝导下,9岁的马友友进入正规的音乐学院学习。那时的马友友已经跟许多名家合作演出过,出了个人专辑,上了畅销排行榜,已颇负盛名。但是,他的成长经历并非一帆风顺。正处在青春期的他个性变得异常叛逆,他蓄起了披肩长发,误交损友,开始旷课,抽烟,酗酒……庆幸的是,马友友在朋友的劝导下及时悬崖勒马,专注学习,大学毕业后重新回到古典音乐的道路上,重新调整了自己的人生。或许,对于马友友来说,人生道路正因为曲折,才特别显得有征服感。
1972年,17岁的马友友在哈佛大学继续学习,他没有选择音乐,而是开始了人类学的研究。这段时光对马友友来说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他感到自己的思想上了一个新台阶。他开始把自己少年时代的种种失控行为放到透视镜里分析,并从自己身上开始,领略欣赏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他说:“哈佛大学使我学到了怎样分析音乐,懂得了音乐是怎样组合的,又是怎样激起听众兴趣的。”
马友友大胆地尝试新的音乐元素,尤其体现在他的《巴赫灵感》专辑。马友友因对巴赫的全新诠释而风靡世界,被誉为是对20世纪古典音乐界的一次伟大改革。许多现代音乐评论家说,马友友的大提琴穿越了国界、战争、宗教,琴声里饱含了生命的激情和爱情的震撼……
正当马友友处于事业顶峰期,却遭受了一场重大危机。从20世纪80年代起,他不断地把世界各地的民乐、通俗乐甚至边缘乐器都融入到他的创作,这个举动触怒了严肃音乐界的保守派。1992年春天,维也纳国家剧院取消了与他签订的演出合约。连恩师斯坦恩先生也拒绝与马友友同台演出,他对马友友说:“孩子,你在自以为是的轨道上滑行得太远了,难道你想把古典音乐变成儿歌秀?”在马友友被迷茫和无助彻底包围时,妻子吉儿安慰他说:“贝多芬说过‘规矩就是用来被打破的’,你认为所有的古典音乐都是当时的民歌和流行音乐的最佳组合,你不愿意我们的孩子和孩子们的孩子只知道莫扎特和巴赫,而不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有别的音乐存在过!你没有错!这不是一个妻子的看法,而是你最信赖的朋友的由衷感慨!”
1999年,马友友酝酿了10年之久的《巴西之魂》专辑问世。经过旷日持久的论战,格莱美第12次给他“加冕”。2000年,他为电影《卧虎藏龙》演奏主题曲,这首新古典大提琴曲获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音乐奖。2004年春,他再次获得第43届格莱美大奖。迫于公众和媒体强大的舆论压力,维也纳国家剧院再次向马友友发出邀请。
马友友说,音乐是有色彩的,有画面的,有视觉的。在音乐的表达上,他能把任何曲子演绎和诠释得生动感人。他是在用一种人文的情怀和历史的眼光解读音乐,并用他人生的经验和修养在翻译作曲家的心灵。他相信演奏的最高境界是听众真正与演奏出的音乐产生共鸣。马友友以丰富的面部表情展现着故事和景致,以出神入化的演奏,引领人们进入一个个无限美妙的视觉与心灵世界。
在乐器中,大提琴是最接近“人声”的奇妙乐器,马友友的琴声将其“人声”的灵性发挥到了极致,清新委婉,兴味无穷。就连巴赫无伴奏组曲,到了马友友的手里,都变成了一幅幅如梦如幻的音乐诗画。
“一切艺术无不是为了‘交谈’,借着音乐,你可以知道数百年前的伟人在想什么,比如贝多芬,比如巴赫。”马友友说,“借着音乐,你可以了解他们的音乐思想,这是多么奇妙,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当我通过音符重新诠释那些伟大作曲家的心灵,引起共鸣的时候,就是身为演奏家最‘荣耀’的时刻。”
他想告诉人们的是,音乐本身具有丰富的可能性,它可以带给人们不同的灵感。更为重要的是,音乐可以教会人们用更多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就会减少,世界也会变得更加开阔。
马友友永远记住老师们教给他的,“想一想不同的人不同的故事有什么共同的地方”。他相信,“每个国家、每个社会都有音乐,音乐是表达我们心里最可贵的思想感情的,人生最重要的是不同地方与国家的人与人之间有更多了解,更多沟通”。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马友友从一个顶级的大提琴演奏家迈向了一个新高度,致力于各民族音乐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和推广教育工作。
马友友非常喜欢阅读人文历史类的书籍,他了解中国和法国的许多历史故事,觉得其中蕴藏着无限乐趣。这位生在法国、长在美国的音乐家,虽然身体里流淌的是纯正的中国人的血液,但他说英语要比汉语流利得多。尽管如此,他每次回国演出,无论是在台湾还是上海,答记者问都坚持说汉语,而且他还要求把用英文提出的问题翻译成汉语。这和他的家教有关,他和姐姐小时在家,父亲规定他们在家一定得说汉语,吃饭时要叫得出菜的名字才能动筷子,写信要写中文才回信。因此马友友虽然没有长时间生活在国内,但汉语说得相当不错,而且他极不愿意在说汉语时夹杂英文。这样的背景使他在国际乐坛中能独有儒雅、清新的中国气质,加上天分和努力,终于成就了这样一位少有的、不参加任何世界音乐大赛就扬名世界乐坛的音乐家,他那炉火纯青的琴艺、富于多元文化色彩的独特魅力为人们所追捧。70多张专辑,16次摘取格莱美音乐大奖的傲人纪录,奠定了马友友无可取代的大师地位,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提琴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