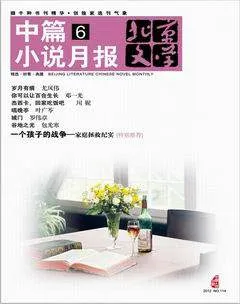一个孩子的战争——家庭拯救纪实
他曾是老师和同学眼里聪明优秀的神话,然而,神话出人意料地破灭了。绝望中,父母把他送到军事化训练营里,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对于孩子和父母来说,这是思想洗牌的“战争”、灵魂重塑的“战争”。
“战争”并没有随着军事训练的结束而结束:孩子的坏毛病复萌,父母之间的教育理念“战争”升级,高考前夕巨大的压力一度使他面临精神崩溃……千钧一发的时刻,是什么帮助这个艰难的家庭赢得了这场拯救孩子的“战争”?
同样的孩子,同样的父母,同样的家庭,中国也许还有千千万万。徐世立以其亲历的种种给予了面临同样问题的家庭一面镜子。学习也好,反思也好,规避也好,愿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在镜中照见自己。
站在苦难的门口
“站在苦难的门口”,是儿子参加2009年湖北省高考自拟的作文试题,我立刻拿它作了本书前言的题目。
儿子高考一结束,我便瞒着他开始写这本书。书出版的时候,第一个感到震惊的将是我们的儿子。那时,儿子在大学念书的可能性很大,当然也不排除别的可能。从现在起直到此书出版的这段时间,我们夫妇必须将此事瞒得密不透风,双方家人中也不能让任何人有丝毫察觉。
世上竟有这样的写作。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原因说来也简单,这是一本主要是写他的书,儿子知道了很可能不让写,此书便会夭折,甚至永远不可能问世。而我和妻子晏紫却认为此书应该写,因为我们不仅仅是为儿子写,也是为与儿子同龄同代的孩子写,为每天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几千万中国家庭写。和世面上许多内容重复的亲子、励志、成功成才类书籍不同,这本书是写苦难与黑暗,失误与教训,沉沦与挣扎,拯救与自救,理解与和解;写沦陷之后的浮升,写人和命运,以及人与命运的关系。
这样真实地写出并以这样的方式写,我们确实感到有点对不起儿子,但不写出更对不起儿子,这是我与晏紫的共识。也试想说与儿子知道,儿子未必不让写,思来想去,我们不敢冒这个险,宁可委屈儿子。
我的文联同事李贺明曾经说,“儿子是上帝派来磨炼你们的”。可哪个独生子女又不是上帝派来磨炼他们父母的呢?又有几个“特保儿”家庭不曾弥漫一个孩子的战争硝烟?做独生子女的父母,我们无“往”可继,但有“来”可开,无“前”可承,但有“后”可启。此前若有这样一部书对我们“启后”、“开来”,我们当不致走那么长的弯路,人脱去几层皮,在黑暗里摸索到儿子成年。经历了之后,我们才强烈意识到中国早该有这样一本书,却没想到,突然有一天命运安排此书由我来写。我想如果我不写出,若干年内,恐仍将难有这样一本书问世。
天、地、人,物、事、力,各种因素聚合于我一身,我遵从天意。于私,是为儿子,为了如他所愿将来能“更加地完美自己”,同时不忍心辜负他106天的艰辛之旅以及于106天的困厄中写出的97篇日记和6万字的真情文字。于公,我们欲“启后”。这与我的职业和职业道德有关。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开拓者王凤仪有言:“道”是行的,不行没有道;“德”是做的,不做没有德。昏暗的夜街,我一脚踏进无盖的窨井,一身伤痛。我爬了出来,抚痛而去,头也不回,可我明知身后的行人正熙攘而来,明知必有人和我一样跌进窨井,有人会比我更惨更痛。我若如此这般,私心以为失德。我写这书,是站在井口提示后来者绕道,是找来石块将井口围拦,是用木板在井口竖起一块标志,是用手电、烛火在黑暗里亮起一束微光。
准备材料、构思此书时,我常会想起鲁迅当年喊出的那声“救救孩子”,想象鲁迅忧心如焚的样子,想念那句“肩起黑暗的闸门,放孩子到光明的地方去”的话,常常想,常常就被这些话触动,感动。有媒体、网站和教育刊物报道,中国现在有若干千万“问题学生”,后被有关部门否定。虚假新闻或数字不实应该否定,但“问题学生”这个客观存在的庞大群体却很难否定,很难装作没看见。至于该不该给学生贴“问题学生”、“差生”的标签,则又当别论。有多少个“问题学生”就有多少个“问题家庭”,就有累以亿计的“问题家长”。问题是,我们至今还没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写作之前,我就想到要用这篇写在书前的文字给将来突兀看到这本书的儿子作点心理铺垫,翻开书,儿子会迎面碰上“问题学生”、“差生”、“择差教育”这些刺目扎心的字眼,这篇文字或能起到镇痛减痛的效果,切望儿子挺住。儿子,这次你不会是又一次“站在苦难的门口”,因为你已经长大了,成人了,对“苦难”已经有了较深的感悟,而且已将“苦难”置于案几,跃然纸上,呈现于考场。个人的苦难能使别人受益,这样想,疼痛是不是会减轻些呢。
我还特别想借这篇文字为此书做个宣传。我不避讳,因为我心存着一个美好的愿望——每卖出一本书,或可挽救一个人、一个家庭;多一个人看这本书,就多一个孩子或家长早日拔身于泥淖而绰厉前行。
1 绝望短信
“这小孩完了”,是我收到的一条短信,发信人是晏紫,“这小孩”是我们的儿子修远,读高一上,收信时间是2007年2月4日。那时,我正在37年前插队落户的宜昌县一个叫谭家冲的小山村里写作。那天我几乎一夜不眠。儿子出了“问题”,a266e093fa64b917f5c4cccd6f7895e5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家庭、学校以及周边亲友一切试图力挽颓势的努力均不奏效,儿子像一架失事飞机,带着巨大的惯性往一个我们不愿看到的低处坠落,着了魔一般,我们,以及与我们有关的大小家庭无所作为,穷途末路。
此前一个多月的2006年11月17日,晏紫就给我发来“修远情况很不好”的短信,那时她还没有这么绝望。“很不好”以至“完了”,都在预料之中,整整一个高一上半学期,儿子不听课不做作业只上电脑打篮球,上课就睡觉,怎么可能好又怎么可能不“完了”呢。
晏紫是武汉一所大学的老师,当她以母亲和老师的双重身份对儿子感到“绝望”时,这种绝望也是双重的:母亲对儿子的绝望,老师对学生的绝望。
记得2006年初中毕业前夕,班主任把我叫到学校,当着我和儿子的面说:“徐修远聪明、优秀的神话已经破灭了!”语文老师第二天对我说:“你的儿子油盐不进。”又一天夜晚的学校操场上,副校长兼物理老师得知我是徐修远的父亲后说:“你的儿子软硬不吃。”现在回想,作为父亲,当初对儿子恼羞成怒地转述这个“八字标签”真是愚不可及,愤怒淹没了理智,它没能使儿子知“耻”而后进,反而成为他后来干脆自我放弃的催化剂。等到明白时错已铸成。
客观地说,今天的中国,绝大多数人尚未意识到教育与自我教育是每个人毕其一生都需要学习与实践的一项重大、艰深的工程。教育之所以艰难艰深,盖因它面对的是各各不同的人,一个个禀赋、品性各异的活生生的个体。中国以伟大的教育家孔子为荣,孔子以自己千年不朽的教育思想和普世价值观傲立于人类文明之巅,然不无讽刺的是,当孔子学院如今在全世界遍地开花(截至2010年6月,91国,302所,孔子学堂272个)时,中国自己的教育却问题成堆;应试教育四面楚歌,至今仍东奔西突找不到出路。长期以来,“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精髓被束之高阁,相互关联互为依存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有意无意形成共谋,孩子、学生成了教育生产流水线上的标准化产品,不符合“标准”的学生被流水线剔出,成了“次品”或“废品”,大量的所谓“问题学生”、“问题孩子”便由此产生了。明明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明明是我们的教育问题成了“问题教育”,恶果却落在“问题孩子”、“问题学生”身上,这不公平。记得多年前邓小平说过这样的话:这些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的失误。中国只提“科教兴国”,不提“教育立国”。我不明白,这么多年了,教育和社会道德伦理都这样了,为什么不以教育立国?我以为“教育立国”立的是国之魂魄。
从表面看,儿子从一个优秀的学生滑落到“问题学生”只用了短短两年的时间,而实质是,由于我们的种种失误,这种滑落从儿子出生不久就开始了,无数失误的因累积成了“问题”的果,认识到这一点,我和晏紫用了16年的时间。
我这里说的“失误”,主要是指我们家庭教育的失误。因为这些失误,我们和儿子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及无数不同内涵的泪水,以及无数个揪心揪肺的日日夜夜。
儿子出生后刚满100天,就被我们送到郑州他姥姥家,回家时已经4岁半了。最令我们吃惊的是他强烈的“唯我”意识,任性、暴躁、自私,还有对周围人的冷漠,糟糕,儿子让老人惯坏了。我们一开始就错了,错得我有时认为儿子后来一切让我们操心劳神的习性都是对我们原始错误的报应,都是我们必须承受的惩罚,以致后来将他送到被称为“魔鬼训练营”的地方时,他所承受的巨大的身心痛苦,我都认为他是在代父母受过!
我想在这里说出一件事情。说出它,除了对儿子表达我的愧悔,还因为它太隐秘,太匪夷所思,不说出我不得安宁。
那时儿子大约5岁。有一天我坐在卧室阳台上看书,儿子静悄悄地站到卧室门口。晏紫不在家,儿子很孤独。独生子女都很孤独。儿子想过来,又怕打扰了我,或者怕自己不受待见,犹豫不决的样子。我一直知道他站在那儿,却没有让他过来的表示。儿子终于忍不住朝我慢慢走来。走到阳台门边,他站住了,怯生生地望着我。我仍然没有理他。虽然多年不在一起,因为血缘,儿子对父亲依然是有感情的,记得刚回武汉的那些日子,只要一听见我下班上楼的脚步声,他就欢天喜地地跑出门将我的拖鞋放到楼梯口,然后又羞涩地蹦跳着赶紧跑进门去。现在,他想和父亲亲热,或者玩玩,说说话,或许还希望父亲能将他抱进怀里。可是我没有,身子一动不动,眼睛仍在书上。不一会儿,儿子的脚迈过了阳台门,他的小手轻轻触碰了我的腿。见我仍没反应,他十分忸怩地歪斜着身子靠到我的身上,长时间不声不响。按常理,接下来该发生的情形理所当然地应该发生,可是我竟然让一切理应发生的情形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没有用行动去填补儿子情感的饥渴,我没有在他十分渴望父爱的时候给他一句亲热的话语和一个爱的拥抱。
难怪儿子后来和我不亲。
第一次回想这个细节时,我的心发紧,不能自恕。我曾经无数次指责长大后的儿子的冷漠,却不知自己人性中隐匿着更为冷酷的一面。回想我的童年,我虽然出生后一直没有离开过父母,但我只有母亲抱我的记忆。我怀疑父亲从来就没有抱过我。父亲活到78岁,直到生病我送他住院时,我们父子才有了生平第一次肌肤相触。我不知道这和我缺乏对儿子肌肤之亲的欲望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有时候想得极端了,就觉得,当一个中国父亲的儿子并不是一件什么幸福的事情。
2 坠落从电脑开始
小学毕业时,儿子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与晏紫的大学一墙之隔的一所初中。整个小学阶段他都出类拔萃。他几乎每年每学期都是三好学生,作文、英语多次在省、市、区比赛中获奖。他酷爱运动和艺术,乒乓球、篮球、游泳、自行车、象棋、绘画、声乐、舞蹈、钢琴,无所不会。进入初中后他的成绩依然一直全班领先,全年级10个班500多人,初二的一次期末考试,他是年级第二名。他曾获得武昌区艺术小人才一等奖和“雏鹰少年”称号,还被武汉市团市委和武汉市少工委授予“雏鹰勋章”。但到初二下的2004年底,情况发生了变化:儿子要买电脑。
儿子的滑落还有一个不被我们认识的重要原因——初一一过,日子不知不觉进入了中考应试期,课业压力陡增,所有人陡然紧张起来,而此时的儿子正处于身体与心理的转变期。应试如魔罩,但凡意欲上进的学生都难逃其掌,而对抗是没有出路的。
自控力一直是儿子的弱项,我们完全能想象买电脑的后果。但防线已经崩溃,买电脑大势已定,于是我与他“约法三章”。我以为,即使从表面看,儿子的“完了”确是从买电脑开始的。
一边是日日不断的长时间上电脑,一边是在书房被控制被劝说的不自在不自由。2005年4月,儿子从同学处借来一种叫做PSP的掌上微型电脑,将电脑中的游戏下载拷进PSP,然后坐在床上被窝里夜以继日。但借的终是要还的,很快,他向晏紫提出要买PSP,这时离买电脑才三个月。“五一”晏紫带儿子回郑州,5月2日,儿子就拥有了一部2400元的新PSP。是儿子他小舅买的,晏紫的弟弟是北京一所大学的老师。
儿子特别擅长将“约定”、“公约”变成一纸空文。不久,“约定”全面废止。
7月初的一天,心力交瘁的晏紫在电话中对小舅哭诉:“你把我害苦了!”
3 滑向溃陷的边缘
PSP最终被我没收了,儿子对我难免怨恨。这期间,语文老师也曾没收过他的MP3,他竟然上课也把耳机挂在耳朵上。儿子的外形也在悄然变化,留长发,根根拉直,向四面扩张,据说是超女周的“笔畅头”,拉动了整整一代人的头发生长。上衣越穿越大,下面长齐大腿,身子里面顿觉空空荡荡,总替他460c07f6497648dee57878e1090a8e32472ce599f4d8fff2e713d3797c6876f8感觉风全面占领身体的寒冷。裤子越穿越长裤腿越穿越肥裤脚越穿越大,在地上拖出须子啰嗦的毛边,边走边扫街似的。我后来知道了这叫“嘻哈裤”,用以配合“嘻哈一族”的街舞,全是网上“淘”来专卖店“搜”来从美国快件邮来,价格不菲,七八百元一条是家常,而且破洞百出。鞋只穿一种:运动鞋。价格从二三百元起步,几年间飙升到每双一千多元,全名牌,不是耐克就是阿迪达斯。其后,街球替代了篮球,街球又衍生出了街舞。篮球街球街舞,听歌上网看碟片,成了儿子生活的主旋律,而中考正一天天临近。
中考调考前一月的月考,儿子的年级成绩排名是500多人中的234名。我再一次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