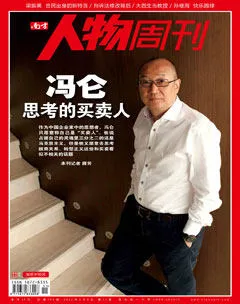干
2012-12-29 00:00:00达达ZEN
南方人物周刊 2012年11期

“你应该把在都柏林的最后一晚献给奥多诺霍(O’Donoghue)酒吧!”结束近一周爱尔兰东西海岸线的穿越回到首都,帅气友善的司机Galvin半开玩笑半郑重其事地对我说。
几天相处下来,我选择相信他的推荐。对于大多数“中国太遥远了,没有去过中国”的爱尔兰人来说,Galvin显然更清楚国际旅客需要的是什么——他的父亲年轻时就专门从事代理当地贵族和富人前往东方旅行的业务,父亲退休后到西班牙一个不知名的小镇安享晚年,他将这一摊子买卖接了过来。
“把行李和你的摄影装备留在酒店,好好喝几杯。”我记下Galvin的话。步行近半小时,从酒店找到位于老城区的奥多诺霍。推开它沉重的橡木门脸的那一刻,我立刻开始后悔,不是因为别的,这里正是我需要的都柏林!
我得立刻回酒店取相机。
橡木门里是另外一番天地,光线幽暗、气氛温暖,像时光机器,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愉悦感:这空间从来不曾遵从所谓的建筑学甚至基本的几何原则,嘎吱作响的地板、坑洼凹凸的桌面、木料拼凑的隔断几乎找不到一条平整的直线(你可以想象在阳光下曝晒过的报纸的形状),人们不偏不倚地将臀部嵌入高脚椅的凹陷中,喝酒、谈笑或静默;风笛、手风琴、宝思兰鼓、六孔哨的声响充盈耳廓;黑啤酒特有的焦糖的甜味与烤麦芽的糊味已使人欲醉。
“要点什么,先生?”
“一品脱健力士(Guiness)!”点完酒,我找到一个角落的位子坐下。坐在我旁边的是系着红色围巾的白发先生。
“你好,来都柏林旅行?”我问道。
“算是吧,从纽约来,好久没回都柏林了。”显然,这是爱尔兰众多海外移民中的一位。
一位多愁善感的饮者坐在伦敦、纽约或北京的酒吧里,伤感地对着酒杯自言自语,呢喃着家乡的绿地和山青水秀。一个陌生人不慎的言辞会让他勃然大怒,从他摇曳闪亮的眼神里折射出聚焦中的喧闹不安和骚动,关于爱尔兰人的常见传统观念就是这样一幅图景。而在他的故乡爱尔兰,同样镜头下的当地人却大多是欢快、健谈的,原因无他,酒也。低质或者干脆根本无从寻觅的健力士黑啤酒通常会使爱尔兰人觉得身在异乡,这种有一层白色脂装物漂浮的黑啤酒甚至超过了爱尔兰威士忌,被誉为爱尔兰国酒。它使用烘烤过的大麦、啤酒花、水和酵母通过上层发酵技术酿造,具有极深黑的颜色和独特的口味,现在的Stout黑啤酒(上层发酵的烈性酒)的定义和规范基本都从它而来。
喝酒,尤其是在酒吧喝酒,对爱尔兰人来说远不止一项单纯的享乐活动,它是一种社交方式。酒吧是喝酒、吃饭、1pDMriaSuRUSyxiq34LDiDs+90DqO90KTPyaWG9HUAU=娱乐的场地,更是写作、思辨、延续传统音乐和踢踏舞的场所,是整个爱尔兰文化的基础。
上了年头的吧生并不会马上把新灌的酒递给你,而是在吧台搁一会儿,等泡沫全然从黑色海面伸展出来。“一定要喝一大口。”吧生递啤酒时会笑着对你说。
奥多诺霍吸引人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关于带有传奇色彩的乐队——都柏林人(The Dubliners)。1934年建立之初,都柏林人乐队就选择在此驻场。酒吧墙壁上挂满黑白照片,是乐队数十年发展的视觉日志。它们的作品被众多知名的乐队翻唱,包括爱尔兰最富盛名的民谣组合富里兄弟(The Fureys )、谢默斯•埃尼斯(Seamus Ennis)和乔•希尼(Joe Heaney)。当其他国家的传统音乐在流行音乐的攻势下走向衰落时,爱尔兰目睹了一个奇迹,年轻人捡起老调子,并把它们推向前进。有人说,爱尔兰的古老曲调可以追溯到莱茵河中部那些叫塞壬的水妖,那时迷人的曲子能使过路的水手丧命,现在在这小酒馆,我却心甘情愿的沦陷。
更多关于人文旅行的资讯,详见《Across穿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