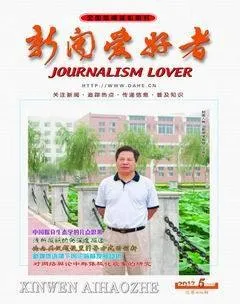刘翔世锦赛夺银报道的文本分析
【摘要】本文以美国合众社对“刘翔夺银”事件的体育报道为材料,从用词、句子和篇章三个层次,对报道中使用的文本策略进行了具体分析,揭示了体育报道的文本表层之下隐藏的意识形态,以及报道如何利用这些文本策略对事件的解读进行了有效操控。
【关键词】体育报道;文本策略;意识形态;操控
2011年8月,世界田径锦标赛在韩国大邱举办。在男子110米栏决赛中,刘翔因对手被取消成绩而获得银牌,却引起不小的争议。国外媒体是如何报道“刘翔夺银”事件的?这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思索和启示?本文从美国合众社的一篇报道为材料,用批评文体学的方法从词汇、句子和篇章三个层次,对报道中使用的文本策略进行具体分析,从而揭示该报道的文本表层所隐藏的意识形态,以及报道是如何利用这些文本策略对读者的解读进行有效操控的。
用词
该报道在用词方面颇费心机,这主要表现在两类词的使用上:动词和名词。该报道涉及的主要事件是罗伯斯如何“影响”刘翔,致使对手与金牌无缘。因此,罗刘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动词在“重现”客观事实的过程中就显得举足轻重。作为事发后的报道,只能是对已发生事件的“重构”,重构的过程也就无法避免报道者的意识形态对事件的过滤。
涉及罗刘之间动作的动词依次有:tangled,pulled,touch。Tangled(纠缠)为不及物动词,掩盖了罗布斯“有意为之”的事实,动作的指向性也变得模糊不清。这句话可以理解为罗刘二人“纠缠”在一起,所以两人都应该对此事负责。Pulled(拉)在正文中出现了两次,皆用作及物动词,动作也都指向刘翔。可是,这两次出现都出自刘翔之口,只可理解为是他本人的一面之词。Touch跟tangled的用法如出一辙,被用作不及物动词,遮蔽掉了动作的指向性。更有甚者,此处用了并列主语,进一步暗示动作的施为者是罗刘二人。Touch前面的动词seem不可小觑,“似乎碰/摸/拍/刷到”使得touch的动作是否发生成了问题。不难看出,该报道将罗伯斯严重的有意违规行为进行了“低调”处理。其中传递的信息是:对罗的判罚有失公允。
名词的选择和运用在操控阅读位置的预设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反映了作者本身的态度。报道在表达选手之间“碰触”这一概念时先后使用的名词有:pulling(拉),crucial interference(致命的干扰),tangles(绞),hitting(打),physical contact(身体接触)。Pulling出现在导语中,与disqualified相呼应,应该是借用大赛官方的用词。此词意义比较明确、具体。crucial interference和hitting分别是参赛选手刘翔和奥利弗的用词,代表了各自对“碰触”的定位。tangles和physical contact是该报道真正认可的“真相”,它们使得这一严重的违规行为归于无形,这是因为和前面的三个名词(词组)相比,词的意义更加模糊和不确定。如此,给读者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事情压根就没有那么严重,罗布斯有点冤。
报道使用不同的名词性短语对罗刘二人进行定位并对赛场表现作出微妙的评判。罗伯斯被冠以奥运冠军头衔,“闪电般的起跑”和中途的“遥遥领先”,这些信息被“前景化”而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而对于罗伯斯颇有争议的冲线却保持沉默;相比之下,刘翔在冲线时的“急剧降速”反而被凸显了出来。该报道对阅读的视角进行了有效控制,让有关罗布斯的积极的信息和有关刘翔的消极信息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反映了该报道对两位选手竞争实力暗度陈仓式的价值判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本报道通过对动词用法的细微控制和对不同名词(词组)意义的精心选择,二者互相支撑,操控了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使其顺着作者预设的方向进行。
句子
该报道的话语在句子层面上也有很多讲究,它们在暗藏报道的立场,影响读者的解读方面不容忽视。报道在传达罗伯斯被取消资格而引发的位次晋升时,在句法层面上精心设置了机关:
(1)A Cuban counter-appeal was dismissed,giving the title to American Jason Richardson.(古巴队反对裁决的申诉被驳回,冠军落入了美国人詹森·理查德逊的手中。)
(2)…said Liu,who had finished third but was bumped up to silver.(……刘翔说道。他是第三个冲出终点的选手,但是突然间被提到了银牌的位次。)
句(1)中,用现在分词giving引导的伴随状语来表述美国人晋升冠军,这样显得水到渠成,顺理成章,这是通过伴随状语“与谓语动词同时进行”的语法特性来实现的。换句话说,理查德逊摘冠自然而然,非他莫属,无可争辩。
句(2)中,有关刘翔晋升的信息是以who引导的非限定性定语从句表述的,在从句的两个并列谓语之间安置了一个转折意义非常强烈的连词“but”,它传达的信息是:刘翔获得银牌出乎预料之外。动词词组bump up(突然增加/提高)更加凸显了晋升的不自然。
(3)Robles and Liu first seemed to touch when clearing the ninth hurdle,and then again on the final one.(罗伯斯和刘翔在跨越第九道障碍栏时首次似乎相碰,这在跨越最后一道障碍栏时再次发生。)
句(3)是对罗伯斯两次“碰触”刘翔的表述,这是一个由and连接的并列复合句,第二个分句的主、谓语部分被巧妙地省略掉了,只剩下频度副词again和作为地点状语的介词短语。这样做实际上是对“核心信息”的遮蔽,在与“seem to touch”产生的模棱两可的模糊句意的合谋之下,很容易绕开读者的注意。路透社的报道与此形成鲜明对照:“Robles…made contact with Liu at least twice…”这里不但提到了两次,而且前面用了修饰词“at least”,肯定了有两次犯规,且存在两次以上的可能性,对罗伯斯“故意碰撞”的事实毫不隐瞒。由此看来,此处对从句句子成分的省略是瞒天过海的文本策略。
语篇
除了选词造句层面的话语策略外,该报道在语篇层面的话语策略也值得关注。首先是引语。引用什么,如何引用,以及什么时候引用,完全在作者的掌控之中。该报道对刘翔的引用如下:
“When I approached the ninth hurdle,Robles pulled me.…”(当我跨越第九道障碍栏时,罗布斯拉到了我。)
“I thought I would be the champion or at least second. But Robles pulled me.”(当时我想我会得冠军的,至少也会得亚军。可是罗布斯拉到了我。)
以上引语都是直接引语,给读者造成一种忠实再现刘翔原话的假象,其实则是作者精心安排的结果。辛斌认为,直接引语不但有强调作用,更能引起读者的注意,而且使报道者与引语间保持距离,表明他对引语的内容持保留或反对态度。[1]很明显,报道引述刘翔的话不是赞同他说的话,而是别有用意。两句引语中间没有任何过渡语,将其并置凸显了引语中的重叠信息“Robles pulled me.”由此让人产生了一种错觉:刘翔是一口气说出这两句话的,他对罗“拉”他耿耿于怀。其实,这两句话完全有可能是刘翔在不同场合说的,而且不止这些信息。
在提及与判罚相左的观点时,该报道采用了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混合使用的方法,在文本规约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对信息进行了调控:
Oliver…said such tangles in an action-packed race should be no reason to change the result.(奥利弗说,在如此高度激烈的比赛中,这样的纠缠绝对没有理由改变比赛结果。)
“So he might have gotten dq for hitting Liu,man that happens almost every single hurdle race…”(他可能会因击打刘而减速,哥儿们,那种事在每一场障碍赛中都在发生……)
报道首先采用间接引语对原有信息进行转述:奥利弗认为,在高度激烈的比赛中,这样的“纠缠”绝对没有理由改变比赛结果。然后改为直接引语支撑其转述:“他可能会因击打刘翔而减速,那种事在每一场障碍赛中都有发生……”可以看出,奥利弗的确认为击打这种事很普遍,但他的话是不是意味着“绝对没有理由改变比赛结果”呢?报道正是利用了间接引语提供的阐释空间,有意曲解或夸大所引文本的本意,使其为自己的写作目的服务。间接引语“预先调整了对直接话语的感知,即对将出现的直接话语的主旨用语境预示,并用作者的语气去渲染。经过这样的处理,转述话语的界限就变得极不清楚了”[2]。
其次,语篇的衔接与过渡也参与了报道的意识形态建构。报道对刘翔的“抱怨”进行两次“再现”后,采用副词instead,引出理查德逊与刘翔截然相反的态度:
“I thought I would be the champion or at least second. But Robles pulled me.”(当时我想我会得冠军的,至少也会得亚军。可是罗布斯拉到了我。)
Instead it was Richardson,who said he was just doing the best he could.(相反,倒是理查德逊说他只是全力以赴。)
这样的文本衔接预设了一种阅读期待:刘翔应该像理查德逊那样大度,不应当斤斤计较。
The decision left the Cubans angry.(裁决让古巴人大为恼火。)
“He won the race. That's what we know,”said Robles' coach Santiago Antunez.(“他赢了比赛,这点我们都知道。”罗布斯的教练桑迪亚哥·阿图涅茨说。)
以上两个段落之间只是简单并置,但却可以产生一种逻辑上的“印证”错觉:判罚决定让古巴人愤怒,这从教练的反应可以得到印证。教练作为争议的当事人之一,其态度和观点显然不能代表集体的古巴人。至于古巴人是否真正感到愤怒,作为读者的我们只有“服从”文本的权威。Fairclough指出,句子、语段之间的搭配关系并不是在词典中能够找到的搭配,它们是由文本生产者在某个文本中建构出来的。当然,这种建构是由作者的意识形态决定的。
最后探讨一下该报道的逻辑框架。报道的主体部分体现出三种对待判罚的态度——支持者:刘翔;中立者:理查德逊;反对者:古巴人、罗伯斯、教练和奥利弗。很明显,报道主体没有充分地支持导语。也就是说,该报道对官方的判罚并不认可,至少持保留意见。报道在意识形态上流露出对罗布斯的同情和对刘翔的贬抑,只是新闻报道的文本规约压抑了这种价值取向的明确表达,从而以一种暗流涌动的方式潜行于文本的深层。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对于判罚,刘翔教练的态度如何?有没有其他参赛选手支持判罚?这些信息都被排除在了文本之外。另外,报道避开比赛规则不谈,却暗暗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了来自各方反对的声音,这显然也是作者“精明”的文本策略。
结 语
表面客观公正的报道背后,其实是报道作者价值取向主导下文本策略的明调暗遣。该报道不论在用词、句式选择还是篇章层次上都对文本进行了微妙的操控,从而为读者预设了特定的解读位置。这些话语策略的运作影响了读者对报道事件的认知和评价。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这些文本策略都以“隐性讯号”而非“显性讯号”的形式运作,很难引起读者的警觉,反而在不知不觉中解除了读者“对抗式阅读”的武装。因此,对这种貌似客观的报道,采用批评文体学的文本分析方法,完全可以揭示文本真实的意识形态。
参考文献:
[1]辛斌.《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中转述方式和消息来源的比较分析[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3).
[2]Volosinov,V.N.,Ma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M].New York:Seminar Press.
(作者单位:青岛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编校:赵 亮